撰文:那国毅
那国毅:德鲁克管理学专家,德鲁克管理学院资深教授,曾在美国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师从彼得·德鲁克,著有《百年德鲁克》、《走近德鲁克》等,审订《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的实践》等。本文发表于《中国企业家·国家商业地理》2009年9月,本刊授权转载。
2009年是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诞辰百年。
该年5月至6月,我用六周的时间再次穿越美国大陆,沿着德鲁克的足迹,去实地考察和研究德鲁克管理思想形成的历史沿革。
为此,我访问了德鲁克管理研究生学院、美国德鲁克协会,拜见了德鲁克98岁的夫人,会晤了美国德鲁克管理学专家,并置身于德鲁克1950年-1970年所执教的纽约大学管理学院,感受历史的脉搏。此外,我还参观了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原总裁斯隆在创建斯隆管理学院时,曾听取过德鲁克的建议)。
德鲁克说过,“伟大的心灵必然遭遇不凡的际遇。”而他整个的人生轨迹——在奥地利成长、德国求学、伦敦实习、美国工作和生活的每段经历,无不发生在20世纪波澜壮阔、风云际会的历史背景下,“呈现社会的图像,捕捉并传达这一代的人难以想象的那种神髓、韵味与感觉”(《旁观者》)。

从旧世界到新世界
1909年11月19日,彼得·德鲁克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奥匈帝国的财务官员,创办萨尔茨堡音乐节,曾参与进言奥首相避免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母亲是奥国率先学医的女性之一。祖父是位银行家,祖母是舒曼的钢琴弟子,在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担任独奏,乐团指挥是赫赫有名的马勒。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德鲁克从小就出入哲学、数学、音乐等知识分子沙龙,每天沉浸在智慧的殿堂里。他童年时就见过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作家托马斯·曼、欧洲最大政党法国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斯特恩伯爵等传奇人物。
1950年,德鲁克随父亲阿道夫去看望熊彼特(当时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美国经济学会主席)。阿道夫问了自己的学生30年前问过的那个问题:“你现在还跟人提起你将来想被后人记得什么吗?”熊彼特说,答案不再是他年轻时所说的要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欧洲美女的情圣,“如果没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你就不能说你已改变了世界。”德鲁克从未忘记过那段对话,而且这成为他衡量一生成就的指标。

2009年6月9日上午,我有幸在加州克莱蒙特德鲁克的家中拜见了德鲁克夫人——多丽丝·德鲁克。她今年已经98岁,但仍然精神矍铄, 每周打两次网球,出行是自己开车,我想这些大概都足以计入吉尼斯大全。
一见面,我们就开始用“德语”交流(德鲁克的语言)。刚刚寒暄两句,她就问我,“什么是知识工作者?”我没想到她会突然问我如此专业的问题。我说,“知识工作者就是使用自己头脑中的知识,为组织做出决策从而使组织产生绩效和结果的人。”她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你说的对,知识工作者是做决策的人。”我们午餐时,我问她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她告诉我,她正在给一家日本媒体写一篇关于知识工作者的文章。
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的家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这次终于如愿以偿——1937年,德鲁克和新婚的妻子多丽丝移民美国,先后在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纽约大学研究生院(20多年)担任哲学和政治学教授、管理学教授,从1971年起,一直任教于克莱蒙特大学的彼德·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
2000年,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委派我去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学习,师从德鲁克。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2008年,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考取了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的MBA,她是我的骄傲。我们在一起经常用英文来讲“德语”,分享新的知识和感悟。
当我走进德鲁克的家中,看到德鲁克那对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藤椅——德鲁克就是在这张藤椅上多年写作、思考,他的著作的封面照片就是他手执眼镜、坐在藤椅上,这是他一生的最佳写照;看到德鲁克的书架上的藏书,以及简朴而庄重的家具,立刻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超俗脱凡的思想圣殿。

客厅墙上悬挂着唯一的一个奖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唯一能看懂的字就是阿道夫·德鲁克。我问多丽丝这是什么。她说,这是奥匈帝国的皇帝和总理颁发给阿道夫·德鲁克的奖状,是她在德鲁克2005年逝世后,在整理彼得·德鲁克的遗物中发现的。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件,记录着德鲁克家族昔日的辉煌。在他父亲获得匈帝国奖状的100年后,德鲁克于2002年6月20日获得美国总统布什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这两个荣誉见证了德鲁克父子两代人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
我并没有问多丽丝一个八卦问题:如果她看了2009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会不会对其中恋人在车站相会的场景感到熟悉?但类似浪漫的一幕的确发生在德鲁克和她身上。

《大师的轨迹:探索德鲁克的世界》一书写道:1933年,纳粹执掌德国政权后不久,德鲁克前往伦敦,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当证券分析师。一天,德鲁克如往常一样,到地铁车站搭车上班。当他搭长长的电扶梯往上走时,竟然看到法兰克福大学时认识的同学多丽丝在另一座往下走的电扶梯上。两人激动地互相挥舞着双手。德鲁克到了顶端后,立刻换搭另一座电扶梯往下走,却发现多丽丝已换搭他原先那座电扶梯到上面来找他。经过一番折腾,两人终于会合到了一起,后来共同度过了60多年。
在欧洲逗留的这段期间,德鲁克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一名经济学家。他每周都会搭火车去剑桥大学参加凯恩斯主持的研讨会。就在这位伟人眼前聆听教诲时,德鲁克“突然领悟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满屋子的人,包括凯恩斯本人及聪明有才华的经济系学生,只对商品的行为有兴趣,而我却更关心人的行为”。因为这种关心人的倾向,致使德鲁克决心投向管理的领域,以至于日后以管理顾问为终生职业。
虽然自称“旧世界的年轻人”,但德鲁克最终告别了欧洲那个“亚特兰蒂斯神话”。他后来对《财富》说,“1937至38年的美国令人难以置信地兴奋。许多事情在接二连三地发生。社会气候完全不同。在欧洲,唯一的希望是回到1913年,而在美国,尽管遭遇了经济大萧条,但没有人往回看,他们总是朝前看。那真的太振奋人心了。”
和美国的商界及社会一道,德鲁克经历了20世纪“天真无私人的夕阳岁月”。
对美国的贡献
就像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德鲁克发现了管理学。《商业周刊》评价战略大师钱德勒,“在商业史上,BC(公元前)就代表钱德勒之前(Before Chandler)的时代”,同理,在管理史上,AD(公元)就代表德鲁克之后(After Drucker)的时代。
到美国以后,德鲁克给英国几家报社做驻美记者,也为一些欧洲金融机构提供财经方面的咨询服务。1939年至1950年间,德鲁克出版了4部巨作,分别是《经济人的终结》(1939)、《工业人的未来》(1942)、《公司的概念》(1945)及《新社会》(1950)。他深入挖掘“组织中的社会”,被聘请为通用汽车的长期顾问,编辑《财富》杂志,在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都待过,教书成为他的终身职业。
1943年1月,因《经济人的终结》及《工业人的未来》带来的影响力,33岁的德鲁克应邀到通用汽车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考察,做“工业秩序的解剖”。《公司的概念》成了第一本“有关组织、管理和工业社会的书”,开创了“管理”这门学科。
但这本强调分权、劳资关系、公共职责的书被通用汽车视为禁书,其公司图书馆拒绝收藏。通用汽车的总裁斯隆更是不满,他亲自撰写了《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1954年完稿,但10年后才出版,一年后斯隆辞世)。1993年,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再版前言中写道,“通用汽车之所以至今仍然步履蹒跚、无法自拔,主要的原因也是受制于《公司的概念》这本书在五十年前所指出的问题……我愈来愈好奇,通用汽车除了分拆之外,是不是能通过自发或恶意的接管,创造反败为胜的传奇?”2009年6月1日,通用汽车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美国政府提出破产重组的申请。斯隆与德鲁克历尽半个世纪的争辩终于画上一个句号。我认为,两位大师的争辩上演了20世纪最精彩的友谊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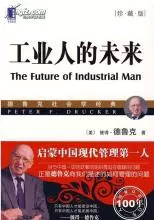
事实上,斯隆对德鲁克的影响很大。德鲁克在《旁观者》中写了一篇“斯隆的专业风采”,以表达他对这位“巨星”的谢意。斯隆的贡献是创建了职业经理人这个行业(manager as a profession)。而德鲁克的贡献是创建了管理学(management as a discipline)。斯隆和德鲁克开创性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这是20世纪事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两个伟大贡献。

1953年,斯隆以个人捐款的形式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了斯隆管理学院。2009年6月,我专程前往波士顿参观斯隆管理学院。墙上有一幅斯隆的标准像,他身穿黑色西装,手轻抚在桌子上,神情凝重而庄严,有一种内圣外王的气质。顿时,我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在斯隆管理学院的墙壁上有一幅铜牌,上面镌刻着:“本建筑是以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命名的。他是麻省理工学院1895届毕业生,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忠实儿子,企业活动家和慷慨而富有远见的慈善家。”斯隆留给后人如此多的宝贵财产,但没有什么比“麻省理工学院的忠实儿子”的评价更恰当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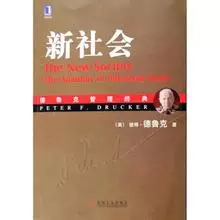
由于德鲁克对通用汽车的咨询,奠定了他作为企业咨询顾问的地位。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不断前来朝拜,IBM、花旗银行和通用电气等纷纷寻求他的指点。1981年,杰克·韦尔奇担任通用电气CEO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德鲁克。早在50年代,宝洁后来的CEO雷富礼的父亲在通用电气克罗顿维尔培训中心就认识德鲁克,其书架上收藏了《管理的实践》(1954)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年轻的雷富礼就看过这些经典著作。
历史是如此的相似。2000年,雷富礼就任宝洁CEO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拜访德鲁克。“在克罗顿维尔培训中心他与我父亲交谈之后,过了整整40年,在加州克莱蒙特德鲁克那陈设简朴的家里,我和他终于坐到了一起,一起畅谈他思考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管理世界”。在德鲁克的帮助下,雷富礼把宝洁从泥潭中拉出,创造了一个市值1500亿美元的公司。
2005年11月11日德鲁克逝世后,有人说德鲁克的时代结束了,他的思想过时了。雷富礼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德鲁克在向美国微笑”,称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德鲁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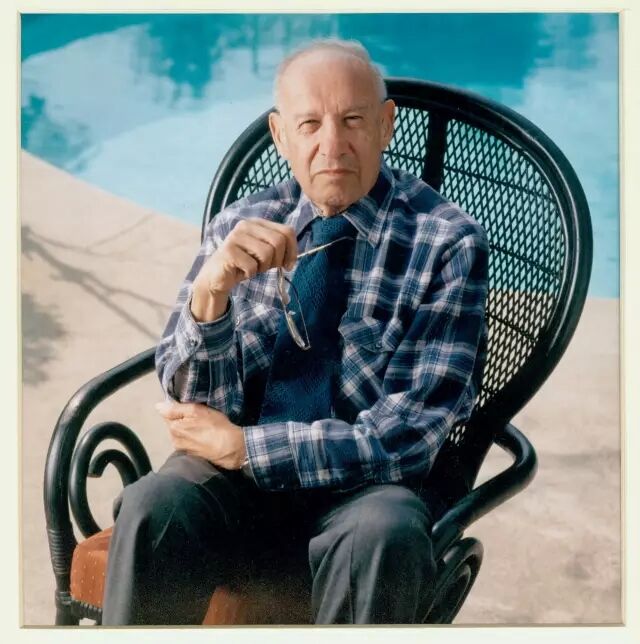
Google的CEO可能从来没有阅读过《新社会》(1949),但是他们所创造的群体文化却与德鲁克的预见非常契合。半个世纪以来,德鲁克是如此洞悉未来:1950年代初,他指出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的崛起;20年后,又是他首先警告日本可能陷入滞胀;早在《不连续的时代》(1969年)中,德鲁克就提到了“知识经济”,“知识工作者”将领导新时代;《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提倡大企业也能创新……汤姆·彼得斯说:“在经营管理学的所有方法中,有80%是由德鲁克创造的,他是当之无愧的经营管理学之父。”写《基业长青》的吉姆·柯林斯曾经在德鲁克家呆了一天,仿佛向《星球大战》中的尤达大师寻求智慧。
2002年6月20日,德鲁克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颁奖词是:“德鲁克大量的著述使我们的国家极大地获益,并且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以及现代商业世界,美国举国上下将共同庆祝他的卓有成就。”
德鲁克对世界的贡献
德鲁克生前曾经说过,他对日本的影响要比美国大。1966年6月24日,日本政府授予德鲁克一枚三等瑞宝勋章,以表彰他对日本企业管理以及他为日美友好关系所做的贡献。
2009年6月23日,我在美国德鲁克管理协会看到这个奖状。自1959年德鲁克首次访问日本之后,每隔一两年他都会去日本讲学。有三位纽约大学的教授对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他们是德鲁克、戴明和朱兰。德鲁克为日本企业讲授管理和市场营销,戴明把质量管理带到了日本,朱兰向日本介绍生产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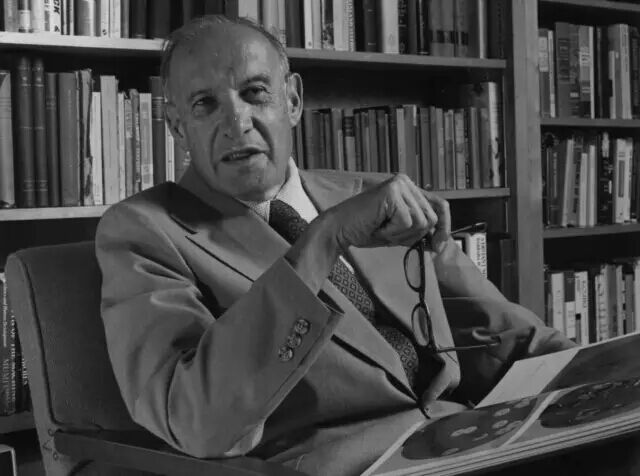
在德鲁克的思想轨迹中,1927年在汉堡大学读法律的一年多时间是他学习受益最多的时期。他读了数百本书,其中有两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是爱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之反思》(1790),“柏克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是要在连续和变革间找到平衡。这样的精神,随即成为我的政治观、世界观和日后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二是斐迪南·杜尼斯的《社区与社会》(1887),“杜尼斯给了我一个永难忘怀的启发:人需要社区,也需要社会——个体从社区中获得地位,在社会中发挥功能。”
当年德鲁克想把通用汽车变成一个“自制工厂社区”,但实验没有成功,后来他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企业身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生和日本企业有着深入联系的原因。
2005年德鲁克逝世后,丰田公司的高管专程去克莱蒙特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以表达他们的哀思,在与杰克逊院长的会见中,丰田的高管说,丰田之道就是德鲁克之道。德鲁克在《下一个社会的管理》(2002)是这样论述丰田之道的,“虽然,通用汽车公司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但在过去20年里,丰田公司却是最成功的一个……紧紧围绕其在制造业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整个集团的运作。”
德鲁克对日本零售业的发展也倾注了大量精力。日本伊藤集团创始人伊藤雅俊是德鲁克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他经常与德鲁克一起探讨企业经营。为了感谢他长期的捐赠,2004年,美国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更名为彼得·德鲁克与伊藤雅俊管理研究生院。在教学楼里的墙上,悬挂着两人的年谱。2000年,我在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学习时,有幸结识了伊藤雅俊的儿子、伊藤集团的现任主席,他送给我一本他父亲写的书,书名为《顾客至上——从一家小店到全球连锁》。该书是1998年用英文出版的,在谈到伊藤集团的成功时,伊藤雅俊特别感谢德鲁克对他的指点。
《德鲁克看亚洲》(1997)是基于德鲁克与日本大荣集团的创始人中内功长达两年的书信问答而结集出版的书。这不是德鲁克重要的著作,但对我的影响很大。从他们两人的对话中,我才真正了解商业的功能和价值。中内功说,“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分销现代化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构建一个免于浩劫的和平社会。”这也应该是企业家的使命。
2001年,德鲁克给日本德鲁克研究专家上田惇生的信,使我们理解了德鲁克与其他管理学家的不同之处。与汤姆·彼得斯和迈克尔·彼特不同,“我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欧社会以及西欧文明的崩溃,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人们对社会的关心。企业以及经营管理并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还有社会意义,我们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上来认识这一点。”
德鲁克想把企业变成社区的理想一生都没有放弃过。杰克·韦尔奇说,“全世界的管理者都应感谢德鲁克,因为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人和组织在社会中的作用。”
德鲁克与中国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德鲁克就来过中国。他当时应国家有关部门邀请,就中国如何有效使用世界银行贷款一事提供专家建议。为此,他访问过北京、天津、内蒙和西安。他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百折不挠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给德鲁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如同1937年德鲁克移居美国后,看到美国人在经济大萧条后仍然向前看,全力以赴参与到“新政”之中。
2005年11月25日,美国《商业周刊》刊登了吉姆·柯林斯回忆德鲁克的一篇文章,题为“学生终生难忘的教诲”。他引用了德鲁克个人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彼得·德鲁克先生对您的盛情不胜感激,然恕本人对以下诸事不能效力:投稿或作序;稿评或书评;讨论或座谈;加入任何委员会或董事会;填写调查表;接受采访;以及在电台或电视上抛头露面等。”

然而,德鲁克非常例外地先后两次为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题词,这表明他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由香港光华集团的董事长邵明路于1999年在北京创办。2000年,他在美国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师从德鲁克,与德鲁克有多年的交往。
2000年5月12日,彼得·德鲁克为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的成立题词如下:
“迅速培养称职的管理人才和创业者,使他们能与世界顶级强手竞争,显然是中国最需要的,也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为中国管理者和创业者提供全世界最优良的管理知识和管理工具,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国际事物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管理的成败系关世界的福祉!这使我突然想起,德鲁克在早在《管理的实践》中谈到管理的重要性时说道:“而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管理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管理的工作也更加艰巨。欧洲能否恢复经济繁荣,这首先取决于其管理层的工作绩效。过去遭受殖民统治的原料生产国能否像成功地发展经济,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否迅速地培养出称职负责的管理者。管理层的能力、技能和职责的确对整个自由世界利害攸关。”
作为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现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首席发展顾问,2001年7月6日,德鲁克特意拍摄了一段对中国管理者致辞的录像片。8年前,我很有幸将这段录像译制成中文。德鲁克的致辞如下:“……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懂得如何管理,知道如何去领导企业并促进它的发展,也知道如何去激励员工和让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
2005年我应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邀请,审订了《管理的实践》中文版,同时为该书撰写了推荐序。德鲁克管理学中的核心是什么?责任。责任的内涵应该是:Do well(创造高绩效),Do Good(做好事),Do no harm(不作恶)。基于我对德鲁克管理思想11年的系统研究,我找到了灵魂与生活的相关关系:灵魂的质量决定管理的质量,而管理的质量决定我们生活的质量。
我们纪念德鲁克的百年诞辰,不是仅仅为他唱诵赞美诗。德鲁克从来不愿被称为“管理宗师”,他说过,“上帝不需要管理咨询顾问”,“我最好的一本书应该叫《管理无知》,很遗憾我没有写”。他的贡献已经深深铸造在历史中。德鲁克与管理学是同义词。我们继承的他的遗产是不够的,我们还要面对未来,迎接新挑战: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