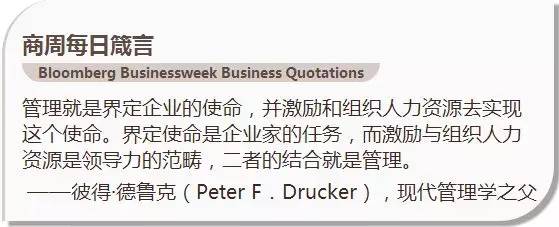
撰文:John A. Byrne、 Lindsey Gerdes
编辑:冯艳彬
翻译:倚橹
他是管理学的开山祖师。今天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实践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他的思考
这也是一个对资本主义自我祛魅的故事。德鲁克逐渐变成“公司化美国”最强有力的批判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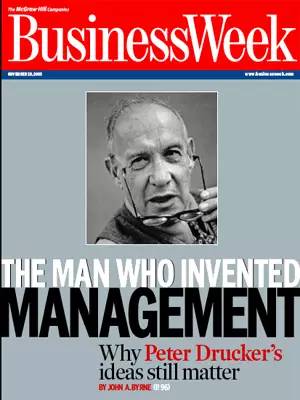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11.19-2005.11.11),现代管理学之父,其著作影响了数代追求创新以及最佳管理实践的学者和企业家们,各类商业管理课程也都深受德鲁克思想的影响。
十年前,德鲁克逝世那个月,美国《商业周刊》封面追思“The Man Who Invented Management”。该文由时任《商业周刊》副主编、管理学及商学院报道编辑约翰拜恩(著有《蓝血十杰》、《韦尔奇自传》等)撰写。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经常会在报道商业或管理故事的时候见到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或是与他交谈。

2005年4月,我坐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一座质朴无华的大宅的客厅里,离德鲁克的右耳只有一步之遥——当时,他也就只有这个耳朵还能听到声音。尽管离得这么近,我还是得向他喊出我的问题,得到的经常是一句“什么?”而非答案。然而,当他终于听明白了我的话时,他的思维依然十分活跃,虽然身体已然老暮衰颓。
他以前总是说,到了他这把年纪,“一个人不再为长寿祷告,而是祈求安然辞世。”自那时起,他便诸病缠身,从危及生命的腹部肿瘤到髋部骨折。两个耳朵里塞着超大号助听器,胸膛里装着心脏起搏仪,德鲁克需要凭借一台助步车才能在这座位于韦尔斯利大道(Wellesley Drive)上的庄园里走来走去。
在那个早春四月的上午,穿着黑色棉拖鞋和刚及脚踝袜子的德鲁克看起来异乎寻常地虚弱疲倦——完全没兴致回顾他创造过的传奇。“我不太擅长内省,”他以自己那为人熟知的带着奥地利口音的低沉男中音发出抗议。“我不知道。我能说的只不过是,我确实帮助了一些人高效率地去做正确的事。”
现在,还是让别的人来为德鲁克盖棺定论吧。11月11日,这个95岁的老人在睡梦中安然辞世,离自己的96岁生日只有8天。
“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思想家。”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前董事长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在德鲁克去世后说。
“他是现代管理学的缔造者和发明人,”管理学大师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指出,“在上世纪50年代初,对于如何管理那些已呈失控状态的复杂到难以置信的组织结构,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德鲁克是第一个为我们提供行动指南的人。”
英特尔(Intel Corp.)创始人之一安德鲁·S.格罗夫(Andrew S. Grove)补充说:“像许多哲学家一样,他言简意赅,却在普通管理者心中引起共鸣。正因如此,他的那些简明扼要的陈述影响了难以尽数的日常商业操作。我在几十年中便受益于此。”
彼得·德鲁克的故事,也就是管理学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现代公司和管理者兴起的故事。若非他的分析,几乎无法想象那些四面扩张、遍布全球的大公司的勃然兴起。
但这也是一个德鲁克对资本主义自我祛魅的故事。在20世纪末,从表象上看,资本主义不仅奖励业绩,更鼓励贪婪。尽管奖励给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巨额财富有助于打破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层级划分,但德鲁克却对此深感厌恶。

在他迎来耄耋之年后,企业界和学术圈中都有人表示,德鲁克的时代已经过去。另外的一些人则指出,德鲁克变得漫不经心了。与此同时,许多靠着著书立传、四处演讲而暴富的新一代管理学大师和权威取代了德鲁克的地位。德鲁克在晚年表露出来的对商业贸易的质疑和幻灭令他不再关注大公司,而转为向非盈利组织提供建议。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德鲁克已对商业管理领域心如死灰。
但德鲁克的传奇并不仅仅是一段旧史。无论是否得到承认,今天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实践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彼得·德鲁克的思考。他的学说为每一个思想领袖绘出了蓝图。在一个速效对策和花言巧语大行其道、华而不实的幻灯片课程充斥其间的世界中,德鲁克深知,担任团队和组织机构带头人的这份工作充满了复杂性。他教会了一代又一代的管理者,要择优录用,关注机遇而非问题,要站在顾客的立场,了解自己的竞争优势以及持之以恒地强化这些优势。他相信,对于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有天分的人才都是最重要的元素。
文艺复兴人
当然,早在这些应景的赞美之词铺天盖地而来之前,德鲁克仍在世之时便已成了一个传奇。他是大师中的大师,大圣人与点子王,老前辈与老烦人精,所有这些集于一身。他在记者、教授、历史学家、经济评论员和故事大王等多种角色中转换裕如。
在他长达95年、成果累累的一生中,德鲁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讲授的领域涵盖了宗教、哲学、政治学和亚洲艺术。甚至,他还写小说。但显而易见,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商业领域。正如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之于经济学,戴明(W. Edwards Deming)之于质量控制,德鲁克也是管理学的开山祖师。
在目睹了纳粹政权的残酷压迫后,德鲁克对现代企业寄予厚望,认为它可以打造众多人类共同体,为工作于其中的人们提供生活的意义。在接下来的50年中,德鲁克倾其才智,帮助众多公司将这种崇高的理想化为现实。
他总是能洞察潮流——有时比其他的人早上20多年。“想要引述一个并非由德鲁克发明或首次提出的重要现代管理概念,结果多半是废然无功,”管理学作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奥图尔(James O'Toole)表示,“这让我既满怀敬畏,又灰心丧气。”

在德鲁克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为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著名首席执行官们提供过咨询,名单上有通用汽车的小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P. Sloan Jr.),也有英特尔的格罗夫。
——是德鲁克,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了“分权”(decentralization)的概念,这已成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型组织的基本管理原则。
——是德鲁克,在上世纪50年代,最早强调员工应该被当成资产来看待,而不是需要消除的债务。
——是德鲁克,仍是在上世纪50年代,开创性地提出了将公司企业视为人类共同体的观点。这个共同体建立于信赖和对员工尊重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的盈利机器。这一观点令德鲁克在日本人眼里成了神一样的存在。
——是德鲁克,依然在上世纪50年代,便首次清晰表明,“没有顾客就没有生意可言”,这一简明扼要的论断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营销思维模式。
——是德鲁克,在上世纪60年代,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早地强调了重实务、轻文饰的重要性,宁要组织结构化的经营实践,而不要那些具有个人魅力、令人崇拜的带头人。
——还是德鲁克,在上世纪70年代,撰写了大量有关知识工作者对企业贡献的文章。要到很久之后,其他人才认识或理解了在新经济时代知识远胜原材料的道理。
他走在了时代大潮的前面
德鲁克将观察视为毕生事业,如拾穗人般捡拾起那些看似十分简单但却常常可以带来惊人后果的点子。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在1981年韦尔奇成为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后不久,他与德鲁克在该公司纽约总部会谈。德鲁克提出了两个被认为改变了韦尔奇职业轨迹的问题:“如果你现在没有开展一项业务,你是否还会进入这一领域?”他问,“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打算怎么办?”
这些问题令韦尔奇首次萌生出大规模转型之念:通用电气旗下的各项业务必须要在该领域内排名数一数二。如果没做到,韦尔奇便会下令对该部分业务进行整顿,或是将其卖出或关闭。这是令韦尔奇将通用电气重新打造为过去25年中最成功的美国公司之一的核心战略。
德鲁克在通用电气所起到的作用是启发指导性的。为首席执行官们提供简明扼要的答案并不是他的风格,相反,他更愿意提出问题,揭示影响绩效的主要因素。他在某次给咨询客户讲课时说:“我的工作是提问。给出答案是你的工作。”

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投资银行公司(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 Inc.)的创始人之一丹勒夫金(Dan Lufkin)在60年代经常求教于德鲁克。他回忆道:“德鲁克从不会给你提供一个答案。开始一段时间这相当令人沮丧。但是,尽管这需要人多费一点脑筋,却对我们帮助巨大。在你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后,你不仅会由衷地对他缜密的思维大为崇拜,还会被他惊人的远见所震撼。他远远走在了时代大潮的前面。”
德鲁克的念头常是信马由缰的,他可以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想到一系列看似不着边际的事,但最后却汇集成某些明确的商业概念。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发表一席演讲,话题从歌德《浮士德》中金钱的作用到他祖母为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弹钢琴的故事。但所有这些故事都为他的观点服务。“他的思考是循环递进式的。”在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讲授“德鲁克论管理学”这门课的约瑟夫·马恰列洛(Joseph A. Maciariello)指出。
德鲁克的天才部分在于他在看似毫无关联的不同学科中寻找共性的能力。身为管理学大师的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是德鲁克的长期崇拜者。他曾问自己的这位老朋友,是如何想出如此多的原创观点的。德鲁克若有所思地眯着眼睛道:“我通过倾听学习。”他顿了顿又说,“倾听我自己。”
在学术界中,这种随机应变、非线性的思维模式有时候会给德鲁克招来罪名:不够严谨,著作没有可量化的研究支撑。“尽管他写了那么多本书,据我所知,没几个教授会把这些书列入MBA学生的必读书目,”奥图说,“彼得永远都不可能在那几家大的商学院拿到终身教职。”
非凡经历
我第一次见到德鲁克是在1985年,当时,我正努力让自己胜任《商业周刊》管理学编辑的这份新工作。他邀请我到科罗拉多州的艾斯特斯公园去。他和妻子多丽丝经常在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露营地的一间小木屋中度夏。我记得他建议我多喝水,摄入大量维生素C,慢慢适应高原反应。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去了解德鲁克其人与他的工作。我们共进三餐。我们一起在露营地的小径上远足。我从此对他的非凡经历有了亲密了解。
1909年,德鲁克生于奥地利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之家,这使他似乎注定要做些什么伟大事业。德鲁克记忆中的维也纳是一个文化和经济中心,他的父母便积极投身于如火如荼的事业中。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德鲁克一家在同一间会员制餐厅里享用午餐,同样在阿尔卑斯湖边度假。
当德鲁克8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弗洛伊德时,他的父亲告诉他:“记住,今天你见到的可是全奥地利——甚至全欧洲——最重要的人物。”许多个傍晚,他的父亲阿道夫(Adolph)和母亲卡罗琳(Caroline)都会在维也纳家中的会客厅里与知识分子精英聚会,讨论的话题从医药到政治以至于音乐。彼得收获的不仅是谈话内容,更重要的是世界观和表达方式。
当希特勒于1927年召集第一次纳粹集会时,身为新教教徒的德鲁克正在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法律。他上过凯恩斯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课。除了大学生的身份,他还在汉堡一家经营出口业务的公司当职员,在法兰克福的一家商业银行担任证券分析师。

德鲁克经历了希特勒崛起的年月,很早就意识到中央集权的威胁。1933年,他关于德国重要保守派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尤里乌斯·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的论文被结成小册子发表,触怒了纳粹,以致于被禁并遭焚毁。4年后,他发表了第二本小册子《德国的犹太问题》(Die Judenfrage in Deutschland),亦遭受到同样命运。仅存的一本如今收藏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中,上面还盖着纳粹的十字章。
在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不久,德鲁克移居到伦敦,在一家伦敦银行担任经济师,同时继续进行经济学的写作和研究。他于1937年来到美国,为几家英国报纸担任通讯员。与他同行的还有新婚燕尔的妻子多丽丝,他们是在法兰克福遇上的。“美国真是令人兴奋,”德鲁克回忆说,“在欧洲,唯一的希望就是重返1913年。但在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在向前看。”
德鲁克也是这样。在正式加入位于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之前,他在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兼职教过一段时间书。他有时简直是一个颇为严厉的工头儿。一位曾就读于本宁顿学院的学生回忆道,德鲁克称她的论文“像撒着欧芹叶的大萝卜”,恨得她“简直想拧断他胖蛤蟆样儿的脖子”,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不幸的是,这家伙才华横溢又大名鼎鼎。至少他真的教了我一些东西。”
德鲁克在本宁顿学院担任政治学和哲学教授。在那里,他于1945年得到了对通用汽车进行研究的机会。这是他第一次得以窥见企业运行的堂奥。这次考察促成了具有突破性的《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一书的出版,也促使他决定于1950年赴纽约大学商业研究生院。
大约在这段时间,德鲁克听说了当时任职于哈佛大学的熊彼得的名言:“我深知,以著作或理论而留名后世是不够的。除非令人们的生活从此不同,一个人就不算真正有所创新。”
开宗立派
他把熊彼得的建议铭记于心,一边开展自己的咨询生涯,一边保持着教师和作家的生活状态。德鲁克最著名的作品《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出版于1954年。这本以“生意是什么?”和“管理增长”为章节题目的书把美国企业当成大学实验室里的青蛙,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剖。
该书成为德鲁克的第一本管理学畅销书,而其书名本身便是一种宣言。德鲁克写道,管理既不是科学也非艺术。它和医学或法学一样,是一门专业技术。管理学意味着人尽其才。正如德鲁克本人指出的:“我之所以写《管理的实践》,是因为当时并无有关管理学的书。那时我已经度过了10年的咨询和执教生涯,但相关著作却寥寥无几。于是我就着手来写这本书,清醒地意识到,我正在为一门学科奠定基础。”
德鲁克在纽约大学执教21年。他为公司高管开设的课程是如此的火爆,以致于授课地点不得不设在附近的一所体育馆中,把游泳池抽干加盖,才能摆得下几百把折叠椅。
德鲁克1971年移居加利福尼亚,出任时称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的社会学和管理学教授。但他一直被认定为一个外行——作家或许,学者未必——不被商学院们放在眼中。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说,他拿到了两个研究生学位,其中包括一个商业管理博士,但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德鲁克,甚至连他写的书都一本也没读过。甚至连德鲁克在纽约大学的同事也反对授予他终身教职,因为德鲁克的主张并非严格的学术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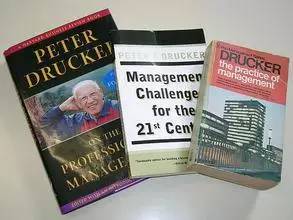
多年来,顶级精英商学院的教授们表示,他们根本就不会花时间去读德鲁克的书,因为觉得他太浅薄。而在德鲁克去世前的那几年,即便是在以他命名的克莱尔蒙特彼得·德鲁克管理学研究生院,院长也表示过:“这个牌子正在走下坡路。”
德鲁克在80年代开始对商业乃至于资本主义本身产生深刻的怀疑。他不再将企业视为缔造共同体的理想空间。事实上,他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企业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大获全胜,而他一直所提倡的平等主义原则一败涂地的地方。借助文章和演讲,德鲁克逐渐变成公司化美国(Corporate America)最强有力的批判者之一。
当大规模企业兼并盛极一时之时,他却对鲁莽的合并和购并大唱反调。当企业高管们致力于建造商业帝国时,他却激烈反对人员臃肿、助理满天飞的低效。在一篇发表于1984年的文章中,德鲁克令人信服地指出,支付给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一路飙升,已经呈失控状态,他请求董事会将首席执行官的报酬限制在不超过普通员工20倍的范围内。让他出离愤怒的是,公司管理人员常常在解雇数千名员工的同时为自己敛得大笔收入。“这在道德上和社会责任上都是不可原谅的,”德鲁克写道,“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80年代的恶意收购潮被当下的许多修正主义者们称为改进美国效率和生产力的关键阶段,但在德鲁克看来,这却是“公司资本主义的终极失败”。他随即将华尔街交易员比做“互相偷对方羊群的巴尔干农民”或“守着食槽互相咬的猪”。他还坚持认为,高达数百万美元的离职补偿金令管理层变得鼠目寸光,只顾自己。“当你拥有了黄金降落伞的时候,”他对一个记者说,“你实际上就是在鼓励管理者吃里扒外,狼狈为奸。”
德鲁克一度对美国的公司价值观如此不满,以致于他冲动地说出:“虽然我相信自由市场,但我对资本主义持严肃怀疑态度。”
曾经少年轻狂
我们总是爱把德鲁克当成一个一生下来就满口金句、高深莫测的老人。至少我是总这么以为。他的演讲总是慢慢悠悠、极有分寸,永远带着浓重的维也纳口音。他的智慧不可能来自一个毛头小伙子。
正因如此,我们很容易忘记,德鲁克曾经的少年轻狂,他对一个女人和与她生的四个子女始终不渝的爱(直到临终前,德鲁克仍会亲昵地称呼结缡71载的妻子“喂,我亲爱的!”),以及他令人莞尔的游戏人间的自嘲精神。
在他早年间为帝杰证券提供咨询时,该公司的合伙人飞到加利福尼亚,在德鲁克的家中与他会面。在某次标志性的长篇大论后,德鲁克觉得大家都需要休息一下了。

“好啦,小伙子们,”他说,“咱们休息几分钟怎么样?去游个泳。
这些高管解释说,他们忘记带游泳裤了。
“用不着游泳裤啊,反正今天这里只有男的。”德鲁克回答说。
“于是我们就脱掉衣服,赤条条地在他家的游泳池游开了。”当时的团队一员查尔斯埃利斯(Charles Ellis)回忆道。
当然,德鲁克从来都不是那种西装革履式的管理咨询顾问。他总是喜欢明快的颜色:翠绿色的衬衫、针织领带、宝蓝色夹克配蓝条纹衬衫,或是羊毛法兰绒衬衫配土黄色休闲裤。
德鲁克总是在家办公,堆满了书籍和档案的书架在重压下咯吱作响。他从来不用秘书,通常自己收传真、接电话——他承认,自己很爱煲电话粥。
隐私至上
然而德鲁克也是一个极其低调的人,很少透露个人生活,即使是在自己的传记中。德鲁克告诉我,名为《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的这本书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传记。
毫不令人意外,在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的德鲁克档案中,也仅保存着一封他妻子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多丽丝从一张1950年代的报纸上剪下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刚刚从一夜好梦中醒来、身穿格子呢睡袍的英俊男子,另一张则是一对热恋中的男女,隔着一盘夜宵四目相对,深情凝视。她将黑白照片粘在一张薄薄的复写纸上,写下这样的字句:“我爱你,在略显忙乱的清晨。我也爱你,在更为浪漫的黄昏。”这封信没有注明时间,也没有署名。
多丽丝在自己尚未出版的回忆录中披露了她和德鲁克在伦敦时的旧事。为了逃过持反对意见的母亲的耳目,她曾将德鲁克锁在一间煤窖中。当多丽丝的母亲在盛怒之下把家里翻个底朝天,搜捕那个和她女儿私定终身的男人时,彼得却在晚上的大部分时间藏身于阴冷黑暗的小洞中。多丽丝的母亲一直希望,女儿可以嫁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某个成员,或是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德国人。她最不愿看到的事,便是女儿嫁给一个奥地利穷光蛋。
在他的晚年,随着健康一步步恶化,德鲁克的磁场也在逐渐消失。尽管他在企业圈里仍有追随者,但德鲁克日益将注意力转移到非盈利机构的领导者身上,比如美国女童子军的弗朗西斯·赫赛尔宾(Frances Hesselbein),以及加州莱克福里斯特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 Church)的创始牧师华理克(Rick Warren)。

撰有《标杆人生》(The Purpose-Driven Life)一书的华理克将德鲁克视为良师益友。“德鲁克告诉我:‘教会管理层的职能是让教会更像一所教会,而不是一个企业。只有这样,你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华理克说,“商业只是他的一个出发点,为他创造一个影响各式各样领导者的平台。”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德鲁克很关心自己将被以何种方式铭记。1990年,他曾激烈抨击过一本对质量控制大师戴明大加吹捧的传记作品。传主戴明一直被德鲁克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当奥图教授试图评价德鲁克1945年对通用汽车的经典研究的影响力时,他得出结论,这位大师不仅没有给通用汽车带来任何影响,反而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这家公司里的不受欢迎者。“我把分析结果寄给彼得,他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与我一一核对,”奥图回忆说,“他对此不太开心,因为他不喜欢那个结论。他觉得他对通用汽车造成了巨大影响。我觉得他要不是对自己太宽宏大量,就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与此同时,当时年逾八旬的德鲁克为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写了一篇有严重缺陷的序言。在其中一段,德鲁克引述斯隆的话称,弟弟雷蒙德(Raymond)的死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悲剧”。然而,雷蒙德实际上比艾尔弗雷德晚去世17年。在另外一段,德鲁克指出,该书之所以延迟出版,是因为斯隆“拒绝在书中提及的通用汽车职员仍在世时发表此书。就在书中提到的最后一名在世者过世的那一天,斯隆同意了出版”。事实上,斯隆在前言部分毫不吝惜地对14名同事大加赞扬,而当《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出版时,所有这些人都还活着。
这些错误到底是出于马虎大意,还是因其脑力衰退使然?很难下个定论。但德鲁克的确已经不在巅峰状态。德鲁克商学院院长科内利斯·德·克勒伊弗(Cornelis de Kluyver)有充分理由相信,德鲁克的影响力正在衰退:这家商学院已经很难从捐赠对象那里获得大笔资助。为了向可怜巴巴的经费中增加一笔2000万美元的捐赠,克勒伊弗在2003年同意为商学院增加一个冠名。新的冠名人是伊藤洋华堂集团的(Ito-Yokado Group)的创始人伊藤雅俊(Masatoshi Ito),该集团拥有日本和北美的所有7-Eleven连锁商店。学生们表示抗议,甚至在院长办公室外游行示威,张贴布告,谴责这一变化。
德鲁克支撑着病体主动站出来对学生们讲话。“我觉得,我死后最多三年,我的名字很可能就会毫无价值了,”他对他们说,“如果把我的名字拿掉就能换来1000万美元,那就加油干吧。”
2005年4月,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我问德鲁克他最近在做些什么。“没什么,”他回答说,“我在慢条斯理地把东西整理起来。我很确定,我不会再写新的书了。我没那个精力了。我的写字台乱七八糟,什么都找不到。”
我几乎为问了这个问题而感到内疚,于是开始对他的成就大唱赞歌:38本书、不计其数的文章、咨询会、对那些世界上最知名的领导者的广泛影响。但他对自己大部分的成就都深感不安,甚至不屑一顾。
“我最好的工作都是早年间完成的——上世纪50年代。从那时起,就不过是些细枝末节了,对不?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逼着这个九旬老人进一步回顾反思。“你看,”他叹息道,“我这个人实在是无趣。我是个作家,作家的生活并不有趣。我的书,我的作品,或许是有趣的。但那不是一码事。”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