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月会邀请一位嘉宾,让他们谈谈最喜欢或印象最深的人和作品。本期是物理学家李淼。
李淼,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也是中国做活跃的科普作家之一,著有《超弦史话》、《越弱越暗越美丽》、《<三体>中的物理学》等。他最新出版的书是《想象另一种可能》。
毫无疑问,如果要从科学家中挑出一个人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爱因斯坦。
我上中学的时候多半时间用来玩了,那个时代没有高考。1978年,我考上了北大,之前不了解爱因斯坦以及他的相对论。大学读到一半,我知道狭义相对论是怎么回事了,当时读的是著名的朗道和栗弗席兹 的《场论》,这个理论的震撼力量我整整消化了半年。到了大学最后一年,我好高骛远,学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然后我对自己说,我要做爱因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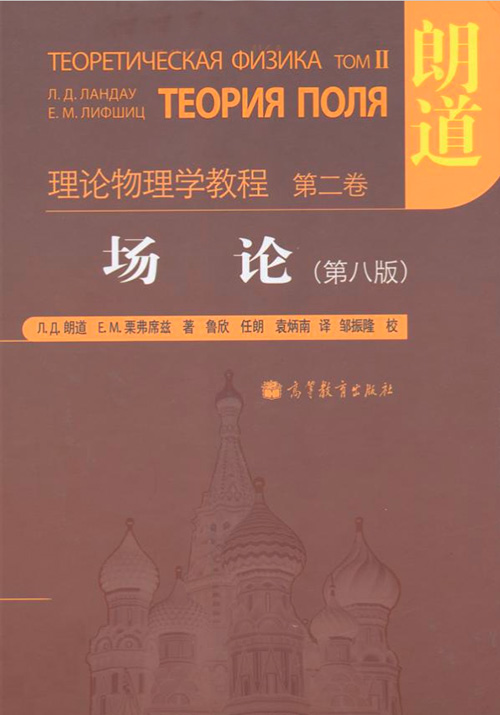
除了爱因斯坦本人,没有人再能成为第二个爱因斯坦,连费曼都不行,我这样的普通物理学家更不用说了。当年在哥本哈根大学的玻尔研究所读博士的时候,我对同学说——其中有丹麦人还有巴西人等各种人:“我过了26岁了,不是物理学天才了”。同学们说,你在玻尔研究所拿学位,不是天才是什么?
反正成不了爱因斯坦,就尽力做一个较为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吧,这是我从26岁到50岁时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现在也没有变。
科普写作是件必然的事还是偶然的事?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判断是偶然的。如果是必然的,为什么在中国大多数科学家不写科普?那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我写科普是必然的呢?人家可能会这样推理:李淼说过小时候喜欢文学,现在,他在玩各种跨界,还玩得很嗨,他有写作才能啊,因此他迟早会写科普。
我小时候确实喜欢文学,那时不用学好数理化,就有时间读小说。人是一种特别的动物,特别之处在于人对世界很好奇,如果不是文盲,TA就会通过阅读来了解世界。我小时候,除了一点可怜的科普小册子之外就只有小说好读,《艳阳天》,《创业史》,《红旗飘飘》之类的。我父亲有一次得了大病住院,我去看他,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一本被翻得破破烂烂的《林海雪原》,我就顺便读了——原来世界上还有比《艳阳天》更好看的小说!那时,《林海雪原》还是禁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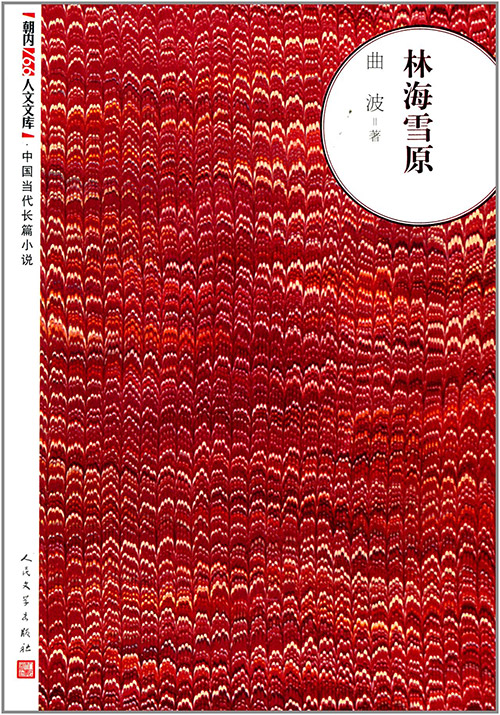
我不仅迷上了文学,接下来也迷上了诗歌——不是现代诗,是古典诗词。邻居有个叔叔做秘书工作,喜欢舞文弄墨,我古典诗词的底子就从他和他的藏书里学。
学习物理学是一个特别苦的生涯,我上大学后就几乎忘了文学。我经常对人说,在美国的时候我进书店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数学物理学书架,一个是科普和科学家传记书架,其他地方基本不瞄。读不读中文小说呢?也读,金庸和古龙。最多加上柏杨——尽管他不写小说,但《皇帝之死》和《皇后之死》很像小说。
我爱读科普,可是,在美国是没有机会写科普的,写科普的几乎都是白人大牛。什么《纽约时报》啊,《科学的美国人》啊,都是这些人的天下,哪里轮到我们写。
1999年我回国,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里管人事的牟克雄有一天跑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李淼,你是研究超弦理论的,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你给《牛顿科学世界》写一篇关于弦论的卷首语吧。我答应了,磕磕巴巴地写了一千字,因为是南方人,拼音不准,那时又没有搜狗输入法。这是我的第一篇与科普有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最后,我预言,十年以后,不懂弦论的人将无法研究理论物理,这个预言让很多人不高兴,因为弦论是少数人研究的,比较难。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个预言只对了一小半,的的确确,弦论的方法现在渗透到很多物理学领域中了,例如粒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宇宙学,还有数学。但是,我不仅对弦论本身作为这个世界的终极理论不乐观了,我甚至觉得我们在一千年以内难以验证它。
网络时代,任何人都有写作和出名的机会,我也不例外。我潜水,在天涯潜,在国外的一些中文网站潜,潜来潜去,毕竟还是要冒头的。这一冒头不得了,就养成了灌水的习惯,也养成了写作的习惯。我的《超弦史话》就是在同事建的一个BBS上一段一段写出来的。这书不容易懂,不是好科普,我的初衷也不是科普,是写比较专业的弦论知识和故事。
后来我给《新发现》写专栏,风格慢慢地变成通俗了,也还不那么易懂。感谢主编严锋教授,他能够接受宽容我那时的科普风格。现在呢?我的《三体中的物理学》还是有些章节不好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用半年中的空闲时间写的,无法将它写成一本所有人能够读懂的科普。我常说,如果给我一年时间,也许它就能成为一本《时间简史》。可是,读者挺厚爱我的,还是比较喜欢这本书。再说,有多少人能读懂霍金的《时间简史》?那是一本可以用来装饰书柜的书,用万维钢的话来说,是知识青年的一种刻奇。

我不想利用年轻人的刻奇,因此我后来写的半本书特别通俗,好像也有趣,可惜我写了一半觉得精力不够,一放就是两年。哪天能捡起来呢?不知道。不完全是精力的原因,我在等待科普市场真正地火起来——那时拿出来,能挣点版税。
我常说,现在我的英雄已经不是爱因斯坦了,因为我够不着。我的英雄是卡尔·萨根和贾雷德·戴蒙德,前者是天文学家兼科普学家;后者是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兼科普学家。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科普不仅仅是科普,还含有新观点,是一种异类的学术著作。我想在退休之后变成他们,写两本科普,可以传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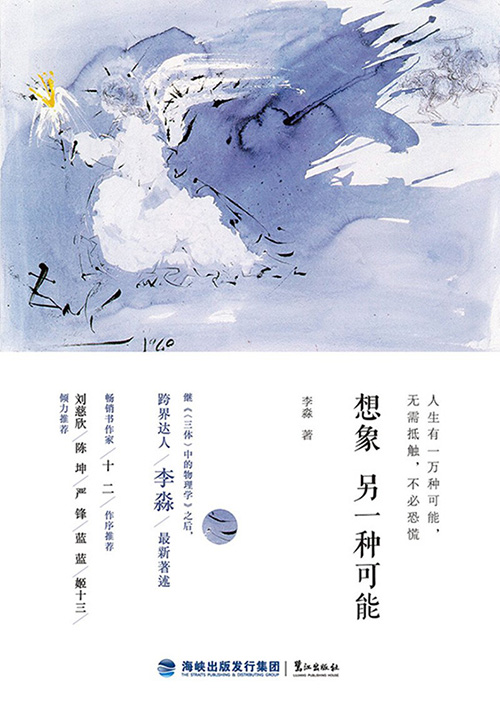
——————
李淼,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也是中国做活跃的科普作家之一,著有《超弦史话》、《越弱越暗越美丽》、《<三体>中的物理学》等。他最新出版的书是《想象另一种可能》。
题图:2015年6月27日,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81岁的Benny Wasserman与其他人化装成爱因斯坦的样子聚集在一起,创造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大的爱因斯坦集会”。图片来自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