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如今万物都可“MBTI”。全称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分类依据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划分的8种类型:i与e代表着内倾与外倾,从内还是从外获取力量,n与s代表着现实还是概念,t与f指向思索与感受,j和p则导向计划还是随机应变。
一只狗也可以分出是i还是e,表情尴尬肢体僵硬的为i,迅速与周围打成一片的为e;一张办公桌照也能透露是j还是p,整洁利落的为j,混乱随意的为p;观看电影《封神》时n人和s人是不一样的,n人能透过现象思考,s人沉浸于鲜活的细节;谈恋爱时f人和t人体验不同,f可能与你一同落泪,而t人提供解决方法。
当MBTI提供了一套互相对立的指标帮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我们真的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吗?
好在一切早已注定
以流行的帖子看来,通过MBTI自我认同,人们在乎的不仅是性格特征,更想要探究自己是如何应用这些特质来生活、工作以及恋爱的,成功与赚钱也成为了MBTI关注的一个指标——有帖子统计了16型人格的收入分布,并提问为什么intp收入最低。暂且搁置MBTI的科学性,它赋予众人的安慰是:做不到的不必强行做到,世事自有模式,如同对于“相信你自己,什么都可以”价值观的逆反。成为不了别人、非如此不可,反而令人们长舒一口气。

命中注定的感觉能够安慰人心吗?博尔赫斯相信,时间并不是由现在流向将来,而是由将来流向我们,人们总是溯流而上,未来转变或溶解为过去,这样的想法缓解了他对于未来手术的忧虑。
人们还喜欢用命定论描述爱情。《缘分天注定》是一部浪漫爱情电影,来自伦敦的女主在纽约遇上了一位帅气的男子,两人一见倾心,但女主认为恋爱的命运会由天命指示,不能擅自行动,于是她为男子编织了许多游戏:假如她随身的一本小说卖给二手书店后被男子淘到,假如她进入一家宾馆的电梯而他碰巧从同一层楼走出,那他们就是天生一对。恋爱的资格在于领会上天的意思,而那指示(sign)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像是路过的电影海报、二手书店旧书上的签名甚至是一场太阳雨。这仿佛在考验凡人是否辨认出上天偶然发出的慈悲提示;男主辨认出女主手腕上不规则的雀斑,认为它们连成了星空的仙后座,这深深打动了女主,也成为日后相认的浪漫证据。从杂乱无章中辨认出可能的讯号与规则,二人瞬时心有灵犀。

电影《星际穿越》同样有辨认讯号与规则的情节,这被解读为亲子之间的羁绊能够穿越时空。女儿相信父亲绝不会抛下孩子,所以能够辨认出手表看似无序的运动,将之解读为莫斯电码。这就像托卡尔丘克在小说《最后的故事》中写的,一切都可能是某种指引,梳子上的上百根头发、突然的头痛和毫无征兆的缓解、丝袜上的洞,以及丝袜从上往下、笔直如刀锋般的抽丝。按照这些作品的逻辑,追随冥冥之中的指引,人就能解决难题、进入正轨,或用流行语说——命运的齿轮因此转动。
土星照命,无法逃避
在MBTI流行以前,星象论命深入人心。它的主要观念:不同的星球特质对应着各类人间事项,比如太阳为男性、力量、声望;月亮为女性、哺育、财富;水星为资讯、智力和交流;土星是缓慢、死亡、磨难等,具有丰富的文学阐释空间。托卡尔丘克在《糜骨之壤》中写道,星盘是天空印在个人生命上的印记,就像信封带有邮戳一样;然而这种印记又像是某种形式上的太空监禁,仿佛罪犯在监狱中的纹身编号,意味着个人无法成为别人,有着无法逃避的命运。
桑塔格为本雅明撰写的《土星照命》正提示着他独一无二的特质。土星一般被形容为干燥、寒冷与缓慢的,桑塔格强调了土星对个性和知识分子气质的影响:土星的影响使人变得漠然、忧郁与迟钝,迟钝是忧郁症性格的一个特征,言行笨拙是另一特征。本雅明的土星气质体现在他的方向感差,看不懂街上的路牌,却因此获得漫游的艺术,因为任何的十字路口都充满着可能。另一方面,土星气质又标志着自我建设的艰辛工程,甚至代表着工作狂,“一个人只好去工作,否则,可能什么都干不了。”桑塔格写道,土星的成功来得极为缓慢,这是适合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气质——本雅明每天的摘录、学习如同他在街道的漫游,将工作变成了一剂药与一种强迫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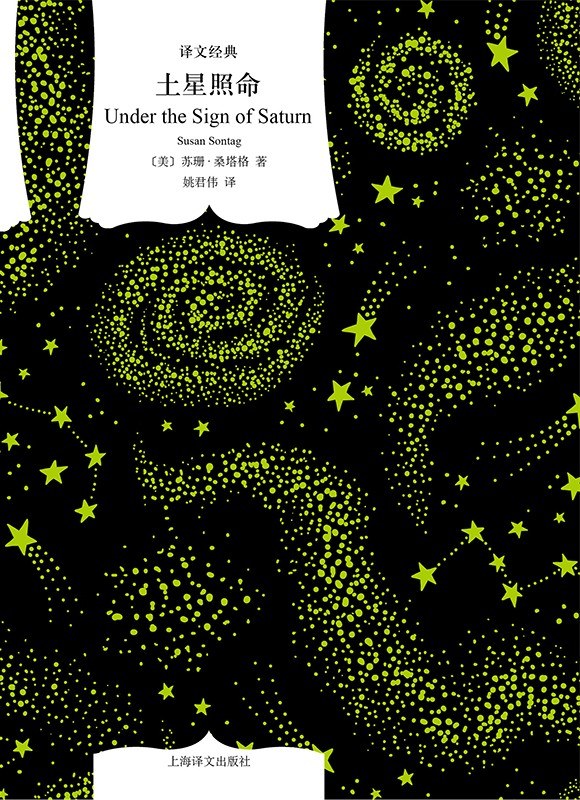
[美] 苏珊·桑塔格 著 姚君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6
沉浸于漫游、收藏的本雅明是“土星人”,他善于积累,坚定不拔,持续推动事业发展与自我改造。在《糜骨之壤》里,“土星人”的形象则不太正面:土星人脑门宽大、眉毛浓密,疑似纵欲过度;木星人仪表堂堂,自信而富有魅力,适合做领导。
土星照命的本雅明实现了“无法逃避的命运”,经典的文学人物也负载着如此宿命。钱理群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中重新梳理了两位文学经典人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演说揭示了这两个文学形象的特质以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经常运用这两种形象自我认同,简单来说,堂吉诃德代表着热情、行动、充满信念与群众统一;哈姆雷特象征着迟疑、冷静、思索,以及难以将自我投入运动之中。
内与外、思考与行动、群众与个人,种种二元对立的区分与MBTI如出一辙。二十世纪许多知识分子本来属于哈姆雷特的队列,最后却改造自我、加入了堂吉诃德的队列当中。典型的变形比如何其芳,他看到了快活的、明亮的、阳光的延安;相比之下,有些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就不太成功,他们长久地陷入自我冲突之中,好像需要在扮演别人和回归自我之间挣扎,不知道应当听从“心”的声音还是顺从于“智”的规则,前者指向浪漫派的心灵自由,后者为现实派的强制裁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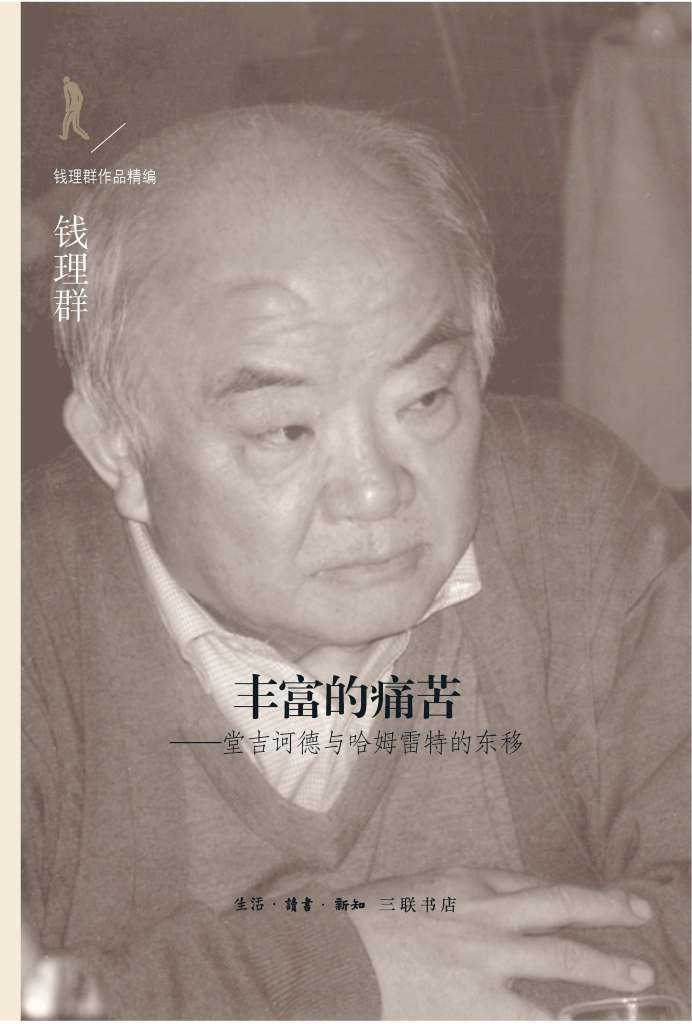
钱理群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5
值得思索的是,在与哈姆雷特的对比中,堂吉诃德显然拥有更多的美德。改造后的知识分子称自己如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旋转,接着消逝于其中,与此同时个人的问题和苦痛也开始消失。钱理群写道,“在一个孤独的个体陷于走投无路的绝望的时候,突然与一种万众一心地奔向同一个明确目标的强大集体意志力相遇,产生心灵的震撼。”如此说来,成为堂吉诃德犹如一种对于个人困境和烦恼的解脱方案。
“死鬼”常在,“业力”难消
对哈姆雷特的否定和贬抑,几乎成了一种时代思潮与风尚,与此相对应的还有静与动、怀疑与确信、向内与向外、象牙塔与十字街头的系列譬喻,就像手工劳动赋予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以工作的自足、身体完满的感觉。叶圣陶羡慕做一个鞋匠,因为工作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思想,而在于工作本身的自足与完满。周作人也将务农看做志业的典范,因为能恢复身体与土地和真实世界的感觉。只是并非所有人都相信堂吉诃德的热情是万能的。
上世纪80年代,诗人杨牧写道,急于关心现实的诗人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愚蠢”、“迟钝”和“无知”当中,“有时难免就像那衰鄙的魔侠堂吉诃德,骑在瘦马上,挥舞一柄愚蠢迟钝的长枪,不知这一些所为何来。”他将堂吉诃德的形象比喻成一个困于紧张、囿于偏见和愤怒的知识者,“长远不断的精神紧张终究可能蒙蔽了知识的洞识和良知的判断;自囿于偏见、愤怒和顽冥,何尝能成就一个诗人。”

有意思的是,屠格涅夫在解读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两种人格时提示了他们的民族与地方色彩:哈姆雷特是一个北方人的精神,而堂吉诃德象征着南方人。这也令人不禁想到丁尼生的诗句——明媚、热情、变幻无常,是南方;沉郁、诚朴、柔软温存,是北方。人格可以演化为地域风气和集体特质,个体的特点通向集体的命运,这又与中国近代作家和思想关注的“国民性”相通。
根据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研究,“国民性”的替代性概念,竟是有着宿命意味的“业力”。在1912年《越铎日报》创刊时,鲁迅写,国人虽然摆脱了政治桎梏,但要摆脱长达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并非易事,因为有种业在起作用,“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
“业”本是印度哲学的karma,指的是决定现在状态的过去的力量,“种业”就是历史形成并且遗传下来的民族的业。之后历史的进程中,鲁迅不断加深对“种业”之顽固的认识,“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多受死鬼的牵制。”对于难以驯服和清除的“死鬼”、“种业”的观察奠定了鲁迅其后在小说《阿Q正传》对“国民性弱点”的批评,即便“国民劣根”听起来比“种业”更具有遗传学、社会学的感觉,潜藏着可以批评乃至清算、重塑的希望。
业力听起来过于神秘,托卡尔丘克在《最后的故事》中讲述,唯有燃烧痛苦才能消除业力,人们渴望自己能像树木一样,在冬天剥离死去的组织、剪去错误的枝条,在新一年到来时重新变得清白又无辜,然而,这很难实现。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