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李斌
校对丨于墨林
编辑丨安西西
也许你只记得电影《最爱》是郭富城章子怡演的,《边境风云》是孙红雷王珞丹演的,《最心疼的女人》是刀郎唱的,《野蛮生长》是李宇春的最新专辑……
但在这些电影和音乐的背后,有一个不为大众所知晓的名字陈伟伦,这个一直躲在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其实在圈里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十几年来,他跟很多歌手、大导演合作,也在不少电视节目中担任音乐总监;他说更愿意做一个制作人,而不是一个歌手或音乐人。
前几天,当音乐财经第一次见到陈伟伦的时候,好像突然理解了他为什么喜欢躲在幕后。见面之前,印象中的陈伟伦应该是一个很牛的制作人,而且还是那个留着中长发的形象,但那天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陈伟伦已经剪了精神的短发,差点没认出他来。
他说起话来语速很慢,也没有之前想象中那么“牛”,闲聊了一会,瞬间觉得采访陈伟伦可以是一件非常放松的事情。我们每提出一个问题,他都会很认真的思考一下,然后娓娓道来。不经意间还会突然冒出一句:“我今天说的好细呀!”

与生俱来的音乐细胞
陈伟伦的音乐启蒙从他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由于从小学习吹小号,又幸运的遇到了一位新潮的音乐老师,所以陈伟伦小学的时候就组建了一支电声乐队。
也许是天生对音乐非常感兴趣,上了初中后,陈伟伦开始自学乐理,而那个年代,又赶上了港台流行音乐入侵的时代,包括香港的四大天王、Beyond等,而同一时期国内的摇滚乐也开始流行,唐朝、黑豹、崔健、魔岩三杰,这些人对陈伟伦早期的音乐启蒙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没过多久,陈伟伦所在的城市张家口开始流行打口带,这个时期也成为了他音乐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大批的国外音乐进来,一下子打开了陈伟伦的音乐世界。正在上高二的陈伟伦又组织了他的第二支乐队,他是乐队的主唱和吉他,比他大一届的张博(现SAG的创始人)是乐队的贝斯。
当时在张家口这座小城市里,很多人都在玩摇滚,这支高中生乐队也经常在小酒吧里演出。就在临近高三毕业的时候,他们在张家口第一中学礼堂里组织了乐队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演出,当时还请了一支社会上的乐队跟他们一起表演。
陈伟伦回忆:“那场演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唱的歌其实很幼稚,但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因为我们学校是张家口的重点中学,大家都在备战高考,从来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突然有这样一场演出,学生们都疯了,很多人脱掉上衣,似乎还有人在礼堂里放火。结果没等演出结束,就被校方叫停了。”
大学毕业那年,陈伟伦在学校音乐厅里开了一场个人的音乐会,而那时的陈伟伦已经创作了不少自己的原创作品,那场毕业音乐会又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遇到对的人和好的机遇
大学毕业后,陈伟伦直接来到了北京,刚好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使他进入一个电视节目剧组,到全国各地的偏远山区采访少数民族文化,比如到贵州、云南、内蒙古、陕西、四川等地区采访当地的少数民族音乐人。
这档节目差不多做了两年,陈伟伦在这期间采集了很多不同民族音乐的采样,到现在还保留着,以至于他在后来的音乐制作中还会经常用到当年采集来的音乐元素。陈伟伦说:“这次的经历也是我音乐之路的又一个转折点,对我触动很大,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民族音乐,特别是侗族大歌、苗族情歌和木鼓舞,还有表演性特别强的川剧和傩戏,包括后来给左小祖咒做的音乐里面还用了不少当时采集来的元素。”
2005年,陈伟伦又遇到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华裔音乐人Evan chen,开始了陈伟伦两年的音乐人助理生涯。十年前,数字音乐还不是很发达,所有音源都是硬件,所以每次做歌的时候都需要插很多线。陈伟伦每天的工作几乎就是插线、调试设备、整理硬盘文件。
陈伟伦说:“Evan是一个要求非常苛刻的人,就连文件夹的命名都要非常规范,一个音乐的Demo是什么时间打出来的,几月几号第几个版本都要标注清楚。他教会了我一个非常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态度,也是从那时起,学到了真正国际化的制作标准。”
Evan chen还与陈伟伦一起创立了一个音乐厂牌Tea Records,把中国音乐的元素放到世界音乐中。他们共同创作了几十个Ambient Bea风格的世界音乐,尽管后来的传播不是很广,但对于陈伟伦来说,那段经历非常有意义,这是他把中国元素放到世界音乐体系里的第一次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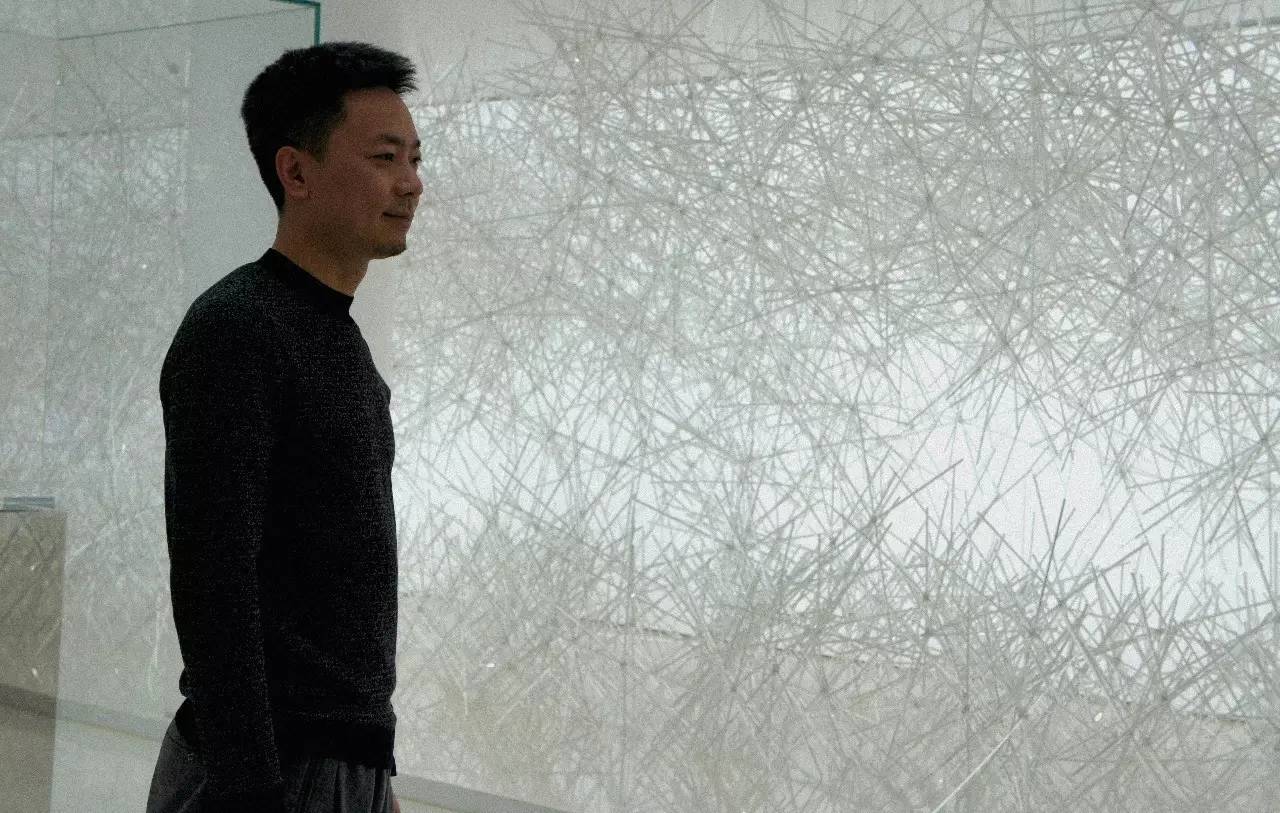
站在歌手幕后的人
采访中,陈伟伦几次提到,他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在音乐这条路上,一直都在遇到对的人。接触和熟悉了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的陈伟伦,开始了自己独立制作音乐的路。
他曾为左小祖咒、许嵩、周云山、刀郎、李宇春等歌手担当专辑制作人和编曲,提起跟左小祖咒的合作,陈伟伦表示:“跟左小合作的那几张专辑,他对我很信任。我像做自己的音乐一样去做这些音乐,再把左小独特的声音放进去了,最后我们真的像创造出来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
在陈伟伦眼里,左小祖咒最厉害的是他的艺术判断力和审美能力,他的歌词非常好。而且他很坚持自己的艺术态度,别人会说左小祖咒唱歌跑掉,但他甚至还会更夸张的表现这一点,最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从音乐层面我很感谢左小,他给了我很宽的自由度。”
最近,李宇春的新专辑《野蛮生长》数字专辑销量突破了600万,在这张专辑中,陈伟伦也担任了制作人。这也是陈伟伦与流行歌手的一次全面合作。谈起跟李宇春的合作,陈伟伦坦言,当初还是纠结了很久,因为在他看来,接李宇春的专辑压力确实蛮大,跟李宇春合作过的制作人太多了,如果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但两个人见面后聊的很投机,李宇春当时聊了很多自己对音乐的看法和追求。这也让陈伟伦更有信心去做出不一样的音乐。
“其实专辑做起来也并不轻松,我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做了四首歌的制作及专辑母带的制作。这张专辑很成功,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完美。所以希望2017年我们能有更深入的合作。”

在电影配乐中找到自己的个性
除了跟艺人合作专辑制作,陈伟伦还做了不少电影原声的配乐,比如纪录片《进藏》、程耳导演的《边境风云》、顾长卫导演的《最爱》的电影原声。《最爱》还获得了2011年金鸡奖最佳配乐提名。
陈伟伦表示:“大部分国人对歌曲更感兴趣的是歌词,对音乐本身的关注度并不敏感,但把音乐放在电影里就会很具象,让视觉和听觉结合在一起,所以做电影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自由创作的机会。”
之前陈伟伦为央视做的一个手语公益广告的配乐,只用了钢琴和小号两个乐器,但他认为那个音乐感染力却非常强,所以影像跟音乐结合的时候,传达力会变得更鲜明。
在他看来,电影音乐对于影像来说不是一个附属品,音乐在电影里是一个包容的、综合的艺术呈现,有时候是平行的、有时候是交叉的,有时候音乐在先,有时候音乐在后。有时候会在欢快的故事下配一段很伤感的音乐,或者在伤感的桥段里配一些节奏快的音乐。陈伟伦说,这是为了尝试做出更有自己独特标签的音乐。
类似这样的处理方法在陈伟伦的创作里非常多,包括在《边境风云》中,男主人公被贩毒团伙活埋的场景。在男主人公怀着对新生活向往和残酷现实的矛盾中,陈伟伦运用了一首非常柔情的哼唱,这使得残忍的镜头富有更加深刻的情感。
无论做电影音乐还是电视音乐节目,都让陈伟伦积累了非常有价值的经验。“目前电视媒体在中国还是主导并有巨大传播量,一方面可以了解更多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和更多优秀的音乐人、媒体人合作。以前我是作为一个乐手来参与,现在是作为一个节目的音乐总监,一步步的提升自己,也希望在这些平台上传播和放大自己的音乐理念。”陈伟伦说。

之前你的专辑《夜之色》找了很多歌手和乐队来演唱,为什么不自己唱?
陈伟伦:我做的是一张音乐制作人专辑,所以我的第一张专辑出来大家都很奇怪,说为什么不是自己唱的。我找了很多当时还不为人熟知但现在却很火的歌手来唱这些歌。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你不唱歌大家就不认识你。所以我准备在明年发一张自己演唱的专辑。
我不想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音乐人,而是制作人,因为制作人的职责让我的音乐延伸的更广泛,比如《进藏》有很多部分需要把民族元素用交响乐模式展现;《本草中国》则用更多的民族乐器来表现中国医药的精髓和故事,我希望能从制作人的角度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音乐之路。
你更多时候是在幕后,做了这么多年制作人和编曲,你觉得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在哪?
陈伟伦:中国目前只有词曲版权,还没有编曲版权,但我觉得一首歌50%以上的价值都来源于编曲和制作,但这50%的价值没有被体现,包括乐手也是这样,只能拿到一点点劳务费,版权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所以音乐人一直很辛苦,我身边原来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后来都放弃了音乐这条路,非常可惜。在国外音乐行业更发达和规范,大家认得制作人的价值,也知道在一个乐队里谁是贝斯手,但在中国很多人只认识唱歌的人。
你觉得中国有乐坛文化吗?
陈伟伦:中国没有乐坛文化,乐师和制作人永远都在幕后。而国外是协作为先,所以产生了先进的和声、节奏和多样的音乐。像最早的欧美音乐也是从非洲传过去的,那里有很多群体性的节奏音乐。
但中国音乐历史中,很少有协作意识,所以中国大部分是旋律线条的音乐,很少有和声和复杂节奏。另外,中国的传统就是诗歌不分家,诗就是歌,歌就是诗;所以也导致了中国人现在的审美,听音乐主要听歌词。

你以前很少做大众流行音乐,在你近几年接触流行音乐市场后,你有什么新的认识?
陈伟伦:传统唱片行业模式就是给艺人收歌,一年收100首歌,然后从这里挑出10首,再打包一起出专辑。现在看来是很落后的,因为那些音乐不是自己做的,只是作为一个商品放在那,谁觉得合适谁买。
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音乐市场发展太缓慢了。其实世界当今的模式就是更独立化,更个性化,而且有连续性,作品用来反映音乐人的生活过程和状态。其实国内有一些独立音乐人的方式已经很国际化了。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流行音乐市场只是针对一小撮音乐圈子,包括电视媒体:《中国好声音》(现为《中国新歌声》)、《中国好歌曲》,大家推广的音乐仅仅是一个狭义的流行音乐。希望有更多的新模式出现,有个性的音乐人跟流行市场有更多的对接。
其实中国现在已经有丰富多彩的音乐形态,也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新乐府,很多音乐人都很有个性,都具备流行的潜质。
跟顾长卫这样的导演合作过之后,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陈伟伦:顾长卫是一个非常艺术的人,他也愿意做更多的尝试。他的每一部电影的每一个桥段剪辑版本不下10个,都是一些很微小的镜头。电影配乐也是,每一段音乐的修改版本都有很多很多。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样做会被认为是纠结。但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玩得开的人,他愿意做更多的尝试。
你也做了不少跨界和融合方面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陈伟伦:前十年我们太孤立了,总在说西方音乐什么样,中国音乐什么样,像是翻了一堵墙。其实国外的音乐家在使用中国音乐元素方面,甚至比中国人做的还牛逼。中国人看上去很开放,但在文化层面依然很闭塞,没有把自己置身于世界,不够宽容和自信。
我现在做新乐府,有很多人会说,把老祖宗那点东西都毁了。但其实新乐府是在创造,我们想创造一个新的模式,并不是给中国传统音乐穿一件新衣。我们必须放眼世界。用当今世界音乐审美的语汇去发扬中国文化。
你觉得可以让世界接受的音乐理念是什么?
陈伟伦:我的创新理念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一些精华的表现形式放到世界音乐审美语汇中,做的是一个全新的音乐,而不是单纯传承旧音乐。传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原封不动地去继承,师父怎么教的就怎么做,一点不能变,500年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另一种是把祖先的东西消化成现代人应该有的状态,用现在的音乐形式去表达。新乐府要做的就是这个,可以让中国人把遗失的找回来,也可以让世界人接受。中国音乐本来应该在世界音乐领域有一席之地,只不过我们没有跟进世界的音乐语汇,让世界听到。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