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期主持人 | 徐鲁青
下班后只有精力刷小视频,没力气看书看长电影,好像成了人们的常态。
在《花束般的恋爱》里,主角上班几年后,从打《塞尔达》的文艺男变成只能玩《智龙迷城》的社畜,再也看不进书了。最近网络流行的二创改编,各大城市的男女主角踏遍文艺地标,最后都因为工作太累,兴趣渐行渐远而分手告终。除了玩笑,评论区也会出现“我也是男主”、“文化体力”耗尽等感慨。“文化体力”对应着生理体力,指没有体力参与较为深度的文化、艺术等活动。就像在剧里,男主角看到一墙的书,说自己已经“读不进去了”。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读不进书了?
观察身边的朋友们,很多人都开始放弃完整电影,只看解说,吃饭一小时就可以刷完四五部大片。从多年前开始,我也习惯了看剧调至1.5倍速,一边快进,一边跳跃到大结局。最近微短剧的风行或许也和当代人文化体力有关,一分钟一集的长度,刚好掐准了我们的耐心值。

另一方面,市民夜校和老年大学却好像火爆起来,原本是老年人占大多数的课堂,现在涌入很多打工后倍感疲惫的年轻人,有媒体把市民夜校看作人们文化体力的唤醒地。疯狂报名抢夜校的年轻人是为了什么?作为文化记者,每天的工作就是和书打交道,你有文化体力不够的时候吗?你如何看待文化体力不足的焦虑?
也欢迎读者给我们留言,说说自己的看法。

01 看烂片也能治愈,口水歌也有门道
徐鲁青:上一天班之后没有文化体力做深度思考,只能回家刷短剧,你们怎么理解这样的状态?
潘文捷:可能是没有吃饱。忘了哪本畅销书里有谈过,人意志力不够常常是因为饿肚子血糖低,吃饱了之后就不容易在超市疯狂采购,不容易和人吵架,可能也会更有力气阅读海德格尔吧。
林子人:其实《花束般的恋爱》是我家属强烈推荐我看的,他有一次出差在飞机上看了这部片子,大为震撼,回家后就拉着我又一起看了一遍。看完后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家属对这部片子印象深刻,他其实是对片中男主角的境遇心有戚戚:加班、出差和应酬不断吸干了自己的精力,回家后就真的只想躺倒刷抖音了(不过也是托抖音的福,家属对最新影视作品的了解程度比我高多了)。我家也有满墙的书,他从头到尾读完的书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徐鲁青:有时候看烂片会给我一种治愈感,特别是在情绪脆弱、精力衰竭的时候。人在特别疲惫后容易质疑事情的意义,但小视频娱乐可以阻断我去面对这些问题。看“俗”一点的烂片,每个人都活得热热闹闹的,觉得也挺好,还有什么过不去呢。

潘文捷:如果幸福是快感的总和,那么获得幸福人生的秘诀就是吸毒。虽说甲基苯丙胺之类的物质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为啥有些文化消费尤其令人上头上瘾呢?我特别喜欢看大烂片、狗血剧的剧情吐槽,一个是本身剧情狗血夸张,二是解说up主狂喷的语言又搞笑又让人站在制高点上。
仔细想想,这也是高超的技巧不是吗?阿多诺批判流行音乐工业化,现在大家都不听鸿篇巨制的古典音乐,改听几分钟一首的歌曲了。但是流行音乐能做到用同一个4536251做出这么多歌来,还产生了不少名作,也多少有点儿神乎其技。
我们说文化体力的时候往往说的是消费,如果从生产的这一头去琢磨,并不是用同一个和弦走向的任何口水歌都能红得起来,也不是任意一个短剧都那么令人上头,其中也有不少门道。
董子琪:阅读真的需要门槛。观影好像好很多,最近看不进去书的时刻,就会看电影,看老电影、新电影、不知名的电影,找回了过去的一点感觉,也有一些更细微的观察——像是许多流行电影里都会安排男女主人公读书,像桑德拉·布洛克在《触不到的恋人》里就一直在读简·奥斯丁的《劝导》,《缘分天注定》里凯特·贝金赛尔和约恩·库赛克因为《瘟疫时期的爱情》结缘。这些文本与电影本身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也成为了富有意味的注脚。 这是不是意味着流行文化与严肃经典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转化和流动的可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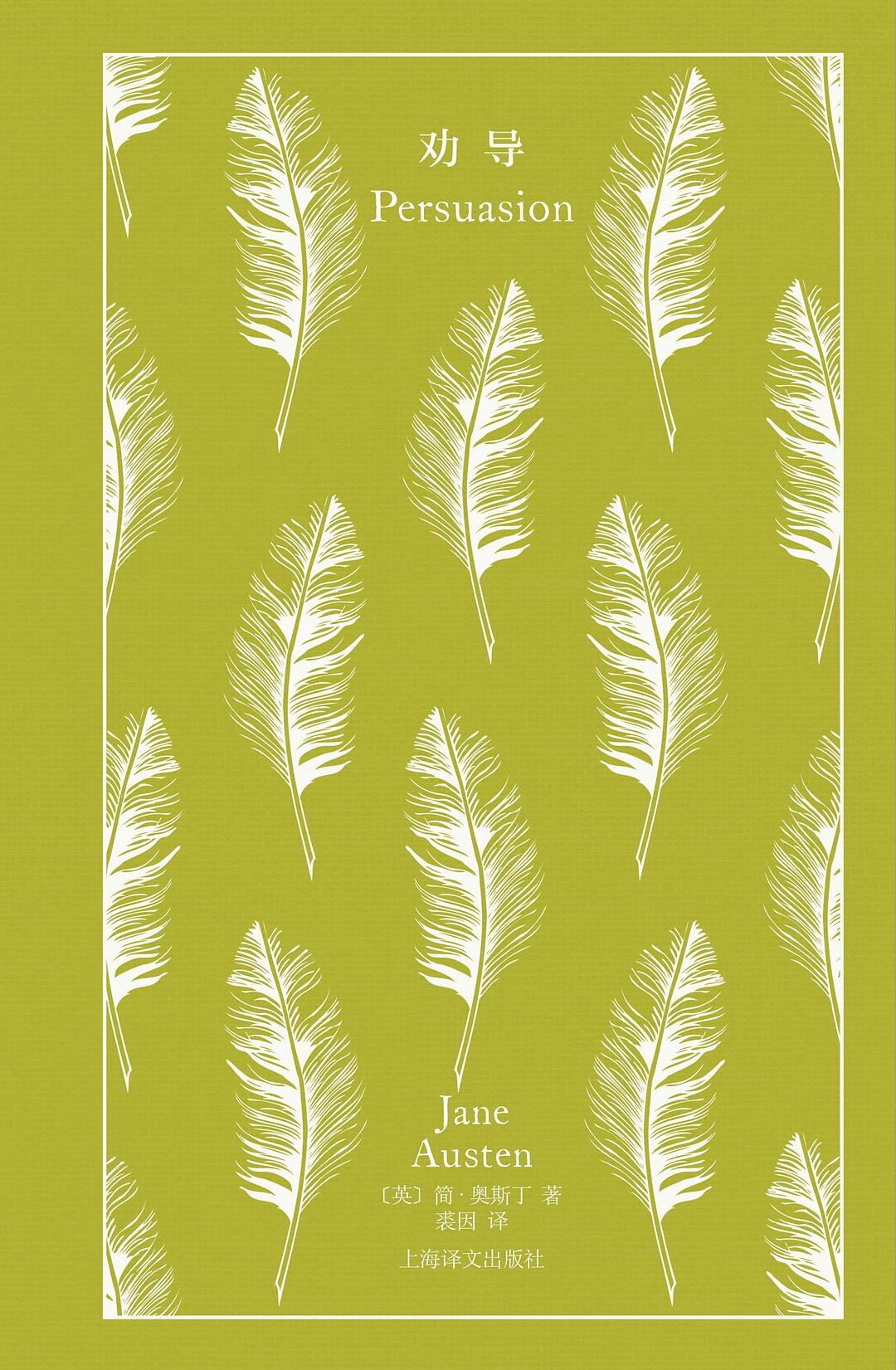
[英] 简·奥斯丁 著 裘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10
02 资本主义将重构我们的生活、希望和关系
徐鲁青:你作为文化记者的状况是什么样,有文化体力不够的时候吗?
林子人:托工作的福,我们文化记者有很多机会从事文艺活动,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我们能一直保持文化体力!就我个人而言,文化体力被消耗的时候,恰恰是自己被要求亲历各种文化现场的时候:展览、演出和讲座,新书、电影和电视剧,我们被要求时刻保持敏感的文化雷达,向读者介绍最新的热点事件,但记者的注意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我们没法做到时时在场。
今年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体力,我腾出更多时间看书,大大减少了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间,对绝大多数综艺节目更是敬而远之。打开任何超过一个小时以上的视频我都要斟酌一下,能利用独自吃饭的碎片时间看完的视频再好不过了。于是我发现自己最近都在看动画片,现在在追《间谍过家家2》和《葬送的芙莉莲》。
的确,文化记者能参与各种文艺活动,但我们能抱怨所谓充沛的文化体力带来的倦怠吗?《躺不平的千禧一代》这本书的作者安妮·海伦·彼得森也是一位文化记者,她在书中提到的一个现象我感同身受:她认为最应该对倦怠感负责的是社交媒体平台,它进一步模糊了工作与娱乐的界限,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每时每刻都是产出内容的机会,你的社交账号就是一个精心打造的个人品牌,这一点对知识工作者来说甚至更加重要,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内容输出和表达自我。她写道:
“那些原本能抵消或缓解倦怠的时刻,就这样被社交媒体撕得粉碎。社交媒体使我们沉溺于记录发生的事件,而与事件的实际体验疏离。它也把我们塑造成毫无必要的多任务处理者。它还侵蚀了人们曾经所谓的闲暇时光。而其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点也许是,它摧毁了独处的可能性:凯尔·纽波特(Cal Newport)借鉴雷蒙德·凯斯利奇(Raymond Kethledge)和迈克尔·欧文(Michael Erwin)的定义,将‘独处’描述为‘自我心灵不受来自其他心灵的输入影响的主观状态’。换句话说,与你自己的心灵作伴,与经验揭示和挖掘出的所有那些情绪与念头作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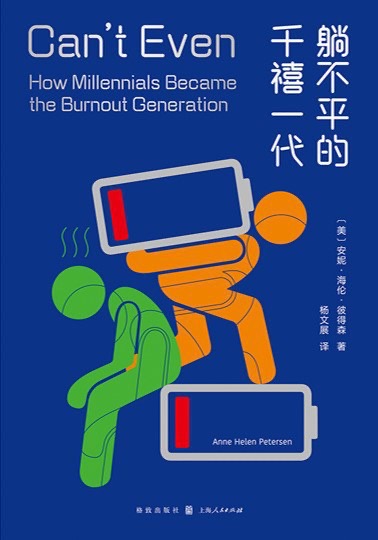
[美]安妮·海伦·彼得森 著 杨文展 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10
徐鲁青:《躺不平的千禧一代》里描述,美国的“千禧一代”(1981—1996年间出生的人)深陷职业长期倦怠,筋疲力竭的状态一直持续,休闲时间被工作不断挤压侵占,所剩无几的休息花在手机上。我很喜欢美国记者Ezra Klein给这本书写的评价:“我们以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经济的方式。但如果时间足够长,它的影响还不止于此:资本主义将组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关系。”
不仅是与人的关系,还有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的愉悦感被重塑了,但愉悦不是生命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吗?看来这个系统不会到点下班,更不仅仅影响我们的银行进账,它潜移默化地潜入生命的方方面面。
尹清露:认同鲁青说的,资本主义将重构我们的生活、希望和关系。我认为用《花束般的恋爱》来说明这一点十分合适——当生活被压榨到精疲力尽,连看书的力气都没有,自顾不暇之时又怎么指望认真恋爱呢?上次还跟同事聊到,身边这么多有关婚恋的愁苦和吐槽,前怕NPD(自恋型人格障碍)后怕凤凰男,好像恋爱更多是关于两人如何互相戕害而不是互相治愈,但这并不怪人本身,而是我们压根没有身处让人有余裕“对别人好”的环境中。扯远了,我想说的是,首先要明白看不进去大部头不是你的错也无需怪自己,在无助疲惫的时候,guilty pleasure也可以成为救命稻草般的生命之光。
子人说到最近看动画片较多,然而疲惫的时候,即使是动画,我也只能看泡面番或者无厘头的中二作品,尤其是和现实没有太多关联的作品,比如最近爱看的《辉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讲的是精英学校的会长和副会长互相爱慕却死撑着不告白的故事——因为距离现实太远,看了就会觉得放松。前几天兴致勃勃地打开了期待已久的浦泽直树的《冥王PLUTO》,其中对中东战争和AI的指涉实在是太压抑,在文化体力不足时,已经很难把它当作娱乐向作品来看了。还依稀记得以前在大学时是很沉迷于浦泽老师那些既魔幻又宏大的叙事的,这样看来,我非常能共情《花束》男主角的经历。

03 没有了文化体力,更无法直面人生的深层无聊
徐鲁青:虽然很多人都感到文化体力不够,但现在市民夜校却很火,人们打完工还会去上几节音乐戏剧茶艺课,好像是几年前没有的现象。上班之余,“想学门手艺”也是这些年经常听到的话。手艺好像和文化体力所指的“高雅文艺活动”不同,有一些实用性,但又不会多耗费文化体力。
潘文捷:市民夜校的快乐在我看来既有薅羊毛的快乐,有社交的快乐,也有真的学到什么东西的快乐。
董子琪:文艺夜校看起来非常有趣。我萌生过学个手艺的念头,也很向往老年大学的课程,总觉得其中酝酿着某种诗意,就像是枝裕和电影里会让老太太去学习古典乐,应该有超出培训的意义吧。
其实上海有许多培训项目,价格不贵,还有补贴资助。我也读过相关的报道,觉得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人想要在公司职场和家庭生活之外寻找到另外的空间,一个可以与人联结同时又发现自我的场合。这意味着一种对于个体身份多元化的想象,因为平常人们总是固定在一些家庭角色与职位中,而这样的场合能够让人们稍微喘口气。

作家保罗·索鲁回忆过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夜校,向来尖酸刻薄的他,对于那些努力奋斗学习外语的年轻人,变得非常温柔。他能体会到当时在夜校读书的同学们迫切渴望念书的心情,鼓励他们说,人人都知道夜校是个好东西,但是坚持上夜校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因为他们白天全部都要工作,“只能说他们是值得的,他们在尽他们所有地寻找自己在中国大众中的出路。”
但另一方面,年轻人是不是过于相信培训了呢?之前参与过一个活动,分享“年轻人不想上班”的话题,在场的年轻读者的反应也很有意思:有一位读者表达,不想上班的gap之年,她其实也得不到真正的休息,因为总想要充实自己,所以总要报上几个班,再学几门外语。这样的情况也相当普遍。这是文化体力旺盛的体现,还是无法直面人生的深层无聊呢?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