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窄播
我们时常羡慕别人家的城市,有着合理的道路动线、温情的街头生活和繁荣的小店经济。虽然有本地习俗和历史建设等等原因,但令人羡慕的城市生活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
每一座城市在走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断面临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与选择:城市建设最核心的动力是什么?
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为了适宜宁静的生活环境,基于完全internet化的交往方式,进入一个远离中心制、享受疏离感的存在状态,人们不必聚集在某些共同场合就能满足各种需要。
在中国,「社区」一词多用于互联网产品上,里面的人群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认识不再重要。
另一方面,这样的生活趋势导致了不容忽视的「社交赤字」。人类对于同伴和群体有着本能需求,但线上关系多不如实际关系深厚真诚、值得依靠。比如人们在发信息时常常面无表情,也容易口出妄言。
在现代大城市里生活的人,看似拥有了个体忍受孤独的能力,实则享受的是既不陌生又不亲密的中间状态。
一个拥有便利生活供给和健康社区关系的城市,是尊重了上述两个人类现代生活的趋势,从中寻得的合理平衡点。说到根本,这些城市尊重了生活其中的人。
人的活动是城市最大的吸引力,也是一座城市得以最重要的驱动力。运用、改造和重建城市空间,让这里的居民——无论熟人还是陌生人——能简单直接地接触彼此,城市的真实活力才能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同时出现。
2023年,中国城市之中也出现许多令人关注的新现象:上半年的淄博和最近的哈尔滨,都在利用新视频平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湖南长沙不断冒出新的餐饮品牌和网红街区,「打卡」变成一座城市的品牌标签;崛起中的小红书,在许多城市推动出现citywalk、骑行、露营热潮,鼓励人们从家中走到户外;重新开放的香港也在着重向内地游客推荐夜经济体验、城市文化旅行;阿那亚为代表的地产商不断创造出一个个乌托邦式的新型商业社区等等。
与此同时,城市出现的难题也始终被人关注:代表着美好往昔的霓虹灯招牌是不是该被拆除,路边小店的管理边界应该到底在哪里,地产行业进入新阶段之后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实现转型,大型公司工厂是否会破坏一个城市的既有生态,重点城市的人口是在流出还是流入都像一道谜题......
城市也因此是我们在2024年将继续重点关注的议题。
回溯许多成功城市的发展历史,类似的问题也曾经出现并且困扰着他们,他们如何度过才是我们需要重视的经验。我们选择了迪士尼乐园、哥本哈根、纽约市和波哥大等四个案例,探讨城市与人、社区与商业之间的动态关系。
本文摘编《幸福的都市栖居:设计与邻人,让生活更快乐》,部分配图也来源于此。该书由理想国于2020年1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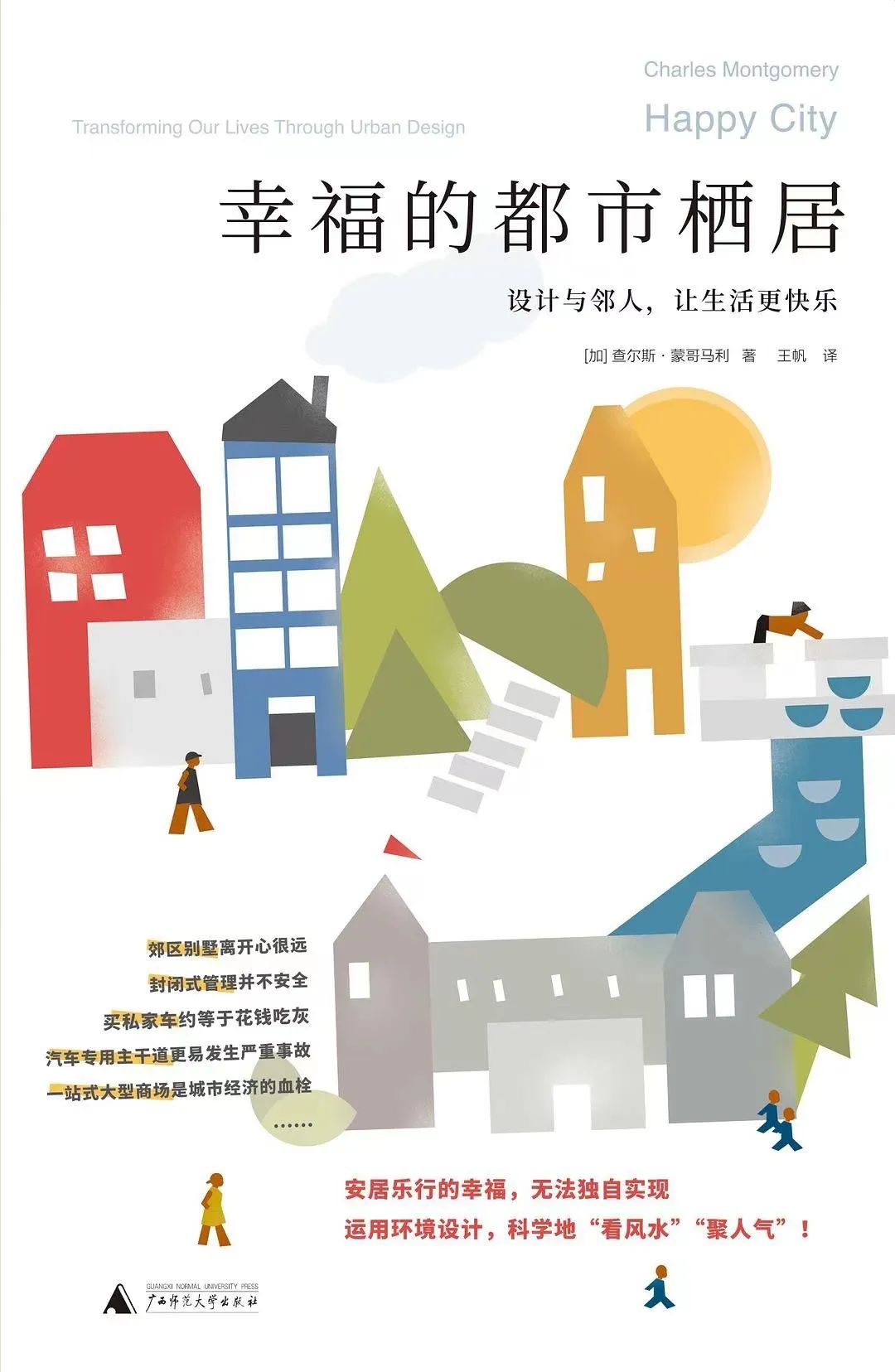
美国小镇大街的美好暗示
神经科学家发现,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人们能够针对周围环境产生社会性反应,评估周围存在的风险和奖赏。
公共空间是人类舞台的重要部分,建筑、景观和人群都在不断提示人们该如何表现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在进入任何一个空间时,神经系统会将眼前看到的内容与之前的记忆进行比较,以便自制出一幅心理地图。
城市是一个能激发记忆与情感符号的集合体:每片广场、每座公园、每面外墙都在发送信息,告诉我们自己是谁,街道又做何用途。
迪士尼乐园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人们提供欢乐与幸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多项调研表示,南加州最具有欢聚气息的街道是在迪士尼乐园入口处的美国小镇大街。
实际上,需要由一座游乐场提供这样的精神服务,也客观上反映出美国日渐衰败的城市公共精神。
游客穿过围绕主题公园的护坡,路过仿造的城市广场和「市政厅」,就进入到美国小镇大街。这里充满着无比幸福的都市氛围,不同年龄不同种族的人们在各个游戏区和饮食点之间推着婴儿车、牵手散步、购买商品和拍照留念。
有人做过实验,在游客人群中加入一些略带冒犯的行为,例如斜着肩膀去碰撞身边来往陌生人人,如果是在当地其他的街道上,此类举动会招致敌意,但在美国小镇大街里得到的是微笑、搀扶的手或是一声主动的道歉。
实验者故意丢下的钱包,也会被正在欢庆的人们送回来。两位成年男性实验者随机搭讪陌生人,请求拥抱,美国小镇大街上的男男女女会毫不犹豫地敞开双臂。
虽然游客们前来此处就是特意寻找开心的体验,但不要忽视周围景观所带来的心理启动效应。
美国小镇大街上没有一家店面的高度超过三层楼,顶楼被专门缩小为原有的5/8,看上去有一种舒适亲和的玩具气息。同时,从条纹图案的遮阳篷、到金灿灿的橱窗文字再到每面墙上的人造石膏细部,每一处细节都是为了让人们沉浸在放松的怀旧状态之中。
神经免疫学先驱埃丝特·斯腾伯格第一次到访时被这里迷住了。「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们懂得什么是神经科学很久之前,他们已经精准地发现如何用设计让人从包含焦虑与恐惧的地方来到一处充满希望与幸福的乐园。」
大脑将记忆和情感联系起来。美国小镇大街上古雅的火车站、难以接近的城堡等地标性建筑都极富唤起作用,立刻引发人们关注景观,降低人的焦虑情绪——在复杂环境中,人会对身处之地产生疑虑,这时会不可避免地感到焦虑。
嗅觉是一种触发机制。无论是糖果条纹的遮阳篷,还是人行道上弥漫的熬制巧克力软糖的甜味,迪士尼空气之中的气味记忆让人感到平和安全。这些记忆可能来自游客自身的经验,也可能出于对过去时光的一种想象感受。
有一些痴呆患者护理机构的开发者,学习了这样的成功经验,他们在机构的公共区域里会复制一个迷你版本的美国小镇大街,用地标性建筑和街上的活动来让住院者想起自己的过往生活,平复自己的心情。
哥本哈根生活的渐进改变
1962年,在战后经济蓬勃发展的推动下,欧洲城市像美国城市一样,进入一个急速的建设扩张期,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也不例外。
为了尽力容纳快速增加的私家车数量,城市建筑的空隙不断被改造成停车场。古老的街道是狭窄的,挤满拥入的车辆,噪声和废气充斥其中,警方在高峰时段无力疏导交通,这座城市甚至看上去就要崩溃。
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不断被提出,要将城市道路拓宽、加速和封闭,还想再在哥本哈根南区建立一条穿越湖面的封闭式的高速公路,旨在疏通城区向南的车流。
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思路。因为如果拓宽市中心的道路,一定会破坏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瑰宝,而在城市上空不断架设高速桥梁,又将垂直空间不断复杂化。
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建筑系的扬·盖尔团队,被邀请参与哥本哈根的城市建设计划。但是,盖尔的妻子英格丽德却对丈夫和同事们的建设热情表示出深深的怀疑。
英格丽德是一位出色的环境心理学家。在她看来,城市规划人员和建筑师们都极少考虑社区与居民的关系。每当他们引以为豪的新楼完工后,之前效果图中所描绘的嬉戏孩童和闲聊母亲,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盖尔决定,转向从城市规划和社会心理等角度重新理解人与城市、心理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在一个个会议里无休止地争论是否应该修桥铺路。
在一次旅行中,盖尔夫妻发现意大利古城锡耶纳是一个好样本。因为那里的设计师不太注意建筑本身,反而专注市镇建筑之间的人类活动,城区未被「理性」的规划者重新架构,也未被越来越多的汽车侵占。
他们把观察点放在原野广场。这里坐落于锡耶纳的心脏地区,在每一次全城巡游中都可以当作必经舞台。原野广场内低外高,从市政厅起一路扩散并上斜,止于一条宽阔的半圆形步道,道边伫立着一排威严的五层高大型建筑。
盖尔夫妇驻守在此,记录视线中人们的动向。
从早上开始,人们穿过石头拱门和阴暗小巷进入广场,他们会陆续停下脚步,聚在咖啡馆或餐厅聊天,店铺多有外摆,甚至都溢出广场的北缘。
在半圆形的步道边上,每隔一小段有一根齐胸高的石柱,人们可以倚在上面歇息。这些古老的石柱除了给人靠一下之外,已经毫无其他用途,但并没有因为阻碍人流行进而被拆除。
整天的时间里,一直都有人盘腿坐在广场的倾斜砖地上,而穿行其中的人们不经意就会放慢脚步。下班之后,穿着考究的人们还在此相聚畅饮,也有全家人带着宠物在晚饭后来这里一起散步。
盖尔意识到,即便原野广场这样的城市空间是当地文化和气候的反映,但是出色的空间设计可以引人聚集和逗留,从而塑造人群行为。「原野广场把锡耶纳人捧在了掌心。」
每一个古老城市的市民都有自己的骄傲感,总是相信自己的城市及其市民文化只能以符合自己的方式运作。锡耶纳的美好却引发了抵触。「我们是丹麦人,不是意大利人,才不会在冰天雪地的大冬天坐到咖啡馆外面喝卡布奇诺!」
由此,盖尔团队选择渐进地更新哥本哈根,交通工程师只计算车流量,而他们优先选择计算人流量。
渐进更新的基础是观察市民对于细节变化的反应,据此再去进行调整。比如,在哥本哈根的街边每新加一张长椅,盖尔团队都会去数在此坐坐的人有多少。
一张面朝来往行人的长椅,使用率是一张面朝花坛的长椅的10倍。聚在建筑工地边上的人,比百货商店展示窗前的人要多,停留时间要长,而且当施工人员一下班,围观群众也就立即散去。
路面空间增加后,车辆就会变多;增添自行车道,自行车就会变多;如果为人增加空间,人也会变多,也就有了公共生活。
他们建议哥本哈根把一些道路变成步行街,和广场形成一片网格,渐渐地让步行区域覆盖整个市中心。他们还让这里与经过规划的自行车道相互连通,鼓励城市的其他地方的人骑车前往这里。
于是,以非机动车形式涌入这片区域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多,自行车得到了规模化普及。
盖尔团队还会清点许多维度上的人流数字:坐在咖啡馆外的,观看街头表演的,或只是坐在长椅上、喷泉边的,甚至还要清点只是在街上闲逛而什么事也不做的人。
渐进更新会积累出好的效果。以格罗布略泽广场为例,从1968年正式禁止停放车辆起,咖啡馆几乎同时就自发地摆放外摆,室外的消费者有更高的松弛度,也能成为来来往往人群眼中的风景。
盖尔团队的城市理论在今天的中国都具有启示性意义:最吸引人、最引人驻足观望的,永远是其他的人。
哥本哈根市中心现在满是户外咖啡馆。据盖尔最后一次统计,全部座位接近9000个,而在1968—1995年间,在哥本哈根街上闲逛的人增加超过2倍。
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拒绝「锡耶纳」时刻,早就忘记了当年那种不情愿的自负情绪。即使在丹麦这个北欧国家最严寒的冬日里,你也能看到很多人在广场上裹着羊毛毯,啜饮小杯浓缩咖啡。
小店才是社区的塑造者
光秃秃的裸墙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并不鲜见。
宝马古根海姆实验室证明,了无生气的长墙不仅加速行人的脚步,还会让人们的情绪更加低落。盖尔也发现,如果一条街上所有的外墙都形制统一,极少设门,也缺乏变化或功能,行人会尽快离开这条街。相反的是,如果外墙各具特色,有很多开口和多样的橱窗,人们会不自觉地慢下脚步,也更常停留。
2006年,纽约曼哈顿下城区把东休斯顿街、果园街与勒德洛街之间原本就不大的地块改成一家大型的全食超市,整块街区的外立面几乎都变成全食的烟色玻璃墙。
参与街区心理之旅的一位志愿者说,走在这里的幸福感远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低得多。他们沿着休斯顿街往东再走一个街区,感觉就会立刻好很多,那一段街道非常粗陋,但是有生气,也有很多商店和餐馆。
西雅图的一家非营利组织「未来智慧」派出过一组志愿者,站在路边假装自己是迷路游客,他们选择的街道类型有两种:一条路两边光秃秃,另一条的两边则是小店列立。
志愿者们按要求站在人行道上端详地图,装出迷惑的样子。在活跃的街边环境中,路过的行人停下帮助这些「游客」的可能性,是对照组的4倍。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型零售商开始对市中心展开攻势,行政管理者又对干净街面有一种狂热的追求,夫妻店、小餐厅和路边摊被成本承担能力更强的零售大卖场所取代。
当一个零售巨头霸占了整个街区后,恶果不仅在于城市美学变得更加冰冷和单调,还在于商品和服务种类的大幅减少,直接损害附近居民的便利和福利,特别是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超大型建筑和光秃秃的街道把周围社区居住者的日常空间挤出到步力所及之外,外出社交、参加志愿活动也都变少了。街道的温情和社交气氛被洗刷得一干二净。
所幸的是,一些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大型开发商损害街道社区的社交功能。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规定,禁止设立延伸较长的空白外墙,新商铺和餐馆的门加展示窗,至少要占整个门面的80%。
在20世纪80年代,丹麦多数城市已经限制银行在主要购物街上开设分支机构,无趣的银行外墙会吸走人行道的生气,数量太多就等于宣布了这条街的死刑。
在曼哈顿的街区,常常看到四大银行各据街角,互不相让。纽约市从2012年开始采用新的区划制度,限制上西区主要街道临街层的店面宽度。在阿姆斯特丹大道和哥伦布大道上,占地宽度超过15米的建筑必须至少要有两家非居住用的店面,且要设置透明外墙。百老汇大街上的银行门脸,也被限制在8米之内。
此类举措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大型零售企业和银行吞噬掉太多夫妻小店。后者是社区的灵魂,也是街区的塑造者。一位社区议员说,「药店、鞋店之类的小店铺对我们来说无比重要。」
拯救这些小生意,也就是拯救人类尺度的街区。温哥华的例子能够证明,密集城市可以在满足商业房地产需求的同时,保持建筑的友好性。消费者对低价的冲动不会使街道失去生命力。
温哥华的法规迫使想在城区之中获得生意机会的大卖场零售商必须改变旧有形态。市政厅附近的家具建材超市和服装折扣店像汉堡肉饼一样被夹在中层,其下是一排的临街小店铺,上面是绿意盎然的花园公寓。
这些大卖场的入口被安排在建筑拐角处,旁边门面由一家星巴克、一家杂货店和其他几家小商店所分享。
威廉·怀特的「三角效应」
美国记者威廉·怀特长期用延时摄影拍下纽约街头和广场上的人群,他的团队在不厌其烦地统计之后发现:人几乎总是选择和别人坐在一起,哪怕是和陌生人;往往在步行人流最大的地方驻足聚集;聊天时喜欢迎着门口的人流或选择人多的角落,而不会挪去一旁。
要知道的是,纽约曼哈顿中城的「反社交」公共空间是全世界最密集的。
1961年,曼哈顿颁布一个初心良好的法令,允许开发商建造更高的楼房,条件是必须在该地块同步建设公共广场,这些私有的公共空间通常被称为「附赠广场」。
之后几十年发生的事不断表明,将公共生活的定义权交到个体开发商手中有多么危险。
1968年,通用汽车在其位于第五大道的庞大楼宇前建设了一个广场,以此换取七层楼的加高,但是广场被设计到沉于地下,四周设置围栏,行走其中会发现,围栏恰好在人们的腰际。
这样的思路并不鲜见,至2000年,曼哈顿中城和金融区一半以上的附赠广场既不引人驻足,也不刻意逼人退散。
这正是设计意图所在。理查德·罗斯设计过曼哈顿中城和市中心1/4的附赠广场,客户对他明确要求,广场的设计要让人们快速通过,而不是停留。
市民将城市向上建设的空间交给开发商,以换取急需的地面公共场地,但开发商通过设计把这些空间偷了回去。
威廉·怀特的追随者们创立了一家非营利组织「公共空间项目」(PPS),在纽约尝试着修复一些状况最差的地方。
洛克菲勒中心的业主方曾向该组织寻求建议,如何安装防护刺才能防止人们坐在他们广场的紫杉树下或是触摸树木。广场管理方一直将「人」视为问题,他们不想费神应付流浪汉和乱丢垃圾的人。
PPS建议业主增设供人休息的长凳,而不是加强对树的保护。业主方改造了广场,让它容纳而非拒斥人群,巨变渐渐开始,洛克菲勒中心现在成了整座城市到访量最高的地点之一,也为这里的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美誉度。
怀特和他信徒运用的是被称作「三角效应」的方法:安排至少三个外部的刺激物,促使在此空间中的人们相互靠近,近到他们可以开始彼此聊天。
最简单的三角效应,可能是将一座公用电话亭、一个垃圾桶和一张长椅放在一起,或者允许街头艺人在一段台阶附近表演——广义上来说,一切能让人放慢脚步、亲近彼此的方法都可以。
曾经担任纽约市总规划师的阿曼达·伯登,让「三角效应」更为大胆地运用在对附赠广场的改造之中。曾经人迹罕至的通用汽车大楼广场由此重获新生,公众的舒适与商业的光鲜融合到一起。
广场的一个角落里有着六棵皂荚树和一汪浅池,那里设置了许多可移动的桌椅,适合周围的人们前来午餐小聚。广场正中心坐落着一座玻璃立方体,让人联想到贝聿铭在卢浮宫中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而这里是一家苹果商店的入口。
这个空间让生活速度、熟悉程度各不相同的纽约人相遇。人们又让空间变得更为有趣、更具价值。
怀特理论的实践让更多城市设计者意识到,即使外表最丑的地方,也能拥有温暖人心的力量,让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放慢脚步,让陌生人彼此熟悉。
自行车道是一座中央公园
1971年,唐纳德·阿普尔亚德对旧金山的几条平行街道做研究,发现交通与社交间的直接联系。
在一条交通流量较低(2000辆/天)的街道上,孩子们会在人行道和马路上玩耍,大人则在家门前的台阶处社交,人人都表示自己与道路两侧邻里的联系很是紧密。
另一条与之类似的街道每天却有8000辆车通过,社交活动和人际关系水平急剧下降。还有一条类似的街道,日均通过车辆达1.6万,公共场所空空荡荡,社交联系稀少且距离疏远。
这些街道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就是车流量。
哥本哈根的交通局长尼尔斯·托尔斯略夫说,如果某条特定街道的人停下脚步,盘桓不去,他们会认为这是一项圆满成功,因为创造出一处值得驻足的地方。
对停车方式的设计也会影响社交。布鲁金斯学院的研究员、交通规划师劳伦斯·弗兰克发现,如果附近商店门前有停车场,人们认识邻居的可能性就会变低。
原理很明显:商店设置停车场,目标客户便从本地人群扩展到开车驶入的多重群体。换句话说,宽敞方便的停车场是分散型城市的标志,也可能是消灭街头生活的凶手。
洛杉矶市中心每英亩的停车位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点,而这里的很多街道都极尽萧索。20世纪90年代末,洛杉矶斥资修建了标志性建筑迪士尼音乐厅,希望能为邦克山街区注入活力。
为容纳超过2000辆汽车,洛杉矶发行1.1亿美元债券,在音乐厅正下方建了一座6层停车库。这既给洛杉矶爱乐乐团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为履行合约、偿还车库债务,乐团每个冬季举行的音乐会高达128场),又没能恢复区域内的街道活力。
因为开车去迪士尼音乐厅的人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建筑。他们把车停在地下,乘数段自动扶梯后到达门厅,离场路线完全一样。周围的街道依然空空荡荡,缺乏咖啡馆、酒吧和商店,没什么在这些小店稍作停留的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城市规划教授唐纳德·舒普说,「想全面体验洛杉矶的标志性建筑,起点和重点全在停车库,而非城市本身。」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做过一个激进而成功的尝试。这里曾经深陷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以及内战的血腥泥潭。一位名叫吉列尔莫·佩尼亚洛萨的政治家发现公园也许能让本地人重新振作。
他相信,一个好的公共空间能让人们分享自己、了解彼此,帮助所有人打破阻隔。
1994年,吉列尔莫出任波哥大市公园、体育及休闲方面的专员,他计划利用市府所拥有的废弃土地新建200座公园。但是,这座城市在公共空间上的赤字极大,200座公园无法有效填补,而购买新的土地则意味着高额的财政支出。
吉列尔莫在「自行车道」项目上发现了机会。该项目在波哥大已经运营数年,每个周日都会在13公里长的繁忙道路两端设上路障,把道路还给骑行者、散步与慢跑的人。
这样的道路像是公园的暂时延伸。即使在这样一座阶级固化、暴力与恐惧肆虐的城市,「自行车道」还是可以将各阶层的波哥大人汇集起来,富人和穷人有机会相识,甚至不同派系的人都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接触。
吉列尔莫扩大了「自行车道」项目的应用范围,最终划出一座由100公里的城市主路互联而成的交通网。每周来这儿享受公共空间的骑行者、轮滑者及推婴儿车散步的人,数字都会超过万,「比教皇的到访还受欢迎」。
中央公园总设计师F. L. 奥姆斯特德对此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自行车道」项目可能就是波哥大的中央公园。
这是人类在现代城市历史上成本最低的公共空间项目:资本投入几乎没有,只需购买一些路障,维持秩序的人员也多是志愿者。
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让一座城市变得对市民友好,真正需要的只是政府意愿。
越来越多的城市会举行「无车日」,让步行、骑行和轮滑的人们在多条主干道上自由活动。市民们可以在这里聚众练瑜伽、跳舞,玩飞盘,甚至打太极拳。当然,更多的人只是来散散步,或者懒洋洋地躺在折叠椅上。
对于参与其中的市民而言,这是一次浸入式的社会观念启蒙,他们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城市的街道究竟为什么而建,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是否一定意味着逆来顺受。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