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整理 | 实习记者 覃瑜曦
“河南说唱之神”的歌曲《工厂》MV日前在网上流传。我看了这首歌的两个版本,一个是原始版本:巨大烟囱矗立,几个小孩在村头废墟间玩耍;另一版用不同的电影片段剪辑而成,取材自《钢的琴》《白日焰火》《hello树先生》还有贾樟柯的几部电影,电影片段以这样的形式融为一体,配合着歌词所唱的,“我不是热爱这里,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工厂的烟雾都盖住了星,周围的村庄都被他合并。”
这首歌以回忆视角展开,“小时候河水就不是很清,现在它换来了金钱和病,搬不走的人,成为了钉。”这样的哀婉目光在去年《中国奇谭·王孩儿和乡村巴士》中出现过,只不过,土地庙拆除以后,田野上矗立起的是一间公共厕所。

从《工厂》这首歌,我还想到了另一首济宁话说唱《机器铃 砍菜刀》。山东小城的生活虽与河南乡村不同,但也有类似对雾霾盖住星空的哀叹(“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但被霾盖住了光明”)以及对童年游戏的追悼(“你知道我有多想回到老家和泥巴,再捞着那些光腚家伙去坑里逮青蛙”)。 当然也有美化的怀旧视角的创作,像是华北浪革的《县城》里唱,“千重山,万层浪,比不过县城一碗汤。”
由《工厂》《中国奇谭》再到《机器铃 砍菜刀》,我不禁想到了曹寇笔下的县城生活。他的《鸭镇往事》以长三角江边小镇为背景,人们在乡镇与市区间来来回回,他当时说,因为中国城市现在分为三六九等,资源非常集中,乡镇如同被遗忘一般,这种遗忘不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乡间盖起超豪华的大别墅,可是走进去什么都没有,还是一张“文革期间的长板凳”摆在那里。
近来关于县城生活的报道也增多了,像是《南风窗》的《人在县城,逃不过命》,还有关注县城贵妇生活的报道。在菏泽车站唱《诺言》的郭有才也走红了。比起对于现象或生活方式的描述,我更想与大家聊聊所谓的“县城美学”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

01 《工厂》适配了“山河四省”的生活
尹清露:《工厂》MV的精神气质可能跟很多年前万能青年旅店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比较像,都有一种工业城市的苍凉感。我很喜欢它两种合成器音效的叠加:一个是类似于笛子声的温暖悠扬的合成器音效,一个是MV开头工业的冰冷噪音。我发现笛子好像是流行音乐比较喜欢用也经常用得比较出彩的一种乐器,让人感到有些冰冷或工业风的流行歌,加入笛子后增添了一种古典、温暖但也有点苍凉的韵味。
笛子的音效非常适合这首歌,我印象很深的是《工厂》MV开头特别宽的烟囱和庞大的工厂,是北方人小时候比较熟悉的一种景象,这样以重工业为主的北方县城,一方面总是给人一种冰冷的忧郁感,另一方面又有回忆中温暖纯真的部分。这种双重的心理感受,和听感的二重性也是很搭的。
我还去听了《机器铃 砍菜刀》,仔细看了这两首歌的歌词,发现主题都是出身县城的男孩们,他们虽不情愿,但又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希望保留自身那来自县城的纯真,但最终被金钱腐蚀灵魂。《工厂》的歌词说“我需要很多钱来将我的自卑和不安掩埋”,同时又督促自己不要忘记家里的兄弟姐妹,像在告诫自己不要遗忘那个纯真的自我。
“河南说唱之神”的音乐风格应该属于Emo Rap(情绪说唱),专辑封面也有非常典型的Emo Rap的元素,比如一个流泪的骷髅头。Emo Rap从美国传入,内容与平时大众印象中“我最牛、 keep real”的Rap风格很不一样。Emo Rap本身与Emo Punk、独立乐等有交叉,这种风格里面有很多旋律性与抒情的部分,带来一种很真诚的感觉,这种风格也会关注抑郁、孤独、焦虑,甚至是自残、自杀的主题。
Emo Rap非常适配县城主题,强调了一种“想要逃离但又无法逃离的内心状态”。由此我还想到国内的“杀马特”,他们其实就是从这些EMO音乐、流行亚文化过来的,被本土化成了杀马特。想到杀马特,大家也会觉得他们是想要离开小地方但又找不到合适方法的一群人,他们标新立异,又可能会因别人嘲笑而感到自卑。
董子琪:这种美学风格和实际状况的适配,能解释弹幕里的山河四省“陪一根”。
徐鲁青:提到县城,在音乐领域我会首先想到五条人,他们几年前也因为县城风格火了一把。2009年五条人发了第一张专辑,名字就叫《县城记》,五条人的风格与郭有才、《工厂》就很不一样。首先是地域差别,一个是南方,一个是北方,五条人的MV里更多的是台球厅、洗头小妹、打工仔和夜宵摊。欣赏五条人《县城记》的听众,大多还是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看上去如此不同。

五条人对于县城及县城身份始终带着一种戏谑感。他们不断地解构县城的苦和乐,并且对这件事情不以为然。他们对乡土和海丰有天然的骄傲感,《县城记》里有一个宣传词叫做“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他们认为海丰蕴含了足够丰富、值得他们去唱的东西。《城市找猪》唱道:“我们在城市里面找猪......我们在想象中度过了许多年,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这首歌里有对城市和农村关系的反思,但他们不将自己看作主流秩序里的边缘人,反而会从边缘对中心发出一些反讽,而这好像又是身处中心的人希望听到的东西。大城市听众喜欢五条人,会不会正是因为五条人的歌不那么适配县城人被苦难、被关怀的这种想象?
董子琪:五条人对县城美学有一种“审美自觉”。这种戏谑、自省和为县城光荣的自觉,让他们的歌曲能够和白领、知识分子沟通。
林子人:我是在《新说唱2024》第一次听《工厂》的,“河南说唱之神”在海选唱了这首歌。老实说他的表现一般,节奏稀碎,走调,从说唱的角度来说是不合格的,但第一印象是歌词平实、让人有“痛感”。后来在社交网络上看了《工厂》的MV,惊为天人。歌词中流露出的不得不背井离乡但又无法抛却故土羁绊的无奈感伤,以及一种很难与外人道的自卑与不安,让人心痛。“河南说唱之神”在这首歌中言说的似乎是一种普遍性的、属于经济文化边缘地带年轻人的情绪。我的家属是河南人,他告诉我,每个成绩不错的河南学生从小就知道他们必须考出去,去外地发展;我也依然记得,结婚前当我妈妈的一位朋友听说我的男友是河南人时,无意识露出的惊讶表情。
董子琪:这两天我听了郭有才的《诺言》,为其中的审美自觉感到震惊。他是一个出生于1999年的年轻人,但却将自己打扮成四十来岁的样子,还用一层黄色幕布盖住自己的镜头,仿佛是在邀请听众来嘲谑自己,但歌唱时又非常感情充沛。他自称是“菏泽树哥”,这说明了他的风格并不是天然土,而是经过媒介和文化学习后的土味。“你我不能抗拒命运的左右”这样的歌词,呼应了那则关于县乡的报道“逃不过命”的标题,同时也是“我不是热爱这里,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的另一种诠释。

02 县城像是洁净城市的脏背板
潘文捷:在县城生活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地域等级,就像曹寇所言“中国的城市分为三六九等”。现在有许多关于县城的报道,点开一看就知道它写错了——记者写到县城后看到农村的乐队和大戏,不对,那不是县城,那是农村;还有人写在县城感受到乡镇的什么什么,那也不对。从农村到乡镇,再到县城,其实县城是在这条鄙视链的最上端。
我从小在江苏一个县级市生活,这样的地域鄙视链还是存在的。不光是行政单位等级上的鄙视链,而且还有江苏省内的南北鄙视链。我们算是一个苏中县城,全国百强县36名,但是我们隔壁县城江阴是全国百强县第二名,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总有一个隔壁家的孩子比你家更强”。韩起澜在《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里说其实苏北并没有明确定义,它是随着苏南的定义而出现的,苏南人为了界定一个跟他们不同的他者,才出现了苏北人,他们并不care苏北人之间有没有很大差别,也不care你是苏中还是苏北。这就像现在我们讨论县城时,好像县城也成为了大城市的他者,大家不care它到底是县城、乡镇还是农村。空间变成一种时间的隐喻:县城是落后的,大城市是先进的;苏北是落后的,苏南是先进的......地域差异不仅仅指的是空间差异。
我非常不能够理解这样的鄙视链,因为其实是农村人喂饱了县城的人,如果没有农村人,县城人都得饿死,也是县城给大城市提供了人力资源,如果没有县城持续的人才输血,大城市是不可能发展这么好的。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梦寐以求看到一个先进的国际化大都市,但是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跟贫民窟是在一起的,而这里的贫民窟的处境并没有比县城的处境好,后来我到北京也是这种感觉。
董子琪:“时间感”也体现在我们要讨论的MV、歌曲和小说中。不仅是先进和落后的对比这么简单,《工厂》MV给人的感觉不是原始的、落后的,而是被污染的、肮脏的、丑陋的。
潘文捷:干净和先进落后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县城给人一种现代化过程中混乱与被淘汰的感觉。其实,“双手干净是一种巨大的特权”,所以,现代化过程中被淘汰的产业都去了哪里,这个问题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值得思考。
我家在县城,家对面原来是纺织厂,很多废水排到我们家面前的那条河。直到过了一阵子,我妈妈告诉我一个“喜讯”,为了建设干净的长江三角洲,工厂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家门前那条河就干净了。我不知道那个工厂转移到哪里去了,但是它不可能消失,这个产业肯定还要继续存在,它肯定转移到了更不发达或者更加需要这个产业的地方去了。产业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向来是从先进的地方到落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干净”的感觉跟先进落后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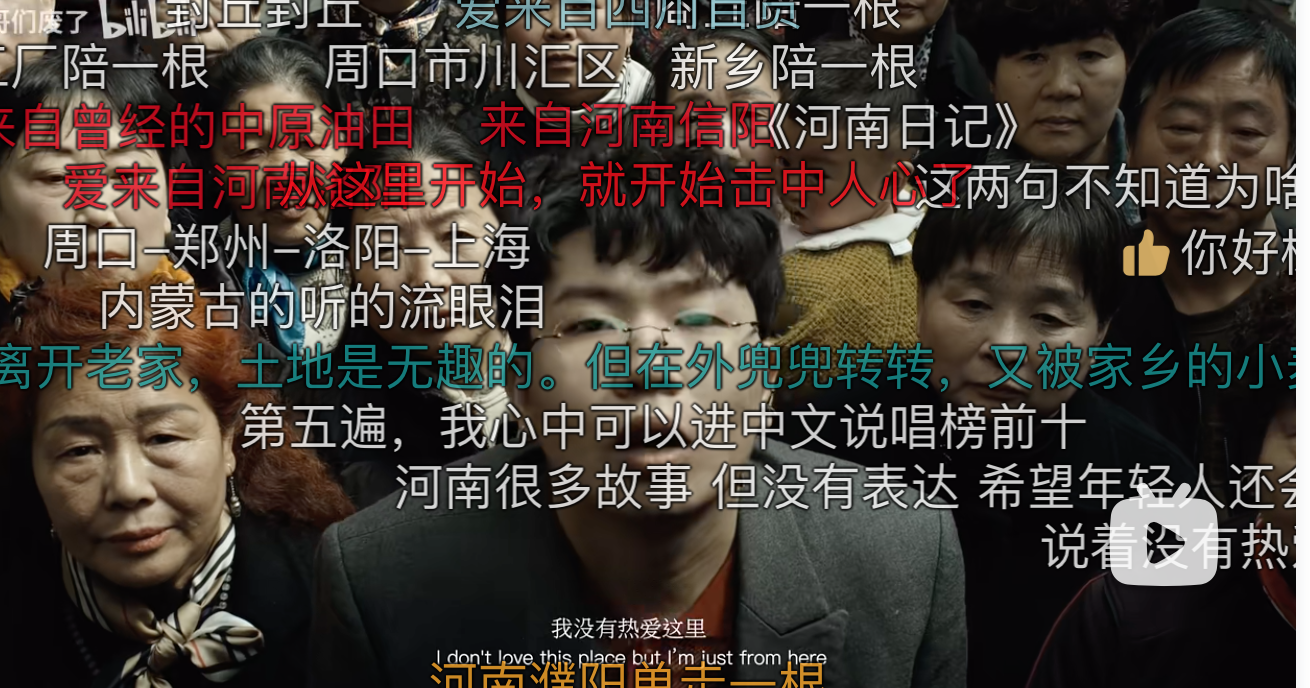
徐鲁青:说到干净,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人生第一次到江浙沪县城的时候。我老家的县城主干道两旁基本上就是菜市场,大家提着自己种的菜、家养的生鲜到路边卖,鸡和鸭被关在笼子里,抓出来的时候扑腾得羽毛都飞出来。边上基本都是基建施工,都是灰。我第一次去常熟时,发现他们有沿河的步道,空气也非常好,路边的绿植是没有灰的。哇,真的是一个有钱的地方才会这么干净。
林子人:近年来县城叙事/美学的崛起,反映的是人们对长期以来在舆论场和主流价值观占据统摄地位的发达-落后二分法的祛魅和幻灭。进步主义叙事告诉我们,只要你够努力,你就能离开边缘进入中心,你现在在边缘遭遇的一切问题都将因此得到解决。但当进步主义叙事破灭,我们更加看清的是,发达-落后二分法的本质是通过将财富、人力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利用地区性差异来获取巨额利益,而这种利益并没有惠及全社会的人。在了解这一点后,我对所谓的城市中的三六九等、任何地图炮言论都深恶痛绝。
03 向往基层生活,又受其束缚
董子琪:回应到文捷之前说的,县城在时间上、经济上可能都比较落后,所以它反而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慰藉,仿佛是一个大家想回去就可以回去的地方。很多报道都是以此为题材,包括南风窗《人在县城,逃不过的命》,还有之前《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的县城贵妇。这好像是一种置换:我在小县城置换到了更大的空间和更为优渥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在大城市只是一个PPT女工,但是在县城,我就可以过上在大城市想要的生活。
潘文捷:我外公之前在上海工作,后来觉得拿着上海的退休金可以在家里活得挺舒服,就回到老家养老了。他好像就是所谓的“县城贵妇”。我之前看到一些关于县城文学的短视频,背景音乐基本上都是“走不出,看不破”,好像大家都说县城是“走不出”的,但其实我觉得县城也是“回不去”的。如果回到县城,很多人在大城市的生活是一定会被指指点点的。你的圈子非常固定,所以但凡你有一点格格不入,那么很可能就要被闲言碎语淹没。
县城的文化生活确实是一个问题。像我们是传媒行业,可以去电视台或者家乡的报纸,但是县城的报纸内容是非常受限的,自主操作的空间很少。我们那里也有本地作家,但凤毛麟角。
董子琪:我记得你以前转给我一个乡镇作协的视频,吐槽的是即使再小的地方它都能自成一个王国。例如在体制内被视为末端的基层协会,它也会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矩。
潘文捷:我记得他说他挤进了地方的作协,每次有外地贵宾来,他们都要设宴款待,特别是有像上海、北京这样大城市来的作家,他们就觉得一定能听到或学到一些东西,结果大失所望。哪怕一个人的能力很强,县城人就是会对大城市人有滤镜,好像是地方边缘人和主流中心人的区别,其实双方的真正品质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只是位置不同。
董子琪:以前采访作家尹学芸,她一直在天津的一个县工作,同时也是基层作协的成员。她也有接待北京或上海这类大城市作家的经历,要陪对方爬山,对方作家可能就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会务工作人员,跟她吹嘘说“我下个月就要有一篇文章发XX杂志头版了”。尹学芸当时心想着“我也有一篇要发”,但是她没说,她觉得说了不合适,但心里还是不服气的。
尹清露:县城贵妇和《工厂》这些想要走出县城的人相比,他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经常能看到对于县城美学的一种批评。因为县城有很多具体的美学元素,所以会有人化非常90年代或2000年初期风格的仿妆,像是小时候理发店门口会贴着眉毛特别细、穿红色皮衣的女生海报,但很多批评会认为这可能更多是一种想象。包括县城美学拍的一些照片会以破败的商店街作为背景板。
同时我在想,这会不会有性别上的区别。因为县城贵妇在大家眼中是不用去工作的,那她就可以享受到比较优渥的生活,如果是男性的话,好像从小被灌输的是“要去打工赚钱”的观念。例如,在三联那篇文章中,姐姐原先在城市里当自由撰稿人,她后来回到县城成为县城贵妇,她的弟弟则在备战考研和工作。当然这个例子可能比较微妙。

李孝悌 著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5
林子人:这两日我在读历史学家李孝悌的《琐言赘语:明清以来的文化、城市与启蒙》。李孝悌指出,做中国城乡研究的西方汉学家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对整合性很高的地方,其中市场是很重要的因素。近二十多年里,户籍制度松动、人口流动障碍减轻,再加上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中国的城乡连续性再一次凸显出现。但是李孝悌提到,她在去中国乡村考察时的强烈感受是乡村的束缚性,“它有各种组织性的力量把你限制住,当然可能还有经济生活的制约。”相对而言,“城市可能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你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城市可能有更多的商业活动,城市也可能有更多的艺术活动。”我想,这些特征在前现代中国存在,在当下也存在,不然年轻人也不会一直在争论是去大城市还是返乡了。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