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恢复高考47年后,2024年高考报名人数高达1342万人,相比2023年增加了51万。
提起高考你会想起什么?是六月闷热的天气,英语听力前下过的大雨,送考的家长老师们一声声“加油”,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一分打倒几千人”?如果说前者代表个体关于高考的回忆,那后者就显露出它作为选拔性考试的残酷面向。
当下,结束了高考的年轻人正面临着进入高校的“第一道门槛”:填报志愿。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流行的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近两年来直言“孩子学新闻就拖走”的张雪峰,考生的专业选择并不总是与分数、个人特长与爱好密切关联,还与就业前景或未来人生“牢牢绑定”。
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从2013年起在全国四所重点高校对农村籍学子展开相关研究,十年间他对约2000名重点高校学生做了追踪研究,并与其中的百余位农村籍学生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深入访谈。他们进到大学,然后经历了什么?那些赢得了高考搏杀,从农村或小镇“逆袭”进入全国重点高校的的学生们,在这里面临着哪些此前未有、同龄人也未必感受得到的挑战?


在日前出版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中,谢爱磊发现,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进入重点高校后变得孤独、迷茫,“当旧的考试节奏消失殆尽,自我也就失去了坐标。”先是失去了具体的题目和考试,毕业后又失去了边界清晰的校园,做题家们如何面对生活?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谢爱磊进行了专访。
01 没有谁是天生的做题家
界面文化:最早为什么想做关于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的研究?为什么选择做一个长达十年的追踪研究?
谢爱磊:研究是从2013年开始的。我自己一直做农村教育研究,持续关注农村学生的发展。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背景:当时精英大学里农村籍大学生的比例有一点下降,2012年起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来应对这一现象,例如面向贫困和农村地区的专项计划。政策出台之后,精英大学里的农村籍大学生比例确实逐年在增加。
我更关注的是这些学生进入精英大学之后的学习生活。这也是我们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人特别关心的事:当一个人拥有在精英大学受教育的机会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机会,顺利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另外,当时一些面向贫困和农村地区学生的举措实际上是一种“优惠政策”,大众想当然地觉得,这批进入到精英大学的农村籍大学生会不会存在学业上的问题,一些极端个案被报道出来,比如有个别学生在大学里沉迷游戏、学习困难甚至辍学。如果故意把这些负面印象放大,可能会造成我们对这一群体认识的偏差,甚至是对他们的污名化,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看到他们在大学里真正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
界面文化:在调查过程中,会有学生称自己“小镇做题家”吗?
谢爱磊:“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大概2020年才火起来,我的研究开始于2013年,那个时候学生们不会叫自己“小镇做题家”,但他们的叙述里的确有很多和“做题”有关,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叫自己“做题机器人”。这一方面代表他们的苦恼,在应试教育模式下人生好像只有一条赛道,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反击”,他们反思自己过去接受的教育是在培养“做题机器人”,没有发展他们的个性、独立性和其他素养。

谢爱磊 著
北京贝贝特·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5月
不仅他们不会自称“小镇做题家”,我也不太愿意把他们叫做“小镇做题家”。我之所以用这个词,甚至作为书的标题,是在某种对话的意义上使用的。我想和那个时代的学生的声音、遭遇,以及“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进行对话,让人们知道当学生们自嘲“小镇做题家”的时候到底在自嘲些什么。
我总觉得下定义或者贴标签可能会让某个群体“动弹不得”,让人误以为他们是一成不变的。我想提供的是一个理解这群学生的框架,从“游戏感”、心态、反身性去理解他们,再理解背后宏观的历史和结构性原因。
不管被叫做“小镇做题家”还是“读书的料”,如果要通过某种特殊的群体“标签”才能获得力量,那这种力量很可能是假的。真正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去寻找,而不是通过被贴在身上的标签中去寻找。书里的不少学生通过分析自己、分析社会逐渐改变,在思考过程中逐步发掘属于自己的个体的独特性,而不是沉迷于从标签里寻找自己。
界面文化:书里不少学生说“教育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你怎么看待教育对于农村学生的重要意义?
谢爱磊:教育有它的重要性,但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因素有很多。他们大概的意思是,对于自己来说,教育是他们比较依赖的一条路,他们的主观判断也是这样,但这不意味着教育是他们擅长的路。
没有谁是天生的做题家,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在求学路上有很多客观条件限制,他们更难遇到好的师资和教育资源,这些学生本来就更难成为客观意义上的“做题家”。
02 教育只是社会的一小环,不该过于理想化
界面文化:像是“做题机器人”或者“机器人”这样的自嘲,是否体现了农村籍大学生适应精英大学过程中的困难?
谢爱磊:我的研究对象长期生活在农村或者小镇,早期的家庭学校教育经历使得他们很可能没有经历过丰富的文化活动,他们的家庭也可能很少有主流社会认可的文化资本投资,学生到大学之后很自然会产生茫然失措的感觉。
学业上的困难也是存在的。谈到学业,学生们会用“搞定”来描述,就是说到期末考试时我突击一下,提前问问学长学姐记一记重点,也能拿到一个很好的分数,毕竟考试的套路是老的。“做题”的确可以帮学生在大学里获得分数,但学到真东西和考试拿到分数是两回事。我之前评阅论文的时候看到一个观点,大致是说今天国内顶尖大学的大学生在“假学习”,学生可以为了高分认真在课堂上互动、和老师讨论,他们好像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却没有赋予这件事多少意义。
那么当学生说自己是“做题机器人”的时候,还可能意味着:我在大学里考试没问题,但“学到知识、增进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对将来的工作有所帮助、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思考”和“考得好”是两回事。学生也会反思只培养做题技能的高中教育反思,也反思大学教育,比如有些课程是不是有点“水”?有意义的学习是不是少了一些?学生和老师的互动是不是少了一些?

还有一层反思体现在高中和大学教育之间的差异上。高中老师是把课内的东西“嚼烂”教给学生,课内的东西学好就行,但大学老师课上讲的只是皮毛;很多学生原先的教育经历里自主学习的成分非常少,合作学习的尝试也很少,但是大学课堂常常有小组合作、自主学习。也就是说,过去的学习经验没有办法让学生为自己大学的学习做好准备,两者之间有天然的鸿沟。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部分是希望能够反击某些针对“小镇做题家”的刻板印象,另外也想说明有一些影响年轻人大学体验的因素,与城乡有关,但不是被城乡所决定的。不少并非来自农村或小镇的学生也跟我反复提到,他们也有同样深刻的感受,我说,那是因为我们面临共同的结构。
界面文化:这个结构具体是什么样的?
谢爱磊:这个结构首先指的是教育系统:眼下,高中教育越来越强调对单纯的学习环境的营造,学习主要是高强度的“灌输”、机械的学术训练还有无休止的竞争和筛选。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结构主要是收入不均衡。两个方面其实是相互影响的,教育有双重功能——社会化和筛选——在收入不均衡加剧的情况下,它的社会化功能就比筛选功能得到了更少的强调和重视。大家越强调教育的筛选功能,就会越强调应试能力,不让自己被筛掉。这其实关涉到社会分层的问题,教育是很被动的。
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提到过,当一个社会越不平等,尤其当教育能对一个人未来收入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教育内部的竞争就会越激烈,甚至个体遇到的教育模式也会不同,比如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家长可能会倾向于权威式的教养模式,而不是民主型的教养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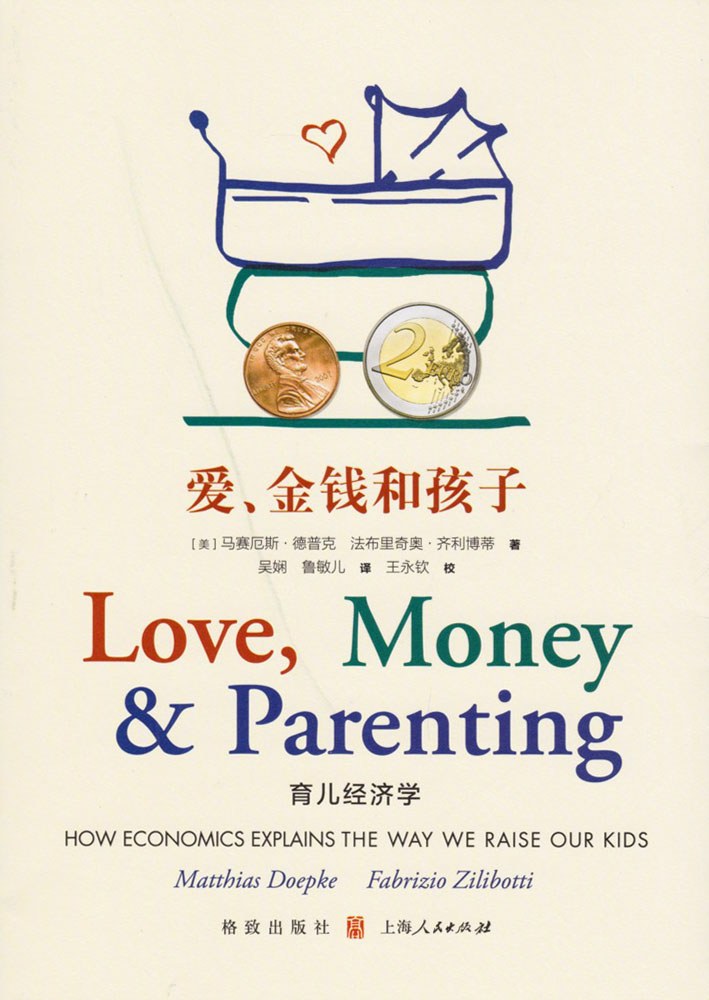
[美] 马赛厄斯·德普克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 著 吴娴 译
格致出版社 2019-06
“教育/知识改变命运”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有着无可厚非的正当性,但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太多因素在影响社会流动的机会。既然教育只是社会系统里的一小环,那么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就不该过于理想化。教育有改变命运的潜能,但是这种潜能的发挥比较有赖于我们整个社会共同做一点事,比如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更高质量的就业......如果我们想要让教育发挥更好的作用,就必须创造出这些条件。
03 不是对教育悲观,而是对文凭价值下降担忧
界面文化:在今年的高考月,很多人发现这种“无可厚非”的正当性似乎正在动摇。一些家长和年轻人似乎在重新审视高考和教育的意义。你怎么看社会下行期人们对教育的悲观?
谢爱磊:从客观上来说,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教育对个体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还是正向的。我是做教育工作的,总相信教育的力量。但是我们现在处在特殊的经济周期里,大学生就业确实遇到了挑战,而高等教育本身又进入了普及化的阶段。2023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60.2%,说明我们处在一个“大部分人都能上大学”的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大学文凭带来的回报很难直接用学历本身来衡量。教育又常常被视为一种投资,当投资的回报不充分的时候,大家对它感到疑虑是正常的。此时就会越来越强调教育内部的分层:要不要上一本大学?能不能上985、211?再进一步,能不能读C9大学或者海外名校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地更多的不是“教育能不能改变命运”,而是“什么样的教育有助于改变你的命运”。我想人们也许不是对教育悲观,而是对文凭价值下降的担忧。

界面文化:“什么样的教育有助于改变你的命运”让我想到近期引起热议的“中专学生入围全球数学大赛决赛”。不少人非常惋惜这样天才般的人物没能去普高、没法去更好的大学深造等等,我们怎么理解大众对中专的“偏见”?
谢爱磊:这件事引起我的思考,当我们发现一个特殊人才的时候,整个社会好像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一种教育优绩主义的思路里去,用学校的等级来衡量人的能力、价值和尊严。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文凭社会里,总习惯用学校的层次和文凭的等级来衡量人的价值,衡量人的能力和他们应当的尊严。
好的教育是另一种思路。在中专里学习又怎么样了呢?中专里的孩子同样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其实所有在中专的孩子都有优秀的可能,优秀不一定要表现为在竞赛里拔得头筹,表现为没有进入“顶级大学”,是不是也可以是在他们自己专长的领域发挥才智、自得其乐。
我知道这有点理想化,但个体接受的教育不应该被简单地作为标准用来衡量学生的智商、区分学生的努力程度,我们更不能依据它来判断一个人的全貌,尤其不能把它与学业之外的东西挂钩,比如品行、道德。否则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教育与社会地位的分配有关,先入为主地认为身处在某些教育机构中孩子就具备某些特质。其实,这也是公众较难接受职业教育的重要原因。
界面文化:现在高校生中出现了“考公”、“考编”热,但也有人会认为年轻应该闯一闯,而不是逐大流去追求铁饭碗,我们怎么理解这种现象?
谢爱磊:在充满机会的年代愿意大胆尝试,这是理性判断。在外部风险加大、经济环境变化的时代选择稳定,同样是一种理性判断。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农村家长教育观念的文章《“读书无用”还是 “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当时有部分人认为农村家长的观点就是“读书无用论”,是不理性的,但我观察发现,实际上他们对现在的教育机会、社会流动有一些理性的观察和新的思考,这就是农村家长的一种理性的态度。只是批评农村家长的态度无法解决问题,更应该从入学机会、学校适应等结构性的问题入手,帮助农村学生更顺利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04 过度重视智育,学生陷入“意义贫困”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精英高校农村籍大学生认为自己在大学生活中“缺乏游戏感”,他们的“自卑”其实是“自我低估”。具体来说这种游戏感是什么,怎么理解他们出现这种自我低估的倾向?
谢爱磊:“游戏感”第一是要“看见”,能“看到”大学里有些什么东西。对于很多农村籍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早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经历使得他们去到大学之后首先看到的还是和学习相关的东西,看不到学校还有学习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也不知道这些生活领域里有哪些内容,所以他们会自嘲说:“我就是做题机器。”
“看见”其实很重要,其次就是“喜欢”。当你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愿不愿意探索尝试,这也很重要。访谈中有学生表示愿意去试试,也有部分人不那么喜欢,会觉得这些和他们原来的生活模式不太一致。很多学生会提到一个词“功利”。比方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某些学生组织或者社会活动和自己原来的价值观有冲突,但是参加却可以在综合评定里加分。
第三个方面就是有准备,可能得有一些技能储备、知识储备,更重要的还有文化方面的储备。社交的时候别人跟你聊篮球、聊歌星、怎么追星怎么抢票,如果你对这些事情没有概念,那么难免会在社交场合感到局促。
界面文化:“看见”、“喜欢”和“有准备”三者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出现“缺乏游戏感”的体验吗?
谢爱磊:是的,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游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缺乏游戏感不一定会导致什么很不好的后果。也没有谁是100%缺乏游戏感,只是有些人游戏感多一点、有些人少一点,重点在于这是一种个人的感受。
缺乏游戏感不是一种病,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在做“病理化”分析,把一个可能的由社会结构造成的问题,看成是专属于个体和群体的性格缺陷,好像生病了一定要用药去治。我就认为“游戏感”是一种心态,是可以通过探索、尝试改变的,心态会影响后面的行为,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心态。
界面文化:你提到担心“病理化”的分析,这让我联想到,很多年轻人试图超越主流标准(比如成绩)的“游戏”,最后好像都成了一种新的卷法、一种新的竞争。比如卷运动、卷外貌,连在社交平台晒“躺平”的博主也要卷粉丝量。这些本意是玩耍、游戏、取悦自我的东西,到最后都变成了一种可能消耗和伤害自我的大型竞赛。你是怎么看这种“卷”的泛化?
谢爱磊:这确实很有意思:跑到另一个赛道的人最后又“卷回去”了。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嵌入市场”的时代里,就是说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被经济活动影响,经济活动的逻辑向外无限扩散到了其他生活领域,而个体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竞争性的经济逻辑中。

但我认为“开辟另一个赛道又卷起来”这件事本身也许无可厚非,因为退一步讲,它毕竟展示了多元的选择,结果也许并不尽如人意。我其实比较看重他们在非经济意义上单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种尝试,它可能也许反映了普通人在价值观层面的一些深度思考,比方说,我们可不可以有超越经济逻辑和现实利益的生活意义、理想、信仰与终极关怀。
界面文化:即使顺利毕业,很多人在工作中会自嘲又变成了“大厂做题家”。在你看来,为什么这种状态延续到成年人的工作甚至情感生活(985相亲群等)中?
谢爱磊:我把这种状态称作“意义贫困”,指人好像被困在了什么地方,比如教室、考场或者公司的格子间,生活里的其他东西好像得不到关照,自己总觉得很迷茫。前面提到这个时代经济逻辑泛化到生活的其他领域,而很多人又把这套逻辑内化,从单向度的经济意义上追求自己的价值。那么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难免会怀疑此前自己相信的东西。
但是此时,除了经济意义,好像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别的坐标来衡量。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当我们试图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思考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竟然找不到另一套非经济意义上的话语,在人文向度上思考人还可以是什么样的。好的教育应该提供给我们这些思考的话语和工具,教育不能只是技能训练,它应当直指心灵。
我们常常说教育追求人“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但我们在教育实践中感受到的是对智育的过度重视,强调学业成绩。当教育的重心被放在如何通过机械训练帮助学生进入大学,他们在面临学业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时候,自然会觉得“我的人生怎么被限定了”、“我怎么这么狭隘”,而教育本应该为学生能拥有更广阔的人生做准备。
就像教育家鲁洁曾说过的,教育要实现两种目的:有限目的和无限目的。有限目的指的是使我们的孩子具有谋取生存的手段,能够为经济生活做准备,但无限目的其实是更重要的,它意味着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思考“为何而生”,能够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
(除书封外,本文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