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在人们纪念完卡夫卡诞辰140周年的一周之后,另一位生于捷克的作家米兰·昆德拉离世。
至于这两位作家的关联,我们从昆德拉的许多作品里都能窥见一斑。昆德拉曾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说:“在我们的世纪,是卡夫卡将不真实性合法地引入小说艺术之中。”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对什么是“卡夫卡式”做出了精妙而深入的分析,他写道,“我之所以这样强烈地坚持卡夫卡的遗产,之所以像捍卫我个人的遗产一样捍卫它,并非因为我认为去模仿不可模仿的东西(即再一次去发现卡夫卡式的东西)有什么教益,而是因为他的小说是小说彻底自主性的上佳典范(即作为诗的小说)。弗兰兹·卡夫卡通过小说的彻底自主性,就我们人类的境遇(按它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说出了任何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思考都无法向我们说出的东西。”

在1980年6月的《辩论》杂志里,昆德拉发表了一篇题为《布拉格,消失的诗》的文章。这篇美妙的文字令人感动,读者从中不难看出布拉格对于昆德拉的意义。这是孕育了他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产生于一个“小国”,却如此丰富、清醒、无限且深入人心。正是这种文化将昆德拉与卡夫卡连在一起,也将历史上的混乱与未来世界极权主义的深渊连在一起。
《布拉格,消失的诗》
撰文 | 米兰·昆德拉 翻译 | 董强
01 小国组成的欧洲比大国组成的欧洲对于未来更加清醒

哈谢克与卡夫卡同一年出生,早一年辞世。两人都忠于自己的城市,而且,据传,他们还因一起参加过捷克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而相识。
很难找到两个在本质上如此不同的作者。卡夫卡,素食主义者,哈谢克,酒鬼;一个为人谨慎,一个放浪形骸;前者的作品被认为很难读,是加密的、封闭的文学,后者的作品广受欢迎,却登不了严肃文学的大雅之堂。
然而,这两位看上去殊异的作者,却是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代、同一种气候的孩子,他们讲的也是同样的事情:人怎么去面对一个巨大的官僚化机制(卡夫卡)或军事化机制(哈谢克):K面对的是法庭和城堡,帅克面对的是奥匈帝国军队的极权。
几乎与此同时,在一九二〇年,另一位布拉格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在他的戏剧作品《R.U.R.》中,讲述了机器人的故事(英语“机器人”一词就来自这个捷克语新词,后来大行于世)。机器人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后来跟人类打了起来。他们没有痛感,纪律严明,最后成功地将人类赶出地球,接下来便是机器人的秩序帝国的天下。人类在这样一种奇幻的极权主义浪潮之下消亡的意象,在恰佩克的作品中重复出现,就像是一个执念、一种梦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文学开始受到未来的美好幻觉和革命末世论的诱惑,而这些布拉格作家率先洞察了进步的隐藏面,它黑暗的、具有威胁性和病态的一面。
这些作家都是他们国家中最出类拔萃的,因此,这不能被视作偶然,而是一种他们所共有的特殊目光。是的,那是由小国和少数民族组成的另一个欧洲的清醒的目光。它们一直都只是事件发生的客体而不是主体:犹太少数民族,置身其他民族中间,经历着焦虑的孤独(卡夫卡);捷克少数民族,被纳入奥匈帝国之中,帝国的政治和战争与他们完全无关(哈谢克);新生国家的捷克在一个由大国组成的欧洲里也属于少数,这样一个欧洲根本不问捷克的意见,就直愣愣地冲向下一个灾难(恰佩克)。
以战争为主题写出一部伟大的喜剧小说,正如哈谢克在《好兵帅克》中所做的,这在法国或者俄国是很难想象的,会被视为丑闻。这需要对喜剧有相当特别的认知(喜剧可以打破一切禁忌,把一切严肃的东西都拉下台),也需要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一个犹太人或捷克人不太会去认同大写的历史,不会在历史的舞台上看出什么严肃性和意义。他们远古的经历使得他们不会去敬仰历史这个新的女神,不去赞美她的智慧。因此,小国组成的欧洲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不会轻易被希望的宣传所蛊惑,比大国组成的欧洲对于未来有更清醒的认识,因为大国总是随时准备在光荣历史的使命中沉醉。

02 布拉格的虚构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
令卡夫卡和哈谢克的作品不朽的,并非对极权机器的描述,而是两位伟大的小说人物,两个约瑟夫,K和帅克。他们代表了在面对极权机器时,人的两种基本的可能性。
约瑟夫·K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他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进入法庭,而法庭像加尔文的上帝的意志一样不可把握;他想要理解它,并被它理解。因此,他就成了一个虔诚的被告:尽管没有任何人跟他确定开庭的时间,他仍然按时赶到审讯现场。当两名刽子手将他带到刑场的时候,他还让他们躲开警察的目光。对于他来说,法庭不再是一个敌人,而是他不断追寻却无法获知的真理。他要在无意义的世界里注入意义,而且这样一种努力却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帅克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对塞尔维亚的侵略。战争伊始,约瑟夫·帅克,身体棒棒的,坐进轮椅里,让人推着穿过整个布拉格,前往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他扔掉借来的拐杖,带着战争的热情高呼:“打到塞尔维亚去!打到贝尔格莱德去!”所有见到他的布拉格人都被他逗乐了,开怀大笑,但是权力机构对帅克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完美地模仿了周围人们的各种手势,重复着口号,参加各种仪式。但是,由于他一点儿也不觉得严肃,他把所有事情都转化成一个巨大的玩笑。
在一次军事弥撒中,拘留营里的士兵也参加了。卡兹神父喝得醉醺醺的,做了一次冗长的布道,指责士兵们犯了罪。帅克穿着监狱犯人的长短裤,开始大声地抽泣。他假装被神父的话感动了,逗得朋友们开怀大笑。即便在战争中的一支军队彻底的操纵之下,不严肃的精神也保证了帅克作为人的内在完整性。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帅克成功地活了下来,因为他与卡夫卡的那个约瑟夫不同,他拒绝看出其中有任何意义。
令人赞叹的是,在布拉格的虚构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想象的世界里的伟大人物,帅克和K,都与生活本身融为一体。诚然,卡夫卡的小说从公共图书馆里下架了,但是,今日的布拉格每天都在上演他的小说。因此,它们变得极其出名,在布拉格人的日常谈话中不断被引用,跟哈谢克本就努力平民化的作品一样深入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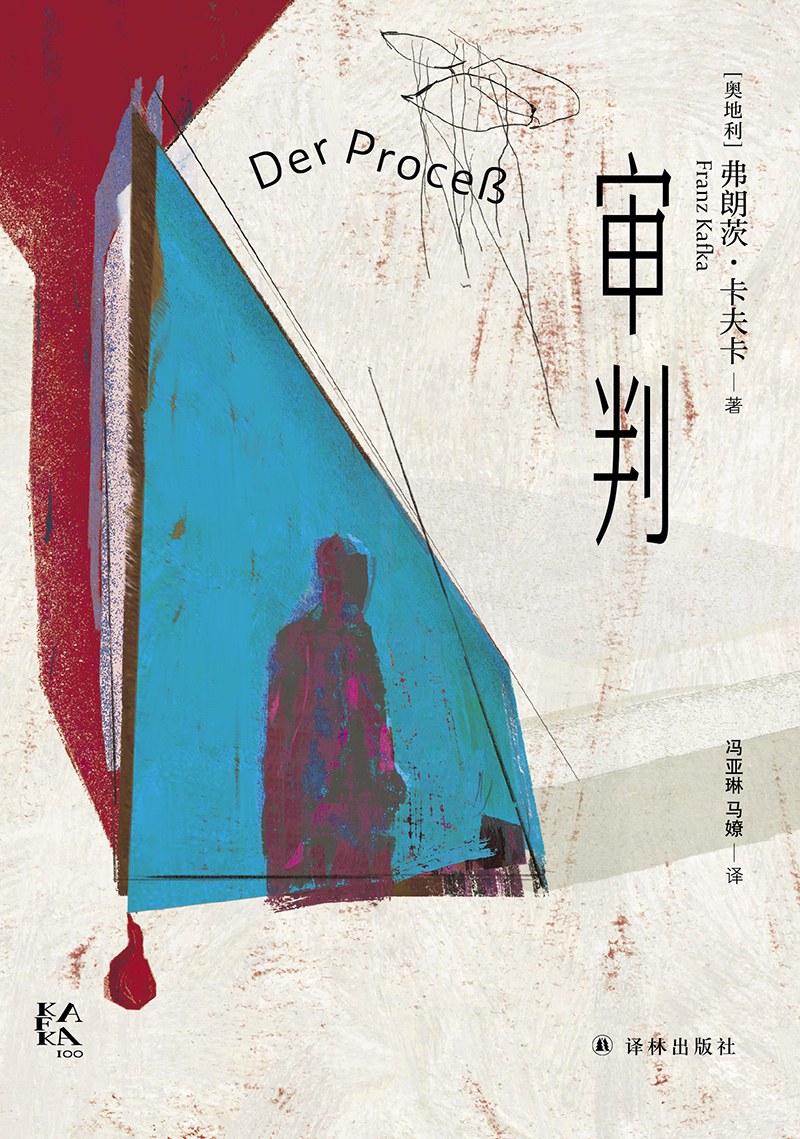
在一九五一年著名的斯兰斯基审判期间及之后,我们见到了成千上万个约瑟夫·K;当时,在所有层面都有着无数类似的审判:定罪、撤职、处分、迫害,五花八门,伴随着无数被认为有罪的受害者不断的自我批评,他们千方百计要去理解法庭并让法庭理解自己,直到最后一刻还希望在碾轧他们的荒诞机器的运动中找出一种他们能理解的意义来。作为虔诚的被告,他们做好了准备,要去帮助他们的刽子手,即便到了绞刑架下,他们还在高呼:“万岁!”(他们觉得这种可笑的忠诚具有一种伟大的道德性,诗人拉科·诺沃麦斯基(Laco Novomesky,1906—1974,捷克诗人)出狱后写下了一组诗来歌颂这种忠诚。布拉格人称这些诗为“约瑟夫·K的感恩” 。
在布拉格街头,帅克的幽灵同样存在。一九六八年,在俄国人入侵之后不久,我参加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集会。他们等待俄国人任命的新任党魁胡萨克来与他们讲话。但他根本就没来得及张嘴说话,因为每个人都在高喊:“胡萨克万岁!党万岁!”整整持续了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胡萨克的脸越来越红,最后只能离开。无疑,是帅克的天才给了学生们灵感,发出了这令人难忘的掌声。
在这两种不同的“万岁!”声中(绞刑架下的被行刑者,以及面对胡萨克的大学生们),我看到的是两种面对极权的极致态度。布拉格文学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对这两种态度下了定义。
03 卡夫卡和哈谢克通过在布拉格喊出“受够了心理学”
“受够了心理学!”卡夫卡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哈谢克也完全可能这样写。事实上,这位行为举止像个傻子、在任何处境下都开始滔滔不绝讲些没头没脑的话的帅克,究竟是个什么人?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他感受到的是什么?他这种无法解释的行为的动因是什么?这部小说表面上通俗易懂、信手为之的特色,不能掩盖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帅克这个人物是以何种奇特的、非常规的方式构建起来的。

布拉格作家的这种反心理学态度比那些著名的美国小说家的做法超前了十年、二十年。美国作家在叙述中摈弃了内心反省,转而采用行动、事件,试图从外部把握世界可见的、可感知的一面。布拉格作家的做法在本质上有些不同:他们并不热衷于秀肌肉,或者描绘外部世界,而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去理解人。
这种对人的新看法体现在一种令人震惊的境况中:两个约瑟夫都是没有过去的。确实,他们来自什么家庭?他们的童年是怎样的?
他们爱自己的父亲、母亲吗?他们的生活轨迹是怎样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正是在这一无所知中,出现了全新的写法。在他们之前,让一个小说家最钟情的,是去寻找心理上的动因,也就是说,去重建那个将过去与当下的行为连接在一起的神秘纽带,去追寻“逝水年华”。就在这逝去的年华的质地里,隐藏着灵魂迷人的无限性。
卡夫卡并没有放弃内省;但是,若我们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跟着K的推理走,乃是徒劳的。我们感受到的引人入胜之处,并不是他灵魂的丰富多彩。K的推理完全被他专制的、暴君式的处境所局限,他完全陷入其中。布拉格作家们的小说不去问在人类的心灵中隐藏着什么样的珍宝,而是去探问:在一个已经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一个人的可能性还有多少?小说家的探照灯只照在一个单一的处境上以及面对这一处境的人身上。只有在这样一种态度中,才有着需要一究到底的“无限性”。
然而,就在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对内心的探索已经达到了可能性的极限的时代,卡夫卡和哈谢克通过在布拉格喊出“受够了心理学”,开启了另一种小说美学。二三十年之后,萨特提出自己的意图不是关注人物的性格,而是聚焦于人的处境,即“人类生活的所有基本处境”。他试图抓住这些处境的形而上的一面。在这样一种美学氛围中,布拉格小说家们的写作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为人所熟知。但是,正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入领会这一转向的原始意义:在一个外在的决定因素越来越对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世界里,内在的动因不再有什么意义。
新的小说趋势摈弃了心理小说的惯例,从历史来看,它与极权世界将要来临的预感是相关的。这是一个充满意义的巧合。

[法] 米兰·昆德拉 著 董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6-20
书摘部分为《不解之词》中的《布拉格,消失的诗》第3-5小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