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期主持人 | 尹清露
整理 | 实习记者 左佳华
就在加拿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逝世两个月后,一件被掩埋了太久的秘密浮出水面:近日,门罗的小女儿安德丽娜·斯金纳对加拿大媒体《多伦多星报》披露,称自己童年时曾经遭受继父盖瑞·弗兰姆林性侵,母亲对此知情,但仍与弗兰姆林继续生活,直到他于2013年去世。
根据安德丽娜的描述,虽然她在事后告诉了生父,她的生父却决定向门罗隐瞒此事。当安德丽娜时隔25年终于向门罗坦白真相,门罗的反应是“感到自己被背叛了”,似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跟一名受害者说话,而受害者正是自己的女儿。从安德丽娜的自述中可以看出,性侵对她的一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她因此患上暴食症等病症,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她找到了应对创伤的方式,她如今是安大略省的一名冥想和正念教师,擅长治疗童年创伤。

这次事件引起了广泛的震惊和讨论,也把“作品与艺术家能否分开看待”这个老问题摆上了台面。一个被普遍提起的观点是:门罗之所以能把人性的复杂刻画得如此精彩,说明她曾亲身经历过。门罗带有类似情节的短篇小说《破坏者》,也由此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它包含一名年轻女孩被年长的标本制作师性侵的情节,而他的女性伴侣却对此视而不见——尽管她曾资助过女孩上大学。然而,这种事后归因的做法又是否妥当呢?
抛开“作品与本人”的亘古议题不谈,事件真正令人心情复杂的地方在于如下事实:一名写出了女性内心最细微复杂的感受和心声、被誉为女性主义典范的作家,她的真实行为却背叛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讽刺的是,在门罗拒绝为女儿伸张和辩护时,她用到了“厌女文化”一词作为理由——根据安德丽娜的回忆,门罗对事件的回应是“她太爱他了,如果我期望她拒绝自己的需求、为孩子牺牲、弥补男人的过失,那么我们的厌女文化就是罪魁祸首。”
01 性侵丑闻与性别的双重标准
林子人:我的第一反应是巨大的震惊,第二反应是失语,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应这种感觉。我觉得,事件当中所有知道安德丽娜被继父弗兰姆林性侵但是保持沉默的人——不只有爱丽丝·门罗,还有安德丽娜的生父、在弗兰姆林被判有罪后没有披露此事的媒体、门罗的传记作家,以及门罗家族的其他家庭成员——他们全部都是这起性犯罪的共谋,这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
与此同时,门罗的身份又非常特殊,让事情变得空前复杂。首先,她是一个拒绝站出来和丈夫割席、保护女儿的母亲。其次,她是一位长期被认为对女性的生活处境有敏锐观察和精妙书写的小说家,也因此被贴上了女性主义的标签。与此同时,她的盛名又让这种沉默得以持续到她去世。
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当中,最让我震惊的一个细节就是刚才清露提到的,门罗用“厌女文化”这个说法来为自己开脱,她坚称这是女儿和继父之间的私事,和她本人无关。我觉得任何有正常良知的人对这段话的第一反应肯定都是愤怒:作为一个母亲,你怎么可以对女儿的痛苦熟视无睹?“厌女文化”作为女性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可以被用来作为母亲置身事外的借口吗?如果是这样,女性主义的理论又有什么存在意义呢?

与此同时,我又觉得门罗变成被攻击的靶子,这件事情本身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门罗的说法,即我们要求一个女人站出来去弥补男人的过错。它确实是“厌女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事件当中,女儿是受害者,母亲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真正的施害者又在哪里?我们指责门罗未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但这一切的源头难道不是她的两任丈夫都放弃甚至辱没了作为父亲的责任吗?我不是想为门罗开脱,我想表达的是一种对于性别双重标准的困惑。
上周有两位知名作家被爆出丑闻,除了门罗,还有尼尔·盖曼。他被多名女性指控有性侵的行为,但是尼尔·盖曼的新闻热度就没有门罗那么高。在当今社会,男性得到父权制的层层庇护,他们享有完全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表现在于即使他们出于一己私利做出严重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旁观者的反应大多数时候都是:他好混蛋,但是也并不奇怪。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问一问这些男性犯罪者,你为什么要知法犯法?你在践踏弱者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呢?很多情况下,做错事的男性好像是一个默认的既成事实。与此同时,我们的怒火倒向了别的地方。在指责门罗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在加剧我们的愤怒?

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件事对女性主义试图重构“母职”观念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些年女性主义群体内部一直在反思母亲的身份对女性是否是一种束缚。很多文艺作品、社会学研究和纪实作品都在讨论,为什么女性难以成为完美无私的母亲,为什么不是每个女人都想成为母亲,以及为什么有缺陷的母亲也是值得理解和同情的。我最近看了一部相关主题的电影《暗处的女儿》,根据费兰特的小说改编。影片讲述的就是一个年轻时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因为职业上的抱负——抛弃女儿的母亲。
门罗事件是一记非常沉重的拷问。它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包括一个母亲的自私在多大程度上有道德正当性?一个母亲可以选择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吗?可以选择爱丈夫胜过爱子女吗?如果选择更爱丈夫,是不是就沦为父权制的“伥鬼”,进而失去了女性主义者的资格?
尹清露:我困惑的是,事件中门罗作为父权制的受害者,但好像又是某种加害者,这让她的位置变得非常复杂。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门罗在得知真相后对她女儿说:“But you were such a happy child.”门罗在这句话中好像在隐藏什么或者在转移目光。
她逃避的东西是什么?也许是父权制的束缚,也就是她不愿意面对的东西。子人所说的重建母职叙事,虽然有《暗处的女儿》这样的作品出现,但是大多数时候当我们说重构“母职”的时候,这些“自私”的母亲还是爱孩子的,只不过除此之外她们还想做快乐、自由自在的母亲。她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过分的事,或者像门罗一样触及到根本矛盾。
徐鲁青: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是,当时她去拜访门罗,门罗主动提到自己读到的一篇短篇小说,内容关于一个女孩因为她继父的性侵而最终自尽。门罗对小女儿说的是,那她为什么不将这件事情告诉母亲呢?小女儿可能是听到门罗的反应,联想到了自己,才决定把遭遇写在给门罗的信里面。事件的发展如我们后来知道的,门罗没有对这件事做出反应。后来小女儿在文章里面写道,她相信门罗已经回答了关于故事中那个女孩的问题,她没有告诉母亲,因为她宁愿死也不愿冒被母亲拒绝的风险。我读到这里挺心碎的。
另一方面,当门罗站在文字层面听到这件事情时,她的第一反应也像我们一样,认为母亲肯定会保护她的。但是事件实际发生的时候,会有一种理念和事实或者自身处境的割裂。

董子琪:我注意到报道的几个细节。其一是门罗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并不是完全地无视,她是有反应的,她搬离了她和丈夫弗兰姆林的家,到另外一个公寓里面独自居住了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全家人都知道了这件事。门罗女儿的继父写信给小女孩的亲生父亲吉姆·门罗。他在信中说,事件发生有一段时间了,并声称是小女孩先勾引他的,他是一个受诱惑的、无辜的对象。只是后来门罗没有坚持,她还是回来了。
还有一点,小女孩没有选择告诉她的妈妈,背后可能是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女孩自述她第一时间告诉的是她的继兄,哥哥告诉了自己的妈妈,也就是她的继母,继母才转告了她的父亲。这种多环节的传播,不知道有多少信息在中间流失。所以安德丽娜的姐妹在事后回忆说,他们的父亲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没有去跟门罗对峙,低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但是他还是交代了他的大女儿回门罗家的时候,不要让小女儿和他的继父单独待在一起。显然这是很难做到的。
这可能是多方面问题的叠加,母女关系、父女关系多方面造成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处境。然而我觉得这非常可信,因为小女孩第一时间告诉的是跟她年龄最接近的哥哥,哥哥告诉了自己的妈妈,非常符合现实的逻辑。如果是在影视剧里面,很可能她第一时间就告诉了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就会简单很多,现实更含混。还原事实时,报道也应该提到这些方向,而不只是说门罗是个恶女。
02 作家的作品到底有多少自传成分?
徐鲁青: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人们对她的评论是:她书写出女性自我的迷失,对控制的甘于臣服,这些东西始终萦绕在门罗数十年的作品里,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如果她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没有经历过自我的迷失、对于控制的臣服,门罗可能的确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尹清露:我读门罗的作品时,也会觉得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不断地在逃离、做出妥协但仍处于迷失中的女性。我昨天又看了门罗比较晚期的作品《逃离》,很具体地讲述了一个女孩从哪里逃到哪里,但中途又折返回去,最后并没有逃离成功。
只不过,艺术家创作的东西是否能就这样联系到ta的人生,或作品有多少自传成分?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记得门罗在采访里面提到,她的写作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有这么多自传成分。当然这句话也可能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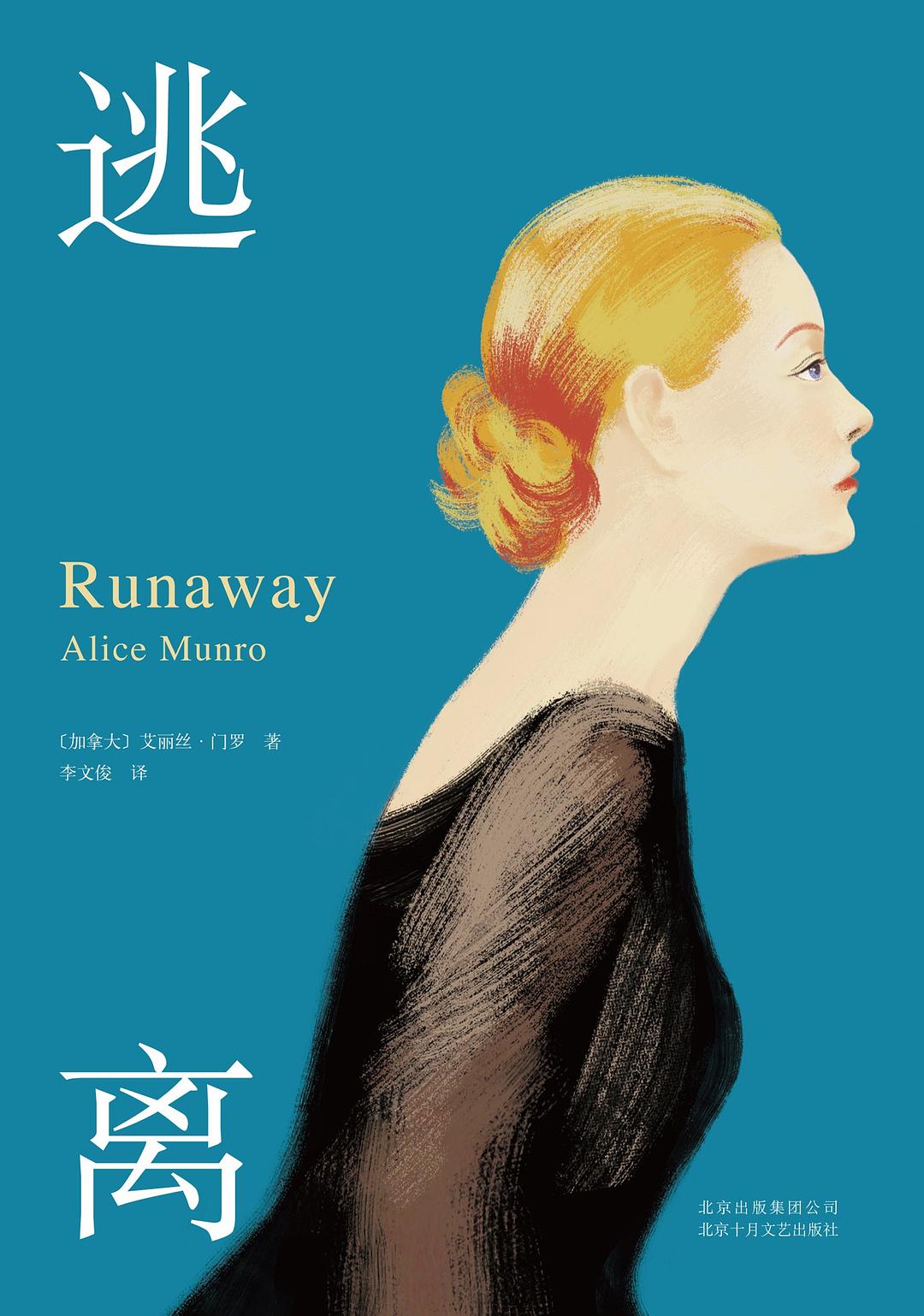
[加] 艾丽丝·门罗 著 李文俊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2016-10
前不久的电影《坠落的审判》探讨的问题跟门罗有很大的重叠。在法庭上,检察官想把女作家的小说情节和她是否谋杀了丈夫强行关联起来,而检察官几乎是作为一个丑角被呈现的,导演很明显在批判这种视角。
董子琪:辛波斯卡有一篇比较讽刺的文章,她说一些读者从日记自传或自传体小说里面想要寻找到作者的真我。就像许多人在读《红楼梦》时,会将书中情节对应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这是一种历史的而非文学的读法,好像文本后面有一个谜团,作者的写作如同谜语,需要抽丝剥茧地推理真相。
先不说这种读法是不是能够接近文本或者作者真实的意图。辛波斯卡说检查自己的良心很困难,但审查别人的良心是没有痛苦的。而且这是相当民主的做法,它的民主在于虽然读者可能在文笔、思想、地位和名声上都远远不如这个作者,但是读者可以检视作者的良心,从而可以证明我们的某种信念,即我们是更好的。带着这种信念去阅读,就像是在挖矿、找寻宝藏和意外得财。辛波斯卡指出,有很多读者会发现指控作家有道德瑕疵,反而能松一口气。
潘文捷:我发现门罗是1931年出生的,门罗发现这个事情是1992年,她当时是62岁。我想指出一点,门罗生于1931年,真的年纪很大,戈尔巴乔夫也是那年出生的。你能想象这件事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家里是什么样子吗?而且就门罗的出身背景来说,她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一个小镇。我在《The Daily Beast》中看到的分析文章提到,在门罗所处的那个时代,在西南安大略的这个小镇上,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会被掩藏起来的。这就是她所处的生活处境。
门罗的写作被叫作“南安大略哥特式风格”,她的作品中有很多哥特文学的元素,包括乱伦、孩子被遗弃等。1973年门罗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就谈到了她成长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哥特”,这种哥特式的生活与对秘密的隐藏密切相关。罪行发生在不为人知的地窖中,在门罗的生活环境中这些事情都是很常见的。

中国媒体纪念爱丽丝·门罗或者介绍她时,都谈到门罗并没有完全认可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门罗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仅仅限于我赞成的某些方案。”她认为女性主义作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是别人强加给她的。她在写作的时候并不考虑女性主义的政治,只是考虑故事情节是如何发展的。我并不是说门罗不是女性主义者,或者没有女性主义思想,而是认为不应该从教条的角度去理解门罗写作中的女性主义。
我发现作家有很鲜明的特点,他们很不愿意称自己为某某主义者,不愿意给自己贴上标签。因为一部小说变成了某某主义小说,会把整个故事用来做政治教条的宣言。
另外,门罗一家非常有文化,全家人都在引经据典——女儿下定决心吐露这件事是因为看了一本小说。子琪写的稿子也谈到她的继父引用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说是女孩引诱他的。女性主义者总是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那么门罗自己是不是一个受害者呢?首先是丈夫背叛了她,按照刚才子琪的描述,她基本上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的人。她跟女儿好像也没有很亲密,女儿并没有直接跟她讲。这在亲子关系中非常常见,孩子以为父母会对孩子说“对不起”,但是父母却跟孩子说“没关系”,父母往往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我不是在说门罗没有做错,但我也能够理解门罗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03 被简化的女性主义教条与复杂的生活情境
尹清露:非常认同文捷所说的。女性主义通过这些年在大众话语中的传播和流变,不可避免有简单化的倾向。它被简化成教条,再把这些教条去对应到一个你认为应该符合的女性身上。这本身就非常不女性主义。
我在北京电影节参加了戴锦华和许鞍华的对谈讲座。感受特别强烈的是,讲座明显被安上了女性主义的视角,戴锦华作为主持人也被强行安排了任务,要向许鞍华提出问题:你的作品中女性视角怎样?你是怎么呈现女性主义的?许鞍华将这类问题化解掉了,她说因为自己是女的,写自己的事情比较顺手而已。很明显能看出来,一个是从理论出发,一个是从复杂生活或者创作面向出发。很多读者用教条去评论门罗时,我也觉得非常不公平。

林子人:文捷指出门罗的年龄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不能忘记门罗是以92岁高龄逝世,她的人生基本上跨越了大半个20世纪。女性主义也差不多是在这一个世纪中才出现突飞猛进的进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到历史局限性的问题,再加上她是一个生活在加拿大小镇的女性,当地的社会氛围本身就很保守——在熟人社会中主动袒露家庭丑闻,当事人要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这个事件中肯定很多人都做错了事情,但是他们做出的选择不是没有讨论空间的。
董子琪:最让人失望的一点是门罗在后来《纽约时报》的访谈中还表达了对丈夫崇拜,这成为了她与女儿断绝往来的最后一根导火索。这么厉害的女作家,为什么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有明显缺陷的男人,有着如此深厚的爱意呢?
尹清露:很多人用爱女/恨女的逻辑来评论门罗,这对于事件的思考完全没有帮助。子琪提到为何门罗会这么深爱丈夫,这是理想脚本(女性应独立自强等)和实践的偏差,这个偏差难道自己就没有吗?大家都没有办法按照理想话语去生活吧?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思考理想/理论面对具体伦理时的张力。
之前读过人类学者Saba Mahmood的研究,她致力于研究伊斯兰教和女性主义的交叉性。她提出一个观点——女性主义意义上的能动性是非常狭隘的,不足以解释非自由主义传统女性的诉求,比如伊斯兰教女性的渴望、情动或者意志。我们通常会觉得女性能动性=对抗父权体制,但是Mahmood扩宽了其定义,她把性别能动性看作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通过互动而被塑造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视角也适用于门罗。就像文捷所说,门罗生于1931年,我们要把性别政治放在这个特定的生活世界里,而不是从已知的、消除了不平等的立场出发。比如,子琪提到门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她其实是远离了自己的丈夫一段时间的,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以及,我发现门罗强调自己没有办法写出长篇小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生孩子后需要做很多家务,没有足够时间写作,她肯定有一些怨恨或受害者情绪。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所有这些都考虑在内,再去思考事情是怎样的?而不是直接惊讶地说再也不读门罗,或者诺奖的组委会应该把她除名。
Saba Mahmood的研究提到,研究者的使命并不是提供一个可以被证实正确的理论,也不是要自圆其说,或者说自己的立场有多对,重要的是提出一个(被普遍认为早已被解决的)询问,而询问会引起更多的询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打破自己,得到进化。

04 写作与文学的道德
潘文捷:门罗的名声如日中天,她因此好像变成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偶像,所以这件事情越发不能说出来。沉默中有怀疑、无知、恐惧,有懦弱,还有对名声陨落的恐惧。假如你是门罗,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偶像,还得了诺奖,家里的这个事情也没有被报道,会有凭空把它说出来的契机和动力吗?
林子人:当丑闻真的曝光了,作为一名知名作家真正恐惧的到底是什么?你担心的是读者因此抛弃你吗?是作品的价值骤然下降吗?这些问题对读者来说也是一个拷问。反性骚扰运动之后,这样的事不停地在发生,电影界也有不少先例。 Woody Allen是一个如此有才华的电影导演,但他同时被认为有恋童癖倾向,跟自己的继女结婚。那我们要抵制他的电影吗?放到门罗的例子里面,这一事件肯定会影响我们对门罗文学遗产的看法,但要怎样去看失德作家的作品也是一个很难得出答案的问题。
我昨晚在读《Drawing The Line:What to Do with the Work of Immoral Artists from Museums to the Movies》,中译本《划清界限: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作品》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书中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一个创作者有道德缺陷,是否意味着作品的美学价值会打折扣。这本书给我一个重要启发:这是一个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的问题。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希特勒,希特勒在进入政坛之前一度想要成为画家,他确实画了很多风景画,虽然谈不上画技高超,但是水平也不赖。从画作中我们恐怕非常难看出他日后会成为纳粹头子、20世纪最大的恶棍。在这个案例里面,创作者的道德缺陷和作品的美学价值是彼此没有联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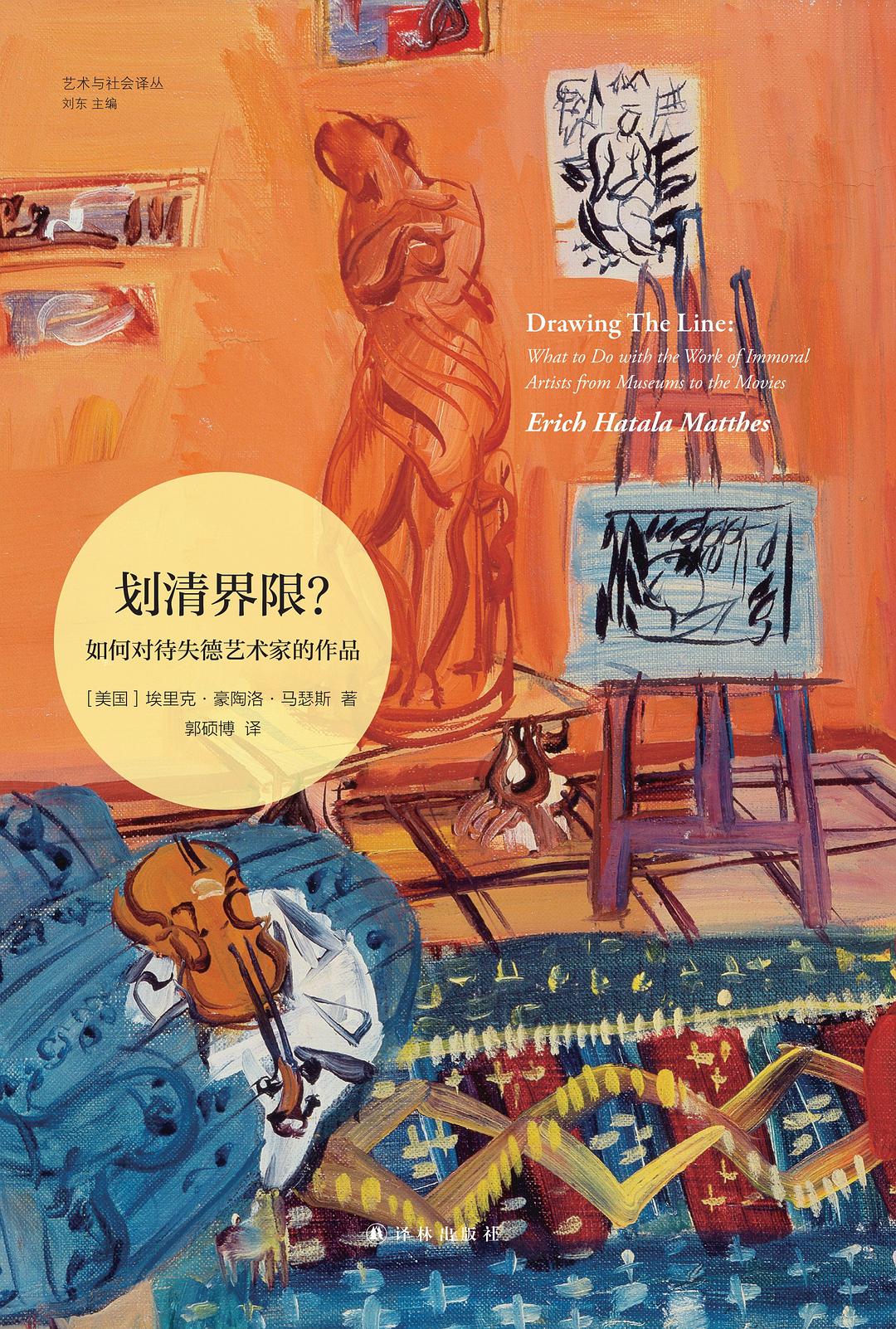
[美]埃里克·豪陶洛·马瑟斯 著 郭硕博 译
译林出版社 2024-8
门罗的情况更加复杂,我们普遍认为她的小说有一些自传色彩。她创作的故事会引导读者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思考女性的处境。我们身为读者不可避免地去问,门罗是不是通过写作来为自己的道德缺陷辩护,这种做法又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对作品的评价?《划清界限》第一个章节从正反两面探讨了这个问题。
根据“非道德论”(immoralism)的观点,解释艺术家的行为以及TA的行为对其作品的意义时要特别谨慎,有时候艺术家的道德困境反而会让作品产生更高的审美价值。我们没有理由坚持认为道德有缺陷的作者肯定会创作出审美上更差的作品,很有可能情况是相反的。现在我们知道门罗的人生中有这样一件事时,我们可能会对她的诺奖颁奖词有了不同看法,但是我们没办法去掩盖评价积极的一面:门罗确实用精妙的语言写出了很多女性不为人知的困境。我们可以称门罗的写作或许包含了她的道德缺陷,但是它带给了读者思考,那这个思考就是有价值的,她的作品也是有价值的。
董子琪:子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人和言作为两个不同的面向,不能因为某人的话说得好就推举他,也不能因为某人不好就否定他的一切。两者的关系是可以被讨论的。
尹清露:Saba Mahmood曾说:“Virtuous habitus is acquired through virtuous habits.”有德行的惯习是通过善行去达成的。但是这种行为具体是什么,这也是可以讨论的。写作或许不足以成为这种善行,反而很多人是逃离到文字中,去放任自己的困惑。我们无法把一个人的作品跟他的德行对等,相反,文学也许是一个无底深渊。
潘文捷:虽然可能会存在失望和抵制,但从长远来看,这个事情反而增加了门罗的复杂性,从而增加读者的好奇。有很多人是因为作家本人的故事,才会想去看他们的作品。
林子人:跟在什么年龄进入这个作家的作品也有关系。我买门罗的书时还没结婚,还没有意识到婚姻是个如此复杂的事情。当时读门罗的故事都觉得不够爽快、黏黏糊糊的,不知道这些女人在想什么。现在30多岁的年纪再去看,肯定想法会有所改变。另外,我们还了解到了门罗的生活,我想这会给我们提供更多门罗作品的解读空间。
人类就是这么复杂,黑和白之间有非常多的灰色地带。可能在某一个时间里你是好人,在某些瞬间做了错事,这个太正常不过了。优秀的小说家能够把这种复杂性放在作品里面让我们看到。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