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上个周末,第三次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与美国大选的唐纳德·特朗普遭遇了他人生中最惊险的一幕。当地时间2024年7月13日下午6时左右,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选举集会上发表演讲约10分钟后,现场突然响起数声枪声,特朗普的右耳被子弹击中的提词器玻璃碎片所伤,鲜血迸出。一名现场观众死亡,另有二人受伤。枪手被当场击毙,其身份被确认为20岁的宾夕法尼亚州贝塞尔帕克市男子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Thomas Matthew Crooks)。
飘扬的美国国旗下,特朗普在特勤人员的簇拥中举起右拳高喊“战斗”(fight)的照片迅速登上全球各大媒体新闻头条,并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这一爆炸性事件将对今年年底的美国大选产生何种影响也引发了种种猜测。
7月14日下午,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记者采访了政治学者林垚,从这一突发事件入手,讨论了2016年特朗普首次入住白宫以来美国政治版图的变化、美国社会政治分裂的原因,和欧美各国可能存在的政治僵局。
林垚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职业法律博士,现为上海纽约大学教师。他曾与友人共同主办“选·美”项目,力图为中文公共场域提供关于美国政治的准确信息与深度评论。在他最近出版的文集《空谈》中,中卷《搅梦频劳西海月》汇集修订了近年来他在媒体或其他公共平台上发表过的阐述美国政治的相关文章。
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当下的两党格局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特朗普的卷土重来亦需要被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中去理解:民主党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中与南方白人决裂,共和党则凭借1968年大选中尼克松的“南方战略”和1980年代初“里根革命”发现了动员保守派选民的高效手段。在那之后,共和党的影响渗透到了美国政治的方方面面,从选举制度到最高法院,都越来越有利于推动共和党的政治议程。与此同时,美国的选举制度让两党体系日益成为无法撼动的“超稳定结构”,剥夺了两党温和派候选人脱颖而出的渠道和政治改革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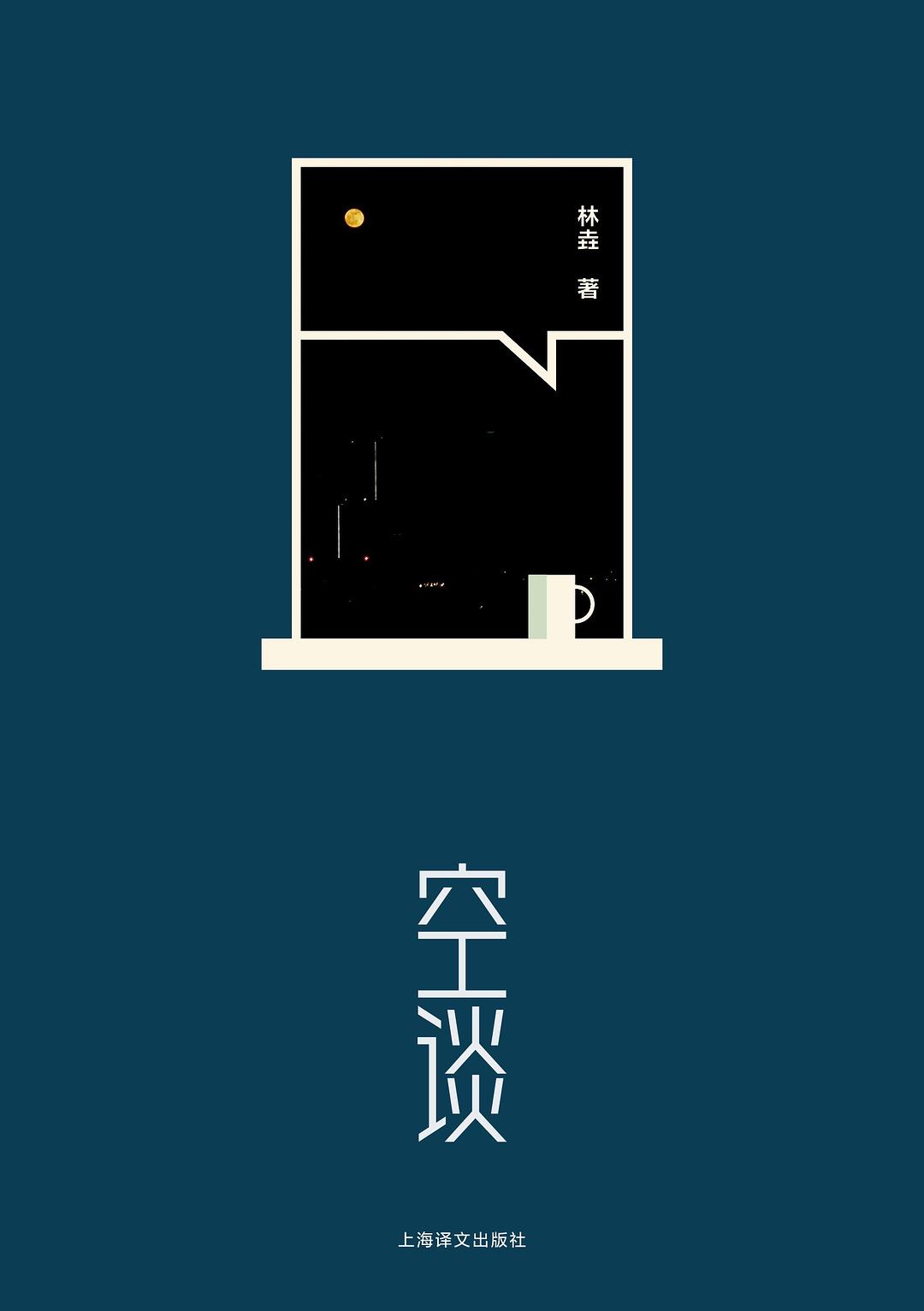
林垚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6
林垚在采访中强调,民主党内部分裂、共和党日益极端化的现状其实已持续多年,这与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有隐秘关系。他认为,2016年以来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反思美国政治分裂时提出的各种解释——包括身份政治令左翼远离了公民政治、经济不平等和“精英的傲慢”让普通美国人转向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都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即美国的政治制度已出现难以修补的裂痕。
01 距离正式投票还有三个半月,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界面文化:看到特朗普遇袭的突发新闻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林垚:第一反应是又震惊又不奇怪。上个月拜登在电视辩论中表现得很糟糕,很多人来问我的看法。我说不着急,还有4个月时间,现在美国政治那么“狂野”,总会有一些小概率事件发生。当然我也没想到有人会在集会上开枪。
界面文化: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特朗普要赢了。”
林垚:现在离投票即正式大选开始还有三个半月,如果是投票前一天发生刺杀,我觉得(特朗普胜出)是一定的,但还有三个半月,还有很多事可能会发生。新闻周期过去之后,或者凶手身份被披露后,或者这一事件的热度被其他事件掩盖后,(特朗普遇袭)未必是一件大事。我比较排斥阴谋论,不觉得这件事是共和党安排的,但如果凶手被发现是一个共和党选民,共和党就很难拿这件事去指责民主党(注:报道显示,克鲁克斯的党派信息登记为共和党,或曾向民主党相关组织捐款)。

界面文化:电视辩论之后,民主党就在讨论推举另外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叠加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你认为拜登有可能退选吗?
林垚:我觉得很难。首先,虽然拜登如果主动选择退出的话确实是可以退选的,但拜登自认为他在过去四年的政绩还不错,也已经顺利走完了初选程序。拜登本身就不是一个善于辩论的人,只是因为在一次电视辩论上口齿不清就被要求退选,他很难接受。
其次,更现实的考虑是民主党内一时推不出一个大家认为有希望赢过特朗普的人选。2020年拜登宣布参选时曾表示自己只会做一任总统,他的潜台词是,我参选是为了击败特朗普,然后就可以放心交棒了。大家当时没有想到特朗普四年之后会再次参加选举,而在此期间,民主党中没有出现一位被推上美国舞台被选民看到的年轻人。
按照现行选举法律规定,如果拜登退选,因为目前的民主党竞选团队是拜登-哈里斯竞选团队,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Davi Harris)就会成为顺位继承人。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党内很多人不太信任她。贺锦丽是一位黑人女性,他们担心美国的中间选民有强烈的种族偏见和/或性别偏见。如果在拜登退选后要求贺锦丽一并退选,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02 选举制度影响下,民主党内部分裂严重共和党日益极端化
界面文化:从2016年至今,美国政治给我们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左翼(民主党)在右翼(共和党)的长期布局下节节败退。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林垚:后民权运动时代的民主党是几个选民联盟的大拼盘:黑人、拉丁裔、亚裔等少数族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精英;住在郊区的白人中产。中产选民的选票是有点摇摆的,他们希望像共和党呼吁的那样给富人减税,但他们又可能看不惯共和党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些郊区白人中产选民有多少会走向民主党、多少会走向共和党,很多时候取决于候选人制造的观感。
蓝领工人阶层的选票大部分还在民主党这边,但过去十几二十年里在逐渐流失,这和工会的衰落有关。民主党希望能把这部分选票拉回来,那就需要推出再分配、工业复兴等经济政策,而党内对这些方面的政策侧重点是有分歧的。
还有过去一年以来的巴以冲突争议: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主党年轻选民认为巴以问题很重要,巴勒斯坦在遭受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应该尽早与以色列政府切割;但很多温和派选民认为巴以问题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少数的民主国家之一,不应给以色列政府施加太大压力。

所以我们看到,民主党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形成了大致势均力敌的两大派别,一派更温和,一派更激进。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即任何一派推出的候选人都难以服众。新人没有与选民发展出长期的基层互动关系,无法靠与选民建立的个人信任拉住一部分忠诚选民,只能靠意识形态来聚拢与自己意识形态相近的人,那么就很容易丢失另外一部分选票。
于是,民主党只能采取一种缝缝补补的策略:像拜登这样的老人,虽然年轻人可能看他不顺眼,但他至少在党内耕耘了几十年,党内的建制派会为他背书,在拉选票的关键时刻会放下成见,呼吁自己的年轻选民基本盘去投拜登。这种情况下,老人就成为了一种黏合剂,争取把党内新一代政治家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黏合在一起。世代交替的过程肯定要在某个时刻完成,老一辈总会退下政治舞台,年轻一代在什么节点上会出现在美国舞台上?如何重新整合民主党?这是民主党在过去十几二十年一直面临但没有完全解决的重大问题。
界面文化:如果这是民主党过去十几二十年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那奥巴马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例外吗?
林垚:奥巴马是一个例外。时任总统小布什在2004年连任成功的时候,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势如破竹,他当时还很得意地打出了一个横幅,“Mission Accomplished”(任务完成)。但伊拉克的局势在2006-2007年急转直下,美国当时支持的马利基政府腐败无能,无法在伊拉克内部弥合种族分歧,很多人开始对伊拉克战争产生怀疑。2008年又恰逢金融危机,很多美国人失业,所以在2008年大选的时候,小布什“天怒人怨”,当时很多人觉得不管是谁出来都能赢。
奥巴马参选也是希望乘这个东风,他得到了民主党内大佬泰德·肯尼迪(Edward Moore Kennedy)的支持。奥巴马当时没有政治包袱,形象比较清新,作为一个黑人,他还能代表美国的历史性突破。当时确实有很多传统上的共和党选民投了奥巴马的票,但事后来看,我觉得这更像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接下来他们反对奥巴马的政策,就不能说他们是种族主义了。很快我们就看到,仅仅两年的时间里,共和党中的极端群体茶党(Tea Party)崛起,特朗普现象其实可以追溯到茶党。它本质上就是对奥巴马作为黑人当选美国总统的一个反弹。

界面文化:这是特朗普第三次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美国总统大选。根据你的观察,从2016年至今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哪些变化?
林垚:我在《空谈》中写过,2016年共和党内同时存在两个现象,特朗普现象和克鲁兹现象。当时支持泰德·克鲁兹(Ted Cruz)的选民认为特朗普不够虔诚、不够保守,不符合宗教保守派的心意。但特朗普胜选之后,共和党内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洗整合,共和党选民也完成了认知失调的调整过程。2020年美国大选时我在美国,看到有一户人家在院子草坪上插了一个牌子,上面写道,“上帝向特朗普低下了头,说你比我还伟大。”
在过去几年里,共和党的党务机器也积累了大量特朗普的拥趸。今年3月,特朗普的儿媳拉拉·特朗普(Lara Trump)出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她就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测试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对特朗普的忠诚度,不够忠诚的人就地开除。所以现在共和党党内没有任何胆敢挑战特朗普的声音,党内的政治新星想往上爬,就需要努力模仿特朗普,发表更出格、更极端的言论。
比如有可能成为特朗普副总统搭档的J.D.万斯(注: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共和党正式提名他为该党副总统候选人)。他在特朗普遇袭事件当天立刻发推,说特朗普遇袭的推动者是拜登和民主党,我们必须予以反击。这还不算他近年说过的最出格的话。万斯多年前出版纪实作品《乡下人的悲歌》时,与如今的他判若两人;当时他还是共和党内的反川派,曾经说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但后来他想要从政时,发现只有拼命讨好特朗普才能上位,于是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特朗普最积极的舆论打手和阴谋论传播者之一。此外万斯近来还说过很多“女人即使被家暴也不该离婚,不然就破坏了传统家庭价值观”之类的话,以讨好党内的宗教保守派。目前共和党内有望攀爬政治阶梯的人都非常极端化,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是从言论到散播阴谋论等等全盘的极端化。

民主党这边分裂的状况还在持续。可能除了俄乌冲突,民主党内部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从经济政策到巴以冲突)分歧都非常大,而且这种分歧是一时难以解决的。
这种情况其实与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有隐秘关系。我们知道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参议院席位为每个州两个,众议院是根据各州的人口比例来分配名额选出的。众议院和地方议会的选举按照选区去划分。这样的制度安排意味着地理因素或人口密度因素会隐秘地扭曲整个政治选举结果的框架。按照州来划分的话,人口密度更小的州相对而言政治话语权更大。因为一个拥有很多大城市、人口密集的州,在参议院里也只有两人,在选举人团里,即使按照普选选票高出另外一个小州很多倍,换算成选举人团的票数,其实权重就下降了。同样一个州里,大城市相比于农村地带,话语权也比它原本该有的更小。
如果美国现在不考虑选区划分,直接进行全国普选,其实这几年民主党总是会高出共和党几百万到上千万票。但这个优势通过隐性的制度安排被冲淡了,陷入了僵局,即共和党即使极端化依然有足够的概率拉住一些保守派选民,冲顶总统,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站稳脚跟,但民主党没有办法往另外一个极端走。在某些选区当然有一些议员会被选民拉着往更激进的方向走,但民主党内很大一部分选民是停留在中间位置的,就会造成党内越来越明显的内部分裂。
03 身份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都不足以解释美国的政治分裂
界面文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在《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中提出,进步派的问题是不像保守派那样敏锐地认识到“道德话语”在政治中的分量,未能有效地向公众传达自己的党派道德政治观念和党派道德政治语言。你是怎么看莱考夫的观点?
林垚:我对这类理论是比较怀疑的。莱考夫提出道德政治理论有很强的时代背景:里根主义兴起以后,可以明显看到共和党内宗教保守主义情绪的崛起,但其实共和党有另外一股强大的支持势力,就是小政府主义者,他们主张减税、去监管,当时共和党的策略是利用宗教保守主义选民的选票推动小政府主义的政策。而这也为二三十年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受时代的局限,莱考夫的理论我觉得存在两大根本问题。

首先,他对政治话语的勾勒本身是有偏差的。在道德政治的框架下,共和党对国家的理解被描述成“严父”模式:国家管好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鼓励人们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但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共和党的财政保守主义倾向——他们恰恰把国家想象成一个甩手掌柜,希望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所以莱考夫对共和党那边的描述我觉得本身是有问题的。
对民主党那边的描述也有问题。民主党对国家的理解被描述成“关爱”模式:要投入建设社会福利,保障大家过得上好日子。但其实对很多民主党人来说,把重点放在国家上本身就错了。莱考夫的框架预设了两边的政治话语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关于国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但其实很多民主党政客和选民思考的是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发展出怎样的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我们不能让一部分人受苦,那我们就要利用“国家”这个工具来调配我们的财富。国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父母”的角色,而是一个工具。
其次,把政治话语抬到如此高的地位,好像在说,“只要把话讲对了,传达出正确的信息,就可以赢得选民。”这有点太小看了其他的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中的其他因素。比如“媒体掌握在谁的手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媒体是更加多元的,如果媒体构成了一个公共场域,人们都愿意阅读了解不同观点的媒体,而不是陷入信息茧房,只了解经过特定媒体过滤后的信息,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还有我刚才说的,选举制度安排增加了某一部分人的投票权重,这样的话就算你多说服了几百万人,也不会达到想要的投票结果。这些其实是我觉得更关键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再去讨论道德话语如何呈现的问题。
界面文化:2016年至今,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社会分裂也有诸多反思:马克·里拉和弗朗西斯·福山批评自由派沉迷于身份政治,远离了公民政治;阿莉·霍赫希尔德和迈克尔·桑德尔认为,经济不平等加剧造成的挫折感和“精英的傲慢”,让许多普通美国人转向反对左翼倡导的平等、自由和多元包容。你认同他们的观点吗?
林垚:你提到了两派,一派是文化派,就是对身份政治、取消文化的批评;另一派是经济派,就是探讨经济不平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我自己可能更偏向制度派,我会觉得这些问题都是表象,内里是制度出问题了,而且这些问题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以前运气好或经济形势好,制度的漏洞没有被发现;也有可能是过去几十年里通过了某些当时看起来不起眼的法律,累积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回到上述两派的观点,我认为文化派的观点是不成立的,经济派的观点部分成立,但没有抓到真正的痛点。
身份政治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制度层面难以改变,左派就试图通过重新复兴社会文化层面对一些问题的关注,让这些意识觉醒之后能够反哺到制度修补上。我在书中提到,美国高校录取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受到批评,保守派认为照顾少数族裔的结果就是对其他人不公平。我个人也认为平权法案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但它为什么不能解决呢?其实有更多深层面的制度安排导致了种族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平等在大范围地持续发生。小学、中学不同校区之间的居住隔离、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经济资源分配不公被地方层面、州层面和联邦层面的各种制度给固定下来,导致了少数族裔占多数的社区中,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一直缺乏教育机会的支持,等到大学阶段,这个差距就会显现出来。因为地方政府、州政府的种种法律制约,改革地方上的校区制度非常困难,最后导致关心教育公平问题的人在目前的条件下只能尽可能小修小补,比如在高校录取的时候采取修正的补救政策。但这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病灶依然存在。如果认为高校的平权运动导致了这些问题,就是本末倒置了。文化派没有看到制度层面更根本的矛盾所在。

至于经济派,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带来的物流链变化、就业机会的外包等等确实导致美国出现了所谓的锈带地区,这是一个真问题。它也确实引起了很多人对民主党经济政策的反感,但这里面也同时存在一些吊诡的现象。第一,锈带地区很多我们认为因为就业机会转移受影响的人仍然是民主党的选民——比如大型钢铁厂或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仍然住在原来的钢铁厂或汽车制造厂附近,仍然同以前的工会人士有关联,其实会继续投民主党。但生活在附近城镇或乡村地带的很多选民,他们可能自己不直接受到就业外包的影响,但他们看到了产业的凋敝,因此产生了一套叙事,认为民主党的政策打击了当地经济。所以我们看到,2016年特朗普在铁锈带的得票率确实上升了,但如果分析具体是铁锈带哪些人、出于何种原因投给了特朗普而非希拉里,这里面的因果链条可能会比经济派的人所呈现的要复杂得多。
这里也涉及到选民接触到了哪些媒体、媒体如何呈现的问题:到底是谁的政策、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形势的变化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影响到了美国的国运?我到底应该怪罪谁?美国大企业的蓝领工人就业机会的丧失、工资福利的下降,除了是全球化造成的结果之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1980年代里根上台以后在不断打压工会。但在讲述美国普通工薪阶层的故事时,共和党打压工会的这段历史就被遗忘了,没有呈现在叙事里。所以我们看到,媒体在叙事呈现上发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经济形势的变化能解释一部分事情,但我们同样也需要看到背后制度的变化:一些州是不是推出了削弱工会的法案?一些州议会是不是在某些条件下仓促迎来了外地大企业的进入?这些大企业进入后是否增加了地方的就业机会?为了拉拢外地大企业进驻,地方政府是否承诺了太多东西,比如给予税收优惠,反而损害了当地经济?这就需要我们去看到具体社区、具体的地方政治。
界面文化:这些年还有许多人提出美国大选的民调在失效。
林垚:对,这是从2016年大选开始的,当时很多民调人士觉得希拉里会赢。回顾来看,民调不准有两个原因:第一,2016年时很多特朗普的选民不好意思公开表明支持特朗普——其实在支持一个你自己觉得不一定会赢的人的时候,你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或者其中一些人不信任主流媒体,拒绝参与民调。第二,美国选举制度的设计导致两边的候选人在支持度接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过高,最后大选结果就是由那么几个摇摆州决定的,哪怕某个摇摆州里相差几万票,也能决定结果。
现在的话,共和党选民特别是MAGA选民(注:“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支持者、特朗普的铁票仓)已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其实在2020年大选时,因为2016年的挫败,很多民调人士重新调整了权重,增加了特朗普选民的话语权。当年很多民调认为特朗普会赢,但是他输了,于是民调又不准了。这意味着今年的民调又要把特朗普选民的权重再调低吗?

界面文化:纽约时报/锡耶纳学院的最新民调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电视辩论后,更多男性转向支持特朗普,特朗普的男性支持率增幅几乎达两倍,以23%的优势高于女性支持率。你在《空谈》中写到,2016年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虽以本土主义为核心诉求,却能获得两大党之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大男子气概(machismo)是特朗普这一次的宣传策略,而从最新民调来看这个策略确实有效。近年来男性保守化、女性自由化的趋势似乎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今年1月,《金融时报》看法的一篇报道就认为,全球性的性别分化正在出现,全球各地的Z时代都在性别极化。你认为性别会是今后影响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吗?
林垚:我觉得应该是会的,其实这个趋势在过去几次选举中大概能看到。我个人对全球年轻人中同步发生的性别分化有点困惑,不同国家的具体差异还挺大的,比如说韩国要求男性服兵役,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韩国男性会在军队内部的有毒的男性气质训练下改变,而且很多韩国男性会觉得(强制服兵役)不公平。欧洲相对来说变化的幅度没那么大,美国的情况是,过去几年里发生了堕胎法案被推翻等重大事件,很多年轻女性会感受到切身影响。
另一点是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思潮很容易在全球其他角落形成联动,比如“非自愿单身”(incel)的概念一旦产生、形成社群,可能很快就从美国或其他某个国家扩散到世界的其他角落,因为很容易能够在网络上找到同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同步的性别分化也是可以解释的,只不过它在美国具体会影响到什么地步,可能还要等这次大选的结果来验证。
04 目前无人能提出新自由主义政经结构的破局之道
界面文化:如果这次特朗普又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接下来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林垚:国际方面,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估计会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就很难在俄乌冲突中撑下去。美国国内方面,最近媒体曝光了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特朗普支持者在策划“2025计划”(Project 2025)。从各方面报道来看,虽然特朗普出面否认了他与“2025计划”的关系,但这个计划确实存在,特朗普在一些集会上公开支持“2025计划”。且不论这个计划的组织性强到多大程度,它背后反映的这些极右理念是存在的,而且极右分子试图在贯彻下去。
特朗普虽然很有煽动力,但在治国上他是一个比较无能的总统。在他就任总统期间,想要利用特朗普当选的机会把极右翼治国理念贯彻下去的那些人,也处于在官僚机构中摸索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以前都没有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经历。所以可能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万幸的是,特朗普基本上浪费了四年,但如果他重新当选,他手下的那些人应该已经准备好,不会再浪费四年时间了,可以更有效地去执行他们的计划,包括如何进一步地控制美国的司法体系。
前几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关于总统免于刑事起诉的一个判决,这个判决非常古怪(注:当地时间7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结果裁定,特朗普可以因其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采取的一些行动而获得刑事起诉豁免权,但无权因以私人身份采取的行动而免于起诉)。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前后,特朗普曾向副总统彭斯施压,要求他拒绝认证支持拜登的选举人票,转而认证伪造的选举人票。他还与司法部长讨论是否有办法废除支持拜登的选票。高院认为,总统与副总统、司法部长商议问题,是总统的分内之事,所以是默认免责的,高院就把这个案件发回下级法院,要求其评估特朗普的哪些行为可以获得刑事起诉豁免权。

高院的保守派大法官还表示,虽然允许通过证据来证明总统的行为无法免责,但任何与总统的核心官方职能有关的内容都不能拿来作为证据。比如说假设特朗普明确向司法部长下令烧掉支持拜登的选票,我们不能用特朗普与司法部长之间的谈话录音来证明他有罪,因为“与司法部长谈话”这件事情本身属于总统的官方职能。如果尼克松还在世他应该会很高兴——当年“水门事件”,高院要求尼克松必须交出录音带,然后尼克松就辞职了。如果回到那个时代,尼克松就可以说这是我的核心职能,别人偷录我说的话不能拿来作为证据。
从全球来看,共有30多个国家给予政府首脑豁免权,其中绝大多数不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中,爱尔兰、法国等国给予了总统豁免权,但由于政治文化的差异,很少有其他民主国家像美国这样同时给予总统那么强的赦免权(美国总统可以随意赦免任何人的联邦罪),所以形不成一个闭环,总统不容易胡作非为。但如今在美国,假如高院开了(豁免权的)先例,再加上已有的其他制度安排,很难保证未来的总统不会作恶、赦免底下为其办事的人,以此形成一个完美闭环。
界面文化: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说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不再有自愈功能了吗?
林垚:事在人为,但总体上的确非常困难。因为就在于美国修宪的门槛太高了,需要两院的2/3再加上3/4的州支持,这个门槛目前基本是不可达到的。因为前面所说的制度因素,虽然民主党比共和党有更庞大的选民基础,但在国会里基本就是势均力敌,很难获得一个绝对多数的票数去修宪,更不用说那些保守州都掌握在共和党手里,基本上不可能通过3/4的州门槛来批准修宪的动议。所以在根本层面上完成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小的修补能不能做到?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但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目前美国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时间,一轮轮的选举熬下去,等待世代交替之后出现一种新的契机。
界面文化:欧洲极端右翼崛起已不是新鲜事,但近期英国和法国的政局变化格外值得注意:英国保守党遭遇惨败,基尔·斯塔默出任英国14年来首位工党首相;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成为第一大政治联盟,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则遭遇失利,屈居议会第三大党。英法两国的政治变化是否具有什么风向标意义呢?
林垚:英法两国的这次选举根本上来说都显示了选民对执政集团的失望,但选民对未来有一个总体上清晰的方向吗?其实可能也没有。法国勉强保住了原来的政治格局,英国看起来向左摆了一点点,欧洲的一些其他国家在右转,但这些都没有太多的风向标意义,更多好像是选民在表达一种不满、一种迷茫。
全球可能正在面临一个重大的转变关口:全球化几十年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政经结构发展几十年后,人们觉得问题已经积累得太多了,想要变化。但往哪里变?现在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服众的答案。对选民来说他们也很困惑,所以只能今天投这个、明天投那个。
我不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不会像百年前那样再出现一次全球性的大萧条,带来政经政策上的范式变化,更糟糕的一种情况是,各个地区轮流发生经济萧条,但这个冲击又没有强烈到所有人都意识到必须或者同步做出变化。
同时还有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表面上来看它跟经济关系不大,但气候变化会影响到农业产出的不稳定、突发高温、洪水等气候灾难,这些黑天鹅事件越来越多,后果都会反映到政治上。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改革越来越迫切,另一方面政府拿不出足够的资源、意愿和能力去改革,因为光是应对突发灾难就已疲于奔命。我可能比较悲观,觉得我们大概率面临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