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武冰聪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系越来越唯分数论?这种单一的、消磨个人特质的偏狭标准,国人该如何应对?”七月北京,在万圣书园的一场阅读会上,一位听众向嘉宾提出了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这位戴眼镜的短发中年女士其实是自问自答,她的选择是用脚投票。她本人曾是北京某顶尖中学重点班的教师,前些年毅然辞职,并把就读于该校的女儿转走,入读某国际学校。今年,她的女儿申请到了牛津大学的Offer。
这场阅读会的嘉宾是新书《学神》的作者姜以琳,她现在是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过去七年,姜以琳以北京的5所重点高中为样本,并在其中两所重点高中进行了深入调查,和许多学生相伴生活。她发现,许多家长和学生都选择了出国接受高等教育。在28个研究对象中,仅有3人没有出国求学和工作的经验。
姜以琳在《学神》中呈现出中国精英学子的再造过程:在顶尖高中,校长、老师每日与学生的微观互动,都助力精英意识的养成。家庭提供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也成为保护孩子免于失败的后盾,这种保护持续到孩子们毕业后进入工作时。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各个阶层都有教育焦虑,但并不是所有家庭都有出国读书的资本。在与正午的访谈中,我们追问,教育体系能否不只是阶层复制,而能更多地促进阶层流动和社会公平?姜以琳则表示,社会学者着重观察现象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不主导给出解决方案。她认为,在目前状况下,教育促进公平的力量,没有人们期望的那么大,本应有更高比例的人群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
姜以琳来自中国台湾,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父母都是学者。通过父辈的关系,她设法进入北京两所重点高中进行调研,她将这两所学校化名为首都中学和顶峰中学。姜以琳的几位担保人中,一位是校长的朋友,另一位是数学老师的研究生导师。姜以琳的常春藤盟校博士生的背景,也帮她赢得了老师和家长的信任。
这项研究从2012年正式开始,姜以琳可以进入两所学校的教室,自由地与任何学生交谈。她邀请了28名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并在他们高中毕业后进行了后续访谈。姜以琳还与13位老师和19位家长先后进行65次访谈。为了解家庭情况,她多次探访三位男生的家里, 还在一名女生的家中住了4天。
《学神》最有意思的发现是——来自北京精英家庭的小孩,会依照成绩高低和学习轻松程度,将同学分为四个等级: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金字塔顶端是“学神”,即不太用功但考试成绩却很高的学生;最底层是“学弱”,即非常用功但成绩不好的学生。
这种分层会延续到大学和职场中吗?即便现实比较冷酷,但姜以琳仍然对世俗成功论持怀疑态度。她希望,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可以赚钱。不过,“当职业跟教育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到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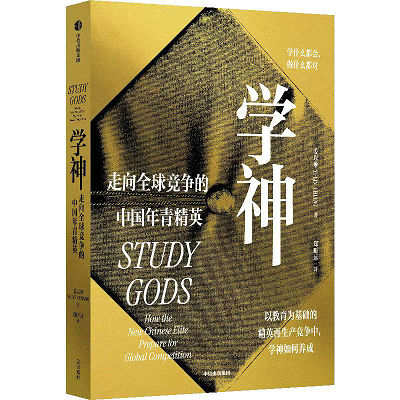
学神的去向
在《学神》的附录中,姜以琳统计了截止2019年,28位受访者大多就读于清华北大、美国藤校等顶尖大学,毕业之后追求更高的学位,或是进入金融等高薪行业,并以工作成绩替代考试分数,持续追求精英地位。
正午:从开始研究到形成本书。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加上疫情这几年的冲击,中国精英家庭的育儿方式和人生选择是否发生了改变?
姜以琳:我不是很确定,现在的精英小孩有什么样的选择和改变,但我想,疫情应该是蛮重要的因素。从我研究中的同一群人来看,经过疫情之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西方世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有些人会回来,回到东亚工作和生活。所以,精英的个人选择也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改变。
正午:28位受访者无一例外地走上正途,即便各个同学就读的学校和薪酬方面存在差异,但仍然符合世俗期待的成果。在您的观察中,是否有叛逃的精英?比如主动选择看起来更差的学校或者薪酬更低的工作,只为了自己的喜好,从而跳出了精英群体。
姜以琳:简单说来,他们大部分都过得还不错。但引用受访者柳向祖说的一句话,他觉得自己生活现在有点狼狈,不像是以前高中那么游刃有余。他可能每天在工作、家庭之间,需要料理很多事,压力蛮大,觉得自己被生活追赶着跑。
我觉得,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不同的经历,可能以前游刃有余,那么现在的反差或落差,就会比较明显。就像我在书中提到的,哪怕是精英也会有压力,随时可能从原有的位置跌落下来,所以,他们和家人才会制作备案选项。
叛逃的精英也有,比如去做自媒体的,或是去做环境保护的,这些都算是相对非精英的工作。不过28人中也大概只有两三人这样选择,而且他们的生活品质并未因为职业选择而出现明显改变。通过父母的关系或是结婚,他们仍然留在精英的群体中。
正午:随着同学们进入大学和职场,学神之类的等级观念是否会延续下来?
姜以琳:精英小孩可能会重新建构评价体系。进入大学之后,如果他成绩不好,那他就换规则。有些精英学生,在北大清华学习成绩不是很好,顶多只是班上的前30%,已经不再是前2%了。他们就会修改规则,觉得大学的目的不是读书,而是要寻找自我,懂得过生活是最重要的,成绩反而是次要的。
他们曾短暂地颠覆地位体系规则,进入社会之后,又因为自己达到的成就还不错,就会再次回归原有的评价规则。
正午:学神、学弱的分类,隐含着一种高低贵贱,也是年轻人进入社会的阶层焦虑的一种预习。在金融、科技等行业的职场,似乎也充满了类似的偏见和歧视。作为研究者,你如何评价这种等级划分?
姜以琳:学生没有政治能力,甚至没什么赚钱的能力,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成绩进行等级划分。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区分哪个学校更好、哪个工作更好?这本身都是加剧不公平的方式。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可以赚钱。我们会希望,每一个工作都给大家好的生活。但是,当职业跟教育整个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到出路。
当然,所有的社会都存在资源分配不均。有人认为,需要资源集中培养人才,从而在奥运、航天等领域使国家大放异彩,也有人认为社会的匀速发展更重要。这也是一个大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万般皆下品,惟有成绩最重要
因为深入课堂调研,姜以琳仿佛带着纪录片的摄像机,记录下北京顶尖中学许多鲜活的教学场景。在这些学校,学生们“膜学神”,以表达对绩优学生的敬仰。而拥有学神地位的学生,甚至会公开质疑老师讲的内容,“把老师挂在黑板上”。
早上9点,首都中学的地理课上,毛老师给32名学生讲解厦深铁路是如何修建的。毛老师解释说,这条铁路原本的规划是沿海岸线铺设的,但出于军事考虑,不得不向内陆迁移。“可是只移动了一千米!这个解释太牵强了!”这时,坐在前排的一名同学突然大声打断。另一名女生也附和。同学们纷纷反驳毛老师的说法,教室里一阵骚动。毛老师试图给出更详尽的解释,但还没等她开口,坐在教室后排的大鹏抬起头望向她,坚定地沉声道:“这方面我能说几句。”毛老师瞬间愣住了,困惑不解。大鹏以老师指责学生回答错误的方式,迅速擦掉了毛老师的板书。而后,他画了一张海岸线图,开始为现场同学讲课……
正午:有读者说,书中的这些精英学生有些可怕,享受到好的资源,甚至是特权,而且情绪不稳,意见太多。等他们长大走向重要岗位,也将对社会带来影响。你怎么看?
姜以琳:根据我在书里写到的内容,有些人会觉得,这些孩子是一群小皇帝,不太喜欢他们。不过,书中呈现的特质并不是他自己发展出来的,而是身边的人和事物,甚至是整个社会都共同促使他这样做的。
你可以说他们目中无人,也可以说他们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从国与国的竞争或者整个社会的进步来看,总要有人去奋不顾身的追求目标。这是事情的一体两面,就如同当我们看到一杯水,描述它是半空,还是半满,取决于你采取哪种视角。
正午:你调研的那些同学读过《学神》吗,他们的评价怎样?据我了解,有名2013年毕业于顶峰中学的学生,曾发文对你的研究有所批评。他说,当时学校并不是唯成绩论,老教师仍想守住素质教育的立场,学生们在面对高考压力的同时,彼此之间仍然保有一种共识:“卷”分数是迫不得已的、错误的。
姜以琳:中文版出来之前,我都还尽量跟他们保持联系。因为我打赌他们没有看到这本书,也没有去看书里的内容。现在中文版出来了,我就不是很敢主动与他们联系,因为生怕他们觉得我把他们描述的很糟糕。但是我还是会在网络上追踪他们的动态,并且和在上海生活的同学一起吃饭。
不过,因为时间比较久远,有些同学记不清自己的高考分数,认不出自己究竟是书里的哪个人。而且,等他们接受到高等教育,大概会知道社会科学的研究的样子,所以,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本书,他们应该不会很生气。
我还是希望和大家维持很好的关系,因为我不是针对个人,而是用部分个人去呈现整体情况。哪怕当时不写书中的这些学生,换成其他学生,所呈现的也会是当时类似的现象。
正午:用通俗的话说,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四个等级之间存在一定的鄙视链。比如书中提到,成绩差的怪人往往被排挤。除了学习成绩,还有什么因素影响了鄙视链的形成?
姜以琳:其实,影响鄙视链形成的主要就是学习成绩。不过,这本书的理论架构也只适用于北京的这几所重点高中,有些同学在这里成绩差,并不代表在全体考生中成绩差。
我探讨的是单一定位体系的案例,其实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成绩最重要。在这样一个小社会中,大家都是怎么维系这种地位的形成?同学之间对于学习成绩的单一关注,形成方式受到了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家庭、学校以及整个社会的氛围,媒体所发布的高等学院校排名,高考状元的报道,都在影响着学生。
正午: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一书主要探讨阶层趣味。他认为,评判阶层的标准,绝非只有财富一项,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同样重要。中国社会的评价标准似乎过于单一,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姜以琳:我觉得,大家会将重点放在大学录取考察的标准。现在大学录取只看分数,如果大学升学要看品味、风范和认知水平,那么大家都会去追求风范、品味跟认知水平。只是,谁可以培养出具备高级品味、风范和认知水平的小孩,是这个社会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大部分人无法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姜以琳还在书中记录下精英家庭的家长是如何影响学生成长的:
女孩Claire的妈妈拥有博士学位和很好的人脉。Claire的妈妈告诉姜以琳,自己对Claire的高中升学没有任何帮助,其实,事实完全不同。她在女儿紧张焦虑的时候坐在她旁边谈心,在女儿需要技术支援时动用人脉。姜以琳写到:“有一次在访问她妈妈的途中,我听到她接了Claire的电话,要她帮忙做个海报,她就赶紧交代博士生,最后大家很快一起印出来一个人形大小的海报。但之后我再问他们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记得。”学神往往将成就归因于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而相对忽略老师家长的助力。
正午:同学家境的差异会影响他们与老师的互动模式吗?
姜以琳:会的。但这不只是受到家庭的经济条件的影响。大部分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的学生,其父母也都是大学毕业,甚至拥有硕博士学位。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差异。
他们的爸爸妈妈,就不怕跟大学老师联系,小孩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出手。而且,家庭状况好的小孩比较敢于跟老师互动,对老师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尊敬感。从我的观察和访谈来看,家境好的小朋友,会觉得自己得到好的分数,或是好的工作机会、研究成果等,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会相对忽略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与作用。
正午:在这些学校,你也看到一些现象,比如学弱得不到顾问即时的帮助,面对家长的身材嘲笑不予还击。他们最后选择排名靠后的大学,这些合力最终形成了持续的不平等。是不是有许多人会“输在起跑线上”?
姜以琳:有些教育社会学家会告诉大家,有些人已经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我们不要再玩这套精英游戏。有些美国学者提出,不要给学生布置任何的作业,因为作业主要是考察爸妈的能力。
其实,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变,过去几十年,大家可以不断往上流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产阶级出现。但现在,中产阶级不可能继续大幅增长,且精英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大幅成长的群体。
主流的声音让我们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而教育社会学会告诉你,少数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
正午:不过,也有人认为,跟柏拉图说的一样,应该让哲学王治国,从而避免庶民的暴政。是不是总会有聪明人站在金字塔尖上?
姜以琳:我反对这样的说法。聪明怎么定义,聪明要怎么测量?智商测验吗?它也是在测量小孩的家人有没有更早开始教他更多的成语或思辨的能力。我们认为,智商测验其实反映了家庭的经济能力。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是,是否聪明纯粹就是依照他的成长过程:谁出生在莫扎特的位置上,谁就是莫扎特。环境对于人的塑造远远大于其他东西。
正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升学与就业焦虑?
姜以琳:大概十几年前,我听了一场一个纽约大学的女教授Guillermina Jasso的演讲。她的研究问题是,若将我们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工资,改成自认为应得的工资,这样的社会是否变得更平等?这是个理想化且不可能实现的前提,但她的发现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去做,社会反而更公平,现在的不平等会缩小。
我理想中的教育,是职业没有贵贱,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不同的职业在薪酬上,不要存在大到难以接受的差异。这也许需要政府推动改变, 也需要人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完——
作者武冰聪,界面新闻记者。
题图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