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提起张大春,很多读者的第一反应还是会在的名字前冠以“小说家”的称谓,但是有“顽童”之称的台湾作家张大春,可是有阵子没有写过小说了。
没有创作小说的张大春在干什么呢?从《认得几个字》开始,他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语文教育上。日前,他的《文章自在》一书也再版了。这本书在个人教育经验外,张大春说这本书也是为了尽到一个写作者的责任。
“当前文化环境下,读者越来越少,越来越低等,或者对我们所写的内容不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语文素质的落差,这不是读者的责任,而是作者的责任。”这是张大春去接近读者的一个迂回策略,他希望透过对语文的琢磨,也许会召唤一些真正对表达有兴趣的人,召唤出有品质的沟通和交流。
在《文章自在》中,张大春指出“文章”与“作文”二者的不同。“作文”是别人叫你写的话,“文章”是你自己想说的话。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苏东坡被贬时有一位仰慕他的学子名叫葛延之,这位学子一路沿着苏东坡贬谪的路线追随他,终于与苏东坡见面得以讨教如何做文章之事。苏东坡指着菜市场上热闹的交易景象,告诉葛延之,买东西“必以一物摄之,曰钱,文章亦也。”
张大春讲述这个故事,是要告诉写文章的人,要想得到经史子集里的学问,需要用“意”去换取,而“意”即个人对一件事情的主张、看法、感受。有了自主意识和表达欲望作前提,才有好文章的可能性。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日前专访了张大春,听他讲述什么才是良好的语文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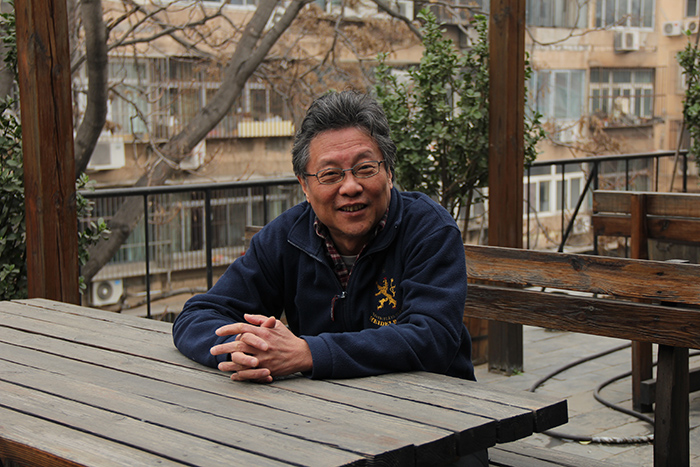
在北京理想国书房接受采访的张大春

“在应试制度下,好文章不一定会出头,坏作文得高分会发生”
界面文化:你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个说法“不要写作文”,现实是语文教育很重视作文,在你看来,语文教育中不应该包含“作文”吗?
张大春:我是有点故意把作文和文章说成两个概念,实际上这是一件事,那就是写作。教写作的目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能够让孩子在八岁到十八岁这段启蒙期,具备文从字顺地从事表达的能力;第二个层次是能够有条理地去整理自己的思维;最高层次能够面对一个话题有方方面面的看法,可以完整地激发出自己的主张。空谈起来,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我们的目的和结果之间已经产生了偏差。
界面文化:所以是中间的方法导致的?
张大春:我有一位朋友,是台北非常有名的补习班语文讲师,他比其他补习老师厉害的地方就在“教作文”上。他告诉我教作文有个秘诀,是有一套“公式操作”,他要求学生每人背20个经史子集里的句子,后面还对应一句白话文。“士君子立志不难,但是能坚持下去却不容易。”再或者,“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道理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反对的不是作文这件事情,也不是孩子不应该从八岁到十八岁学写东西,而是这一整套的训练方式。训练写作文到这种地步,还能训练人思考吗,只能训练人滑头了。
界面文化:你认为目前写作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写作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张大春:老师出题之后,学生会习惯性地去揣摩老师的意思。比如一个题目“雨过天晴”,下过雨了天蓝了,但学生想老师可能是在说一件不好的事情过去了。养成了这个习惯,这个孩子从八岁开始,是在训练自己如何去揣摩他人之意志。面对应试,学生还要揣摩判卷人的意思,所以你要揣摩这个人和那个人,那么’我’在哪儿呢?所以学生写的内容里没有自己的主张、意识、想法。古人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孩子从开始练习第一天,就要有大担当、大志向,作文课不够,更让孩子知道文章是什么,而且要有比写作文更勇敢的思维。
界面文化:书名《文章自在》四个字中,“自在”作何解?
张大春:自在,可以说是歧义或者双关,自在就是回到本我,我觉得文章不应该从命题出发的,现在这种应试作文中,最优秀的人才在的提炼过程中多多少少都在写作文上形成了套路,虽然不出格不出框,但自主意识是薄弱的。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出“要写文章,不要写作文”,文章与作文不同,有读者看了你的书后,称“如果在上学时候看的,可能作文就不及格了”。作文和文章一定是矛盾对立的吗?写得好文章的人一定能写得好作文吗?
张大春:我反对的不是作文这件事情,也不是说孩子不应该从八岁写东西,而是这个一整套一整套的训练方式。本来好文章和好作文不应该对立的,但是事实是往往会发生。在现在的应试制度下,好文章不一定会出头,而坏的作文被评为高的等级是会发生的。因为它符合这些标准,比如有引用典故、成语,甚至用得看似准确,我们怎么会不焦虑呢?

《文章自在》 张大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树立标准会剥夺我们对好文章的理解能力”
界面文化:那这样的问题是需要转变我们对“好文章”的评判方法才能化解的吗?
张大春:好文章没有标准,好文章是从情感的触动、质性的启发这两个方面,为读者带来高度的快感。评判作文可以负面表例,如字句不通顺、字词用错等,但是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个东西。树立标准反而会剥夺了我们对好文章的理解能力,我的书里有6篇选自别人的例文,不是韩愈、苏东坡,而是苏洵,没有徐志摩、朱自清,却有毛尖、林今开。很多读者未必喜欢毛尖,但毛尖笔锋内带情感,在尖锐评论文字背后是有感情的,所以同样写父母的文章,我为什么选毛尖而不是朱自清,就是要从所谓的名篇名著的惯性耽美修辞中跑出来。
界面文化:应该如何改变现有写作教学中的问题呢?如何激发孩子的自主意识呢?
张大春:主要是在出题上。我大学一年级的英文课,英文老师让我们用英文写一篇作文,内容是写“铅笔”,只去描述这支铅笔的外观。我当时很痛苦,因为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出题,他的目的是训练纯粹的白描能力。出题方式不是出宗旨和思想,而是出一个写作方向。再比如,老师在黑板上随便写十五个词语,或者从梁实秋的文章里挑选15个词语,让学生按照顺序写一篇文章,你当然不会和梁实秋写的一样,第一个词到第二个词是怎么跑的,这其实就是谋篇。
现有的应试制度下,不是没有出现过好的题目,大陆高考有一年有一个省的题目是“摔了一跤”,这个题目很容易引导出关于摔跤这件事不同的新想法,虽然它仍不免埋伏一个摔倒了爬起来的想法。但是这个题目很有弹性,等于没出题,正因如此,写文章的人主动性就更强。尽量找到不具备特定指向性的题目,更好是让孩子在每一步学写文章的过程中,每一篇都能想出一个他自己的主题。
界面文化:也就是老师要把自主性交还到孩子手里?
张大春:老师不是来告诉别人怎么写,老师只是一个开矿的工人,真正含金的矿石是坐在课堂里的孩子。出题要惯于用各种方式诱导孩子有更完整更美好的表达,其实老师一点也没有放弃他的主动权,而是要去精心设计一个方式,可以让孩子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老师要主动去挖,因为矿一直在那里。
“教材中减少文言文比重是剥夺学生进入真正汉语精髓的机会”
界面文化: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教育,都会在课本里注意强化很多中国古典诗词歌赋的内容,语文教材中需要文言内容吗?
张大春:减少文言分布事实上是剥夺学生进入真正汉语精髓的机会,台湾的国文教材文言分布在60%,我认为可以百分之百是文言文。其实这并不妨碍你在日常生活上的表述,反而会让你在更亲近和熟练之余,更了解汉语的组织、构造、细微变化。我们生活里面随处都是文言文,比如我们感叹‘往者已矣’,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有别于白话文的另外一种语言。
界面文化:但你在书里讲很多孩子并不能真的理解、运用文言文,这是为什么?
张大春:不论是诗词曲赋还是文言散文,都牵涉到文言语感的建立,它是不能被翻译的,当被翻译之后,比如“抬起头来看见天上明亮的月亮”,它就“怂”了,正是由于不能翻译,诗词的美感才建立得起来。真正的文言,就在诗词里面,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昨夜星辰昨夜风,仔细想这些不是那么需要翻译的东西。文言和白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把它分成两种东西再去理解,两者会越分越远,我们对文言更会逐渐地疏远、离弃,重视古典诗歌这件事情,其实是回到汉语最精炼的核心组织,不仅仅是纯粹美学欣赏。
界面文化:《中国古诗词大会》这个节目前不久引起了很多讨论,你有关注吗?这个节目通过背诵诗歌形式进行比赛,你觉得这种单纯背诵的方式是好的吗?
张大春:我只能说我非常羡慕他们的记忆能力,所有人都应该赶快拍手,没有第二句话好讲。有人说这样的背诵不能让他们学会作诗,谁要叫他们作诗人,他们长远而熟练地浸润在这种诗词典籍的里面,一定是有很强大的热情。其实我自己是不太背的,但背诵事实上是一种去亲近最精致的汉语的行为,这其中也必定带有美学层次的欣赏,我们不必对短期记忆的功效过于苛求。我在写《大唐李白》的时候,我相信李白小时候也是透过一种游戏的方式,背诵了很多前代人的诗词,李白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没有机会成为士大夫,但是他为什么还会背,一定是以游戏的方式。背诵诗词的孩子们难道是单纯为了参加一个节目吗?这个游戏不坏,是令人感动的一种专注和热情,除了鼓励他赞美他,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界面文化:有另一种批评声音认为,小孩子接触很多他们暂时还不能理解的诗词,等长大后会因为太熟悉而失去内心产生触动的机会,你怎么看?
张大春: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我认为明明就是嫉妒他人有非常良好记忆的恶劣说法。一个人熟读熟,宋诗千百,就会丧失情怀,这是什么逻辑?我们当然期待每一个背诗词的人,都能把他背过的每一首诗,有一个丰富内化的经验,但也只能说是,去期待如此。
界面文化:在教育方面,另一个近期备受关注的话题就是性教育。台湾之前出现过小学生依照性教育课本偷偷尝试性行为的事件,也引发了对性教育很热烈的讨论,您觉得当前台湾的性教育做得如何?社会对性教育的各种考量和看法,你有什么见地吗?
张大春:性教育是个暧昧的领域,不从事这个教育,孩子没有正确的性和性别观念,但是有人担忧它和贩卖色情只有一线之隔。性教育方法上,北欧人有很好的想法,比如丹麦、瑞典、甚至德国、法国。虽然好像西方环境很开放,可是他们对孩子的性教育也非常小心,担心者不是全然没有道理,有些东西向西方取经未必不是好事。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我们是顺其自然而得性教育,但我不知道这个顺其自然四个字的刚性有多强。
社会会提供很多的刺激和诱惑,都可能会带来的危险,我们关注的不是只有性教育。所以当我们担忧一个人走偏,其实是担忧他人格走偏,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唯一的东西,不是唯一我们所关心的,甚至他不是焦点,这其实是全教育的话题,性教育和国文教育都是全人格教育。至于具体的方法,还是要交给更多的专家。

张大春和儿子在为《认得几个字》拍摄封面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