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国家被一群疯狂者占领了,你会怎么办?埃琳娜·纳博科夫叮嘱她的仆人收拾行李,叫厨子把腊肠狗带上,并将珠宝放到一件滑石盒子里,还准备了一包鱼子酱三明治。她带着她的丈夫、孩子一起,迅速逃离了首都彼得格勒。他们往南行,第一站便是在克里米亚的最后一个防御阵地,接下来便进入了永远的流放,从黑海到地中海,再也没有回去。很多年以后,她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依然记得在岸边轰隆作响的机关枪声,还有摇摇晃晃用来运送水果干的希腊船只。正是这些船只,将许多俄罗斯难民送往欧洲和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1917年俄国革命并不等同于俄国人的革命,就像伏尔泰所嘲讽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样。1917年俄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多种族、多教派的帝国,除了俄国人之外,那里还居住着波兰人、犹太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穆斯林徒和佛教徒。它的爆发并不是按照一个设定好的革命计划展开的,而是在一系列失误、事故和曲折的命运中前行。它的发生要早于1917年,在这之后,也远未结束。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好几个事件的结合。从冬季君主专制的倒台,到夏季短时期建立的代议政府及其军事统治,再到秋季经由一个少数政党发起政变,这个少数政党被称为“多数派”,或者用俄文原文表示——布尔什维克。
2017年的开始也拉开了十月革命百年的活动序幕,而俄罗斯的反映却很温和。到底该为这个节日致以哀悼、表示庆贺还是干脆忽略掉呢?普京政府发现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历史学家们却看到了一个好机会,他们可以借机思考:在这一长串的变化之中,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布尔什维克最终的胜利。正如下面这三本书所展示的那样:从起源上来说,这场革命是地方性的,但其影响却是全球的。历史之警钟不仅预示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的诞生;它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指引我们思考政治、国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
在革命期间发生过一段长时间的内战,社会的一切都面临着重塑。不管在这之后它迎来了怎样的稳定局面,实际上都是苏联史学家们定义的结果。他们将布尔什维克的接管视作是帝国衰退的必然结果,这是一次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对剥削阶级的反抗,布尔什维克则扮演了具有前瞻性的领导角色。我们对革命的内心图景也仍然是由外国的同情者们塑造的,诸如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和苏联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那些黑白影片镜头里汹涌的人群和挥舞着军刀的哥萨克人时,他们不过是爱森斯虚构出来的场景片段,不是什么现场记录。
革命成功的事实——它怎样推翻罗曼诺夫王朝,怎样打倒政治对手,怎样建立一个新兴国家——为诸多谋求政治改变的国家提供了范例。一个有志于革命的先驱者扔一枚手榴弹便可摧毁一个老旧的政权,这样一种理念直到今天都鼓舞着各行各业的变革推动者们。甚至包括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据称他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列宁主义者,而非民族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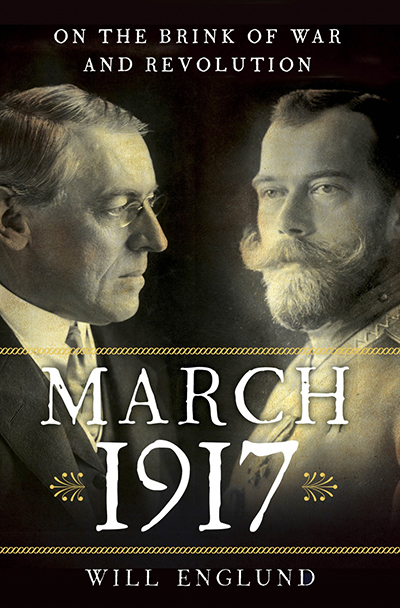
到了三月(在俄国仍然是二月),彼得格勒城愤愤不满的群众越来越多了,士兵们早已不再驱逐这些人。3月15-16日晚,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放弃了王位。混乱之中,当选的议员和没有当选的社会主义者都介入到权力的争夺之中,组织各自的政府,形成了两个互相对抗的权力中心。这只是一次退位,革命还没有到来。就像《华盛顿邮报》的威尔·英格伦(Will Englund)在《1917年3月:战争与革命前夜》(March 1917: On the Brink of War and Revolution)一书中说的,文件被人们用铅笔漫不经心地签署了。这是一本详尽且节奏明快的书,它记录了那个多事之春。紧接下来的是蔓延在俄国内外的混乱,当然还有一定程度的解脱。除此之外,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四月份宣布美国军队参加一战,对抗德国。

英格伦灵巧地将俄国和美国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在这充满了事变的一个月,美国参加战争,俄国从中短暂退出。但它们之间的任意联系看起来却不是很明朗。《1917年3月:战争与革命前夜》一书对处于风口浪尖、面临变化的美俄两国做出了精彩的描述,两个国家的参战和退出,最终不过是引起欧洲、乃至超出欧洲范围以外即将到来的军事和政治结果的微小驱动力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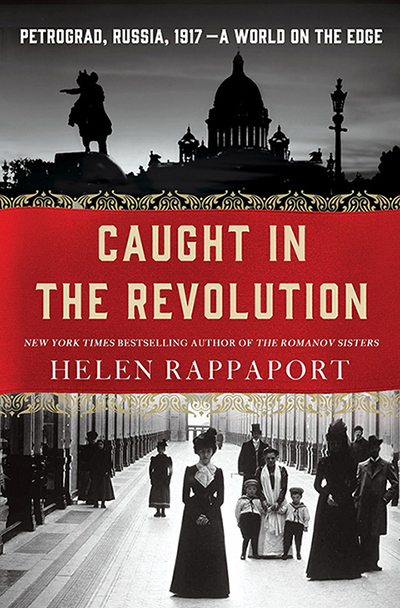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书写都需要原因和结果。唤醒(Evocation)是一种合理,甚至可能是最真实的理解过去的方式。历史学家Helen Rappaport的《卷入革命》(Caught in the Revolution)一书讲述了一队在行动中的启蒙者的故事。他们从彼得格勒结了霜的石子路跑到一辆蒸汽机车上,在这辆用于军事运输的列车上同亲人告别,他们的命运被卷入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命运之中,这个国家要通往何处,却是无人知晓的。它提醒着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从积极为妇女谋取选举权的艾米琳·潘克斯特,到美国的无名记者贝茜·比蒂,所有这些局外人都曾奔赴那个四分五裂的帝国,他们去那里采访故事。见证者们从广泛的阅读——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回忆录和现场报道——中走了出来,这些故事组成了这本书的目录。这本书本身也是见证,是对所有这些试图在亲身经历的过程中了解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的外国人的见证,这些人的运气都非常糟糕。
如果你是一个俄国人,那么从1917年3月到11月这段经历,就像把头放在老虎钳子中一般。法国人后来还为此创造了一个短语“drôle de guerre”(“虚假战争”)用来指称1939年之后一段相似的时期——有什么正在进行中的冲突,但是却没有太多与此相关的新闻,政治上不确定,政府运转不灵,给人一种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的感觉,但到底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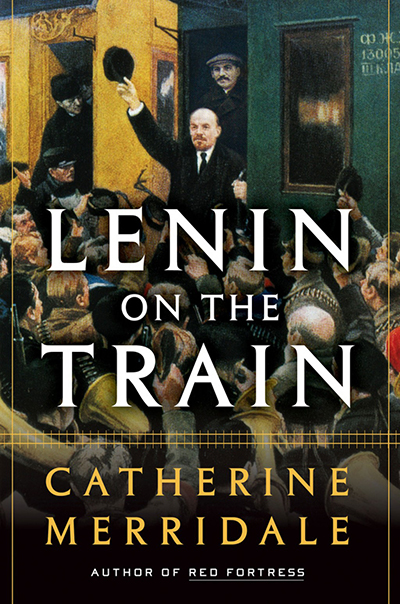
凯瑟琳·梅里戴尔(Catherine Merridale)在她的《火车上的列宁》(Lenin on the Train)一书中,选取了一段发生于那个春天非常有趣的插曲:弗拉基米尔·列宁同其他革命家在一节从苏黎世通往彼得格勒的二等车厢中度过的八天时光。列宁的回乡是一群德国情报员和俄国社会主义流亡分子合作的结果,这趟回乡之旅标志了在秋季即将到来的、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变。俄国社会的转变从列车嘎吱远离站台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列宁禁止在车厢走廊上吸烟,并发明了一种能使人们按票有序进入车厢中唯一一个厕所的系统。
大量的金钱流向东部用以支持反战宣传。但是,梅里戴尔认为,德国直接将钱汇给布尔什维克这种说法还只是一种猜想。她指出针对列宁的部分资金支持,很有可能来自一项依靠战争发财的复杂策划,包括非法销售避孕套和铅笔。
正如列宁知道的,革命政党必须改变公共讨论的术语,而不是在一个已经充斥着各种术语的场地,再添加另外一个可替代的术语。大众政治需要大众宣传,这也是为什么现代革命开始于对传播手段的争抢,而不是设置路障或占领一个军火库。像往常一样忽视政治正确,同必须结盟的人结成便利的联盟,抛弃掉不再有用的旧盟友。如果你想改变一个国家的外交策略,就从转变它的国内政治入手。要知道,一辆满载着活跃革命者的密封车厢,当它沿着轨道前行,就有可能变成别人的麻烦。1917年俄国革命制造了一条推翻政府的秘方,它同时也告诉了人们如何建立政府,即便政府的表现方式有些反政治,但这种风格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查理斯·金是《午夜的佩拉皇宫:近代伊斯坦堡的诞生》(Midnight at the Pera Palace: The Birth of Modern Istanbul)一书的作者,他还写了其他书籍,目前是乔治城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专业的教授。
(翻译:朱瑾东,较原文有删节)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A revolution a century ago that still reverberates--right into the White House
最新更新时间:03/31 12:23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