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一封虚拟的书信,寄给20世纪初聚集在巴黎的艺术家们?从现代绘画之父塞尚开始,直到印象派女画家莫里索,写给印象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分离派、未来主义、抽象主义、达达运动、超现实主义等等流派的艺术家们,聊聊艺术、历史以及巴黎的故事,就如同当年汇聚了各方艺文精英的巴黎艺术教母格特鲁德·斯泰因那样。
现在,有一个人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她叫罗婉仪,出生于香港,现从事艺术创作、写作及教学工作。她写了二十封虚拟书信,收信人是二十位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家,包括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马克·夏加尔、萨尔瓦多·达利等等。其中十四位是男性艺术家,六位是女性艺术家,问答之间,借由文字,重现那个光辉时代的文化氛围,也遥向对当时爱艺术、爱文学的格特鲁德致敬。
下文是罗婉仪“伪装”成法国超现实摄影师、毕加索的情人朵拉·马尔写给毕加索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毕加索若干重要作品的历史背景和画家心路,而且仿佛真的可以走入毕加索与巴黎、毕加索与朵拉的情感纠葛之中。
巴勃罗·毕加索 × 朵拉·马尔
发信人:朵拉·马尔(Dora Maar,1907—1997)法国超现实摄影师,毕加索的情人
收信人: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立体主义画家

亲爱的巴勃罗:
我很别扭。我真的很别扭。我有很多嘴巴。我有很多耳朵。我的眼睛,还有鼻子,我不合比例、歪斜变形、五颜六色的脸。一只黑猫爬到我坐的椅背上。我掉下大滴的眼泪。你说我是最会哭的。你说我是歇斯底里的。是的,很多人都说朵拉·马尔别扭歇斯底里。我说你是歇斯底里的。事情或者会很不一样,如果你和我没有在咖啡馆邂逅,那1936年。

1936年,你在巴黎。你睡得不好,你辗转反侧——你的祖国西班牙发生内战。左派政党组织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成立共和国政府,致力民主改革。另一边,军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得到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发动武装叛乱,反共和国政府。1937年4月26日正午,在位处西班牙北部巴斯克的一个城镇格尔尼卡的市集上,人熙来攘往,平和地、如常地。倏地,纳粹德国空军从上空轰炸。三个多小时后,格尔尼卡一片瓦砾,一片火海。超过一千六百名平民百姓被杀,大部分都是妇女、孩子、年老的人。佛朗哥否认这场轰炸是他所为。
是的,你辗转反侧——你远在巴黎——即便你在西班牙,你什么也做不了。但,你是画家,你可以画。知道了这个悲惨的消息后,你返回工作室,你站在画布前,思量——早在1937年初,你接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创作一件壁画放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展出——你叹息思量,你仰天,或低下头。痛而无以能够言语。这以后的两个月,六个星期,四十多个日与夜,你画。《格尔尼卡》(Guernica)完成。

《格尔尼卡》——高3.5米,宽7.8米——马。牛。女子。人子。孩子。头和手和脚。马,嘶鸣。母亲拥着孩子,无泪。人子躺卧。肢体,支离破碎。肉身的,移位。断裂。张开的口。张开的眼。张开的手。伸出的手指。没有能够反抗。没有希望。没有握紧的拳头。来不及的张望或愤怒。手执的花。死亡。痛与折腾。
万籁无声。有声。无深度的空间。黑色的大地与天。
我知道《格尔尼卡》。你想画一幅敞大的作品放到博览会的时候,我给你找来古老大屋内的一个空置空间作为工作室;你想画有关格尔尼卡的时候,我在你身边——我把你绘画的过程拍摄下来。的确,绘画和摄影,从来没有如此这般亲近紧密过。你说:摄影要记录的不是不同的绘画阶段,而是其中的变化。这样,人大抵可以明了画家的思想历程是如何体现梦想的。
有关《格尔尼卡》,当代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这样写道:毕加索并没有尝试想象真实的情况。是的,画面上没有跟格尔尼卡一丝直接的关系——无城市的楼房、无轰炸机、无爆炸的迹象、无年月日时间的所指。是的,你不在场。你的画,不具体,不明了,没有直指。但你感觉到痛,你画。如此,你在场。伯格继续写道:画是一个抗议——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人们并不知晓这段历史。可不是吗,一切都是有关战争暴力——马、牛、女子、人子、孩子、头和手和脚。扭曲。形象化的文化符号,人共通的图画语言。寓言一则。完全的黑与白和灰。痛。身体反抗的呐喊。直接不直接,具体不具体,《格尔尼卡》已然是个宣言。是的,这是你的个人宣言。个人的、政治的、也是集体的。有关反战,有关和平。那画,可以触动人,让人感受那触动。
在黑色大地与天的寓言下,人想象有关痛。巴黎世界博览会后,《格尔尼卡》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巡回展出。你和你的作品,让人瞩目。当然,相对你最初在巴黎的时候,一切都在混沌中。
是的,你第一次来到巴黎——那是1900年的秋天。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你参与展出作品。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你看过了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画家们的画作。第二年,你再到巴黎,画商安博洛伊斯·沃拉德为你举办个展。我听说,展出的六十多幅作品全部卖出。人都说你的风格,噫,怎么说呢,是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和文森特·梵高和皮埃尔·博纳尔等的糅合。是的,你可以绘画这种风格,你可以创造这种形式。你的技巧不容置疑。我知道,你十分敬重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你曾经模拟德拉克洛瓦的画,又模拟对他说:“你从对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学习中,成就你自己;如此,我从对你的模仿中,而练就我。”马克斯·雅各布曾形容:毕加索有许多故意的模仿;如此确定他不会制造无心的模仿。我听说,你跟雅各布先生处不来。当然那是较晚的事。事实上,他是你在巴黎结识的第一位法国朋友。
几年下来,你在巴黎跟巴塞罗那之间往返。1904年,你定居巴黎——人说这是你的“蓝色时期”(Blue Period)——你住在蒙马特拉维尼昂十三街一座建筑物“洗衣坊”(Le Bateau-Lavoir):老旧破烂肮脏湿冷,无电和煤的供应,没有自来水或排厕设备,乞丐妓女老弱妇孺外国的本地的年轻的画家作家诗人们。穷困呀——是的,曾经,在寒冷中,你要燃烧你的画取得些许温暖——这,怎不让人抑郁郁结。蓝色:年轻人、多愁善感。是的,颜色,从来都懂得说话。而你,你懂得挑色。你减少用色褪去不必要的色彩。简化了的颜色、简化了的线条形体把重量压下来,让位给忧悒。当大家都在谈论野兽派如何从后印象主义中以自发随意的表现形式去追求色彩解放的时候,你挑一种颜色,你绘画。你的画显得特立独行。
当然,你的蓝色时期很快过去。在你的立体主义将要到来以前,你遇到年轻美丽的情人,你把贫穷痛苦的议题挪到一旁。你画当时流行的马戏团表演。你的色彩转向赭色、粉红色,即所谓“玫瑰时期”(Rose Period)。你的人物造型开始简化,趋向几何。这在你绘画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肖像上,显而易见。我听说,在差不多八十多次的写生后,你把先前绘画斯泰因的人像涂改了——最后,她的脸庞看来有点怪异,像纸版或木雕般的一只硬生生面具。我听说,没有人喜欢这画,除了你和斯泰因。的确,斯泰因欣赏你的才华。她不断购买你的画:当我看一幅画,我的手心冒汗,我的心跳加速,我的呼吸显得深沉;我知道,这是一件艺术作品。她这样说。
1907年,你完成了《阿维尼翁少女》(The Young Ladies of Avignon)。我听说,最初的草图是这样的:五个裸体女子,一个男子手执一个骷髅头,一个学生,和在前景的一些静物。这不难让人联想到保罗·塞尚的《浴女》(The Bathers)或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Luncheon on the Grass)。你或从过去传统的母题上找寻现代的寓意。你画人物造型,你的人物形体开始变形如块状或立方体,这你大抵从埃尔·格列柯或保罗·高更或亨利·马蒂斯那里吸取了养分。我听说,马蒂斯先生把非洲雕塑介绍给你。每天,他来回到工作室绘画人体素描的路上,会经过一条摆卖古玩旧物的店铺。那里,他看到一些古怪的雕塑。也大抵在这个时候,你看到了伊比利亚人头像和一些非洲雕塑。这些既简单又几何的立体造型,对你的视觉不无冲击。



无论如何,你的作品在变化中。一切都在变化中。慢慢地,然后是急遽地:没有了背景风景,没有了花草树木,前景和后景的内容混在一起,交错糅合,没有景深不讲求透视,细节取消了,人物形象变得线性、几何、块状、比例不均,赭红和灰绿的平涂,没有技巧的明暗过渡。最后,剩下五个裸体畸形女子,或挂着异国土著民族面具式的脸。你的画看来不完整未完成似的,粗糙笨拙。
按你后来的话说:画,一切破坏的总和。的确,在惯常的绘画形式上,你演绎了不平常,一切都像是意外或改变。你不断地破坏——直至东西内容变得似是而非——你要拆解形体的状态,你想发现形体潜藏的可能性。你的破坏,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大抵又要算到保罗·塞尚的头上来。1907年,被形容为“现代绘画之父” (Father of Modern Art)的塞尚的大型回顾展在巴黎举行。塞尚重视绘画对象的结构造型,他强调物的重量,即物看来如圆柱体、球体、圆锥体等形状,他提出要把前后空间物的外部轮廓联系起来。如果说塞尚在20世纪以前的(平面)绘画尝试表现(立体)雕塑,你从他的感悟中找到启发,你把他开拓的问题梳理:你把自文艺复兴几百年下来的传统绘画标准的透视法,彻底地,切断了。
完成后的《阿维尼翁少女》,一直放在蒙马特山上的工作室,不曾展出。你的朋友们斯泰因或马蒂斯或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或乔治·布拉克都来看过——别扭、新奇——大家都在疑惑:你在自我摧毁,你的技巧、你的天才哪里去了。你画下了许多叫人费解的问题。新的艺术语言,新的美学观点,非一般的眼界,你叫人细味可能的隐喻与诗意。但,当时无人明白这画,无人能为它定义。谁人先把这形容为立体主义——斯泰因说很可能是阿波利奈尔;有人说是画商丹尼尔-亨利·卡思维勒。立体主义的雏形风格被公开认识,亦有说是布拉克的画:他看过你的《阿维尼翁少女》后不无启发。在他其后的一个展览上,曾把马蒂斯等画家形容为野兽的艺术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就嘲讽说:布拉克的风景画充满着细小的立方体。的确,布拉克明白你,立体主义大抵是你和布拉克的奋斗路,而且是在一起最亲密的奋斗路。布拉克曾经形容:两个拴在一起的攀山者。拴在一起的亲密、或紧张,我懂。
1900年,你第一次来到巴黎。1904年,你在巴黎定居下来。1912年,你离开蒙马特山,你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往南走,一直走到蒙帕纳斯。之后,你迁住到巴黎时尚区。其后,你再往外走。1934年以后,你没有再回过老家西班牙。你流放在外。你自动流放。是的,你爱巴黎,你接纳巴黎。巴黎接纳你,巴黎爱你。你在巴黎成就了自己,巴黎成就了毕加索。
是的,一切都是因为巴黎。一切都在巴黎。是的,你在蒙马特和蒙帕纳斯的历史任务大致完成。是的,蒙马特和蒙帕纳斯为你提供的历史空间也过渡完了。

拴在一起的,紧张、或亲密,但,终究要分离。谁可以想象你在巴黎认识的第一位朋友,指导你学习法文的诗人画家雅各布其后跟你处不来;谁可以想象在立体主义奋斗路上,相互亲密交流的布拉克最后跟你分道扬镳;谁可以想象常跟你谈论作品的斯泰因其后不再碰头见面;而你的好朋友阿波利奈尔在一次大战负伤后因西班牙流感而死亡。是的,朋友,亲密、疏远、死亡。你有很多朋友,你有很多爱你的人。你和他/她或她和他在小街小巷楼梯斜坡咖啡馆小餐厅工作室交流,喝酒瞎扯,高谈阔论,笑,唱歌,喊叫。快乐和不快乐,贫穷或忧伤,期盼和努力,失意与竞争。最后,都停下来了。一切都静下来了。最后,你一个人。你变得巨大。你剩下画。伯格说:毕加索的名字大于他的艺术。人们记得毕加索的作品因为人们记得毕加索。
你寂寞,也许。你没有对手,你显得很不耐烦,你只好不停地创作。伯格曾形容你的成功、你的富裕像能够点石成金的米达斯。你可以用一幅画换法国南部一间海边屋。你在餐纸上不经意的几笔涂鸦会被人趋之若鹜地拿去拍卖。但,吃进肚里去的是金,大抵是悲哀。是的,你画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你也造了很多很不好的画。美国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说,不是因为毕加索变得肤浅或敷衍了事;相反,多年来,你已经不再信任自己的熟练和敏捷,你想要避开一切暗示这些东西存在的物事,你让你的画显得怪僻和笨拙。只可惜,有时候,真的显得笨拙乖张。是的,你曾停滞不前,你不无缺点,也许。但,你仍是人们崇拜的毕加索。
而我跟你,也分离了。是的,人们知道毕加索。人们明白《阿维尼翁少女》,人们记得《格尔尼卡》,那都是你重要的作品。人们也记得你重要的作品有很多的朵拉,朵拉和猫,很别扭爱哭的朵拉。人们大概知道朵拉是你的情人,很多情人中的一个。虽然我想别的人记得我:一个摄影师,一个诗人,一位超现实主义的实践者。是的,我知道,在毕加索之后,我有上帝。或者,的确,或者,你曾经就是我的上帝。
你的
朵拉
毕加索回信
亲爱的朵拉:
当然你是很会哭的。我也记得:你是我的缪斯、超现实主义的实践者、诗人、摄影师。是的,绘画和摄影,从来没有如此这般亲近紧密过——那《格尔尼卡》,那在巴黎的一切——久远的记忆,曾经的梦想的体现。我的历史已然成为了一份记忆。虽然一直以来,有些人把它看作神话。也许,人真的需要神话。
巴勃罗
书摘部分节选自《美好年代:写给艺术家的21封信》,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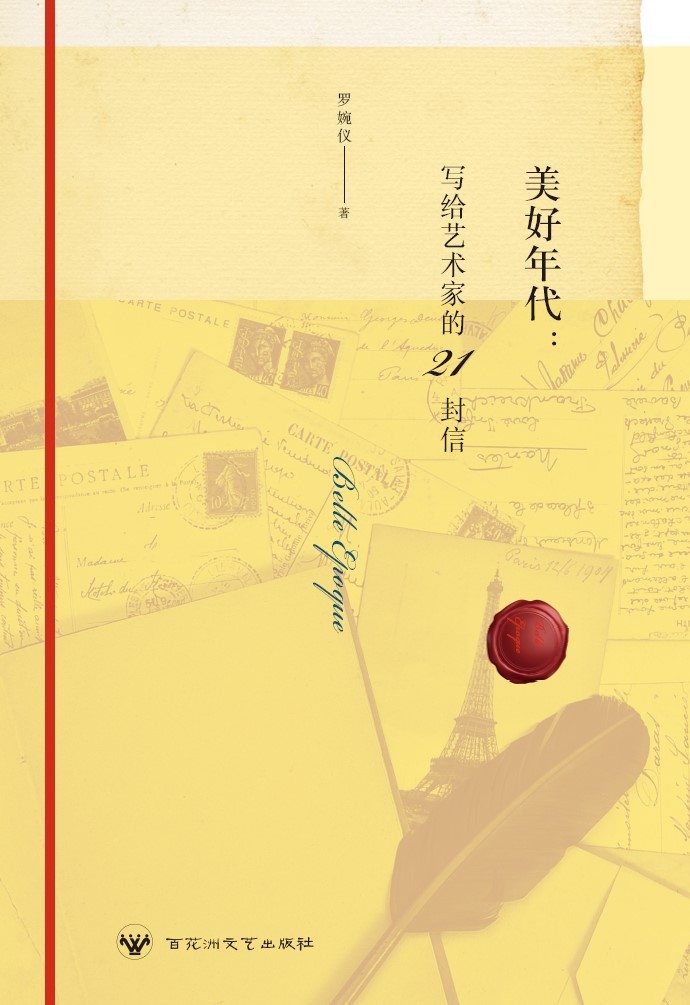
铁葫芦图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04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