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机会,你最想问王小波一个什么问题?"昨日有人这样问李银河,她回答说,早上她去给小波扫墓的时候,有很多粉丝在他的墓前放了鲜花、二锅头或者烟,有一个人放了一篇王小波的文字,一只蝴蝶就一直贴在上面,她很好奇,最近有些物理学家在讲,人死后可能是有灵魂的,只不过是去了另一重宇宙。所以如果有机会,她想问问王小波:你的灵魂还在不在?
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无数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浪漫骑士”和“自由思想者”。而上述的这一幕,就发生在李银河与《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导演程耳举行的一场对谈上,他们对谈的题目是“今天我们如何阅读王小波”。活动开始时,大屏幕上播放了一段李银河读王小波所译情诗、回忆王小波与自己的往事的视频,看着屏幕的李银河不知不觉神色有些忧伤,又带着温情。
二十年过去了,程耳觉得王小波的作品依然像新的一样,令人耳目一新。“王小波的小说,跟当时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对话,他就是写人性本身。”李银河说,而王小波的杂文,“讨论的问题还没有过时,甚至好多地方有退步,所以我觉得他之所以还那么有影响,也跟到现在他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有关系,所以他的杂文还是有生命力的。”

他的幽默和荒诞使他腾空而起,俯视着时代
程耳阅读王小波最大的观感是,他的作品“抵御了时间”,二十多年过去了,依然让人读起来耳目一新。之所以这样,程耳认为,是因为“他的渗透到思想、语言和叙事里的自由,他的冷静和深情,以及他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价值,他的幽默和他的荒诞使他腾空而起,时至今日,他依然俯视着我们今天的时代。”
以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为例,虽然描写同样的时代和同样题材的小说有很多,但程耳认为王小波与同样表达那一时代的所有小说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他没有把着重点放在任何我们已知的对于那个时代特别表面化,或者是今天看来特别陈腐的东西上,王小波新的视角的起点在于,他在他的人物和环境之间,人物和时代之间,找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平衡点,他似乎站在更加宏观、更加俯视的角度看待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里发生的所有事件。”

譬如,在《黄金时代》里,王小波几乎没有写过王二穿什么样的衣服,程耳认为,因为王小波意识到服装是一个年代最表层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即使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写海鹰穿的军装,也是为了写这身军装把她的身体染上了颜色,最终还是回到身体本身。“小波的小说,去除了这些表面化的、风一刮就能吹走的最表层的时代精神,他直面身体,只有这样才能刺穿皮囊直达肌肤。”无论是《黄金时代》,还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程耳发现,在里面王二从来没有抱怨过,甚至他是快活的。他没有把那个时代像像通常描绘的那样黑压压的一片,没有去描写人山人海的情况,大家穿着什么样的军装,如何斗争,而是选取回到个人命运本身,回到“王陈二犯”两个人的感情纠葛上去诉说这个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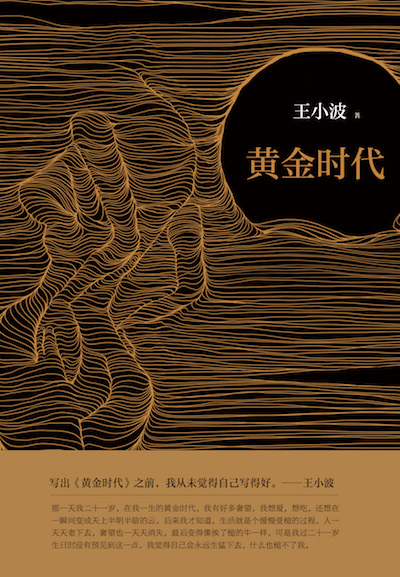
程耳形容王小波是“冷静的深情”,这种文字的冷静是中国文学最近十几年才开始在审美上注意到的,而王小波的冷静又搭配着他的深情。另一方面,是王小波的幽默和荒诞使他“腾空而起,时至今日还在俯视着我们今天的时代”。程耳说自己读王小波常常读着读着就笑起来,有时会哈哈大笑,“这种幽默才是渗透到一种文明或者是一个创作者身上最不可取代、也是最难实现的高度,无论描写苦难也好,快乐也好,他始终是非常幽默、嘲讽的一种心态”。
谈起王小波的小说,李银河说自己只能谈“一点点作为文学业余爱好者的感想”。她觉得王小波的小说跟以前的小说都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是,在中国,文学一直都是政治批判的对象,或者政治解放的号角,从来不是纯文学的。即使是王朔,也还是在解构之前的意识形态,但是王小波的小说,是跟那套意识形态完全不对话,“他在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应该在哪个阵营,或者他应该写红色的东西还是写黑色的东西,他就是写人性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纯文学。”李银河觉得,真正的好作家一定要写永恒的主题,就是人性,人性中的爱与死,所有超越了时代和国家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那样才能真正的成为经典。
王小波不是中文系出身,而是学理工的,读的是人民大学商品系食品专业,李银河回忆,王小波经常要品尝食品,有一回他们要品尝香肠,大家都带点酒配着品尝。“人要是真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话,脑子里的那些条条框框就会多了。”王小波写作从来不曾受到专业训练的限制,借用荣格的理论,所有的艺术家只是一个工具,是艺术品自己压抑不住要爆发出来,艺术家作为它的手写下来,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文学吧,李银河认为王小波即是这样的作家。
至于王小波的幽默,李银河也是深有体会,她在前不久重看了一遍王小波的《2015》,狂笑了七八次,险些哮喘复发。“王小波的幽默是一种真正的幽默,而不是现在那种无厘头、搞笑。他有一种幽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也是非常喜欢。”

王小波是一个极度悲观的人
尽管程耳认为王小波的小说里没有对时代的抱怨,但他依然认为,王小波是一个极度悲观的人,只有一个极度悲观的人才会没有抱怨,才会是快活的。李银河也同意,她一点都不觉得王小波是个乐观的人,在他的小说中曾写道,“我只能强忍着绝望活下去”。
在生活中,李银河可能比王小波更加悲观,她从二十多岁就被存在主义哲学吸引,认为人就是宇宙的微尘,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把这一点参透之后,可以选择出家这样彻底的悲观,也可以选择乐观。李银河与王小波谈恋爱时常常谈论悲观主义的话题,但王小波不太愿意谈论这些,在一封给李银河的信里王小波写道:“你谈到幽冥的问题,最后一切都要消失,人生最后也是烟消云散,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但是在消失之前我们要让一切先发生。”
所以李银河说,她和王小波两个人恰恰是“参透之后的乐观主义”,“选择的是能够在自己生命存在的这三万多天里,尽量地满足所有的欲望,去非常快乐的,尤其是感受一种狂喜。”
拿两个人的爱情来说,李银河觉得爱情中的激情往往在开始时迸发出来,像火一样,但一旦建立亲密关系,激情会变成柔情,火会变成水,但王小波和李银河两个人始终保持着激情之爱。“激情之爱是那种真正发生了浪漫的,像火一样的感觉,作为一个女人来说,能成为激情之爱的导火索,是很难得、很幸运的。这个激情之爱因我而起,我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会有这种感觉,这个是挺好的感觉。”
回忆与王小波的相处,李银河觉得两个人没有什么艰难的磨合过程,几句话就能感觉心灵的合拍。李银河第一次对王小波感到投契,是读到王小波小说《绿毛水怪》的手抄本,其中写到王小波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篇小说的感受,李银河恰好也刚刚读过那篇小说,立刻感到对那本书的理解有心灵上的投契。后来两个人约会时,在北海的山上,王小波第一次把手搭在李银河肩上,“我全身都绷紧了,因为还很陌生,但是那一天我们拉钩了,即使我们俩成不了夫妻,我们也是终身的朋友,这是我们当时的约定,我们约定要做一个终身的朋友。”

王小波写“性”是在表达一种反抗
大量关于“性”的描写是王小波小说一个明显的特征,《黄金时代》在台湾联合报文学奖评审时,就因此而有过争议。1995年《黄金时代》第一个版本在国内出版,曾经有过一次讨论这本书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评论家白烨说,王小波写的性一出来,把以前所有的写性的全毙了。
李银河说,王小波的想法是“性既然存在在那儿,我们为什么不能写”,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可以写呢?“我觉得小波的性,尤其从《黄金时代》里可以看出来,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是一种反抗,那是一个那么不自由的时代,那么压抑的时代,性这么个人的东西都被压抑得那么深重,所以对性的描写和对性的表达本身,实际上是在伸张人性,伸张周围环境对性的压抑、对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压抑。”
程耳说自己非常喜欢王小波对性的表现,“我觉得三句话不离裤裆,是非常靠谱的,绝大多数的好的作品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性,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创作要么在描写性,要么在暗示性”。

当被问到王小波在国外的影响,李银河回忆了一下,到目前为止王小波只有一个英文译本叫《Wang’s love in bandage》(《束缚中的王的爱情》),收录了几个王小波的几个中短篇,此外还有法文、日文、韩文版的《黄金时代》,总体来说国外对王小波还是比较隔膜的。但这天早上李银河去为王小波扫墓的时候,《纽约时报》特意去跟拍和采访,李银河想可能他们也觉得王小波提出的很多问题依然有意义。
李银河觉得王小波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是一个纯文学的作家,另一方面他的杂文表达了一种比较古典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立场。“我觉得也挺可悲的,”李银河说,“在30年前这些东西就很热,到现在还是问题,他讨论的问题还没有过时,甚至好多地方有退步,就比如说他所提出来的最基本的一些人的权利人的尊严,所以我觉得他之所以还那么有影响,也跟到现在他的理想,中国整个制度或者是文化上面,很多最基本的价值还没有实现有关系,所以他的杂文还是有生命力的。”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