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据《卫报》报道,秘鲁-西班牙双国籍作家、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于当地时间4月13日逝世,享年89岁。
略萨与中国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略萨凭借长篇小说《城市与狗》跻身拉美文坛,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一道,成为“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2010年,因“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他获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次年即2011年,75岁的略萨曾经访问中国。在上海的一场活动上,跟略萨对话的作家叶兆言称自己“上台后大脑就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说自己把准备好的提问和发言遗失在了来上海的火车上。叶兆言后来撰文,“拉美文学的爆炸,影响了世界。我们是被影响的一部分,我们是被炸,心甘情愿地被狂轰滥炸,因为这个,我们应该表示感激之情。”
在北京的活动上,阎连科则提及,得知他要见略萨,有15个美女给他打电话要向这位“最老的帅哥”致意,而他三年前就为这次会面准备好了西服,结果最后还是没穿上,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莫言称自己是略萨的书迷,有一回,读《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时,看得很开心,笑到打滚。莫言的妻子抢过书一看,扉页上的略萨英俊潇洒,“又看了我一眼,带着无穷遗憾的表情,扬长而去,晚饭都不做了。”

1994年,略萨就曾经来到过中国,坚持“以一个纯粹的旅游观光者的身份,来细细品味中国古老文明的风情韵致”。当时,最早把略萨作品译介成汉语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赵德明(2025年4月3日逝世)正在翻译作家的回忆录《水中鱼》,略萨在北京王府饭店与他见面,并就某些疑问和原版中的笔误现场进行了解答和修订。

赵德明曾用“自由主义到了令人讨厌的程度”来形容他心中的略萨,略萨的精力相当旺盛,对世界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许多问题都很感兴趣并心怀关切,“一会儿天、一会儿地,巴西的问题、凯尔特的问题、高更的问题,哪儿的手都伸”。他对中国的变化也非常感兴趣。略萨的另一位译者尹承东曾经表示,略萨“对中国政治改革方面的进展、人民的生活及社会福利的改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到了2011年,北京的发展变化让略萨感到非常震惊。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告诉界面文化,当时邀请略萨访华,过程很艰难,因为他曾经在诺奖获奖言说中“大放厥词”,有人甚至给外交部写信表示反对此次行程,但陈众议还是坚持住了,目的是必须让略萨亲身了解中国,否则一些成见很难消除。略萨虽然此前已经来过中国,但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有限,其信息大多数都是从西方媒体获取的。“实地走一走,接触中国人,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触。”陈众议对界面文化回忆起当时开车载着略萨在北京转了两圈的情景,略萨不断感叹:“我上次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啊,北京现在怎么这么多的高楼!”“这里怎么变成这样了啊?”
略萨与文学
略萨于1936年出生于秘鲁南部城市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但10岁时父亲的突然出现不仅生生地葬送了他的美好童年,而且不久即用几近强制的方式将他送进了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1963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小说情节取材于作者在军事学院的亲身经历,在这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唯一的法则。作品对复杂文学技巧的娴熟运用给评论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部小说对秘鲁军事当局的尖锐批评却引发了争议,出版不久就在秘鲁被禁。当时的军政府在略萨母校烧掉了1500册《城市与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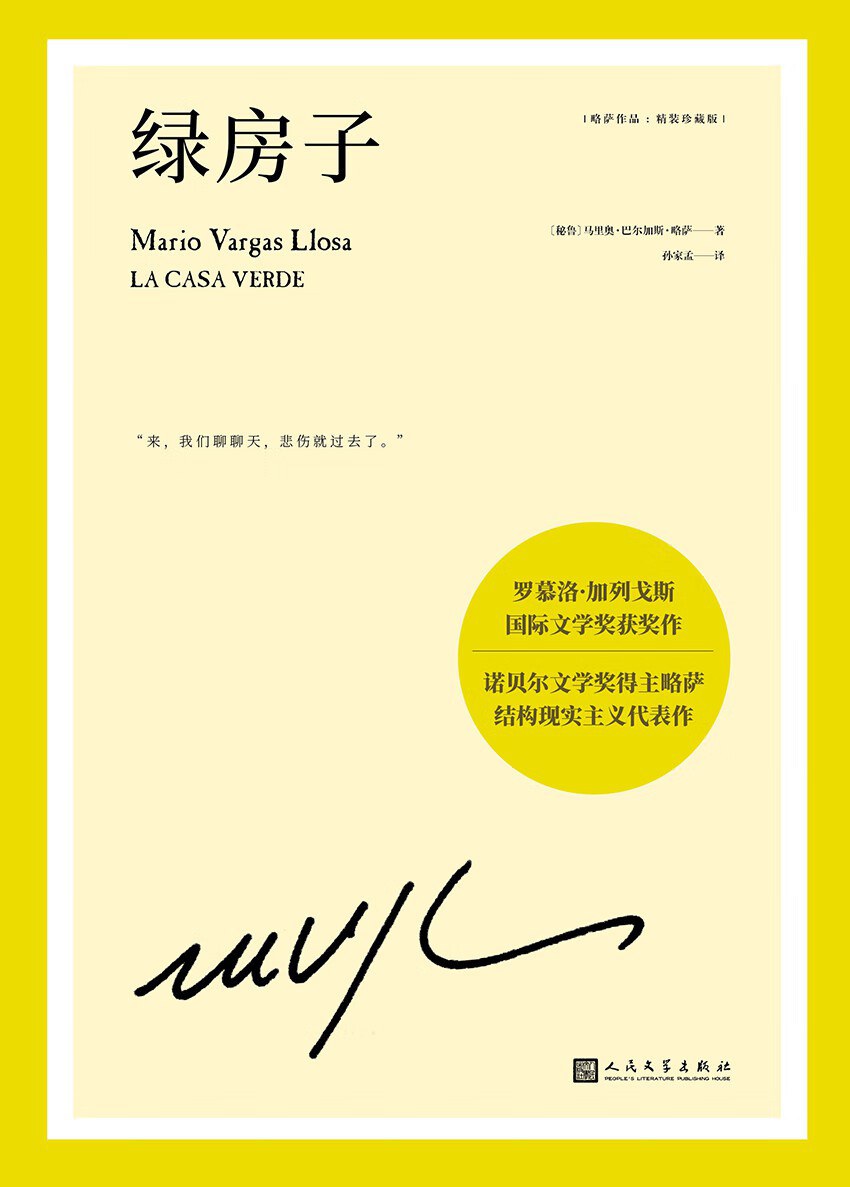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8
他的第二部小说《绿房子》讲述了一个名为“绿房子”的妓院,即将接受教会誓言的女孩转变为“绿房子”中最著名的妓女的故事。小说一经问世便广受好评,确立了略萨作为拉丁美洲叙事中重要声音的地位。
在中国,当被问及哪一部作品是自己的代表作时,略萨表示,“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每个作家都像喜欢孩子一样喜欢自己的作品。”但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略萨的选择是《酒吧长谈》。他说,因为当时费了很大力气写成,希望通过写作表现当时的环境,描写专制政权如何让社会腐朽不堪。这部作品写的是1948至1956年曼努埃尔·阿波利纳里奥·奥德利亚军事独裁统治期间的秘鲁社会现实。
“略萨有政治情怀,但他没有让政治观点湮没作品的文学性,他让书中的每个人物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但他自己不做评判,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在与略萨对对谈上,莫言这样评论道。
“这是作家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而且不容易找到答案。文学可以把政治当作一种手段,但政治不应该把文学当作一种手段。当时在拉美,有很多人写小说揭露政府腐败、军队独裁,他们在政治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最后成为喊口号的宣传品,并没有达到文学的高度。”略萨则回应称,“作家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人,他们应该离具体的政治问题稍远一些。”
略萨与政治
略萨在文学创作之外,还一度从政,他在大学时期短期加入过秘鲁共产党,早期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但后来他逐渐失去信心并谴责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他在1980年代后期担任了数年当时新组建的政党“自由民主阵营”的主席。
1976年在墨西哥城发生了一起著名事件,略萨殴打了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他嘲笑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妓女”。这场争斗究竟是因为政治原因还是个人纠纷,这一点尚且是个谜团,因为两位作家都不愿公开讨论此事。
1989年,略萨曾参与竞选秘鲁总统,并一度是声望最高的候选人。与后来获胜的藤森一起进入第二轮角逐,但最后败给了藤森。竞选失败后,他应聘客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并在那里完成了回忆录《水中鱼》,其中讲述了他于1987年至1990年期间的政治活动。
对此,赵德明曾经表示,“略萨幸亏竞选总统失败,否则世界将会失去一个优秀的文学大师。”陈众议也说过,“2010年宣布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是高兴的。上世纪90年代要把这个奖项颁给他,我会遗憾。那时候他的创作略显私人化,可能与他政治抱负未能实现有关。”陈众议看到,略萨的文学特征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结构现实主义先锋,热衷于宏大叙事,并坚持为民族、为种族代言。第二阶段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略萨曾在后现代思潮的裹挟下“淡化”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批判色彩,在90年代一头扎进“小我”而不能自拔,创作了他和前妻胡利娅姨妈的故事《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以及两部性心理小说,但略萨也很快调整了姿态,在世纪之交回到了富有现实意义的宏大叙事。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11
“获诺贝尔奖一周是童话,一年是噩梦。你无法想象接受采访、参加书展的压力有多大。第一年非常艰难。我几乎写不下去了。” 他曾这样对《卫报》说。后来,他又开始写作。2013年出版《凯尔特人之梦》,2016年出版《五个街角》。 略萨于2023年出版《我向他致以沉默》(Le Dedico Mi Silencio),此后透露将停止小说创作,而将主要精力转向文学评论。
陈众议说,他和略萨的最后一次交往就是他给略萨写信,让他警惕疫情期间西方舆论的操纵。后来,略萨对此事没有进行进一步发言,“不折腾”了。
参考资料:
广州日报《译者谈略萨:幸亏竞选总统失败 他比马尔克斯潇洒》
中国青年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我在虚构中讲述现实》
京华时报《略萨:文学要离具体问题远一些》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