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在劳动节来临之际,你有思考过自己的工作吗?比如在工作中你是否有成就感?你的工作是否还顺利?如果你觉得自己在工作中的感受还不错,或许意味着你是职场上的“幸运儿”。从德勤发布的《2024年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来看,职业倦怠是一种普遍现象,48%的员工和53%的管理人员表示,他们在工作中感到筋疲力尽。
在下面这份关于工作的书单中,不同的作者都指出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如今工作几乎成了自我发展和获得尊重与满足感的唯一途径,但是,由于利润动机驱使着企业的运作,生产力的重担落在了员工身上,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员工的时间进行严格掌控。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的推动下,人们产生对消费品的无限渴望,也宁愿不去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闲暇。
这些作者也给出了提升职场工作满意度的一大指标:掌控度。这意味着能自主决定做什么事,能获得支持去做这件事,工作中拥有掌控力,能够使人持续保持热情。
《星期五不上班》

拜德雅·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3
对于马克思来说,雇佣式就业中,利润逻辑塑造着所有必须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的生活。故而“从根本上说,就业与个人自由相对立:它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将自己出租给某个人或某个公司”。

本书作者看到,马克思经常用讽刺的意味提及“自由(free)劳工”。一方面,人是自由(free)的,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选择把自己卖给任何雇主;另一方面,人也是一无所有的(free of things),因为不占据生产资料,除了工作能力,几乎什么都不拥有。但是这两件事都不等同于自由。真正的自由,作者指出,是“将我们的时间用在我们愿意做的事情上的自由”。
工人要求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远离工作;与此相反,企业则施加压力,要求延长工作时间,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劳动力。大厂计算员工的如厕时间早已不是新闻。本书作者看到,这并不是“坏老板”和“摸鱼人”之间的对立,因为这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者恶意,而是源自“利润驱动体系下,对时间进行严格掌控的结构性压力与员工拒绝被掌控的强烈愿望之间的矛盾”。由于利润动机驱使着企业的运作,生产力的重担就落在了员工身上——每一分钟,都承载着更大利润的承诺。
“这就是我们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频繁的职业倦怠以及没有工作却又需要工作才能生存的痛苦背后无法回避的真相。”作者写道。
《在工作中迷失:逃离资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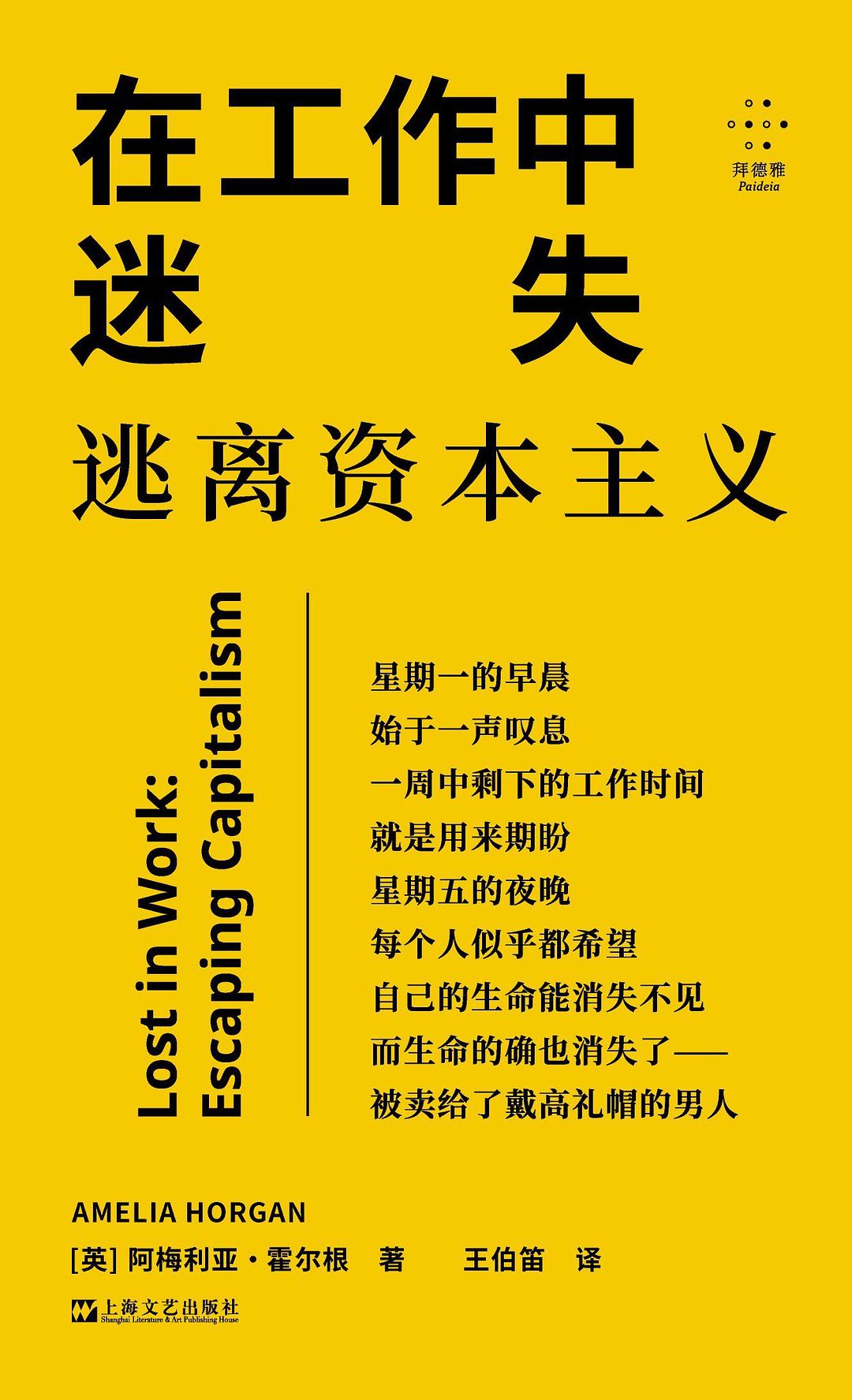
拜德雅·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3
《喜人奇妙夜》中,土豆、吕严的《抽屉里的猫》讽刺了企业与员工之间权力失衡的现象。豆啦B梦穿越到当下,发现打工人生活艰辛,决定用道具改变现状。他掏出了规则指定器:“所有的企业不得加班,加班必须有加班费,不准无缘无故辞退任何一个员工。年末必须有年假,还有奖金。”
然而,这个世界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吕严提醒他:“会不会是因为劳动法里已经有了你说的那些。”
于是,豆啦B梦又掏出移动式监督天平——有了它所有的企业都必须遵守这些规定。“这个就是劳动仲裁委员会吧。”吕严吐槽道。
豆啦B梦不解地问:“你们怎么啥都有,但是不遵守?”
一些企业不遵守劳动法的背后,是劳动者的愿意屈就。埃塞克斯大学哲学讲师阿梅利亚·霍尔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雇主有两种管理员工的方式,一是雇主群体对生活的间接控制——除非极其富有,否则我们需要工作。由于劳动力市场没有办法为求职者提供足够多的体面工作,悲剧也由此产生:对工作的高需求,使得工人愿意屈就,这严重削弱了人们为工资、权益和工作质量等问题挺身而出的意愿和力度。
第二种控制体现在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工作条件。霍尔根谈到,工作中拥有掌控力牵涉的不仅是对日常工作环境的掌控,还包括降低甚至消除员工(基本没有掌控力)、经理(被授予某种程度的日常权力)和老板(对工作环境拥有远多于其他人的权力)之间的权力差异。劳动分工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因为有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值得被尊敬和获得尊严。进行所谓的“低级”工作的人,不仅被当成工具对待,而且这种工具性及其附带的低声下气都证实了他们低下的地位。
但是,这不仅仅是垃圾工作和好工作获取途径分配不公的问题。就连在更有保障、更长久且薪水更高的工作中,劳动者同样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霍尔根看到,掌控力的缺失,是导致痛苦乃至健康问题的元凶。“和热情最相关的权力不是管理他人的权力,而是自主权。人们说’权力是春药’,这只看到了控制他人的权力,却没有看到’自我决定’的权力。能自主决定做什么事,能获得支持去做这件事,是人能够保持热情的原因。”《不再踏入流量的河》中,作者凡之昂这样写道。在现实状况中,职场的权力等级中,作为执行者,劳动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克服困难,为什么要保持增长,也无法对要做的事情拥有最终决定权。
可是,劳动者还是必须工作,因为工作几乎成了自我发展和获得尊重与满足感的唯一途径,失去工作还会带来失去自我的恐惧。在当代生活中,公共生活的概念几乎和参与雇佣工作同义,这让人很难想象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超越纯粹个人的孤立存在。全职工作通常只允许人们在有限的空间培养其他兴趣、技能和社交关系,从而使人们缺乏工作以外的个人和社会资源。
《对工作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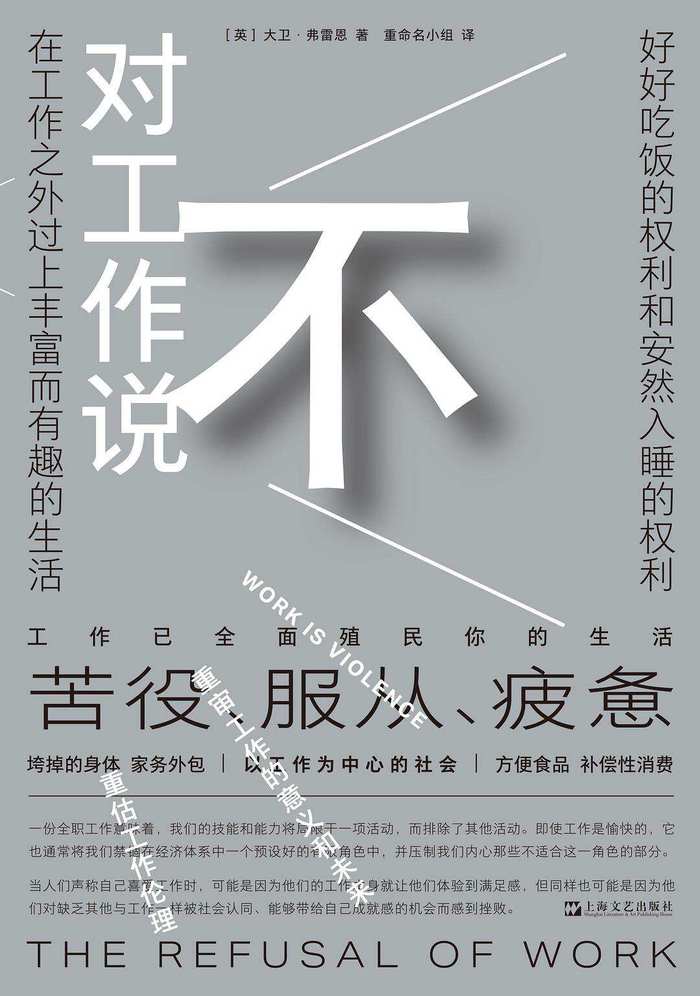
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3
虽然没有人强迫我们工作,然而,社会结构决定了我们必须工作,没有工作的人生极端困难,富人除外。《对工作说不》的作者卡迪夫大学社会学教师与研究员大卫·弗雷恩提出,有偿就业在殖民和统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设想,到2030年,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福祉,把我们引领到一片“经济乐土”。然而,随着这一切的发展,人类并没有从工作需求中解放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用后即弃的消费品被制造和分销出来,大量可疑的、从前并不需要的工作任务又随之被制造出来。闲暇被尽可能地转化和服务于消费。
弗雷恩看到,消费习惯的很大一部分,是劳动异化的产物,因为工作消耗了时间和精力,人们不得不用极其狭窄的技能谋生,这样,人们也会购买节约时间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说吃外卖、请家政工去“购买”更多的自由时间。同时,劳动的异化也促成了消费的需求,因为工作之艰难需要安慰和补偿,消费品中的奢华、逃避和转移注意力,可以帮助人们填补空虚。
人们宁愿不去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闲暇,而是渴望更多的消费、拥有更多的东西。这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是一个旨在产生需求,而不是一劳永逸地满足需求的系统。资本主义的利益相关者推动一种“越多越好”的风气,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在阻止人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感到满意,而是使得人们变得贪得无厌,产生对消费品的无限渴望。
如果说工作显得严肃、僵硬,下班后是否就能满血复活?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闲时间,仅有的空闲时间也会变得紧张和令人焦虑,甚至会让人带着效率感进行休闲,也就是说,让人们努力从少量的空闲时间中,去获取最大的乐趣。这样,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从工作中恢复、补偿工作的痛苦,或者做许多必要的事情去寻找、准备和持续工作。人们当下的许多活动,似乎都是为了保证当下和未来的生存,而不是因为这些活动本身具备价值。
《不再踏入流量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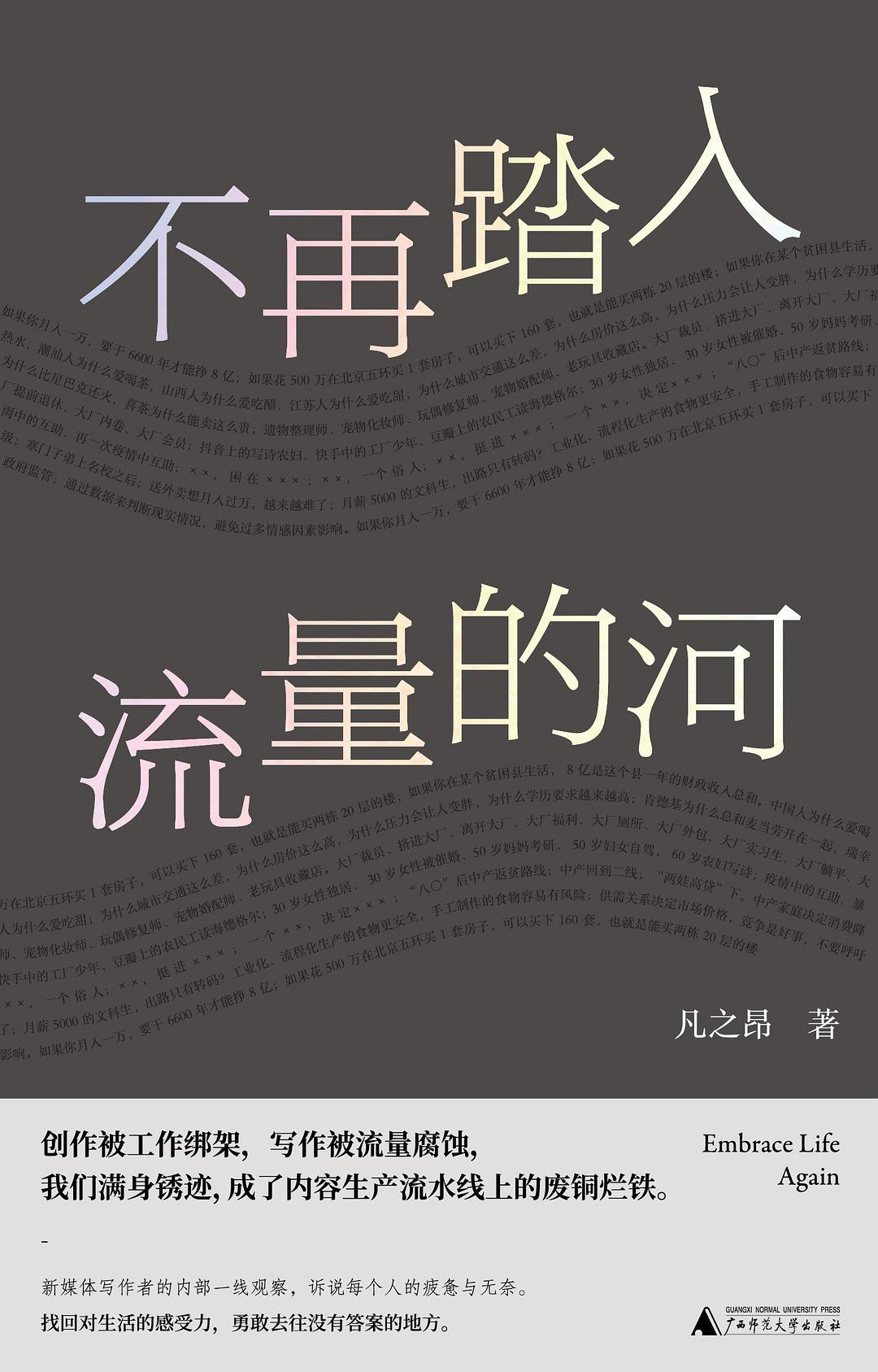
望mounta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2
在当今的社会中,也有人对以工作为中心的现状保持批判态度。
为什么会有人选择不上班?对于阿梅利亚·霍尔根来说,人们在“真受不了”的那一刻,就会选择爆发——可能是上司提出的羞辱性要求;可能是迟到之类的小错误招来的无情斥责;可能是突然醒悟虽然自己的劳动让公司获利颇丰,却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简而言之,就是“个人体验与深层结构和社会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变得清晰明朗的那一刻”。
对于大卫·弗雷恩来说,人们减少工作时间或者完全放弃工作,并不是出于粗暴的反工作道德观,恰恰相反,是出于想要做更多事情的愿望。“意义和自主性的缺乏会主张反抗的渴望”,而雇佣工作这样的功能性社会角色永远不可能与被迫身处其中的复杂、立体的人等同,所以,总是会有一部分自我溢出社会角色,并且希望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体会过吸引人而且有意义的活动的某种理想模式,一个人才会感受到异化的痛苦。因为异化会剥夺人继续体验上述理想模式的机会。还有对一些人来说,抵制工作更接近一种必需,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他们拒绝为就业牺牲身体。基于以上三点,大卫·弗雷恩看到,抵制工作的人通常会有三种路线:垃圾工作、迷你乌托邦和搞坏的身体。
在《不再踏入流量的河》中,凡之昂就大致经历过这三种路线。她发现,新媒体文章需要制造爆款,“作为写作者,我一方面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在由自己的大脑自动生成乏味重复、却看似幽默的句子。另一方面又是这套体系的传承者,教新来的作者如何快速写稿,如何识别什么样的文章最可能成为爆款,如何规避那些热门选题。”凡之昂一边相信数据和方法,认为这些稿件可以带来流量,一边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不满意也没有热情。当写作变成了可以批量化、工业化生产的,工作也就成为了“垃圾工作”。
刚进入某新媒体公司时,凡之昂和同事们还拥有主动创造的热情,她形容自己“满怀希望和憧憬”,想要创作一些“严谨、有知识、有趣”的工作内容,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阅读书籍、文献、学习新领域的知识。然而,在KPI的强压之下,内容本身已经不是目的,营收变成了唯一目的。劳动者也无暇思考什么内容是好内容,只能不断去满足一个个明确而急迫的KPI,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开始不对工作中的任何事物投入热情,只是以最敷衍的方式完成工作。领导也躺平了,这意味这他们不再用自己的思考、智慧或者人格魅力让团队工作更高效,只是借用管理工具,让自己从管理者变成了节点监测员,就这样,过去的创作氛围不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凡之昂发现自己的情绪出了问题,写新媒体文章时,她不可抑制地产生了自我厌恶感,只要一想到办公室就会哭,一看到手机消息就会烦躁。真实的身体反应让她坚定了离开的信念。她不断地追问,赚钱的意义是什么?为了买东西,赚钱买了东西,买完就会快乐吗?为了孩子,孩子是真的需要钱,还是我们以为他们需要?不断地追问下去,就可以发现,工作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甚至赚钱也没有。她看到,“生活的意义跟那些我们能自由支配时间时选择做的事情有关。”不再工作之后,她接触的不再是隐身的读者和抽象的阅读量,而是和具体的、生活中的人产生关联,做了很多公益和义务劳动,她感到,“这些劳动给了我比写新媒体文章高得多的价值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