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铁卢?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为什么到2017年还需要一本新的历史?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更有意思的是,《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的作者伯纳德·康沃尔,前言里首先回答的也是这个问题。
在历史上的战役里,滑铁卢无疑是最时髦的:文学巨匠雨果——这个拿破仑大军团的军二代,在《悲惨世界》里离题万里地去描写滑铁卢大战、拉海圣的争夺战、莫斯科亲王和近卫军骑兵在圣约翰山的突击、老近卫军的慷慨赴死;司汤达这个拿破仑的老兵,在《巴马修道院》里描绘了滑铁卢战场上传来的隆隆炮声;司汤达描述的炮声对夏多布里昂来说肯定不陌生,他是拿破仑送进法兰西学院的诗人,那时却跟随路易十八的宫廷逃亡,在前往布鲁塞尔的路上,他听到从远方战场传来的如同夏日闷雷般的炮声;在他骑马经过的地方,一个英国人正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战场的消息,消息传来,他马上飞奔到海峡乘坐最快的船赶回伦敦,利用时间差捞到了拿破仑战争里的最后一桶金,这个人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支系的创始人。
滑铁卢战役太重要了,以至于关于它的一切都被人铭记并反复提到。战场上的统帅自不待言,拿破仑在滑铁卢以前很久就已经被神化了,滑铁卢是他巨人生涯的最后谢幕;而威灵顿这个仿佛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打碎拿破仑神话的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也成了传奇;抱怨威灵顿行动迟缓的普鲁士元帅格奈森诺;被威灵顿抱怨姗姗来迟但终究还是赶到了战场的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被拿破仑反复催促但最终还是没赶到战场的法国元帅格鲁希;走向滑铁卢战场的道路上的连日阴雨;滑铁卢会战当天的“奥斯特里茨的阳光”;关于这场战役的一切都名垂史册。从政治史到外交史,从传记到回忆录,从绘画到文学,滑铁卢无所不在,甚至连《魂断蓝桥》里费雯丽寻短见的大桥都叫“滑铁卢大桥”。
那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时隔两百年的今天,再去读一本关于滑铁卢战役的书,再去关注滑铁卢战役。作者从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按下不表。在此笔者要从另一个角度——文化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谈一谈为什么我们应该关注滑铁卢战役。

对我们读者而言,历史就像风景,距离越远细节就越模糊,但“主题”或者说“戏剧性”也就越突出,所以历史越悠久,距离我们越远,“伟大的英雄”也就越多。这种英雄是古典史诗式的英雄,他们要么是从天而降的;即使不是从天而降也是天降大任的,虽然在生命的开端,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这种“天命”,但命运会引领他们走上一条追求荣誉、伟业和权力的闪光道路,他们在前进中展现出自己的天赋、力量和个性,伟业成就后,最终迎来悲剧般的结局。这种题材构成了我们熟悉的那种古典和中世纪的史诗,从特洛伊到迦太基,从诸神的黄昏到英灵殿,从熙德(注: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 1043年-1099年,人称熙德El Cid,卡斯提尔贵族,瓦伦西亚的征服者和城主,西班牙民族英雄。)到唐克雷德(塔索的史诗《耶路撒冷的解放》里的英雄,陷入对穆斯林女骑士的爱而迷失了方向),而拿破仑的生平则是这条英雄的、半神人的系谱的最后一页,离我们最近的一页。
这个矮个子科西嘉人从土伦闪亮登场,打到伦巴第,打到埃及,在金字塔下、在红海边、在布伦大营眺望不列颠,然后风驰电掣地跨过欧洲在乌尔姆打败奥地利,在奥斯特里茨的阳光下打败沙皇,在耶拿打败骄傲的普鲁士,一路前进直到莫斯科,然后形势急转直下,在莱比锡战败于团结起来的整个欧洲,最终在1814年被迫退位,被贬为厄尔巴岛上的国王。但拿破仑的史诗在《告别鹰旗》之后还没有完,就在那一年,他率领一千人在法国登陆,然后一路高歌猛进,“衔着三色旗的雄鹰从一个钟楼飞到另一个钟楼,最终在巴黎圣母院降落”,奇迹般地凭借一己之力征服法国,然后率领他的军队向准备四路入侵的敌人进攻,最终在滑铁卢战役功败垂成,黯然离去魂归大西洋。这是拿破仑生平的史诗版本。在这个版本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传统的英雄,一个赫拉克勒斯式的英雄、一个超越了血肉之躯的大理石浮雕般的英雄,其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于被距离湮没的细节。我们知道凯撒曾经放浪形骸,被高利贷的债主围追堵截,但我们不了解细节;我们知道奥古斯都也有一个疯狂的早年,但我们依然不知道细节;我们知道凯撒跨过卢比孔河时说“骰子已经投下”,但我们不知道他沿着大道奔向罗马的时候有没有后悔。那些古代的英雄生命里大部分的色彩和经历已经被历史掩盖,他们脱离了他们的舞台被写进史诗,失去了血肉和温度,变成了浮雕和铜像。甚至连史诗本身也可能是一种误解,爱伦坡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史诗,相反只是一系列的抒情诗和短史被叠加在一起成了史诗。
但是拿破仑距离我们并不远——这正是拿破仑的奇特之处,在近代的历史上史诗式的英雄已经不多见了,整个十八世纪可能只有俄国的彼得一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越过了“英雄”与“史诗般的英雄”间的鸿沟,前者是因为俄国当时还偏处欧洲的边缘,人们并不了解这个国家和这个人,所以给了文人更大的发挥空间;后者则自己就是一个文人,了解文人的方法和趣味,投其所好才取得如此成就。那么拿破仑呢?拿破仑在一个疯狂的年代登场。在文化上,此时的欧洲被庞贝城的发现所带来的复古热潮推至疯狂;而政治上,革命与共和国成了文化上复古潮流的原动力。这是一个在18世纪末的巴黎召开元老院会议的年代,这是一个18世纪末的元老院议员在自己时髦的礼服外边扣上更时髦的罗马托加袍的年代。整个欧洲都被史诗般的热忱所激动,而拿破仑在这个时代横空出世,以惊人的速度爬上社会的金字塔,同时作为一个军事家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在政治上用法国革命的理想满足欧洲的文人,用法国的武力降服欧洲的君王,奇迹般地征服了欧洲人的心灵。彼得一世无意中越过的、腓特烈二世小心翼翼地越过的那条鸿沟,被拿破仑昂首阔步地跨过了,并成了历史上最后一个跨过去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滑铁卢战役永远不会被我们遗忘,因为它是一个分水岭,拿破仑和他所代表的那个史诗般的英雄梦想,如同雷霆一般席卷而来,想要越过“圣约翰山”,莫斯科亲王内伊和他麾下的近卫骑兵,就像是这个巨人的拳头,带着他的咆哮挥舞过来,但功败垂成。1815年聚集在“山的另一边”的那些人,无论是高地步兵还是苏格兰灰衣骑兵,还有他们的统帅威灵顿公爵,并不是另一个这样的英雄——相反他们是一群普通人,威灵顿不喜欢战争,不喜欢杀戮和伤亡,他会紧张,也会恐惧,会抱怨“时针缓慢到肉眼无法辨别的程度”,支撑着他的是意志和责任,而不是对这些疯狂行为的爱。他不会沉醉在战争里,这把他和拿破仑区别开来。

这是一场小人物和伟大英雄的战争,1814年聚集在维也纳的那些欧洲最有权势的人,英国的卡斯尔雷、俄国充满理想但是意志薄弱的沙皇亚历山大、普鲁士严肃方正到缺乏生气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和他同样缺乏特色但是勤劳肯干的首相哈登堡,再加上两个公认的“连基本的道德品质都不具备”的伟大政治家,奥地利皇帝风趣幽默、通达明哲的机会主义宰相梅特涅,更加通达明哲、更加风趣幽默、红透维也纳半边天的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瘸子塔列朗。他们也都不是拿破仑那样的英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连成为英雄的想法都没有。这些聚集在维也纳,原本吵成一团的人听说拿破仑回到巴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团结起来准备开战!他们把英、普、俄、奥四强国的四十万大军送上战场的时候,并没有改变世界的念头,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理想,相反他们只想结束之前二十二年里的史诗故事,并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发生。
经过这决定性的一天,当硝烟散去,一个时代永远地结束了。诸神谢幕,而“我们”——普通人登场,史诗隐去而历史随之而来。这是对1815年发生在滑铁卢战场上的事件的概括,而滑铁卢战役本身也是19世纪的一个缩影:19世纪是普通人的时代和英雄的时代的分水岭,而滑铁卢战役是19世纪和18世纪的分水岭。从时间上说,19世纪从1801年就开始了,但是从1801年到1815年,这十几年完全是18世纪的延续,拿破仑的时代横亘在两个世纪之间,就好像贵族的时代横亘在19和20世纪之间。1801年已经到来,但是19世纪尚未苏醒,19世纪的历史还没有展开,它所有的主题都在幕后等待,等待着滑铁卢的炮声,那炮声就是夏多布里昂、罗斯柴尔德远远的听到的炮声,他们属于19世纪,那是他们登场的信号。
1815年滑铁卢战役让拿破仑的形象隐去,新时代随之到来:这是专业化和进步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军队的组织和装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义务兵役制原本是革命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帝国为了对抗联合起来的欧洲而搞出来的制度。1815年以后各国纷纷恢复了传统的募兵制,只有弱小的普鲁士犹豫再三,最终引入了这种拿破仑式的制度。普鲁士的这支义务兵组成的军队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连续战胜了奥地利和法国的职业军队,迫使奥法两国相继引入义务兵役制。
1841年普鲁士军队又率先采用了后膛枪,后膛装弹的步枪大幅度提高了步枪的发射速度,也改变了步兵战术。在滑铁卢战场上,虽然训练有素的英国步兵发挥了惊人的火力,但是战役的决定性武器依然是刺刀,双方排成方队或更为密集纵队的步兵,互相用步枪齐射之后,就高举上刺刀的步枪冲锋是整个拿破仑时代的步兵基本战术。但是后膛枪让“火力”取代了刺刀,1866年普奥战争中,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采取了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式的刺刀冲锋战术,但是联军的进攻被普鲁士步兵的“弹雨”扫荡,很快被遏制和击退。在交战之后不久,写给皇后“茜茜公主”的信中,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描述了普鲁士手中“可怕的步枪”和步枪造成的惊人杀戮。步枪之外是弹簧和液压制退复进系统的引入,大幅度提高了火炮的发射速度,滑铁卢战场上双方炮兵一天发射的炮弹数,可能被新式火炮在一个小时里打完。快速射击的枪炮制造了威力惊人的火力网,但是也制造了惊人的弹药消耗。在滑铁卢战役里,双方军队所携带的弹药车已经庞大到惊人的程度,125000法军和350门大炮所需要的弹药车已经让滑铁卢战场的交通不堪重负,所以当法军最终溃败时,这些被胡乱停在路上的弹药车彻底堵塞了道路,以至于拿破仑皇帝的座车,还有车上的私人物品,包括拿破仑所有的勋章,都被抛弃在战场上,成为联军的战利品。而滑铁卢的弹药消耗量只是未来战争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唯一可能的解决途径是铁路,英国人史蒂芬森在1814年发明的蒸汽机车,在1830年代传到欧洲大陆,1863年的丹麦战争中,丹麦军队还完全没有考虑使用铁路,在撤退中丹麦军队沿着铁路徒步行军;但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就开始使用铁路运输部队和军需;1870年战争中更是利用铁路快速集结了一支惊人规模的军队投入到法国边境。宣战之际被临时通知向部队报到的后备军人,由于通过铁路运输,反而比法国的职业军队集结得还快,这个奇迹宣告了铁路时代的降临,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指挥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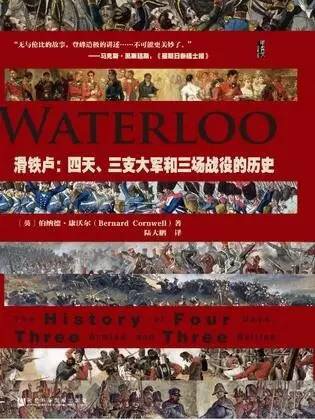
(英)伯纳德·康沃尔/著 陆大鹏/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月
在整个拿破仑的战争生涯里,拿破仑几乎是独自一人统帅着他的“大军团”。伟大的法国参谋长“纳夏泰尔和瓦格拉姆亲王”贝尔蒂埃更多地扮演得是一个伟大的秘书的角色,他能够理解拿破仑的意图,并把拿破仑简短的只言片语变成详尽准确的命令,而很少有失误,拿破仑在滑铁卢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贝尔蒂埃不在他身边(随同路易十八出逃的贝尔蒂埃在滑铁卢之战前的6月1日,在班贝格坠楼身亡)。但在没有拿破仑式英雄的普鲁士,格奈森诺和沙恩霍斯特将军设计了集体领导的参谋制度。普鲁士军人试图以各司其职的专业化来战胜拿破仑的天才,这种制度在滑铁卢战争中并没有表现出它的优越性,但在军队高速膨胀、后勤困难暴涨、动员极其复杂但又必须追求速度的19世纪终于取得了成功。滑铁卢战役以后不到一百年的坦南堡战役里,战役的主角已经从统帅拿破仑和蹩脚的参谋长苏尔特,变成了天才的作战处长霍夫曼上校和总揽全局的参谋长鲁登道夫。旋风般席卷一切,摧毁一切的英雄消失了。滑铁卢之后是芸芸众生的历史,创造出十九世纪的奇迹的是这些紧密合作的普通人,毁灭这个世界的依然是这些紧密合作的普通人。
这就是为什么2017年我们仍然应该关注滑铁卢战役,应该抽时间一览康沃尔绘制的这幅浓墨重彩的全景画,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后滑铁卢的时代里,生活在进步和专业化的时代,是这个分工与合作的社会里的一员。我们之前的那个时代在1815年的那个六月,在圣约翰山前,以一种最戏剧性、最英雄气概的方式告别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滑铁卢战役,如果拿破仑和他的帝国、他的大军团在1812年卫国战争、1813年莱比锡战役,或者以1814年退位的方式离去,它都无法成为一个时代的终结,无法成为一个分水岭。那条在普通人和史诗英雄之间的鸿沟上搭建的桥梁以一种最绚丽的方式坍塌了,拿破仑这个来自科西嘉的炮兵军官,兄弟姐妹一大堆、而且异常抱团的凤凰男,成了最后一个越过它的人,他站在鸿沟的那边作为“不朽者”向我们鞠躬谢幕。而通过康沃尔的这本书,我们饱览他的告别演出,并默默地挥挥手,告别那个已经不属于我们时代的英雄梦。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