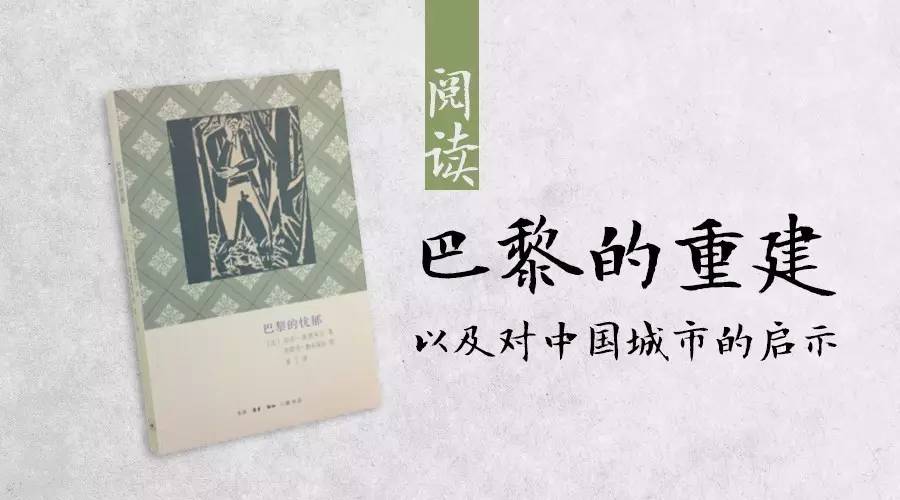
作者:叶然(方塘书社主笔)
1、文人笔下的巴黎
城市面貌改变的速度快过人心。
这是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用来形容十九世纪时期的巴黎的一句话。波德莱尔没有预料到,在今天,这句话竟成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城市的现状。
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是忧郁的,一定不是今天人们眼中的浪漫之都。这是他在《巴黎的忧郁》的著作中对巴黎的定义。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定义,正是因为当时的巴黎正处在拿破仑当政,巴黎城市大改造时期:传统与现代性之都的冲撞,乡村与城市鸿沟的不断扩大,无权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的“城市中心地盘”的抢占,消费服务城市与居住、生活城市的竞争,等等。
城市是为了人的居住和生活而存在。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是动荡时期的巴黎,所以它没有生活,而是政权与财富的角力场所,那时的文化场域亦没有明确的文化体系的承载。
如果说波德莱尔是为了抒情于巴黎这座城市而存在的,那么巴尔扎克甚至福楼拜则是为了批判甚至有着挽留传统巴黎痕迹而存在。在众多真正了解巴尔扎克的读者眼中,会看到,他是将巴黎这座城市的历史地理与城市空间关系综合的相当完美的一位作家,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足以证明。在他披露巴黎真相的笔下,“巴尔扎克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细致地解开并表述了随时随地充满于资产阶级社会子宫中的社会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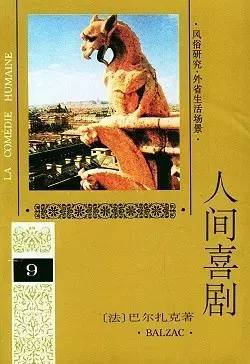
“创造性破坏”的城市建设,是巴黎这座城市逃不脱的宿命。
空间在时间里流动。一战之后,现代性已经成型的巴黎出现在海明威笔下,他长期旅居巴黎的经验几乎统统集结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中。这本书延续至今,成了人们造访、体验、了解甚至邂逅巴黎的必读读本,也成了历史地理的范本之一。
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在恐怖袭击地点上,人们将这本书放在该处,不只是为了怀旧和缅怀已逝的人,更多的是为了表达巴黎一直以来的和平、包容和自由。
海明威笔下的巴黎,咖啡馆遍布大街小巷,酒吧、书店以及大型的广场随便到一处地方就可见。它们出现在巴黎这座城市,于人们而言是一种需求,也是一种生活状态的呈现。而这种状态不论是对本地人还是像海明威这样的旅居客人来说,都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
在之后,海明威将这样的感受写进书信中:“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你今后一生中去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这一席浪漫而又庄重的盛宴,不只是人对所渴求的生活状态的向往,也是对巴黎文化的一种柔软的表达:巴黎是浪漫的,城市空间是流动的,又是充满人间烟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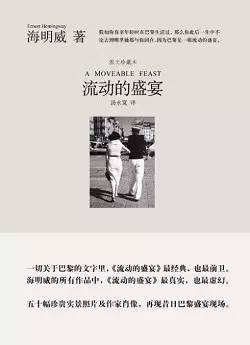
就连时间进入到二十世纪,来自日本的时装设计师山本耀司在提到巴黎这座城市时,也在兴奋地表达:法国尤其巴黎,它具有深刻的艺术理解能力和高于其他国家的文化鉴赏水准,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只要有才华就会被认可和接纳。在山本耀司这里,巴黎真真切切地成为了一座包容度非常强的城市。
海明威笔下所描述的巴黎流动的城市空间,除了这种文化上的包容,已经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也在透露出巴黎功能的另一面:现代性之都——巴黎,它正逐渐成为一种消费服务城市。不论是空间里的大型广场、咖啡馆、酒吧、书店,它们都是消费和服务功能的体现。
从使用功能上看,它们的确存在的合理,但城市还有另外最重要的功能:人们居住的场所。这虽然已是陈词滥调,但往往总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功能。城市居住功能的实现,更应该是一种城市诉求,它包括对权利的诉求,平等的诉求,等等。一座城市的存在状态有时会表达出这座城市的民主与自由化的程度,贫富差距,更代表了包容性。
正如同时期,奥威尔的自传体处女作《巴黎伦敦落魄记》所描述的巴黎一样。他用漂流的生活方式揭露了生活在巴黎贫民窟,底层阶级的人们的生活现状的另一面。试图表达的是,虽然政府给这里的人提供了非常可观的福利以及有爱的照顾,但这依然不能解决他们长期的生活,他们依然无家可归,失业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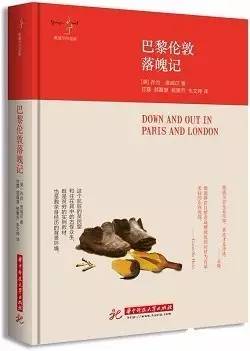
是的,巴黎政府解决了资产阶级人的生活,却始终无法解决穷人的生活,以致巴黎的贫富差距在资本主义背景下,越拉越大。
2、大革命不是城市的宿命
从事不同职业的人都在讲巴黎和它的不同阶段,然而,因为巴黎历史的复杂性,注定了这座城不好讲,从任何单一的方面讲,都是狭隘的,也是不好从巴黎的经验里来借鉴的。
人们习惯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个阶段来对比中国城市和社会的整个现状,也讲述巴黎,而且根据不同的人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来寻找两者的相似之处。其实,这并不能寻到问题的根本,也不能简单地将结果看作问题得以解决的成果。
更多的人试图根据这段历史来解读造成这场革命的根由。在很多人眼中,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贫困造成的,尤其是在旧制度背景下,因为农民长期以来的生活压迫而产生的,而且在同样对大革命进行解读的《乌合之众》中,也没有忽略这一原因。
事实上,其原因并非只是简单的贫困造成的,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就已对此给出了解释。当时的法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其经济已经相当繁荣,农民的权利也比类似德国这样的依然实施农奴制的农民更加自由,包括对土地的使用和支配权。纵使农民感到压迫,在当时的经济繁荣时期,也只是极有可能发生骚乱的社会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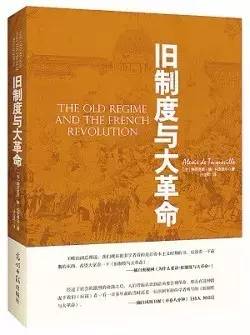
所以,从这点来说,革命的发生的确与贫困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并不是主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革命的发生?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认为,究其原因是贵族的没落而导致的官僚腐败。
贵族的没落与腐化,让底层的人看不到国家和城市发展的未来。而且,在这样上层官僚阶级的腐化背景下,官民之间会发生脱节,财政管理当中,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从未像此时这么联系紧密过。
对此,作者托克维尔总结到: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刻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由此,一场大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正因为这场革命,让当时正在逃难的拿破仑登上了皇位。事实上,当时大部分的人对拿破仑当上皇帝后,会把巴黎建成具体的什么样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是,这场长期的、折磨人的大革命该结束了。在《巴黎城记》中,作者大卫·哈维如是说。
大革命并不是包括中国城市在内的城市的宿命,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就可以放松警惕。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曾倾力推荐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还是从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3、巴黎现代之都的建设
大卫·哈维对巴黎的描述与上面提到的所有文人、作家笔下的法国、巴黎有所不同。如果说讲述巴黎的存在状态以及人们生活的状态,其行家是作家,那么解析一座城市是如何在城建过程中运转的,便需要用另外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当然,两者之间也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划定。
在众多对拿破仑当政时期的巴黎重建的描述中,与大卫·哈维有着相同叙述的还有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本雅明的巴黎史是一种美学,大卫·哈维在对此加以补充的同时,也论述其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范本。但我想,他们都在试图描述一个新的巴黎史:一个新的城市空间和现代之都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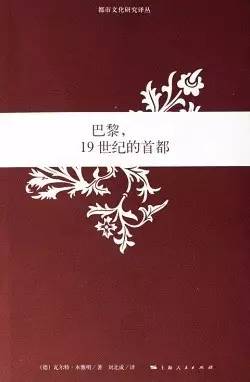
大卫·哈维以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讲述巴黎,其所借助的便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事实上,马克思起初是以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关注世界的,但后来,马克思走上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道路。他认为,解释世界,并不能改变世界,若改变世界,便需要将其放在生产关系和一个经济形态上来看。而大卫·哈维则正是受到了马克思这种思想的影响。
大革命是巴黎现代之都建设的一个节点。大革命结束后,成为新一代执政人的拿破仑开始了巴黎重建的宏大计划,而这个宏大计划的执行人便是奥斯曼。还在任省长的奥斯曼接到命令,便开始了对巴黎实施大改造的计划。
奥斯曼试图将巴黎建成一个全新的、与过去完全割裂的现代之都,让一个新的城市空间横空出世。而这时,便有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它的巴黎大改造计划也被人认为是一种痛苦的“创造性破坏”。
事实上,一座城市的历史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与过去完全割裂是不现实的,也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言的:看似是为了推翻过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城市,其实过去的东西依然会一直存在。
所以,奥斯曼在巴黎大改造后,也被迫下台。当然这并不能说,奥斯曼对这座城市没有贡献。他是今天的巴黎现代性的开端,也在那一时期解决了很多工人阶级的就业问题。
大革命之后,很多乡村里的人簇拥着来到巴黎寻找生计,同时,生在巴黎的工人阶级也已经陷入水深火热当中。而这时,若要解决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本的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所以巴黎大改造计划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而若想要巴黎的重建得以顺利进行,还需要资金以及保障资金的流动性。奥斯曼出于对资金流通的考虑,便开始了将土地兜售给房地产开发商的行为。在资本主义背景下,信贷是土地的基础,然后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而所有的经济活动又将带动金融(资金、价值)的流动性。

不仅对奥斯曼,对很多人来说,若想要发展城市,以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保障金融的流通性必然是第一位。金融若失去了流通性,价值就无法转换,价值无法转换,经济就无法运转,新的价值就无法产生,进而社会也无法正常发展。反复循环,最终就会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发生,意味着就业问题,以及城市发展停滞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所以,奥斯曼在一开始就想到了没有资金流动带来的后果。而这一政策的实施,直接的受益者就成了资产阶级。最终,便造成了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
同时,奥斯曼一直希望将巴黎建成一座现代性之都,这也就意味着巴黎将变成一座消费服务城市,实体制造业将陷入危机。当时的很多制造工厂最后相继被迫搬迁至郊外。此时的巴黎中心真正地成为了一座以金融流通为核心的城市,也成了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又一原因。
大卫·哈维对奥斯曼的这一巴黎改造的行为并没有给予过多的批判,但在他的《叛逆的城市》当中提到了一点:奥斯曼对巴黎重建的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在实施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另一条道路:类似凯恩斯体制的城市建设。凯恩斯体制主要以债务融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而达到解决剩余资本的出路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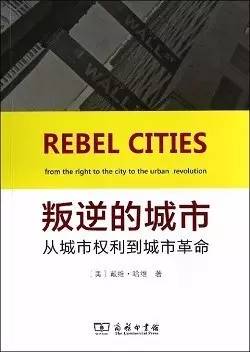
而奥斯曼采取的这一体制,的确解决了以上提到的剩余资本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巴黎重新定义了一个全新的城市人格,从此巴黎的面貌也就成了波德莱尔笔下的样子。
正如大卫·哈维所说的那样:巴黎的城市基础得到了改善,也建立起了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巴黎从此也就真正地成为了一座以消费、娱乐、时装为主的“不夜城”,以吸收庞大的盈余。
这样的巴黎虽不能完全摆脱传统,但也的确与传统产生了强烈的撕扯感,工人虽然一直在为他们的中心城市而争取权利,但最终依然被排斥在中心城市之外。最终,因为过度的消费扩张以及一直以来的具有投机性的金融和信贷制度,最终在1868年,奥斯曼被迫下台。而具有资本主义史的巴黎公社便于此时爆发。
人们怀念被奥斯曼摧毁的那座巴黎,这也是巴黎公社爆发的原因之一。拿破仑和奥斯曼的宏大计划在当时受到众多人的反对,托克维尔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因为他受不了拿破仑的执政方式,才有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诞生。
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天巴黎现代性之都的存在,的确有奥斯曼的功劳。对于一座城市的现代性,我觉得,现代性并不是一定不如传统。只是,在走向现代化生活模式的过程中,能够将其所具有的最先进和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最大程度地介绍给世界,才是关键,也是张扬国家“文化力”的核心,而不是低俗与低价值,以及简单的经济形态的城市。
4、对中国城市的启示
其实,看到这里不难发现,暂且不提社会发展模式,只是就城市发展的模式而言,今天的中国城市在走向城镇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奥斯曼时期的巴黎都非常相似。一如大卫·哈维在《叛逆的城市》中提到的,中国从一开始,便走向了同样的凯恩斯体制的城市发展模式。
而之于这样的城市,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如何避免奥斯曼结果的重演,便需要思考中国城市的未来到底该是如何的。大卫·哈维以巴黎为例,对此给出了解释: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
大卫·哈维提到的城市权利,实则是一种集体权利,以这种权利强行推行城镇化建设。这其中的意思之一是,在过去,城市发展通常采取的是资本手段,而这最终造成的便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上面提到的日益投机性的金融和信贷的崩塌。在其看来,这种集体权利也只能属于资产阶级的集体权利,对建立一个城市资源共享和城市共同体无疑是一种阻碍,更是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没有益处,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这时,大卫·哈维所提出的改革方向是:反资本主义,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的过渡。肆虐的资本主义开发逐渐摧毁了传统城市,过度积累的资本推动着不顾社会、环境和政治后果,无休止蔓延的城市增长,以至于城市本身也成为了受害者。
而将正常运转的城市,从城市权利逐渐以城市革命的方式来完成城市的转型并非易事,但也不是无计可施、没有希望可期待。
既然,大卫·哈维提出反资本主义的城市革命,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要努力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城市和城市共同体。所谓的资源共享并不是像空气这样的共有资源,共同体也不是简单的组合成为一个共同体。
人们通常会将一座城市视为独立的个体,无视其他周围城市的存在,以至于该城市里的产业也是孤立的。这并不是好事,那么此时,就需要转变这种观念。一个独立的城市品牌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这种品牌一直保持独立,不与其他城市和资源往来,也会造成品牌资源的浪费。
对于贫困的解决,大卫·哈维则提出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方向:将类似贫民窟这样的地方,引向旅游。但是,这样的旅游并不是基于山清水秀资源的旅游,而是以目标人群为主要资源。这样的人本身具有很浓的生活气息,而将这样的生活气息合理地引向旅游,对一座城市来说,也有了新的价值。
将城市建设成更符合人们心愿的城市,是人们普遍期待的权利,也是城市革命的最终归宿。巴黎这座城市不好讲,事实上,所有城市都不好讲,因为一百个城市有一百个样子,而不是千篇一律。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