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小木匠 编审 | 了想

大家都知道,续集不好拍(本片是前传),也不好写。像《绣春刀》这样的古装电影,在视觉上,感知上是新鲜的,这种新鲜在第一部已经看过了,在第二部能不能更新鲜?第一部上映时,观众对于路阳、陈舒这样年轻的创作者是非常的善意,其中也包含着鼓励。到了第二部,观众的宽容和鼓励还会继续吗?
对于以上这两点,编剧坦言,压力很大,为什么第二部写那么长的时间,因为一直在改。改什么?之前传言的四版剧本吗?远不止如此。
《绣春刀II:修罗战场》编剧兼导演路阳提到,和编剧陈舒、禹扬三人已经形成了很稳固的搭档关系,这种合作是一种缘分,有着难得的默契。陈舒表示只有路阳才会让自己写武侠电影,而和真正懂编剧的导演一起合作,共同进步,绝对是一种幸运。
专访《绣春刀II:修罗战场》
编剧兼导演路阳、编剧陈舒、禹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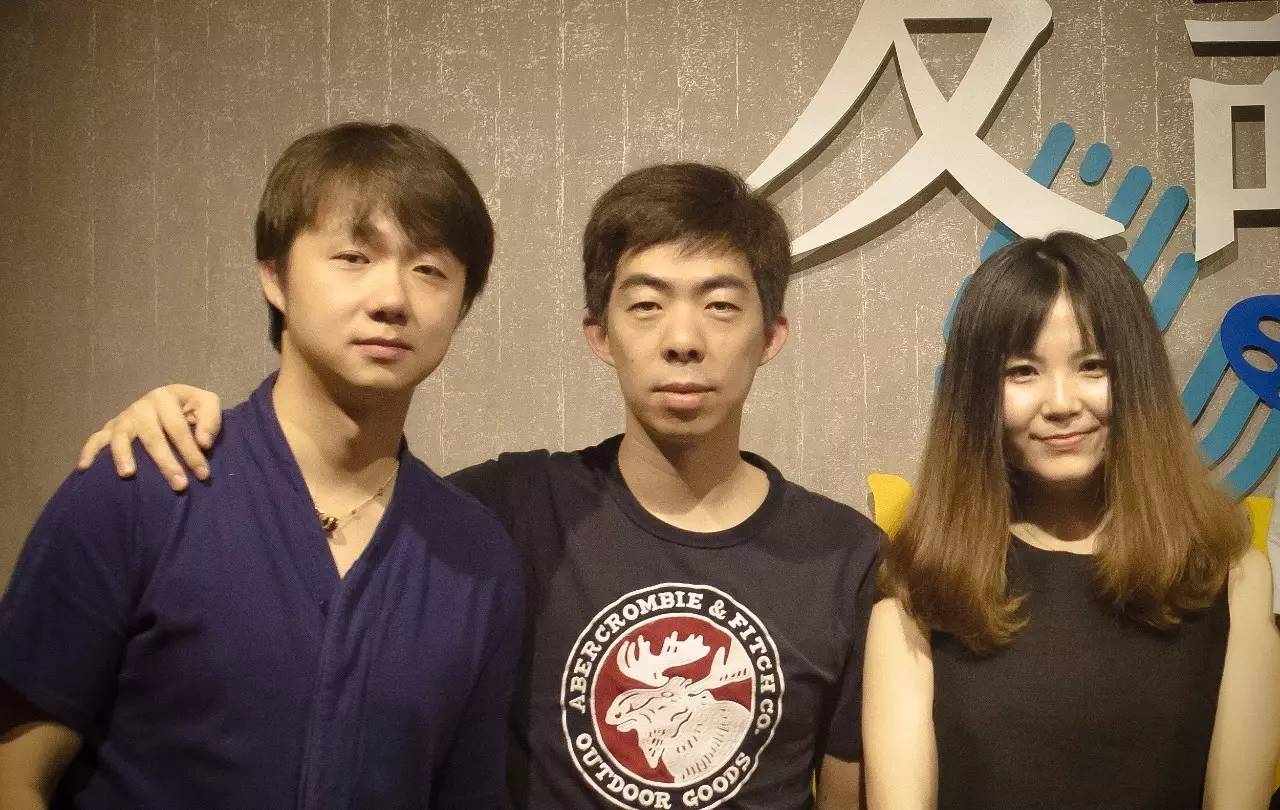
禹扬、路阳、陈舒
选取历史空白,“ 无常簿”是职业特征
路阳:选取这个历史节点是为了让故事看起来更有质感,但不可能做到真实的历史讲述,因为历史也是写出来的
编剧帮:历史上有一句著名的断言: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无论是魏忠贤穷奢尽处的为所欲为,还是朱由检灯枯之时的加油添火,王朝大明都各有各的于事无补。那么本片在历史史实的表达部分是怎样取舍的?
路阳:电影要说的不是魏忠贤、朱由检等这群真实的人,只是构建一个基于历史的故事。选取这个历史节点是为了让故事看起来更有质感,但是不可能做到真实的历史讲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真实历史怎么样的,历史也是写出来的,一定会为了艺术创作进行加工和再造。我们选取历史中有空隙的空白,首先不能违背大历史,另一个方面要在历史的缝隙中去寻找相对来说是合乎逻辑的,存在可能性的部分,再进行汲取。那么,电影和历史肯定不是一回事。
编剧帮:明末的乱世之中,锦衣卫里每个人都有一本无常簿,三位在塑造这个集体的时候做了哪些功课?“无常簿”的作用什么?
禹扬:最早我们考虑的是高压统治下的锦衣卫的特征,在创作过程中肯定会借助一些元素,像无常簿这样的道具的使用,其实更多体现了职业的特征。
路阳:就锦衣卫本身,它是一个特务机构,最早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时,职能主要是对内,后来锦衣卫发生了很多职能的变化,会有间谍工作,谍报工作,监察工作,甚至密探工作,密探谁呢?密探朱元璋下面的文武百官,包括各地方官员,在打听消息的时候要做记录,关于官员在家跟什么人见了面,说了什么话,座位是什么样的,甚至还有画像,会随身做非常详细的记录。无常簿就会变成一种体制化的,纪律化的道具,每个人、每个级别都有。
编剧帮:裴纶在被救之后把无常簿扔进了水里(给了一个特写镜头),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他对自己锦衣卫的身份的放弃?还是说是对明朝治理的一种不肯定?
路阳:以裴纶的格局,他可能不会站那么高,这更像是对他赖以生存的手段和锦衣卫身份的一种放弃,但这种放弃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他是一个成功的锦衣卫,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侦探,办案思路和手腕都很强。
而我觉得裴纶的思想深度,也到不了对体制的质疑,因为裴纶是挺现实一个人,他会更关注现在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需要朋友、需要安全等等。所以他其实是本能的去做出选择的。

编剧兼导演路阳
更“沈炼”的表达与一次理想主义的胜利
陈舒:所谓‘备胎’,我更愿意理解为爱的方式,一种隐忍又暖心的表达
编剧帮:其实有很多观众都很关心“万年备胎”沈炼情感的真正归属在哪里?各位觉得,这一部沈炼的情感收获是什么?
路阳:这一部的沈炼更热爱生活,第一部里面,沈炼唯一的念想是如何做救出自己,救出周妙彤。在第二部里面,沈炼养了一只猫,喂喂猫,有自己的一份悠闲。沈炼在情感上都有他自己的收获,两位女性都对他做出了很大的改观,而且北斋对他是有情感诉说的,但是沈炼不要求你的回报,只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做。
陈舒:所谓“备胎”,我更愿意理解为爱的方式,也就是沈炼的爱方式,是一种比较隐忍的,非常暖心的表达。其实这是非常东方的,也很常态。只不过在现在这个浮躁的环境下,观众会觉得新鲜。
编剧帮:关于那句“水是我吹温的,哪里烫了”,很苏很甜,各位在创作感情戏这个方面有没有克制自己?
陈舒:不是我在克制自己,主要是写剧本的时候,导演在克制我们。比如说我们想写得甜一点,导演总希望我们能够表达得更“沈炼”一些。
其实在第一部的时候,我和路阳导演有一个非常大的争执,沈炼到底有没有睡周妙彤?而当我真正开始理解沈炼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才觉得他真的不会睡周妙彤,这真的就是他的心性,是专属于沈炼的那种“笨拙”和“执拗”,同时也是这个人物吸引人的地方。
沈炼虽然在体制中挣扎,某种程度上是按照自己原有的命运轨迹一步步谨慎的走着的一个人,但是他心中一直还是有一份念想,一点微光,其实在一些细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包括他喜欢的字画,养的猫,包括他的一些犹豫,一些不忍。这些虽然还是散落着的,还并未找到一个具象的“宿主”。但是当北斋出现的时候,那份念想和那点微光就具象到了一个人身上。
你看北斋这个女孩没有武功,没有神通,甚至看上去非常的柔弱,就像沈炼的那份念想和那点微光,也是非常柔弱的,但同时内里又是非常坚强的。因为北斋是特别外柔内刚的一个女性,而且在整个故事中也经历了成长和变化,最终她对于沈炼的回馈,她最后脱离开这个修罗场,只保着一份思念,便是北斋这个人物的弧度,也是沈炼的胜利。

编剧陈舒
禹扬:其实对沈炼的情感都有收获,我们留了更多的留白,有很多的遐想空间。
编剧帮:沈炼到底为什么而战?各位是怎么考虑的?
禹扬:我一直都认为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有自己的隐忍,但是隐忍到一定的程度会有爆发的结果。爆发的结果大概就是,我所要提到的是这些坚持、希望或是爱都会同时闪烁出来,我认为是这样的,还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路阳:在故事的开始,沈炼和净海聊天那场戏,他说,我喜欢这只蝈蝈,他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强壮的黑公鸡面前有一只很小的蝈蝈,摆出了一种战斗的姿态,这种姿态特别吸引沈炼。在明末的乱世,相比强大的魏忠贤,皇帝,或者是信王,沈炼是很微小的,非常微弱的,改变不了任何的大势。其实他在跟所有人作对,没有站在任何一个对立面。他一直以为是因为本能,也许是对北斋的某种奇怪的感情,但是故事的最后,沈炼在拷问自己,我为什么这样做,他一直在追求某种信念,他对北斋的感情可能是很强的一个催化剂,但是真正的觉醒在他自己。即使是跟这么强大的世道作对,也不愿意顺流而行。
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很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情感也好,信念也好,都是需要坚持的。坚持很难,尤其是所有人都说你坚持是不对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坚持自己,坚持自己是电影里面很珍贵的东西。
陈舒:作为一个女性,沈炼为什么战斗,对我来说特别简单,如果是为了家国大义,很帅,但是对于我来说没那么帅,但为了一个想保护的姑娘,甚至还不知道真正名字的姑娘而战,这是一件特别帅的事情。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他就是为他爱的人战斗,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让一个具体的人去做了,就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一次理想主义的胜利。
编剧帮:其实裴纶(雷佳音饰)这个角色是充满着喜剧色彩的,各位觉得本片裴纶存在意义是什么?塑造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陈舒:沈炼作为一匹孤狼,需要伙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能让他从始至终都是孤身一个人,否则他会一直自言自语。裴纶也好,陆文昭也好,在剧作功能上都承担了男主角伙伴的功能。不断赋予主角危机和压力,所以,裴纶的起点肯定是作为主角行动的阻力,同时也作为主角最后一个同伴。
路阳:整个故事推进很快,信息量比较大,在那个阴谋,权力,爱情,看起来有一点残酷的时代,我们希望可以让观众适时放松一下,有一些舒缓。另外,就是让他更靠近观众一点,沈炼做的很多事情是很个人化的,需要借助裴纶的视角去替观众发问,观众有的时候可能是不理解的,你为什么这么做?裴纶有时候会给出一个自己的解释,观众会发笑,是因为观众会发现自己已经比裴纶更进一步的了解沈炼了。

文戏和武戏都是戏,“砍桥”并非易事
路阳:我认为沈炼是经过非常冷静的判断之后,选择了他认为最合理的方式。
编剧帮:山雨、竹林、幽寺、清溪、扁舟等这些极具中国古风的元素,这些在创作中是去实地采景,还是创作完之后去找类似的场景?
路阳:在剧本里面,我们希望呈现一个1627年的北京城,那个时候的北京的水系很发达,京杭大运河从南方过来,然后从现在的通州,那个时候叫做大通河,从南城进城,形成了很多的小的水系,穿城而过,一直到密云,到昌平。但是现在这些水系很多都不见了,我们很希望在电影里面能够让观众看到那个时候的明末的北京是怎么样一种繁华的景象。
具体到中国风,我们知道北京的旁边是不可能有竹林的,我们还是很任性的希望有这种意向化的情形能够在故事里面,美术组很辛苦,他们采景的时候,先后跑了五个省,转了非常多的地方,一个个的挑选我们剧本里面想要的场景,找到合适的,我们再去反复的确认。
陈舒:具体写场景的时候,会首先讨论这个场景的基调是什么,哪怕是动作的场面,这个场面的气氛是什么,人物关系发展是什么?在写作当中会有意识的去思考这一点。
编剧帮:在动作戏的方面,导演是参与动作设计还是说完全的交给动作指导去做?
路阳:写剧本的时候我们会很详细的写出每场戏的动作,像写武侠的小说一样,会写好所有的招式,动作场面里面一样要有戏剧,要去讲故事,要去刻画人物,如果空着就要打,也可以顺畅的理解剧情,那说明这场戏是失败的。
同时在写得完整和丰富之后,演员很清楚这场戏的走势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打,这么打的目的是什么?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都是有必要的。写好之后把这些剧本交给动作导演沟通。怎么打?什么时间,谁占优势,谁占劣势,怎么样反击。动作导演根据我们的需要去设计所有的动作,甚至是可以重新去设计,但是一定要依据这个戏剧去设计。文戏和武戏都是戏,不能把武戏完全单摘出来。
但是你要去依赖你的团队,一定要相信他们,如何去呈现,用什么样的镜头,如何体现速度和力度,他们有非常多的经验和想法。

编剧帮:关于观众对本片结尾“砍桥”的争议,各位有什么想说的?
路阳:我认为沈炼是经过非常冷静的判断之后,选择了他认为最合理的方式。
首先,电影里沈炼让北斋先走,他和裴纶守桥,接下来陆文昭和丁白缨率领的众刺客赶来,迎战的结果是沈炼和裴纶获胜,意味着沈炼的选择和判断是没错的,不用砍桥,让北斋先走,没有顾忌,然后去战斗,最后取得战斗的胜利。从沈炼听到追兵的马蹄声,到让北斋走,然后去迎战,时间很短,这是一个不可能选择的方法。其次,差别在于故事里所有主角并不知道后面还有锦衣卫的大队人马,无从做出判断。
还有一个现实条件就是,很多观众会说为什么不是三个人一起砍桥,但是真正能实施砍桥的只有沈炼一个人,只有一把刀(绣春刀),裴纶那个小刀让他去砍,可能就划一划,起到一点助威的作用。
我觉得有的时候观众会站在上帝视角,联系所有的信息来判断,为什么不砍桥?为什么后来又砍了?锦衣卫来了,他们几个人已经不可能离开了,砍桥其实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北斋离开。其实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铺垫,裴纶对北斋的态度一直在转变,所以最后裴纶对沈炼说,你还等什么,你赶紧砍桥啊,你不砍桥,我们四个人就全在这了。那个时候裴纶不是认命,而是接受了现实,裴纶在面对大队锦衣卫冲过来的时候,是放松的,是冷静的。他知道接下来只要面对就好了。

陈舒:其实(这个时候)裴纶的念想特别的接地气,就是说要捅回陆文昭一刀,这是台词上说的,但深究他的念想也一定不止是这些,后面还有情义撑着。但是他能说出这句话,也是这个人物的可爱之处。
任何类型的电影都需要找到当代的表达
路阳:沈炼是一个有恐惧的人,但是他跟我们很像,某一时刻可以做出我们无法做出的选择,这才是真的有光彩,是我认为的英雄。
编剧帮:如果把《绣春刀》系列定义为武侠片,一个是“武”,一个是“侠”,就“侠”来讲,应该是令人崇拜的大侠,但《绣春刀》系列却表现了几个亡命之徒。对此各位在创作中,是怎么考虑的?
陈舒:前段时间史航老师在微博上发了一条《绣春刀·修罗战场》的评论,大致的意思是说,绣春刀里面并没有一个快意的江湖,也没有一段可以明断的恩仇。路见不平,即刻拔刀相助的,这就是侠,这是快意的江湖,是武侠世界,但是从沈炼看到北斋受侮辱到决定拔刀相助,其实是经历了漫长的,特别真实的犹豫和挣扎,整个过程他的心理层次分了好几个阶段。从这一点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武侠的世界。
路阳:我们想写的更像真实的人,因为江湖离我们遥远,很理想化,很浪漫化。放在现在,如果有人拍一个电影,主人公要去统领江湖,我根本不信,我觉得这个人有病。我们写的故事里面,杀人要犯法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会有犹豫,会有恐惧,沈炼是一个有恐惧的人,但是他跟我们很像,某一时刻可以做出我们无法做出的选择,这才是真的有光彩,是我认为的英雄。
编剧帮:武侠片这个中国独有的类型,曾经在世界影坛取得过令人骄傲的成绩,但近几年市场上受冷遇,《绣春刀》的出现才有所回暖,各位觉得原因出在哪里?对中国武侠片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禹杨:其实(武侠)这个类型是有需求的,只是你得有好作品,因为观众想吃好的,吃不到好的,就不吃这一家了。
陈舒:我个人觉得,无论你写任何类型的电影,特别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当代的表达。其实大家可能都在吃武侠电影的老本,在这个过程中丢失了“当代性”,我们是在试图找回它,虽然并不一定做得很好。
路阳:无论是作为编剧还是导演,我都希望始终把自己摆在一个新人的位置,去探索,去寻找一些好玩的,新鲜的东西放在电影里面。而不是简单的去模仿,照搬以前的套路,我们希望能够像沈炼是一样的,没有套路。技巧和体系是一定会使用的,但是尽量让观众看到我们在尝试找到一些新的讲故事的方法和内容。
「大学自习室」里的“诡异”创作

陈舒:青年创作者不要迷信权威与殿堂,可以崇敬,但是不要迷信。
编剧帮:两部《绣春刀》下来,关于编剧和导演之间合作的智慧,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跟编剧们分享的?
陈舒:其实我和路阳在《绣春刀·修罗战场》之前,合作方式是相对独立的,基本上会我写一遍,他写一遍,通过电子邮件交流,我们的沟通成本非常低,他一稿过来,我基本上知道他想干什么,然后我再一稿过去,他也知道我想干什么。在写《绣春刀·修罗战场》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第一次被关在一起写作,回忆起来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
作为编剧,我的感受是,但凡是导演能够越早介入到编剧的工作当中来,这个案子的成活率,最终的呈现度,完成度,都会比编剧一个人要好很多。而且路阳自身也是一个编剧,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写剧本的时候,呈现出来一种非常“诡异”的气氛,特别像大学自习室,非常轻松,非常愉快。

编剧帮:三位的分工是怎样的?
陈舒:大纲阶段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比剧本更繁复,更痛苦,更冗长。整个故事的脉络、人物的情感走向都要写得特别明晰,可能会达到两万字的,更像一个大分场。大纲讨论阶段会一场戏一场戏的来,三个人讨论一场戏的时候,甚至会进行一个情景的再现,有时候我还会使坏地会说,要不你们两个来演一下吧。每一场戏在写作之前,我们会把人物的核心的台词,人物的状态,整个的环境属性,摸得特别清楚。这样进入到剧本阶段,效率就会非常高。
而且路阳不是一个“放水型”的导演,是要落实到标点符号都必须准确的一个人,我和禹扬已经完全了解导演,比如说,写完这句,导演看看,说,“好”“嗯”“不错”,其实就是不行,因为他没有马上即刻的表现出“就它了”的状态。
路阳:因为那个时候,三个人的思路已经高度统一了,几乎不存在分工的问题,看到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工作方式,三个人都可以写,写累了之后,另外两个人反复的修正,然后再继续写。
禹扬:像沈炼和信王第一次见面的那场戏,大概写了有三天,是因为我们每次写完一遍以后看看不好,删掉,然后再写,再删掉,反复的删,再写,删了再写。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即使说大纲阶段已经很详细了,产生细节的时候,依然要去动很多脑筋。

编剧禹扬
编剧帮:对青年编剧有哪些建议?
路阳:我觉得技巧和经验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找到打动你的人物,当你认识了这个人,相信了这个人,自然知道他有什么样的行为和选择。
陈舒:青年创作者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那些殿堂,可以崇敬,但是不要迷信,找到真正跟你合拍的年轻的伙伴,一起往前走。我们相遇的时候非常的年轻,没有任何作品,但是一定相信彼此,一步一步的踏实往前走。
记者 | 了想、小木匠
实习记者 | 竖 执行主编 | 了想
E / N / D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