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娅·博伊德(Julia Boyd)致力于研究外国人在中国和日本的经历,在相关领域著作颇丰,并颇受好评。在《第三帝国的游客》(Travellers in the Third Reich)一书中,她整理了1918-1945年间到访德国的外国人的日记和信件,展示了他们当时在德国的所见所闻。
本书开篇从一战停战之后讲起——当时的德国经济严重衰败,物物交换重现交易市场(彼时报纸上曾刊登一则广告:“一双牛皮靴可以换一条纯种达克斯猎狗。”)——一直讲到二战末期,苏联红军高喊着“希特勒过时啦!柏林沦陷啦!”的口号进驻柏林。博伊德以一种十分巧妙的方式为读者讲述了那一重大历史时期的故事,于无形之中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不一样的“第三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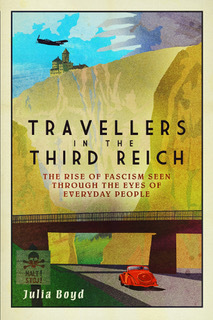
书中有一章在开头写道:“1939年,德国的旅游业并不景气。”根据博伊德整理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外国人到访德国都是在1939年之前,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期间。1937年,德国吸引了将近50万美国游客,而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英国著名商人,创立了Thomas Cook & Son旅行社)直到1939年依然为客户提供前往德国旅游的服务。虽然在国家保护之下,身处德国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未受战争之害,但当时的场景却让他们难以忘怀:纳粹士兵的列队随处可见,十字党徽无处不在,裸体主义的盛行……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氛围当中。
澳大利亚外交官亚瑟·内肯(Arthur Yencken)在休息了几年之后,于1935年回到德国,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打扮得非常整齐,好像衣着和发型一下子都有了全国统一标准”。内肯还注意到,金发的潮流几乎席卷了整个德国。据官方统计,德国1934年染发剂的销售量达到了1000万包。
法国记者达尼埃尔·盖朗(Daniel Guérin)在1933年进行自行车旅行期间,曾参加过一场由纳粹褐衫党徒组织的音乐会。他注意到了那些德国少女对于步行靴的痴迷和狂热:“除了那些靴子,除了那皮革的香气,除了军官那刚强而精准的步伐,再没有其他什么东西能够征服这些布伦希尔德(Brynhildr,日耳曼神话中的女武神)了。”
在当时,纳粹礼随处可见。关于纳粹礼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安东尼·托恩比(Antony Toynbee)觉得:“可以把这当做是锻炼持剑臂(尤指右臂)肌肉的一种方式。”但一位年轻的学生却见过无比滑稽的一幕:一个体型肥胖的男人在骑自行车时,试图用一只手控制方向,另一只手行纳粹礼,结果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


一直以来,传统智慧灌输给我们的观念都是“纳粹显然是邪恶的”,那些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如果不是傻子,肯定就是法西斯份子。然而事实上,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观念。长期以来,我们的评判标准都是非黑即白的两个极端,博伊德却为我们展示了更细微的一面。
其中就包括一些盲目崇拜法西斯的傻子。1935年,前任英国海军情报首脑和皇家海军学院院长的海军中将巴里·多姆维尔曾参观德国达豪集中营,他对营地的舒适和良好的秩序印象深刻,甚至还遗憾地表示:“英国新闻界对德国状况的报道尽是谎言,实在太可耻了。”
有一些传教士的行为也不值得称道。牛津团契(Oxford Group)的创始人弗兰克·布奇曼(Frank Buchman)是上帝的忠实信徒,认为“一切尽在上帝掌控之中”,“上帝掌控的国家”应当由“上帝选中的人”来领导。他在给希特勒的信中写道:“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先驱者将为我们指明出路,”这比他的本意更为真实。

历史上也存在一些不看好法西斯的聪明人,英国著名指挥家托马斯·比彻姆(Thomas Beecham)就设法在当时坚持自我。1936年,他受邀来到拜罗伊特演出,希特勒请他共享午餐,他却发了一封电报一口回绝:“对不起,不能来,祝好,比彻姆。”而在电台直播的音乐会上,他也毫不避讳地表示:“那个老伙计似乎还挺喜欢这样的”。
英国外交部首脑罗伯特·范斯塔特爵士(Sir Robert Vansittart)强烈反对纳粹主义。但他曾经接受邀请参加德国举办的奥运会,他非常意外地发现自己挺欣赏戈培尔这个人。这使得范斯塔特倍感困惑,因为戈培尔是纳粹主义的坚持拥护者,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戈培尔)是个充满魅力的人。”
此外,还有很多人虽然厌恶纳粹,但却热爱德国。所以当时的德国即便处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依然有许多喜爱贝多芬的自由派人士将他们的孩子送到这里来开拓视野。

希特勒所宣扬的法西斯理论不仅使许多德国人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狂热之中,甚至还有一些英国的上流人士也对其痴迷不已。尤妮蒂·瓦尔基里·米特福德(Unity Valkyrie Mitford)出身于英国贵族家庭,对希特勒近似疯狂地迷恋和英雄崇拜使她一步一步接受了“纳粹观”,进而频繁往来于英德之间,不知疲倦地充当希特勒的传声筒,被称作是希特勒的“英国女战神”。第七任伦敦德里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查尔斯(Charles Vane-Tempest-Stewart)也对纳粹德国高度赞扬,曾在两年内六次访问德国。查尔斯15岁的女儿梅丽(Mairi Vane-Tempest-Stewart)的日记中就曾写道:“与希特勒共进晚餐……与萨克斯·科堡公爵共进午餐,然后一起去劳改营。”
这个特点在作家当中也非常普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笔下的德国是“得天独厚”的,那里的景色“如歌剧布景般美丽”,那里的山“高耸却并非无法高攀”。英国诗人奥登(Auden)、作家伊舍伍德(Isherwood)和斯彭德(Spender)都曾对柏林的机械师和水手们情有独钟。于1919年成立的性研究所博物馆曾被视为柏林现代化的标志。奥登在参观这座博物馆的过程中,仔细研究了“那些外表凶猛、充满男子气概的普鲁士军官们”,他们“威武的制服下却穿着带花边的女性内衣,光鲜的外套下穿着到膝盖长的短裤,下端由橡皮筋固定”。这座研究所的图书馆于1933年被烧毁。

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就对德国的机器制造印象深刻。例如,他将有轨电车形容为“一尘不染,就像一个完美的玩具一样闪耀着光泽”,在街道上静静地滑动。但是,在从柏林到巴黎的火车上,他结识了一个神经紧张、坐立不安的矮个子男人,到达法国边境时,他的这位朋友却被一名凶残的官员逮捕了,只因他是犹太人。沃尔夫写道:“我真想把那个军官的肥脖子打得粉碎,狠狠揍他那张迟钝而肿大的肥脸,踢烂他那笨拙的大屁股。”
《水獭塔卡》(Tarka the Otter)的作者亨利·威廉姆森(Henry Williamson)热爱自然,曾参加一战,受重伤后回来过上了隐士的生活。但他在政治方面非常极端,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二战期间因被疑为“德国间谍”而受到关押,但他对纳粹的信念却至死不改。他唯一表示后悔的是自己在三十多岁时还没有足够的智慧,没有意识到“一个拥有巨大艺术天赋的人是无法掌管一个国家的”。

在1936年奥运会上,“纳粹军国主义”得到了非常有趣的阐释。在冬季奥运会上,美国女子滑雪队队长爱丽丝·基埃尔(Alice Kiaer)发现一棵倒下的树挡住了滑雪的线路。她的向导吹响了哨子,树林中就出现了10名士兵。他们成一列纵队在林间滑雪,和谐地唱着歌。帮基埃尔移开障碍物之后,又回到林间滑雪去了。在慕尼黑举办夏季奥运会期间,也曾出现非常戏剧性的时刻,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棒球运动员赫尔曼·戈德堡(Herman Goldberg)想进入奥运村,但是开了几扇门之后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装满了装甲坦克的地堡里。
这届奥运会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人选择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行为视而不见。400米田径赛跑的冠军阿齐·威廉斯(Archie Williams)是非裔美国人,他在接受《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采访时表示:“我回到美国之后,有人问我:‘那些肮脏的纳粹是怎么对待你的?’我的回答是,我没见到任何臭纳粹,只有很多友善的德国人。而且在那里,我也不需要坐在公共汽车的后排。”
博伊德在书中并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她在自传中提到,她自己也是一名前外交官的妻子。她在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老练和机智,可能是经历过无数场令人筋疲力尽的鸡尾酒会之后修炼出来的。在书中,博伊德巧妙地运用了她的“外交手段”,借助那些历史记录,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纳粹德国。
(翻译:刘桑)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