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20世纪德国作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和电影理论家,他早年在《法兰克福报》任记者、评论员,与阿多诺、本雅明、布洛赫等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3年纳粹上台后,作为犹太人的克拉考尔被迫流亡巴黎,后于1941年辗转到达纽约。移居美国后,他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主要从事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研究。
克拉考尔是最早一批被介绍进中国的电影理论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人和电影学者所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在电影和人们的日常经验重新建立关联,克拉考尔的左翼立场和现实关怀,使他成为了最符合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西方电影理论家。他的两本电影研究著作,《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和《电影的本性》都是移居美国之后用英文写作的,前者从魏玛时期的德国电影中追溯纳粹的萌芽,后者则将电影这一艺术形式视作对被工具理性奴役的西方世界的精神救赎。两本书都在美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也让人们对他二战前的作品发生了兴趣,于是在1963年,他出版了一本自选文集,《大众装饰》,其中选取了十几篇他在魏玛时期(也就是他在《法兰克福报》任职期间)的作品,这本书在他去世后成为了建筑、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文献,而它的名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继续去挖掘和重新发现克拉考尔的其他早期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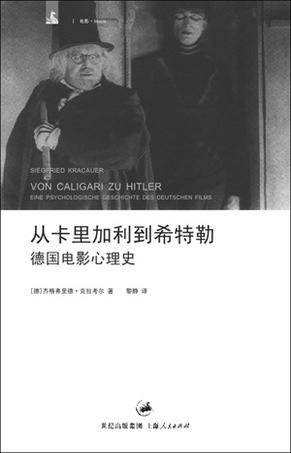
克拉考尔 著 黎静 译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日前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和《侦探小说:哲学论文》两本书,都是克拉考尔在上世纪20年代完成的作品。《雇员们》写就于1929年,那时克拉考尔就职于《法兰克福报》柏林站,他用了十周的时间,对柏林大小企业雇员们的生存空间、工作环境、习性癖好、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进行了调查,他与雇员、工会代表和企业主交谈,走进办公室、职业介绍所和电影院观察,甚至研究厂报、广告和私人通信,他的方法非常类似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或社会学的“参与式观察”,但他本人拒斥任何学派或机构的局外人立场,也让他与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了距离。
他将这次在家门口完成的调查称作一次“远征”,因为在他看来,这一系列在《法兰克福报》上连载的文章涉足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其惊险程度不亚于一场银幕上的非洲之旅。因为“在寻访雇员的同时,它驶入了现代大都市的内部”,比起电影里令人啧啧称其的原始部落,这里的生活在众目睽睽下展开,却并不为人所知,正如爱伦·坡小说里写到的“女王陛下的信”,没有人留意它,正因为它就在台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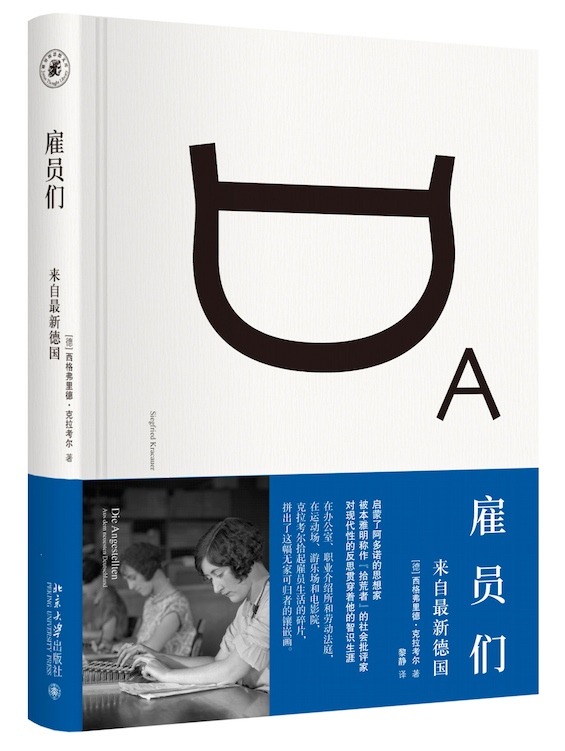
克拉考尔 著 黎静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早在19世纪末,“新兴中产阶级“的概念就已经在德国形成,它将雇员们视为国家和社会的中流砥柱,扮演着抵御动荡的缓冲器角色。1911年颁布的《雇员保障法》明确了雇员的待遇及其优于工人阶级的地位,然而好景不长,被战争和通货膨胀洗劫了财产的中间市民阶层很快又陷入了经济合理化改革的漩涡,在这场改革中,他们大规模地丧失了区别于工人阶级的几乎所有优势:相对的独立性、升迁机会和职位保障,在物质条件上,他们也逐渐与工人趋同了。
于是,我们在克拉考尔的调查中看到,中产阶级想要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上与工人阶级划清界限的努力越发顽固而绝望——克拉考尔展现了这个“中产阶级概念和感受之家”的外观是如何依靠“教育”、“文化”、“职业”等话语得以维系,但与此同时,家园早已坍塌。在他看来,这些雇员们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只能暂时躲入文化工业为他们提供的避难所。1929年的克拉考尔还无从得知,这些中产阶级会成为纳粹党和希特勒的支持者,然而他在他们头上看到的“恐怖的光晕”,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预见到某种政治灾难即将降临。也正因为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暗示,这是一份“来自最新德国”的报道,它见证了魏玛共和国的末路,和一个“新的德国”的危险萌芽(1933年希特勒上台,仅维持了短短14年的魏玛共和国正式宣告破产)。
而《侦探小说》的写作比《雇员们》更早,它于1922年至1925年间完成,但却在克拉考尔去世之后五年才在他的遗物中被发现。在这本书中,他让一种“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看来只是无关文学的粗制滥造”的文学类型——侦探小说获得了一番形而上学的阐释,同时,他也在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学现象上试验了各种形而上学的范畴。这种借由一类文艺作品展开形而上学或历史哲学探讨的方法,来自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克拉考尔曾评价它为同时代最重要的哲学成果之一,同时,《侦探小说》与本雅明1928年的论文《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不同的是,克拉考尔选择了更加通俗,甚至是不入流的文学类型,在他看来,这些充满了奇技淫巧的追凶故事就像是一幅变形画,映射出了人们精神世界中某种不可回避的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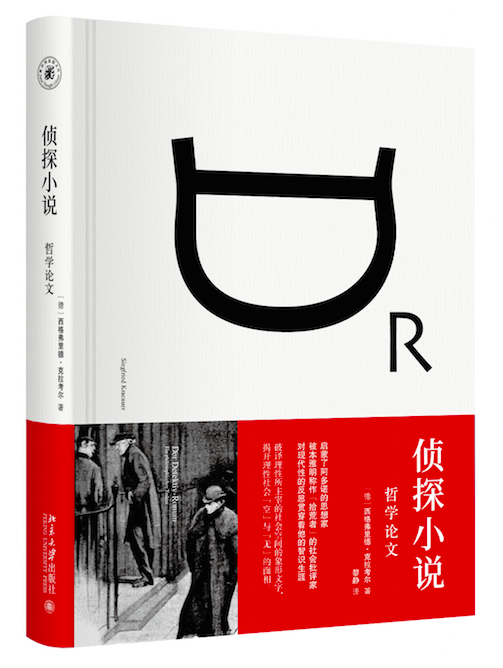
克拉考尔 著 黎静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自埃德加·爱伦·坡1841年的短篇小说《毛格街血案》(The Murder in the Rue Morgue,也译作“摩格街谋杀案”)以来,欧洲陆续出现了一批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福尔摩斯系列)、埃米尔·加伯黎奥(《红色命案》)、加斯顿·勒鲁(《歌剧院魅影》)等都在其列。在克拉考尔看来,这些作家的作品向“全盘理性化的文明社会”“执起一面变形镜”,社会可以在其中辨认出自己的“胡作非为”,而解谜的过程则构成了“对以理性、自治为基础的哲学体系的审美譬喻”:案件的侦破总是始于单薄的证据和破碎的事实,这些事实被除去了语境,剥夺了原初的关联,成为了孤立的客观材料,而侦探要做的,就是在这些偶然事件之间用理性重构关联。因此,侦探小说的张力也许并非源于事件本身的力量和面对罪恶时的战栗,而是真相可能始终未被识破。
推理究竟是还原了真相,还是彻底虚构了真相?这是侦探小说的张力,对应到现实,一战后的欧洲知识分子们也面临着类似的惶恐:理性从神坛上跌落,人们究竟该如何重新搭建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爱伦·坡 著 张冲、张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7月
《雇员们》和《侦探小说》的译者黎静将克拉考尔形容为“魏玛时期的接收器”,魏玛时期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催生了德国第一个民主政权——魏玛共和国。在1919年一战结束到1933年纳粹上台之间短短的十四年间,魏玛共和国经历了通货膨胀、政教冲突、种族歧视、性别与代际矛盾、暴力与恐怖主义等重重危机,同时也孕育了一个艺术、文化和思想的高峰,它既是通向纳粹和大屠杀的毁灭之路,也是无数像克拉考尔这样的人为了一个更人道、更民主、更有创造力的社会而奋斗的历程。魏玛共和国所面对的许多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依然存在,而魏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对今天的世界依然有效,这是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阅读克拉考尔的原因。
在《雇员们》和《侦探小说》两本书出版之际,北大出版社联合北大博雅讲坛举办了“思想的跨界者——克拉考尔”研讨会,在会上,北大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胡蔚谈到了克拉考尔以及那一代一战后的德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救赎焦虑”以及他们为突破这种焦虑所做的尝试。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刊出胡蔚的发言节选,以飨读者。
胡蔚:如何在废墟上重建生命的意义是克拉考尔这代德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题
克拉考尔生于1889年,本雅明生于1893年,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而比他们稍微年长一点的托马斯·曼和里尔克是1875年出生,茨威格是1881年出生,他们这一代19世纪的80后、90后是有一些共性的。他们都在相当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一战,这使得他们身上普遍存在一种救赎的焦虑,他们各种各样行为的动机,似乎都是源于这种救赎的焦虑。
史学界有一个观点,认为一战爆发得十分偶然,战争双方的理由都很牵强,或者说是为了打仗而打仗。1914年的德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非常想要向世界展示它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各种战争宣传画色彩艳丽,征兵广告充满鼓动性,整个市民社会都好像看到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却又无限向往的新世界的曙光,家家户户把年轻的男孩送去当兵,这些男孩戴着个软布帽子就上战场了,根本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等到他们经历了血腥、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他们想象的、被称为“绞肉机”的战争,回归到战后的日常生活,你会发现,这一代人都被打垮了,从身体到精神都彻底崩溃,他们憧憬的新世界突然变成人间地狱。当时柏林的街头,随处可见断臂或是瞎眼的士兵,这种心理的反差、幻灭的情绪,对应到形而上学的讨论就是,当所有意义都失去,当所有关联都是去,怎样去重新救赎,怎样在废墟上重新建构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这就变成了这一代80后、90后共同的话题,这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哲学话题。

一战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终结,艾伯特等一批民主党人于1919年在一个叫做魏玛的德国东部小城召开了国民议会,制定了一部共和制宪法,这就是德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因此1919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前的这段时期,被称为魏玛共和国时期。为什么要去魏玛召开议会?因为魏玛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高地,是人道主义的象征——魏玛是歌德和席勒之城。十八世纪下半叶,当时魏玛公国开明的公侯重视文化艺术的发展,将歌德、席勒、维兰德、赫尔德等知识分子邀请到魏玛公国担任公职,因此在1800年前后,形成了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魏玛古典文学,这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高峰,魏玛小城也因为这段历史而成为了德国文化的象征。
一战结束后的前五年,魏玛共和国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通货膨胀、饿殍遍野。伯格曼的电影中有一个很经典的镜头,记录了一匹还拉着车的马饿毙在慕尼黑街头,一位妇人当场就把这个马开肠破肚,将马肉卖给路边的行人。从1925年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魏玛共和国有一个五年左右的稳定期,这就是现在文化史上通常所说的1920年代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魏玛的文学艺术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首先,从艺术风格上看,出现了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新客观主义是对战前注重情绪表达的表现主义的一个反动,它解剖、展示现实世界,不再美化,不再情绪渲染,而是把破败丑恶、冰冷、道德败坏的城市生活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很典型的文学例子是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描述了一个刑满释放的小人物在柏林都市里的经历,从一个边缘人的视角对光怪陆离的柏林都市进行了记录。
其次,当时的新媒体——电影的表达方式也影响了传统的小说、戏剧体裁,比如《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使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一些新闻报道、天气预报、电影广告杂糅拼贴在一起,情节松散、意识流;布莱希特描写伦敦黑社会的《三毛钱歌剧》也是一个经典的魏玛时代戏剧作品。
再次,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进入了文学创作中,对文学创作方式产生了十分重大、深远影响。总之,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一个文化艺术生活非常多元、活跃的时期,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政治立场的人物都很活跃,既有先锋派的作家,也有传统的作家,既有左翼作家,也有保守主义的作家,大家都有一席之地。随着报业的发展,评论家在魏玛共和国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也变得举足轻重,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里就曾经提到文艺副刊的评论家对于维也纳文化生活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回到克拉考尔, 他的身份很难归类,也拒绝被归类,用德国人的话说,他坐在了“所有的椅子中间”。这也决定了他的一生始终处于局外人、边缘人的位置,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游离于各个派别之外,无论是与“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他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从潜意识心理分析的角度,这也可能与他犹太小市民阶级的家庭出身有关。同时,他也热衷于研究边缘人群、灰色地带,比如“雇员阶层”,再比如作为消遣文学、不登传统经典文学大雅之堂的“侦探小说”。

我觉得在克拉考尔多重身份中,最合适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批评家(Kritiker),这里的批评家是广义的批评家,不是某个领域的评论家。德国文学中的这个传统是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莱辛开始的,莱辛涉及的领域有戏剧评论、文学评论、政治学、教育学和神学等等;在浪漫主义时期,这一传统又由弗·施莱格尔等人发扬光大。早期浪漫主义提出,文学是“渐进的总汇诗”,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包容万象的,永远在形成的过程中,是断片,只有用浪漫反讽来消解有限与无限的分裂。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继承了德国的批评传统,他们并不是要评论某个作家,或者要推出一个作品,他们在各种领域里发表看法,但是背后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更为深层的形而上的思考。
克拉考尔一生开拓了很多“未知领域”,这些领域相互之间似乎没有关联,比如他一会儿关注“侦探小说”,一会儿又去做城市雇员的一个人类学田野报告,过几年又开始研究电影。他很多的创新、开拓,其实都来源于他的焦虑,或者说这是一代人的焦虑。卢卡奇的《小说理论》(1920)曾经影响过克拉考尔,在这本书中,他将他们所处的新时代诊断为“被神所弃的世界”,新时代的人是“先验的无家可归者”。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本雅明,和左翼阵营的卢卡奇、布莱希特,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病里面的人,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废墟时代,寻找救赎的可能。克拉考尔找到的可能是,如“拾荒者”般捕捉庞大理论体系缝隙中微光照见的浮尘,那些无法用概念归纳的、不易察觉的、转瞬即逝、碎片式的日常经验。这也是受到了胡塞尔和齐美尔的影响,“从一个最小的偏门里也可以登堂入室,直接抵达人类本质的核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