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周刊特约撰稿人丁果撰写】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在加拿大努力参政议政,不单单是要尽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和行使我们的基本权利,也不单单是要提升我们华人社区的能见度和社会参与度,让我们成为社会的“主流”社群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和后代,在加拿大创造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为他们扫清华人先辈乃至我们所经历和承受的不平等待遇的黑暗角落,让他们能够在加拿大作为主人公而扬眉吐气地生活,追寻他们的加拿大之梦,建设他们自己所属的社群,发展他们自己的企业和事业,在公共事务的参与和晋升上,没有所谓的“天花玻璃板”。
很可惜的是,我们不少第一代移民在上述所有的领域,做得都不尽人意,尽管我们富裕华人的豪宅不断矗立在大城市或者近郊的黄金地段,我们华人的豪车耀眼地行使在各条主要街道上,我们华人的吃客在考究的中西餐厅一掷千金,土豪们的炫富和种种别人不太理解的行径不断成为英文媒体的头条。

我们的华人人口在卑诗省和安大略省的不少城市占据了三分之一,卑诗省的列治文华裔人口甚至超过了半数以上,但是,我们的投票率、我们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管理人员、我们社区在接受政府拨款的数量、我们在三级议会和政府中的代表、我们在制定三级议会和政府立法和政策制定上的话语权,却是少得可怜,成为加拿大社会中政治上“能见度最小”、“话语权最小”的族群。
我常常讲,第一代移民的“歧视忍耐度”最高,对自己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低下的“忍耐度”也是最高,对自己不参与投票和社会参与“借口最多”。他们自我安慰的理由就是:尽管我们的头脑和智慧很高,但因为我们英语不好,是“虎落平阳”;我们是“游子游客”,大不了“落叶归根”,歧视多了,我们就跟加拿大“说再见”;我们是少数,一张票改变不了政局,不投也罢;华人不团结,搞分裂,国民素质不行(但我行)……总而言之,第一代移民想尽办法为自己不参与社会、不投入参政议政找到心安理得的“理由”。
这种态度和思维方式,让华人社区在100年的历史中无所作为,以至于犹太人社区崛起了,华人社区还在政治社会的末端;印裔崛起了,华人社区还在后面缓慢“爬行”;菲律宾裔韩裔崛起了,华裔在政治参与上和基层选票实力上相对落后;现在,连中东裔(不少是难民)即伊斯兰社群声音都很大的时候,华人的整体声音仍然还是几十年前水平(尽管在三级政府中华裔的议员人数有所增加),这是相当遗憾的事情,也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的现状,华人社区的大多数应该感到这种现状“无法再继续忍耐下去”,我们才有希望。

最为吊诡的是,我们很多第一代移民是为了孩子才毅然决然地移民,但移了民,以为给孩子们找到了一个制度可以万年不变的天堂,再加上父母累积的财富,足可以让他们高枕无忧、幸福无边了。其实不然,第一代移民的无所作为以及“酱缸文化”,让孩子们既看不起华人社区和中华文化,也与父母有很大的“沟通问题”,以至于他们只能在一个虚幻的“主流”里打晃,语言没有问题了,教育也没有问题了,但却摊上了一个他们急欲要摆脱、却又如影随形跟在他们后面的“华人社区”,这是一个四分五裂、勾心斗角、涣散无力、在政治上少有能见度、被其他族裔常常诟病的社区,他们无法引以为自豪的社区。如此一来,在其他少数族裔崛起的新时代里,华裔二代、三代反而成了加拿大的“无根浮萍”,这个“浮萍”还漂不回大陆。一旦社会有风波、有变动,他们就成了最为“脆弱”的一群。
因此,第一代移民必须痛定思痛,义无反顾地进入“政治主流”,积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为下一代建造一个可以让他们骄傲自豪、乐于认同的华人社区!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仅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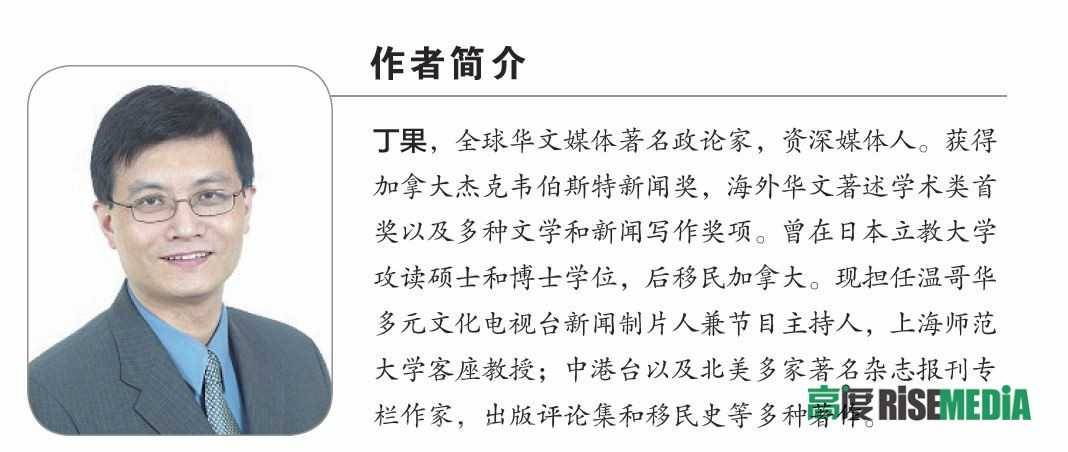
作者:丁果
责任编辑:郭达
出品:高度周刊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