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统的军事强国,目睹大海对岸一个新兴大国不可阻挡地走向崛起,是否会产生恐惧的心态,从而不惜以战争手段来阻碍对方的发展呢?
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许是这样想的。在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这样解释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间连绵数十年,改变了整个希腊世界历史的战争:“雅典的权势不断增长,导致了斯巴达人的恐惧,这使战争无法避免。”根据美国学者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的解释,这意味着“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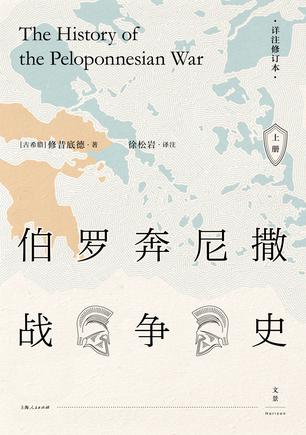
[古希腊] 修昔底德 著,徐松岩 译/注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不过,这位对古希腊历史无甚造诣的学者发明的“修昔底德陷阱”竟大受追捧,甚至有学者撰文称其为“国际关系的铁律”。虽然国内媒体通常认为这一陷阱可以被规避,或者认为这一陷阱已经不适用于当代,却很少有人质疑过这一陷阱在历史上的真实性。
事实上,不管修昔底德怎么想,他自己记录下的那场战争本身就无法为这一陷阱提供证据。如果仅从这本书中读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那我们就恰恰掉进了陷阱——细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反而会揭示许多当代国际关系思想的荒谬,并颠覆我们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许多固有看法。

一场战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把国家看作是内部高度一致、共同追求利益的整体,那么战争的爆发恐怕只能由地缘政治、军备状况和一些偶发事件来解释,因为根据这种观点,一旦形势的变化导致一国能诉诸战争来实现国家利益,该国自然会采取战争的手段。但是,战争所带来的利益与痛苦并非同等地作用于该国的一切成员,因此国家从来不是一颗同质的实心球,政治决策总是无数个人在族群、阶级、党派等社会关系中出于自己的视角(但未必只出于自己的利益)行动的结果。一国是否参加战争,只有对每一参战国的社会进行具体考察才可能得到答案。
民主的雅典为何拥抱帝国、走向战争?

让我们先看看雅典这一方面。许多人都知道雅典是民主政体。根据一般的看法,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总是普通百姓,而统治阶级总能利用战争敛财牟利,那么雅典人民怎么会允许国家走上战争道路呢?其实,以上说法都值得再深究。
准确地说,希腊的民主政体(dēmokratia)是“平民(dēmos)掌权(krateō)”之意。“平民”这个词有时也表示类似现代“人民”的意思,即一国的全体公民,但更常指的是与少数拥有大量土地的“寡头”相对的底层民众。他们过去曾是自耕农,因为天灾或战祸收成不佳时不得不以土地为抵押向富人借债,一旦还不上就失去了土地,只能在城里靠当临时工赚取不稳定的收入,因此他们被称为雇工阶级(thētes)。同是一座城市的主人,贫富差距却这么明显,不免在寡头与平民之间产生冲突。在许多城邦,平民提出了彻底重新分配土地和免除债务的要求,因此爆发了暴力革命。
雅典的民主制正是为了避免重分土地而逐渐形成的一种阶级妥协:任何人就任执政官时必须发誓任内绝不进行所有权改革,而富人则接受平民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民众法庭等国家机关掌握政权。
掌握政权只是第一步,如果不能满足平民的经济诉求,革命仍然在所难免。与雅典的民主化进程相伴随的,是一场独特的历史机缘。公元前5世纪初,强大的波斯帝国入侵希腊。分散的希腊城邦唯有团结才可能打败波斯,而当时刚刚兴起的海军战术在岛屿星罗棋布的希腊地区发挥了高超的战斗力。雅典带领希腊各国的联合舰队击垮了这一波入侵者,但波斯实力仍在。担忧波斯再度入侵的城邦共同建立了提洛同盟,以维持一支常备的联合舰队。本来一直是希腊世界老大哥的斯巴达对此事务不感兴趣(原因下文会介绍),而海军战术最娴熟的雅典成为了盟主(hēgemonia)。此后许多原本向同盟提供舰队的国家,因各种原因改以支付军费(称为贡金)来负担盟约义务,以至于雅典海军在庞大财力支撑下越来越强大,称霸地中海东部。
雅典的这支庞大舰队与平民的经济诉求有什么关系呢?雅典平民为何拥抱帝国?

在当时,一艘三列浆战舰上需要170名划桨的桡手,以开战时雅典海军的规模300艘战舰计,就可以提供51000个就业机会。虽然全部战舰并不会同时出海参加军事行动,但一次出战经常达到60艘以上,也需要雇佣上万人。当时雅典成年公民总数不过4万左右,海军的存在让许多雇工得以经常获得每天1德拉克马的稳定收入。而雅典每年向盟邦收取高额贡金,大都用在了战舰的建造、维护和雇佣桡手上。希腊城邦的财富通过贡金、贸易和关税(雅典是重要的港口和货物集散地)源源不断地流向强大起来的雅典,使平民得以维生,大土地所有者(暂时)没有牺牲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就满足了平民的经济要求。
可是,舰队只在面对战争威胁时有用。一旦和平到来,怎样让庞大舰队的存在变得合理呢?确实,公元前5世纪中期,随着波斯势力再度入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许多盟邦认为无必要继续缴纳贡金,开始退出同盟。雅典人不能容忍同盟的瓦解,他们以武力征服脱离同盟的城邦,将其变为雅典的殖民地。于是,原来自愿建立的同盟,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雅典帝国(这里的“帝国”是就国际关系而言,雅典的政体仍是民主制)。
与雇工阶级在对外扩张上利益一致的乃是日益富庶的雅典工商业者。古典学家弗朗西斯·康福德(Francis Cornford)从史料中重构出这一经济集团对于雅典帝国的形成和走向战争发挥的重要作用。雅典舰队征服之处,多是雅典进口粮食和出口各种制造业产品的目的地和途中战略要地。康福德认为,之所以战争后期雅典在四面受敌的状况下还派出一支史无前例的大型舰队去远征西西里岛,正是为了实现工商业者打开西部市场的宏图。然而修昔底德出于对伯利克里个人的崇拜,没有把后者晚年在政坛上处处受工商业利益集团牵制的情况写出来,这就导致这一点在其书中只留下了蛛丝马迹。
相比之下,雅典的两个农业阶级(大土地所有者和普通农民)几乎没有分享帝国扩张的红利,但一人一票的民主政体下他们无法对抗人数占优的雇工阶级和影响力强大的工商业者。战争爆发之后,斯巴达陆军每年都开到雅典城郊,将城墙外的农作物蹂躏殆尽,让农业阶级苦不堪言。农民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眷恋的家乡田园,搬到有城墙保护的城内居住,挤在神庙等公共建筑或临时搭盖的茅屋中栖居。此后瘟疫大流行,这些进城人员大批地死去,雅典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可以说,他们成为了雅典强国之路的纯粹牺牲品。
走向战争的真正陷阱:骑虎难下的强国模式
雅典帝国的跨国剥削体系使雅典帝国四处树敌,有意脱离雅典控制的城邦往往互相串联同时发难,并向科林斯和斯巴达等反雅典的大国寻求支援。雅典不得不先发制人地打击有叛离倾向的城邦,并主动拉拢原来中立的城邦加入联盟以增强实力,哪怕这些城邦被科林斯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在所不惜。这两种情况分别发生在两个距离雅典数百公里的城邦波提狄亚(Potidaea)和科基拉(Corcyra),其结果则导致了科林斯煽动其盟友斯巴达与雅典开战。
雅典帝国如此庞大,难道就不能牺牲一点局部的利益来换取和平吗?毕竟,一旦真正的大战爆发,平民也不免在海军战事中阵亡。然而修昔底德借一位雅典外交代表之口说出了雅典帝国的“无奈”(I.75):“这个帝国不是我们以暴力手段获得的,是由于你们(指斯巴达)不愿和蛮族作战到底,同盟者才到我们这里来,自愿请求我们为他们的领导者。随后的发展迫使我们扩充我们的帝国,达到现今的程度。我们的主要动机是恐惧,尽管随后荣誉和利益接踵而至。然而,当几乎所有的同盟者都厌恶我们之时,当一些同盟者暴动并已被镇压之时,当你们对我们不再有昔日那样的友谊,反而处处怀疑我们、与我们作对时,放弃我们的帝国就不再安全了,因为任何同盟者反叛后都会投入你们的怀抱。”
其实,修昔底德在这里点出的这种自我劫持的强国模式,才真正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陷阱:当强盛起来的大国吮吸别国人民劳动成果,靠扩大经济基本盘来逃避阶级矛盾时,灾难的种子就已经埋下;当人民从外部的持续输血中获得经济快感,就再也不可能戒除;而帝国一旦因扩张而四处树敌,就反过来论证出了维持帝国强大的必要性。这时,即使帝国势力范围中最边远最无关紧要的部分在敌对阵营的支持下发动反叛,也将触发世界大战:因为如果听任帝国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小弟”反抗,“大哥”的权威就会消失殆尽,帝国就必然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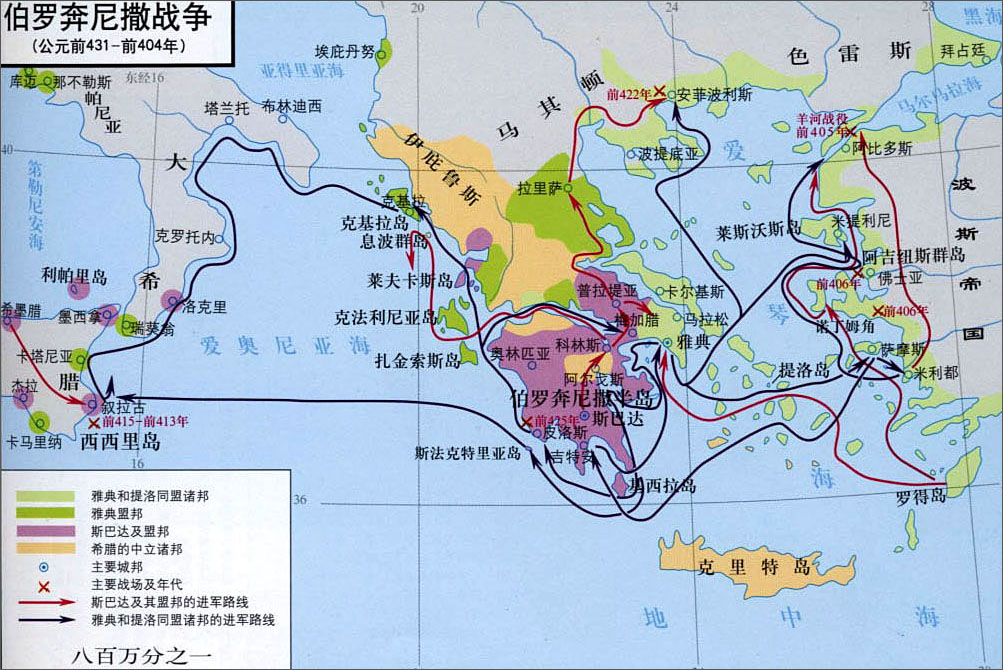
斯巴达:热爱和平的残酷统治者
再看斯巴达一面。我们对斯巴达的印象大概是他们对奴隶的残酷统治,以及其公民群体的整齐划一、千人一面、服从纪律。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斯巴达也许算某种专制政权。许多人以为专制政权总是喜欢侵略扩张,这其实是一种好莱坞式幼稚的“邪恶轴心”想象。大多时候,专制政权忙于保住自己已经有的,而无暇再去取得新的。斯巴达也是如此。
斯巴达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就是将临近的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两个城邦吞并,将其全体公民变为奴隶,这些奴隶被称为黑劳士(Helots)。他们不满残酷的统治,经常企图起义复国。相比之下,雅典从未听说过奴隶起义的事情,因为雅典的奴隶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是非希腊人,他们语言不通、缺乏联系,虽然社会地位相似,却缺乏相互认同和情感纽带,因此各家各户的奴隶固然可能和自己的主人有矛盾,却无法形成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并且总的来说,雅典公民对待其奴隶是温和、宽松的。
可以说,斯巴达强大军事力量的基础,正是对人数数倍于自己的黑劳士的残酷压迫。奴隶劳动让斯巴达人得以脱离生产、全民皆兵,但奴隶起义也成为最大的隐患。正如修昔底德所说(IV.80),斯巴达政权“所采取的大多数政策总是以防范黑劳士为基础的”,而不是什么海外扩张。事实上,斯巴达人根本无福消受任何侵略扩张所得:在斯巴达,一切奢侈都被禁绝,如果官员被发现有什么奢华的生活享受,就很可能被检举落马。斯巴达公民之间的高度平等,保证了斯巴达公民之间不会出现其它城邦常有的阶级矛盾,一切矛盾都被转移到公民与黑劳士之间。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斯巴达自上而下都存在着强大的反战声音,甚至在进军雅典的路上还在不断派使者尝试和谈。斯巴达参战,既是其盟友(主要是科林斯)反复挑拨煽动的结果,也是担忧雅典力量过强会对黑劳士起义提供有效支持——确实,雅典在此后的战争中充分利用了黑劳士的力量,他们为黑劳士提供坚固的要塞和海军支援,帮助他们打游击战,使许多黑劳士获得了自由。
大国博弈背后:阶级斗争的暗潮
但是,如果仅仅从雅典和斯巴达双方来分析这场战争的原因,无疑忽略了雅典和斯巴达之外无数小国的能动性。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容易引导我们将大国博弈看成国际舞台上唯一的决定因素,而小国的行动似乎只是舞台背后无生命的布景。然而我们却很容易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看到小国官方或某一党派的使者到雅典或斯巴达主动请求干涉的例子。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主要讨论小国主动加入战争的一种最常见的动因:阶级斗争。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我们就读到这样一句话(I.23):“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这有时因战争本身造成,有时是内部斗争(stasiazein)的结果。”这里的内部斗争,就是前面所说的城邦内部寡头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因此这个词也常被译为革命或党争,而斗争的双方则被译为寡头党人和民主党人(即平民)。其实当时的两大阶级还没有形成当代政党那样严密的组织形式,但寡头们借助社交聚会确实形成了一些秘密组织,而平民则通过“平民领袖”(dēmagōgos)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平民领袖一般出身于贵族或工商业者阶级,但为了获得政治影响力,他们转而代表平民的利益。
阶级斗争可以靠暴力威胁下的政治妥协来实现(雅典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就是如此),但也可能发展为血腥的武装斗争。修昔底德写道(III.82):“民主党人和寡头党人到处都发生斗争,平民领袖们求援于雅典人,而寡头则求援于拉栖代梦(即斯巴达)人。在和平时期,人们没有求助外援的借口和意愿;但是在战争时期,任何一个党派为了寻求变革政体,总是愿意寻求援军以打击敌对党派,巩固自己的地位。”之所以民主党通常亲雅典、寡头党通常亲斯巴达,不仅有意识形态因素,也和雇工阶级与农业阶级的实际利益有关。雅典舰队所到之处,民主党人为其充当内应;斯巴达人兵临城下,寡头党人为其打开城门。希腊人似乎并不将此看做“不爱国”的行为,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本阶级在其中没有政治参与的国家就不是自己的国家。柏拉图描写了贫富分化让同一个城邦分裂为富人的城邦和穷人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则指出(《政治学》1276a):城邦的本质不是其领土或人口,而是公民按照一定的政体去参与政治;当参与的形式变了,新的城邦就不是原来那个城邦了。各国的党派为了换得某一阵营的支持,就心甘情愿地派兵参加那一阵营,战争正是因此才席卷整个地中海世界。
一国之中的阶级斗争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科基拉的例子在修昔底德看来是最典型的案例。科基拉寡头党人曾在议事会会场暗杀了平民领袖佩提阿斯(Peithias)等50人,被驱逐出境后又在境外建立据点骚扰该城的对外交通,导致了城内的饥荒。后来民主党人在雅典军队帮助下攻克了城外的据点,将这些他们恨之入骨的寡头党人俘获。尽管雅典将领已经尽力控制民主党人的愤怒情绪,将俘虏关押起来加以保护,民主党还是用计把俘虏骗出来,于是就出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IV.47):“俘虏到了科基拉人手中以后,全都被关在一个大屋子里,随后就把他们每20人一组带出去,捆在一起,要他们从两排重装步兵中间穿过;如果两排重装步兵中有人发现俘虏中有他个人仇恨的人,就加以殴打和戳击……大约有60名俘虏这样被带出去戳死。”剩下的人自知难保,在屋内以各种方式自杀。修昔底德感慨道(III.84):“那些被傲慢地统治而非温和以待的人,一旦找到机会就很可能以暴力报复;那些长期生活困苦的人不免觊觎邻人的财产,一旦法律不起作用就有意以犯罪来摆脱贫困;即使那些并非为了私利,而是为了追求平等而参加斗争的人,在不可抑制的激情驱使下也可能采取野蛮无情的过火行动。”
历史、人性与政治
修昔底德对于人性有深刻的兴趣。他之所以写下这本书,就是考虑到人性始终如一,想要知道 “哪些事将会在某个时候以相似或相同的方式再次发生”(I.22),就必须清晰地了解历史。人类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群体之间安全、利益和荣誉的矛盾,雅典人以对外扩张规避矛盾,终不免于一战;斯巴达人将一切生产加诸“外劳”之上,自己却终日担忧反抗;科基拉人将阶级敌人赶尽杀绝却并不能消灭阶级矛盾本身。在这场大战结束后的那个世纪,看到这一切的柏拉图决定将政治斗争消灭在灵魂深处,让欲望成为灵魂中受到统治的那部分;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更现实地看出了:政治并不能消灭矛盾和斗争,却应该是人类优雅地从事斗争的艺术与智慧。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