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指本文作者Charles McNulty,英国戏剧评论家)在翻阅乔治·奥威尔的作品集时,看到他对斯蒂芬·斯彭德和W.H.奥登这两位与他同时代的作家表现出了强烈的摒弃之情,他称他们是“爱赶时髦的娘娘腔”(译者注:这两位作家都是同性恋者)。此番言论令我十分震惊。我耸了耸肩,继续往下读。
而一年前,当我浏览宝琳·凯尔(Pauline Kael,美国影评人)的早期影评选集时,偶然读到了她对莉莲·海尔曼的电影《双姝怨》给出的差评。她的原话同样让我大吃一惊。凯尔先是抱怨“所谓女同性恋倾向不过是心理作用罢了”,接着她又添上了“画龙点睛”的一句:“我一直认为,女同性恋者之所以需要别人同情——是因为她们本身力薄才疏。”

这么几句反同言论倒不会让我对这些伟大作家的印象产生太大改变,毕竟他们才学过人、天赋异禀,没必要为了这些不当言论将其抹杀得一文不值。我并不指望过去的艺术家和评论家成为我们21世纪标准下的某种道德楷模,我也希望后人回头看待今日的时候,可以包容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无知和盲点。
当代人很容易对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大动肝火。其中缘由五花八门。目前,反性骚扰和反行为不检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场运动有望为娱乐业,以及其他许多行业带来迟到的改革。
在职场中,男性滥用权力、压制女性的现象已成为常态,这种过时的骑士精神也应该抛弃。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文化中存在的糟粕,这固然对社会进步有益,但正当大家对去除糟粕的作为纷纷表示赞同时,一个更加滑头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对于那些人品存在问题的艺术家,我们应该怀着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他们的作品呢?
近年来,跌下神坛的演艺界人士越来越多,可其中并没有我特别喜欢的。詹姆斯·托贝克(James Toback,知名编剧、导演,被38名女性指控性骚扰)的电影我一部也没有订购过。我也从未高看凯文·史派西( Kevin Spacey),把他摆到“大师”的位置。而我对詹姆斯·莱文(James Levine,指挥家,被指控性侵犯)的仰慕与关注,充其量不过是我在发展拓宽自己业余爱好时的一时着迷罢了。

但总会有某位我青眼有加、感到莫名亲近的艺术家,最终亲手打破我对他/她人品的一切幻想,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天来临时,我可能并不会干脆利落地丢掉此人的所有著作,删除此人的所有歌曲,亦或是下决心以后再也不去看此人的电影。我不会再对他/她着迷,这是可以肯定的,我甚至可能还会由此讨厌起他/她来,但我心里清楚,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和他/她本人应该分开来看,而且,几乎没有人在做人方面能够达到自己最伟大作品的高度。
这也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他的史诗巨著《追忆逝水年华》中所回归的主题。书中,叙述者追忆起自己年轻时参加的一场晚宴,在晚宴上,他遇到了本书主人翁——作家贝尔格。在光鲜华丽的斯万家族组织的宴会上,年轻的马塞尔坐在一群重要的宾客中间,感到诚惶诚恐,他很快惊讶地发现,贝尔格与他自己“在其畅达优美的书中缓慢而煞费苦心地构建的……一滴一滴,像钟乳石一样沉淀”的人物在外型上毫无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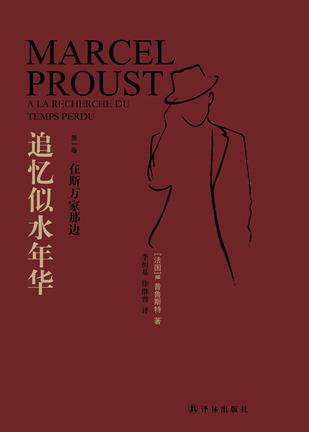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周克希等 译
译林出版社 2012年6月
比起贝尔格粗俗的外表,更令马塞尔糟心的是他那“忙碌自满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书里表现出来的大相径庭”。我们的叙述者是一个天生的哲学家,这次会面后他开始明白,艺术有时候并不来源于艺术家自己的具体生活。
拥有创作能力的人可以把一段经历转化成一面镜子,人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就是创作的独特魔力。有些品质能在社会中区分开不同的人,这些品质通常能成为你进入某个行业的敲门砖,但创作能力不是其中之一,创作能力是一种天赋。
书中,贝尔格深受邪恶的流言蜚语困扰,传言他“卷入了半乱伦之事,后来据说因为金钱方面的问题,此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马塞尔认为,“只有当一个人深陷恶习,无法自拔时,他内心无尽的焦虑引出所谓的道德问题”。对于普鲁斯特来说,艺术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会基于他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基于他所理解的生活真谛和以此衍生出来的存在方式;他的答案将会是一个浅显易懂的文学性答案”。
如果书或者剧本自己会说话,它们口中的故事一定会比作者笔下的世界更精彩,若果真如此,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局限和瑕疵将一扫而空,这样一来,作者将会更快地销声匿迹——出版业和身份政治强硬派本想让我们相信他们会活跃得更久一些的。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提出了著名的“作者已死”的观点;而普鲁斯特则认为,是作者使“身份多重性”这个概念逐渐成型,身份多重性即每个人的身份不是单一固定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包含了无数的自我,而且若想把它们分门别类也不是件易事。
一个以想象他人生活为生的人,必定有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一个创造美的艺术家则肯定比一般人更能接受丑。最近在参加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我非常喜欢他——的画展时,我又想起了这一点。他是一名具有革命色彩的艺术家,但背负着谋杀犯的罪名,传言他在与另一名男子争抢一个妓女时用拙劣的手法阉割了该男子,最终致其死亡。
说到血淋淋的凶杀案,就不能不提本·琼森(Ben Jonson)了,此人是伊丽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时代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家。他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一名演员,并因此被逮捕。然而,他的传记中显示,观众在欣赏他的经典喜剧《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和《福尔蓬奈》(Volpone)时依旧十分享受,乐在其中,丝毫没有被剧作者的私生活所影响。除了杀死剧院同僚的凶手这个头衔外,琼森的名头可多着呢,他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剧作家,学习过程中他研究了大量经典作品;他是莎士比亚的忠实拥护者;此外,他更是一名了不得的滑稽演员,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
历史是经典作品的试金石。作者本身的人品,以及作者的传记,则是影响读者对其作品接受程度的第二层因素,它们虽然能影响读者对作者的态度,却无法抹杀一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的表现力。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虽然疯疯癫癫,歧视女性,但直到今天,他的戏剧都还经常在各大剧院里编排演出,特别是他的《朱莉小姐》(Miss Julie),已经成为了经久不衰的剧目。
声名狼藉的当代艺术家则会受到更多关注。比如说,在伍迪·艾伦的养女迪莲·法洛(Dylan Farrow)爆出其性侵丑闻并提出指控后,演员还应该继续参演他的电影吗?好莱坞的良心(这个词真是大大的讽刺)已经经受过许多考验,在一波又一波的丑闻和一部又一部的烂片之后,好莱坞的试镜邀请函正在逐渐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但艾伦最棒的作品怎么办?反正我在短期内是不能直视《曼哈顿》(伍迪·艾伦1979年电影)了。这部影片中,艾伦对当时还是小女孩的玛利尔·海明威(Mariel Hemingway)处处垂涎,令人作呕,这还是在他爆出恋童丑闻之前就带给我的感受。但我真的可以做到再也不看《安妮·霍尔》、《丹尼玫瑰》和《汉娜姐妹》吗?我还做不到。这些电影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表演,包括米亚·法罗(Mia Farrow,艾伦的前妻,迪莲的养母)出演的好几幕,若是再也无法看到就太可惜了。好在艾伦电影的兴衰只掌握在我们后代的影迷手里,而不是由他在银幕之外所犯下的罪行所决定。

伍迪·艾伦一事,与美国夏洛茨维尔市拆除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将军雕像一事的性质不一样。在我的同事克里斯托弗·奈特(Christopher Knight)的带领下,我很乐意去看看这些纪念雕像,它们(一般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艺术价值,它们之所以放在历史展区有两个原因,一是保护其不受损害,二是提醒人们不忘历史。如果雕像的创作者是米开朗基罗或者贾科梅蒂这种水准的雕刻家(只是一种假设,此处可以有“笑哭了”表情),我的感受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我热爱那些拒绝炒作宣传和各种套路、让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作品。我是这些高级艺术作品的忠实拥护者。
名誉受损的艺术家就不得不另谋生计了。不管是潜规则演员的导演、肆意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胡作非为的演员,还是把黑手伸向孩子的指挥家,他们的丑事都活该被曝光。但如果他们的作品长留于世,人们终究会淡忘他们的恶行。时间会洗刷一切。
我们对这些偶像的堕落之所以感到震惊,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心中把他们供上了神坛,以至于后来无法接受这种落差。我们潜意识里认为自己的英雄是各方面完美的楷模,但(就像普鲁斯特指出的)在创作过程中,人犯些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可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不过,天才与疯子经常相伴而行,我相信每一个人物传记的读者都对这一点有所体会。
我承认,当我读到这些名人的性丑闻时,我的想法就跟推特上那些义愤填膺的网友一模一样——他们真是令人不齿。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许多人认为,这些人的罪行应该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判定,但我不禁思索,在我们都一股脑儿地为过去的事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会不会矫枉过正,把某一点过于放大而忽视了其他东西。
正义的衡量标准十分微妙。但正义与邪恶的分界线则非常明确——也必须明确。正义的势头一旦减弱,历史可能就免不了开起倒车。一个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含糊不清的社会,势必会掀起一场革命。但社会在发展,历史在进步,我们必须坚持原则,坚定自我,对恶行毫不姑息。历史是一个大染缸,因为人性是纠结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语言的发展映射着我们步履蹒跚的进步。我很高兴自己并没有因为奥威尔用“娘娘腔”一词讽刺别人就拒绝他的所有作品,因为在他的另一本选集里,我读到了他写给斯彭德的一封信,信中他向斯彭德解释,虽然自己在媒体面前说了一些伤人的话,但他一亲眼见到斯彭德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当你亲眼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马上意识到,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什么被贴上特定标签或符号的单薄漫画形象”。
再说回凯尔,在她早期的那些惊人评论背后,我看到的是她无所畏惧的坦率,正是这种坦率让她成为了独树一帜的尖刻评论家。她那些政治不正确的观点终将被时代淘汰,但她那直白而爽快的写作风格让她的影评得以长盛不衰。
有的读者可能不太明确我的立场,那么我在此开诚布公地说,我认为那些强奸犯、种族主义者、恐同者等都应该被封杀。但如果有一天,某项研究发现莎士比亚是个猥琐的虐待狂,我相信我并不会因此否定《哈姆雷特》、《李尔王》和《暴风雨》的文学价值。我认为,在看待当代艺术家时,我们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有些当代艺术家的人品并未达到其作品的高度,但不应因为这一点而抹杀他们作品的艺术价值。
(翻译:黄婧思)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