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真实形象和你对他想象可能分毫不差。特朗普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也有少数时候,你对一个人的想象与真实情况可能相差万里。遇见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之前,我对他有多少了解?我(指本文作者Rachel Cooke,记者、作家)知道他有一半荷兰血统,一半英国血统。我读过他的几本书,对书中流露出来的细致和才华钦佩有加——尤其是《阿姆斯特丹谋杀案:西奥·梵高之死和容忍的极限》(Murder in Amsterdam: The Death of Theo van Gogh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但却并没有爱上他的文字,也许是因为他很少透露自己的本性。去年,他从罗伯特·希尔弗斯(Robert B Silvers)手中接过了《纽约书评》主编的职位。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他正在用一种巧妙的方式重振《纽约书评》(视角更丰富,女性作家作品更多)。我的一位小说家朋友认为,布鲁玛是一个“很好的人”,人们在互联网上评价他时经常说他是“全球性的思想家”。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睿智、克制、略显冷漠的人。其实,我对荷兰人有一些错误的刻板印象:我觉得他们都有点儿冷漠。
后来我读了他最新的回忆录,所有此前的想法瞬间烟消云散。这本书实在是让我大开眼界。《东京浪漫生活》(A Tokyo Romance)记录了布鲁玛年轻时在日本生活期间(1975-1981年)的流浪冒险故事。初次在飞机上打开这本书时,我充满了不屑,以为它不过又是豪华版的间隔年回忆录罢了。实际上,它的确有点这种气质。布鲁玛先是描述了自己二十出头时如何渴望逃脱海牙中产阶级上层童年生活留下的“略显阴暗的环境”:住着花园洋房,沉迷于聚会社交。一到东京,他立即发现了生活的真谛。我们稍后会详细讲这个问题,但现在你只需要知道,布鲁玛沉醉于日本文化的起点是穿着高跟传统木屐四处游荡,终点则是他在地下导演和演员唐十郎(Kara Juro)合作的《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中出演了一个角色。旅日期间,他去过色情电影院,和众多男男女女保持情人关系,与伟大的黑泽明导演合作过三得利的威士忌广告。他还参加过舞踏(一种日本舞蹈,舞者通常浑身赤裸涂满白色粉末——译注)演出,只穿一条深红色的紧身内裤登台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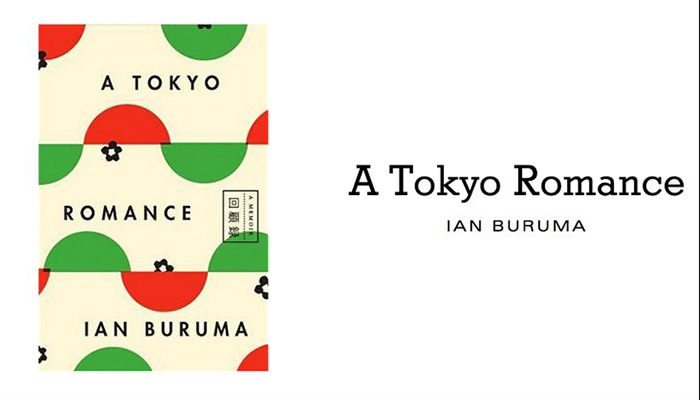
《纽约书评》的员工们是否知道他穿着紧身内裤登台的事情?如果知道,他们会不会就此事取笑自己的总编?我很想知道。不得不说,秃顶、戴眼镜、说话声音很小且有些克制的布鲁玛,完全符合我对他的最初想象。在他身上,我丝毫找不到回忆录中那个滑稽幽默、笨拙粗鲁、纯真无邪的性感年轻人的影子。我不禁疑惑:那个曾经的他去哪里了?今年一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在《纽约书评》极其时髦的办公室(位于格林威治村)见了面。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写回忆录时,他是否觉得他写的完全是另一个人?遗憾的是,他没有正面回答。虽然我被他的两面性深深震惊,但布鲁玛只是以温和的回应作答,好像他的书不是自白,而是练笔。他的表现让我觉得,这不是一本下定决心倾诉心声的回忆录,而是对往事的研究分析报告。
面对我的问题,他说:“是也不是。回忆录能让你认清自己,看清自己的阴暗面。我觉得大部分回忆录都会让作者感到尴尬——你回忆让自己畏避的往事,因为一些人去世而感到欣慰,最起码他们不会再记得你曾经做过的各种事情了。但是回忆录还有另一种特点——它有点儿像小说。实际上,将自己转化成书中角色是撰写回忆录的唯一办法。这能让你和角色保持一定距离。”想象力可能是《东京浪漫生活》之母,因为布鲁玛在日本期间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他说:“所有的一切都储存在脑海中。你记得一些片段和感觉,要做的就是将它们整合成连贯的故事。这个过程需要动用想象力。当然,记忆会受到影响。你总是在不知不觉间重新编辑自己的回忆。”
布鲁玛深谙其道。即便人物角色做对了事情,他也会通过笔法让读者觉得他犯了错。布鲁玛说:“我知道,如果其他人身上带有一点喜剧人物风格,你就要把自己写成更大的喜剧人物。这就像日记——好人不一定写的出最好的日记,最好的日记通常是由不胆怯的坏人写成,内容展现的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坏事。艾伦·克拉克(Alan Clark)就是个例子。蒂娜·布朗(Tina Brown)想在日记中把自己打造成令人愉悦的形象,但这种做法大错特错。”这并不是说布鲁玛是《东京浪漫生活》一书中最重要的角色。他还表示:“日本的生活是一段非凡卓绝的体验,当时在日本的西方人很少,可我始终无法用正确方式写出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后来我发现,我可以借助两个对我很重要的人(唐十郎和麿赤儿,两人都是舞踏名家,正是他们让布鲁玛穿着紧身内裤上台表演)展开故事,这就使得回忆录摆脱了完全的唯我论色调。确定好思路后,写起来就很快了。”

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他为何在多年前选择将日本作为旅行目的地呢?作为年轻人,布鲁玛厌烦好莱坞是正常现象。他的母亲是英国人,家族成员多是英国、德国和犹太名流,布鲁玛的叔叔是深受他崇拜的电影导演约翰·施莱辛格(John Schlesinger)。相较于那些度假时经常遇到的高雅亲戚,好莱坞显然太粗野了。在莱顿大学读书时,布鲁玛选择了学习中文。他觉得中文听起来很迷人,中国食物也很美味,不过他并不是个天生的汉学家。他在书中写道:“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经常和一个中国男孩跳舞,没怎么好好学习中国古文。相比于《论语》而言,中国男孩身上那股‘东方’气质更让我着迷和沉醉。”

但是之后发生了两件事。首先是他看了特吕弗(Truffaut)导演的电影《婚姻生活》(Bed and Board)。在这部片子里,一个年轻的巴黎男孩爱上了美丽却难以捉摸的日本女孩京子(Kyoko,由模特Hiroko饰演)。在电影中,京子似乎是某种幻觉一般的存在。布鲁玛没有理解电影想要表达的信息,却深深爱上了京子:“我想遇到自己生命中的京子,或许还想遇到不止一个京子。在京子们的陪伴下,我将无比快乐。”其次是他在阿姆斯特丹的Mickery剧院看了寺山修司(Terayama Shuji)先锋派天井桟敷实验剧团(Tenjo Sajiki)的演出。他回忆说:“那是一场非常奇怪、莫名其妙、充满色情元素的演出,相当令人惊恐,也很令人难忘。”剧中出现了穿着和服的食人魔、裸体女孩和涂着厚厚艺伎妆的口技艺人。经历了这两件事情,摆在他面前的选择似乎就只剩下一个了——不久之后,布鲁玛动身前往东京。
布鲁玛进入东京的日本大学艺术系学习,专修摄影技术。不过他的心思不在学术上,因为东京的诱惑力实在太大(后来他开始写电影评论,还做过摄影助理)。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是布鲁玛叔叔的熟人的朋友,也是布鲁玛流亡在外的同性恋朋友之一,二人经常聚会。他警告布鲁玛说,西方人永远融入不了日本,始终都是个外国人,因为他们的肤色像豆腐一样苍白。不过,日本赋予了布鲁玛自由,给了他塑造自我的无限可能。布鲁玛很喜欢日本:这是一个没有限制,没有不可能的世界。
舞踏就是很好的例子。迷上舞踏后,布鲁玛开始跟着麿赤儿手下的舞者训练,陆续参加一些演出。表演期间,布鲁玛只能穿着紧身内裤站在台上,任由穿着银色比基尼短裤的女舞者在身边舞动。演出结尾,他还要用手接住舞伴。不幸的是,布鲁玛舞步并不熟练,因此未能集中注意力观察舞伴的动作,最终女舞者重重摔倒在了舞台上。这让他退缩了吗?没有。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另一场演出。这次他扮演希特勒:涂着白色妆容,只穿一条紧身内裤,伴着拉威尔的《波列罗舞曲》翩翩起舞。演出到高潮时,剧团成员穿着缀有鱼干的服装上场。这次的演出比上一次成功不少。
最令人兴奋的部分,还是布鲁玛和唐十郎的友谊。1978年,唐十郎说自己写了一个新剧本,内容包括迷宫、空中飞舞的肉饼、变装皇后、狗神、因胎盘发生的争斗和纳尼亚之旅。布鲁玛听了一阵迷茫,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同意出演“外国人伊万”。用他的话说:“这个角色可能是俄罗斯人,但他宣称自己是午夜牛郎(布鲁玛叔叔导演的代表作也叫《午夜牛郎》)。”这一次布鲁玛要头戴皮革毡帽出演,还要跟着公司参加巡演,坐着面包车在城市之间穿梭。也许这不是他日本生活最幸福的时光。在一次演出时,他彻底忘记了台词。不过,布鲁玛最大的失误是介入了唐十郎和妻子Ri的争斗。他也许觉得自己很仗义,但实际上,此举反映出了他真实的渴望。唐十郎怒吼说:“到头来你还是个普通的外国人!”这句话让布鲁玛终身难忘。多年后决定离开日本时,唐十郎的话依旧在他脑海中回荡。布鲁玛说自己因为担心“染上外国人的气质”而离开日本,他害怕自己无法摆脱“与种族身份息息相关的、想象中的轻蔑和怠慢”。
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的布鲁玛依旧对文化非常痴迷,喜欢坐在法国的咖啡馆里享用咖啡。他说:“努力融入当地生活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不过,如同年轻时对亨利·米勒的热情已经消失一般,他现在也丧失了曾经那份无耻的自信。他说:“年轻时你觉得自己无懈可击。”布鲁玛仍旧定期去日本旅行(妻子堀田江理是日本人),因此不会陷入另一种移居海外之人常落入的陷阱:“我总是发现,很多年老的移居海外者越来越保守。这是因为他们离开的国家已经变了,而他们还不适应,因此不愿意放弃原有的理念。我从不离开太久,这样就不会出现保守的问题。”虽然如此,他所了解的日本也已经不复存在。“日本先锋派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世界也是如此。日本的先锋艺术是世界先锋艺术在日本的变种,但村上春树的小说风格却与先锋艺术完全不同,他的作品充满隐居色彩,非常西方化。”
初看之下,《东京浪漫生活》与布鲁玛的其他作品很不一样(不过他所有的作品都很颓废,一位美国评论家曾说,布鲁玛描述核心情感时喜欢让读者感到迷茫,而不是为读者打开一扇大门)。但是,如果你不再把注意力放在书中朝塑料伞里小便的女演员、厕所里的激情和所谓的“人肉打桩机”上面,你就会发现,《东京浪漫生活》也体现着布鲁玛一如既往的风格:关注没有共同文化限制的社会可能出现何种问题。他说:“你的想法很对。”这让我想起他的《阿姆斯特丹谋杀案》。2006年出版时,此书代表了布鲁玛的巅峰文学水准。但是如今看来,它不过是有点恐怖的娱乐作品罢了。布鲁玛告诉我:“没错。荷兰反穆斯林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几乎未在书中有所体现。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布鲁玛如何看待英国脱欧?“这是一生中最令我震惊的政治事件。我感觉好像被刀捅了一样,很是痛苦。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脱欧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他曾预见到英国会脱欧吗?“没有。我当时更担心特朗普会当选。”展现了二战场景的电影《敦刻尔克》广受欢迎,对此布鲁玛有些惊讶:“人们对二战的关注表达了一种情绪,最近的很多事情也是如此——目前统治世界的这代人对二战并不了解。在我们的成长阶段,世界掌握在一群害怕世界大战再度爆发的人的手中,他们竭尽全力确保世界和平。因此民族主义势头不强,大家更愿意团结合作。如今,真正的法西斯修辞正在悄悄回归主流。因为忘记历史,人们也渐渐忘记了战争的惨烈和痛苦。”

有着15万读者的《纽约书评》应该如何抵制这一切?“我们永远充满怀疑,所以稍微有点儿左翼倾向,《纽约书评》是少数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刊物之一。我们不需要政治上的重新定位,但是我们生活在特朗普时代,因此,相信容忍和民主的媒体肩上有了新的责任。当然,如何应对才是大麻烦。仅仅嘲笑特朗普的粗俗没有任何意义,你需要坚持自己的理念。”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社会问题。在布鲁玛看来,部分英国媒体也很失败。“《观察者报》(Spectator)以前是非常厚脸皮的自由主义者,如今它变得和《每日邮报》一样了。原来它的精神内核源于优越性,现在它对世界充满着怨恨和失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很多人因为怨恨和失望被纳粹所蛊惑。总有些二流和三流小说家、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不受重视,《观察家报》身上已经开始出现这种不好的心态,他们觉得世界将自己抛弃了。”
布鲁玛是如何当上主编的?他回忆说:“雷·赫德曼(Rea Hederman,《纽约时报》的出版商)和很多人吃午饭时表示,要找到应对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我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做到,所以毛遂自荐了。事情就是这样。《纽约书评》的每个人都很聪明,读过很多书,我要理解和吸收大家的想法。前任主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五十多年,他比所有员工都年长许多,是绝对的最高统治者。我不会沿袭他的作风,我更喜欢民主一点的氛围。”
我们又聊了一会他最近在读的书: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的《日记》(Diaries)、克雷格·布朗(Craig Brown)关于玛格丽特公主的新书。他说:“我不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此时,办公室角落里传来了年轻同事的迷人笑声,他的注意力似乎也被吸引过去了。采访结束后,我在湿冷的夜色中向酒店走去,努力想要将两个布鲁玛匹配在一起:一个是真实世界里的布鲁玛,一个是我读过最奇怪、最玄幻回忆录中的布鲁玛——但这就像追逐两只鸽子一样不切实际。最后,我放弃了思考。看到红灯亮起,我决定转头去吃一顿寿司。
(翻译:Nashville Predators)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