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鄙视译者,他是人类文明的驿马。”亚历山大·普希金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一方面,译者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译者和驿马一样,是不出风头的劳动者,甚至常常遭到轻视。由国际译联(全称国际翻译家联盟)牵头、由50位翻译界学者共同撰写的《历史上的译者》一书,将目光转向常常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译者,追问译者为人类思想演变做出了什么贡献。读者会发现,如果没有译者,世界史和人类文明史或许会被彻底改写。
译文的直译与意译之争、忠诚与美丽之辩已经绵延了上千年。今天,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依然认为,好的译文应当不见译者痕迹,让读者感觉就像是在读原文一样。这种要求无可厚非,只是对译文通顺、忠实的要求亦会造成“透明”的错觉,让译者成为隐形人。正因如此,翻译常常被认为是机械劳动和“二等艺术”,全世界范围内的译者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为翻译所作的努力常被忽视;译者名字的字号往往比作者小一号;译者的报酬通常极低……英国外交部首席中文译员林超伦曾经说,有一次开会组织方问到:“茶杯、麦克风、口译员,准备好了吗?”把译员和茶杯、麦克风并列,可见翻译地位之低下。
而实际上,作为历史主体的译者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可小觑。为了揭示这一点,1963年,在国际译联的第四次大会上,匈牙利学者拉多博士率先提出要展开翻译史研究。国际译联理事会决定创建专门的翻译史委员会,计划撰写跨越2500年之久、囊括古往今来各种语言的世界翻译通史。由于范围太大,这项计划不得不被搁置。在1990年,国际译联制定了新的撰写计划,由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教授朱迪斯·伍兹沃斯(Judith Woodsworth)和翻译理论家让·德利尔(Jean Delisle)担任主编,由五十位学者集体撰写《历史上的译者》一书。此书于1995年出版,2012年的新版本进一步强调了后殖民主义和非西方视角。国际翻译史研究界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目标始终如一,他们希望“通过揭示译者对人类知识史和文化史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翻译职业的发展”。
今年4月,中译出版社推出了《历史上的译者》一书的中文版。本书由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管兴忠组织翻译,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青年长江学者马会娟审校。日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了朱迪斯·伍兹沃斯,听她谈了谈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如何让人们开始重视译者在历史上的贡献;并在之后采访了管兴忠和马会娟两位教授,邀请他们讲述了译者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作用和在当下面临的种种困境。

主编:(加) 让·德利尔、朱迪思·伍兹沃斯 译:管兴忠 等
中译出版社 2018-4
朱迪斯·伍兹沃斯:人们认为翻译比写作低级,没想到过译者的贡献

界面文化:《历史上的译者》一书的写法,受到了新史学注重“来自底层的历史”的影响。在你看来,译者相对于谁来说是底层呢?是什么原因导致译者长期以来处于底层或者说边缘地位?
朱迪斯·伍兹沃斯:译者相对于原作者来说是底层。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依然认为翻译和写作相比是低级的——人们说翻译是一面镜子,是一副不同颜色的绘画,是一首用不同调子演奏的乐曲。有的时候人们觉得翻译是机械劳动,人们会说“你就用另一种语言把字都打出来”。
在过去,译者没有署名权。甚至到现在,一些国家的译者名字不在书的封面上出现,翻译的报酬也比作者低。不过幸运的是,在加拿大,译者的报酬常常是政府机构提供的。翻译一本文学作品的报酬还是可观的,只不过版税都给了作者,并不给译者。我自己也翻译文学作品,在签合同的时候体验过底层的经验。出版商合同告知我的名字会在书的第一页出现。我写信问,“不在封面上吗”?得到的回答是,“译者名字并不总是在封面出现的,但是你的话我可以放封面”。最终,出版社也的确把我名字印在封面上了,但是字号非常小,作者名字的字号则很大。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不过,我认为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译者了。现在有很多小说和电影中有与翻译相关的故事,例如《翻译风波》《迷失东京》等。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是“transfiction”(翻译小说),这些小说里的人物是译者,或者小说以翻译为主题,这些创作是把译者推向公共视线的好方法。回到《历史上的译者》这本书,它致力于体现的就是译者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阅读这本书,读者可以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译者的贡献。

界面文化:这本书的写作可以追溯到1963年的国际译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会议。到1990年,委员会又制定了新的翻译史撰写计划。从提出到成型之间,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能否谈一谈“文化转向”对本书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朱迪斯·伍兹沃斯:在上世纪60年代,匈牙利学者拉多博士提议我们应当写作一本世界翻译通史,内容涵盖迄今为止所有国家、所有语言的翻译,但这项工程太浩大了,没有人能够完成得了。所以到1990年,让·德利尔说,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写作这本书,有焦点、有选择地进行这项工程。也正是这个时候,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让我们从过去注重语言学的方向转移开,不再过于关注文本——追究译文是直译还是意译,和原文相比是否忠实。在“文化转向”之后,我们关注译者的主体性以及文化、政治等背景下的译者,还关注译者如何传递理念,引起思想、文学、宗教等方面的变革。过去的翻译历史大多关注语言学和文本,但这本历史书完全是一种新的样貌,是文化转向给我们的写作打开的一个全新的世界。
界面文化:如今我们不难看到,不少书评在谈论翻译的时候常常赞扬的还是译笔流畅、忠实等等。在文化转向之后,你认为这类讨论过时了吗?
朱迪斯·伍兹沃斯:我自己做翻译会尽量做到忠实,不过有时候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一些文化内涵,我会加上一点解释。
书评人评价一本书的时候,会说“作者写得真美啊”,但是也许原作者写得根本没有那么美,是译者的功劳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书评人可能本身并不懂源语言,也没有翻译研究相关的知识,所以在评论一本书的时候,不会意识到译者在里面做了哪些功课。理想的状态是书评人通晓两种语言,能够懂得译者在其中使用了归化还是异化,是不是用了很多注释来对文化内容进行解释。一个好的书评人不仅会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他们应该也会看到译者的努力,告诉大家译者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好让读者阅读起来更方便。

界面文化:书中提到,后殖民理论及翻译实践重塑了翻译,突出了其中的权力问题,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成为了“权力转向”。能否具体谈一谈?
朱迪斯·伍兹沃斯: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总是受到权力因素的影响。我可以给出一个例子就是新教改革时的圣经翻译。在英格兰,《圣经》是由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翻译的。当时,亨利八世为了生儿子不断地结婚,但是天主教会不允许他离婚,所以亨利八世和罗马教廷决裂,并创立了英国国教。丁道尔当时对亨利八世的离婚行为进行了批评,于是亨利八世将他以异端罪名逮捕入狱,施以绞刑,将尸体焚烧在火刑柱上。大约与此同时,马丁·路德在德国翻译《圣经》。德国当时不得不给罗马提供大量的资金,德国人对此并不乐意,马丁·路德认为应该把钱留在德国,所以,他得到了很多普通人和当权者的支持。马丁·路德和威廉·廷代尔做的事情是类似的,但他却没有被捕或被杀害,这和译者与当权者之间的关系有关。
界面文化:这个“权力”指的是什么?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还是其他什么?
朱迪斯·伍兹沃斯:我们可以在翻译里看到各种层次的权力。从大的层面来说,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权力。也有更小层面的权力,比如在某个社群之内的权力。对于翻译研究来说,权力视角不是唯一的视角,但却非常有用。翻译不是一个单独发生的现象。可能你会说一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因为它应该被翻译成中文,这句话不一定准确,可能是某些权力关系在其中发挥作用,而且很多内容被翻译或者不被翻译都与权力结构有关。
苏联时期一些作家不能写作发声,他们就借助翻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在翻译时,对译文进行了再创作来隐晦地批评当权者。例如,哈姆雷特说丹麦的一切都是腐朽的,帕斯捷尔纳克就加了一点内容以批评斯大林统治。但因为它只是翻译,人们也没有太注意。而如果这是他自己的创作的话,肯定要被审查了。在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也是一样的,人们翻译美国左翼小说,由于是翻译作品所以被容忍了,不然一定会遭到镇压。
界面文化:你能从自身经验举例谈一谈女性是如何通过翻译来争取权力的吗?
朱迪斯·伍兹沃斯:有一段时间,女性被允许进行翻译,但是不被允许进行原创。人们认为翻译这种“二等艺术”是适合女性去做的,女性可以在翻译工作中运用自己的创造力。为了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女性开始出版自己的翻译作品。
在加拿大的女性主义运动里,很多女性法语译者利用翻译作为挑战男权语言的工具。法语区分阴阳性——杯子是阴性,桌子是阴性,篮子是阳性。当你说“他们”的时候,你说的是阳性的“他们”或者阴性的“她们”。人们常常用阳性的“他们”,因为阳性包括了阴性。女性主义者厌倦了把阴性包括在阳性里的做法,所以不论是什么情况都会使用阴性。虽然人们常常说“他/她”,可是女性主义者只说“她”——这样做是对语言的颠覆。加拿大女性主义者这种做法不仅是在翻译,也是把翻译作为与男权社会斗争的工具。翻译家芭芭拉·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翻译了很多魁北克作家的作品。举个例子,她曾翻译过一本魁北克女同作家的作品,这本书名字叫做《情人》(les amantes)——大家一般会用“les amants”,但是这本书用的是“amantes”,意思是女性情人——所以芭芭拉想了一个办法,在英译本中把“lovers”拼写成了“lovhers”,生造了一个词来挑战现有的语言规范。

如今加拿大最著名的翻译家都是女性,最著名的作家也是女性,这种现象可能和其历史有关。在历史上,加拿大的男人负责修建铁路、砍伐树木、冶炼钢铁等,女性则在家读书写作、教育子女,男性没有时间做这些。
界面文化:书中提到了历史上的翻译做出的诸多贡献,那么我们今天的翻译还能够做出这么多的开拓吗?毕竟,如今我们还面对着人工智能对翻译职业的威胁。
朱迪斯·伍兹沃斯:很多人问我:“你还教翻译啊,不能用电脑翻译吗?”我告诉他们,机器能够翻译,但是会犯很多错。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三门课程和机器翻译相关,他们可以学习如何利用机器。机器翻译的记忆库来源于译员的输入和翻译,如果过去译员有过翻译,那么机器可以记得;但面对新内容时,机器翻译还是会犯错,到最后还是需要译员来优化翻译结果。人工智能不能够最终解决问题,因为它依然需要人类来开发和进化。在文学作品领域,人工智能更不能代替人类。如果翻译的是某银行财报,也许每年的语言风格都是类似的,只要修改具体细节就可以,但文学作品的翻译每次都是原创性的。
这次我们来到中国,看到宾馆的指示、公交上的标语,很多东西都已经有英语标注了,但是这些英语写得特别糟糕。也许人们应当意识到,这样做对国际形象并不是很好。现在在加拿大,我们也有很多中国制造的物品,购买之后我会发现里面使用指南的翻译写得很糟糕,这对产品的形象并不好。如果大家使用的都是蹩脚的语言,对交流是不利的。在我参加的国际会议里,与会者来自很多国家,比如土耳其、挪威、芬兰、中国、日本,他们都说英语,但说得都不够好,如果有专业译员的话会更好,这些领域都应该招聘翻译专业的学生。我不觉得大量的译员在未来会失业,因为随着各国交流的愈加频繁,对翻译的需求也会增长。也许机器可以让翻译过程更迅速,但我们还是需要译员做更多工作,译员依然会是不同国家之间交流的中介。即使翻译专业的学生毕业以后不从事翻译工作,学习的内容也会在其它工作中得到运用。

马会娟、管兴忠:翻译推动中国近代化,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
界面文化:《历史上的译者》这本书提出要走出欧洲中心主义,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书中有关欧洲翻译历史的部分还是占了很大篇幅,相较而言中国的内容并不是很多。
马会娟:《历史上的译者》的发起方是国际译联,它的宗旨并不是宣扬强势国家的翻译历史,而是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翻译研究。虽然目前高校的翻译理论教学都是以西方为主,但是这本书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大洲,而是写出了全世界的译者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涉及中国的内容不是很多,或许和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化合作的程度相关。这本书的撰写团队来自多个国家,中国部分只有黎难秋和徐式谷两位作者撰写,可能出于他们自身的研究兴趣,中国部分仅谈了佛经翻译和科技翻译的译者。虽然整本书涉及中国的内容比较少,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丰富的翻译历史。
界面文化:书中提到,译者与民族文学的兴起有关,翻译为个体作家确立了范式和灵感,从广义上讲还为整个目的语文化提供了新的文学方向。我们能在中文中看到例子吗?
马会娟:翻译影响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改革。以鲁迅为例,他是旧时代文人,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是用文言文写的。鲁迅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和他阅读大量翻译文学作品以及自己进行的大量翻译实践密不可分。鲁迅很早就关注弱小民族的翻译作品,而他影响最大的《狂人日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受到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的影响。夏志清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不是很高,因为其模仿性很强,但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不论是写作技巧还是思想内容都是开天辟地的。
王小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读了很多翻译文学,承认自己的文学师承是查良铮、王道乾等翻译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显然受到了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作家的影响。莫言的英文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经谈到莫言、余华等中国当代作家没有能力去读英文原著,可以说,他们这一代作家是靠阅读翻译文学成长起来的。葛浩文还特别遗憾地说,如果中国的作家能够像村上春树一样有世界眼光,他们创作内容可能会更加国际化,视野会更开阔。

管兴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很多作家是通过翻译来了解小说的写作模式,而中国的古代文学也与翻译有不解之缘。季羡林说中国的文化有两股活水,其中一股就是佛经。(注: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字典》作序时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时候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伴随着佛经翻译,印度的说唱文学也来到中国,给我们的小说、戏剧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印度文学非常天马行空,给我们打开了想象的大门,例如《西游记》就明显受到了印度佛经翻译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如今还有轮回、涅槃等词汇,都和佛经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界面文化:我国在近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一整套源自欧洲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概念所造成的冲击,翻译是否也会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知识体系建构?
马会娟:翻译在我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举例来说。人们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是也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通过翻译引进到中国的。1920年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就是由陈望道翻译的。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促进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再如,从经济学的领域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孟子、管子等先贤都有很多经济思想,却没有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系统的经济学是从国外依靠翻译引进的,概念更新、术语创立也都依靠翻译完成。在我国,京师同文馆最早开设了经济学课程,并翻译了《富国策》一书(注:该书介绍了创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叙述了商品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等经济学理论, 详细介绍了资本、地租、利息、价值、工价、钱币、 税敛等经济学概念, 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著作),这是第一本把国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翻译到中国的例子,比严复译亚当·斯密的《原富》还要早二十年。如今还有很多经济学术语,仍在沿用《富国策》的翻译创造出来的术语。在近代历史上,很多中国人向日本学习,而日本翻译的第一本西方政治经济学著作又比中国早了十年,仅仅是从书的译介时间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
管兴忠:就像普希金说的,翻译是“译者是人类文明的驿马”,中国近现代接触西方思想都是通过翻译完成的,像“德先生”和“赛先生”等概念、严复译《天演论》里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等等,都对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翻译就像一面镜子,我们也可以在镜子里反思我们自己、看到自己的长处。翻译西方思想的严复在自己的后半生对东西方进行了反思,他说,“在我的晚年,我见证了共和体制存在的七年,也见证欧洲前所未有的四年血腥之战。……今天,当我再次回想孔孟之道时,才发现其包容广阔之处。”(《历史中的译者》第311页)我认为,翻译的另一个重大作用,是在帮助读者接触西方思想之后也能帮助反思我们自己,寻找自己的文化自信。
界面文化:《历史上的译者》专注于探讨译者主体性的问题。今年年初村上春树新作中文版问世,国内读者为村上译本再次吵得不可开交,林少华的译文虽然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也遭到了诸如“浓妆艳抹”等一些批评。这里是不是林少华发挥了他的译者主体性却不受认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马会娟:每一个译者都有自己的风格。翻译更像绘画,而不是照相,画家在作品里一定会体现个人的意志和主观情趣,这难以避免。比如傅雷翻译法语小说,肯定有傅雷的风格在里面。只不过其中有一个度的问题,要看译者个人的风格是否凌驾原作风格之上。傅雷说:“翻译最难的是在过与不及之间。”如果原文非常朴素,译文过于华丽,那么可能是过了;如果译文达不到原文那种风格,那就是不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有个度的问题,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
界面文化:人工智能对翻译职业是威胁吗?
马会娟:我的学生也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常常问我们专业会不会失业。我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其中创造性的因素是机器翻译代替不了的。现在也可以让机器写诗,但是这样写出来的诗只是语言的堆砌,读起来文字也不错,却没有灵魂。机器翻译能够取代一些机械的翻译工作,特别是非文学材料的翻译,也能够帮助讲不同语言的人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帮助理解文字的大概意思,对人类社会是有帮助的。但是在准确度和创造性方面,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说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工翻译,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它对翻译职业构成威胁。相反,人工智能能够把译者从一些机械、枯燥的翻译工作中解放出来,让译者从事更富有创作性的工作。

界面文化:据我所知,翻译的酬劳相对来说很低,即使是挣得比较多的口译工作也被视为“青春饭”。现在国内很多翻译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都不从事翻译工作,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马会娟: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大的翻译浪潮。一次是佛经翻译,一次是西方的科技翻译,还有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作品大量翻译,这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很多新思想。我认为第四次翻译浪潮就是现在,因为国家现在要“走出去”,对译者有很大需求,所以目前全国有250多所高校都有翻译硕士项目,但是学生毕业后真正从事的工作并不仅仅是翻译,翻译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即使是对高级口译员来说,翻译也可能是青春饭,因为随着年龄增大,以及工作十几年后译员反应的灵敏性和对工作强度的适应可能会下降,人们很难仅凭翻译赚钱谋生。
英国外交部首席中文译员林超伦曾经说,有次开会组织方问,“茶杯、麦克风、口译员,准备好了吗?”把译员和茶杯、麦克风并列,可见翻译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很受重视。有时我自己也很纠结,一方面翻译为推动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特殊时期,也能够让人释放思想、给人存活的意义,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诗人穆旦由于受到管制和批判,不能创作,但却翻译了很多外国诗歌。可以说,是翻译让他活着有价值,有活下去的勇气,翻译是这么重要。可另一方面,译者的报酬非常之低,译者为什么要去做翻译呢?不是为了钱,是为名吗?对高校教授来说,他们也不需要依靠翻译获取名声。很多时候,做翻译是因为觉得这个工作有价值。葛浩文说,自己喜欢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乐趣。翻译带来的乐趣和翻译工作的报酬还是两码事,我呼吁社会尊重译者,给译者应有的报酬。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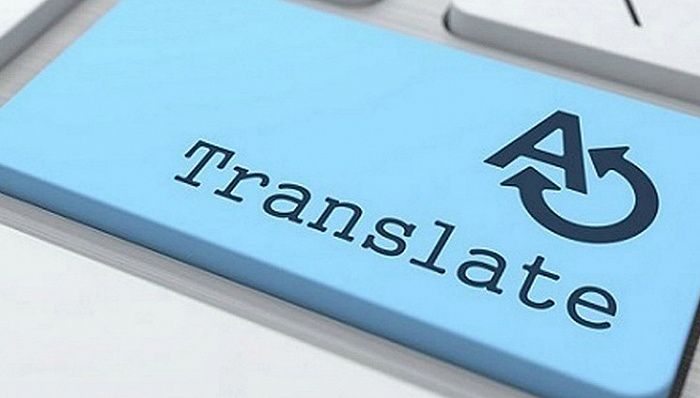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