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已过去四分之一,自2017年而始的 #MeToo 运动仍未停止发酵,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全球。
演员们在发声,学生们在发声,职员们在发声,性工作者们在发声……可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运动。我们很难在以往的公众事件中看到如此多行业、身份、标签下的人们一齐站到台前,勇敢地揭露性侵者。
然而,一些声音还没有被听到、被注意。她们的发声少之又少,却不容忽视。

三月底,一场探讨残障、社会性别与暴力的主题沙龙暨项目启动会在京举行。这场由中国残障观察CDO主办,国际助残联盟(法国)北京代表处及有人公益基金会资助的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
当生活相遇残障,残障邂逅性别,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何让残障和社会性别这两个交叉议题获得更多的关注?
看见
“希望大家看到,看到残障女性在生活可能遇到与残障有关,与性别有关,以及这两个议题交叉后的这些问题。”
——蔡聪,有人基金会残障项目总监,在开场讲话中。
分享中,作为社群个人代表的彭玉娇首先谈到媒体对残障人士的认知与塑造。在百度中搜索“女性”,图片所展现的女性形象是美丽的、健康的,多白人女性;搜索“男性”,可以看见帅气的、充满力量的男性,大部分是白人男性;搜索“残障者”,出现的是群体的现状——生活困难的、需要被照顾的弱者。
也就是说,残障者不分男女,成为失去性别、失去个体形特征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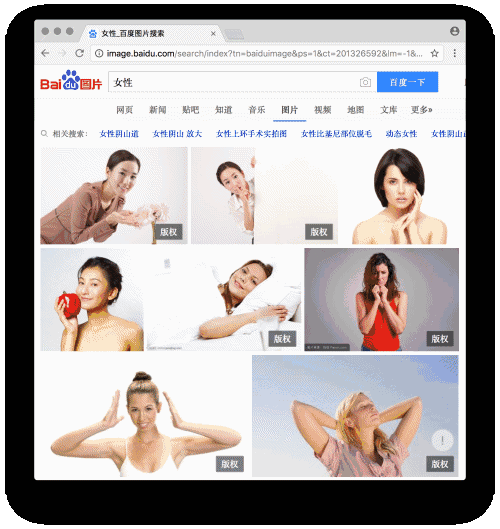
每个肢体健全的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都必然经历性别分工的过程;“男生力气大,女生力气小”、“男孩子去做消防员,女孩子去做护士”等类似言论十分常见,周围人会根据性别提供关于可能性的建议。
至于残障者,他们的性别根本不被人看见,所有分工可能性直接被抹杀;如有人基金会的蔡聪在《奇葩大会》中分享的那样,周围人看见他,都是“可惜了,这辈子完蛋了”诸如此类。残障者整个群体的可能性被一刀切,判定为无,自不用说残障女性。
我们很难想象残障女性在权益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难度之大。2009年,郑州大学的蒋美华、赵子廉以河南省为例,对残疾女性的生存境遇作了调查,总结出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力资源开发不足,就业水平较低;
(二)婚姻家庭不够稳定,容易陷入贫困状态;
(三)所接受的服务和服务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四)遭遇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对待。
残疾女性除了要遭受因残疾而带来的歧视外,还要遭遇因重男轻女的刻板观念、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对待——与残疾男性相比,残疾女性的文盲率高,在业率低,享受低保、接受救济的比例均低于残疾男性。
九年过去,情况似乎没有大的改变。
如果说残障者出生之后是hard模式,那么残障女性一来到世界就迈进了地狱模式。如上文所说,刻板印象中,残障者一般被认为缺失可能性。可以想见,如果残障女性的亲人都秉持着残障者等于残废者的想法,那么残障女性的生活肯定不好过,“我到底是谁”,身份缺失感可以杀人。
由于家长制观念的影响,残障女性被认为是弱小的、没能力自主选择的,尤其是农村残障女性,很有可能会被包办婚姻。生育抚养小孩方面,也有种种担心,残障女性往往会被怀疑是否能孕育健康的后代,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母亲。
此外,残障女性遭遇的暴力也是更为隐性的,上学时可能被校园霸凌,在家中可能遭遇家暴,接受志愿服务、医疗服务时,可能被性侵……

纪录片《算命》中,厉百程通过别人了解到常年被家人虐待的石珍珠,用130块钱将石珍珠带回家,两人成为夫妻。
残障女性面临的种种独特挑战都表明着,将残障女性拿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议题来讨论是有必要的。她们需要专门的舞台,需要站出来,需要被世人看见、得到关注。
赋能
广东省残培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李远红通过图文和视频,作了残障女性赋能的项目分享,提出:残障女性赋能的两个目标是——帮助残障女性提升对身份的接纳与认同,建立自信心;培养性别意识,使其更有能量去面对歧视与压迫。
在残障女性成长项目中,赋能的模式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培训-成长;第二阶段,成长-改变;第三阶段,改变-支持他人。
首先,在全国各地招募想要在社区学习、改变的残障女性,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性别、残障接纳、女性领导力以及亲密关系等议题。培训结束后,基金会将提供给学员三百块钱,让学员利用这笔钱,自由地探索想要去做什么,可以去做什么,通过小型活动挑战、认清自己。最后,对有意愿、有计划去联络社区、去举办推动残障议题发展相关项目活动的学员,基金会支持三千到五千块的项目资金。
这些项目经验极具启发性。在社会对残障者的印象中,残障者要么做算命、按摩的工作,要么闭门家中,不会自理,缺乏工作的能力;甚至,连残障者自身也可能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自我认知往往受到他人评价的影响。
此外,过去对改善残障女性境遇的建议,也往往着眼于宏观,例如,倡导文明的残疾观、增强残疾人社会政策的性别敏感度、发展残疾人教育等。毫无疑问,这些建议是有用的,但从残障女性个体角度出发,这些建议就难免显得大而空了。
加上社会对女性的刻意贬低,在这种大环境内,残障女性很难认识自己的力量。如果对自己的能力有正确的认知,她们的人格、视野、经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蔡聪曾经讲过自己对考上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第一个聋盲人的采访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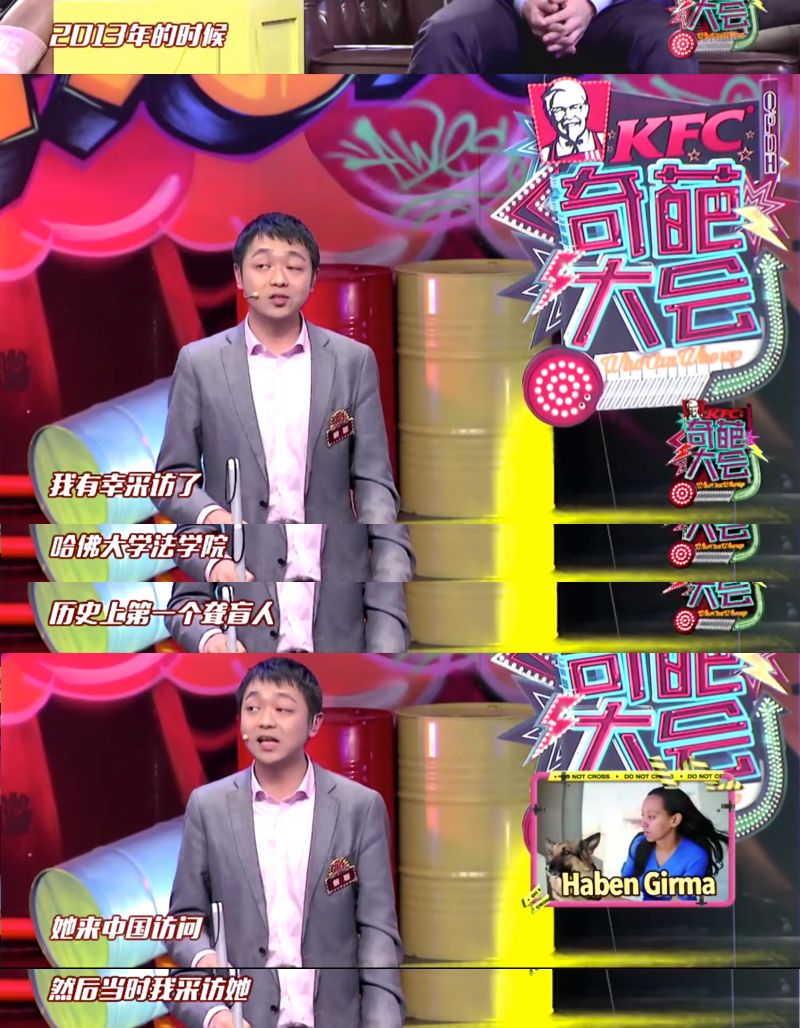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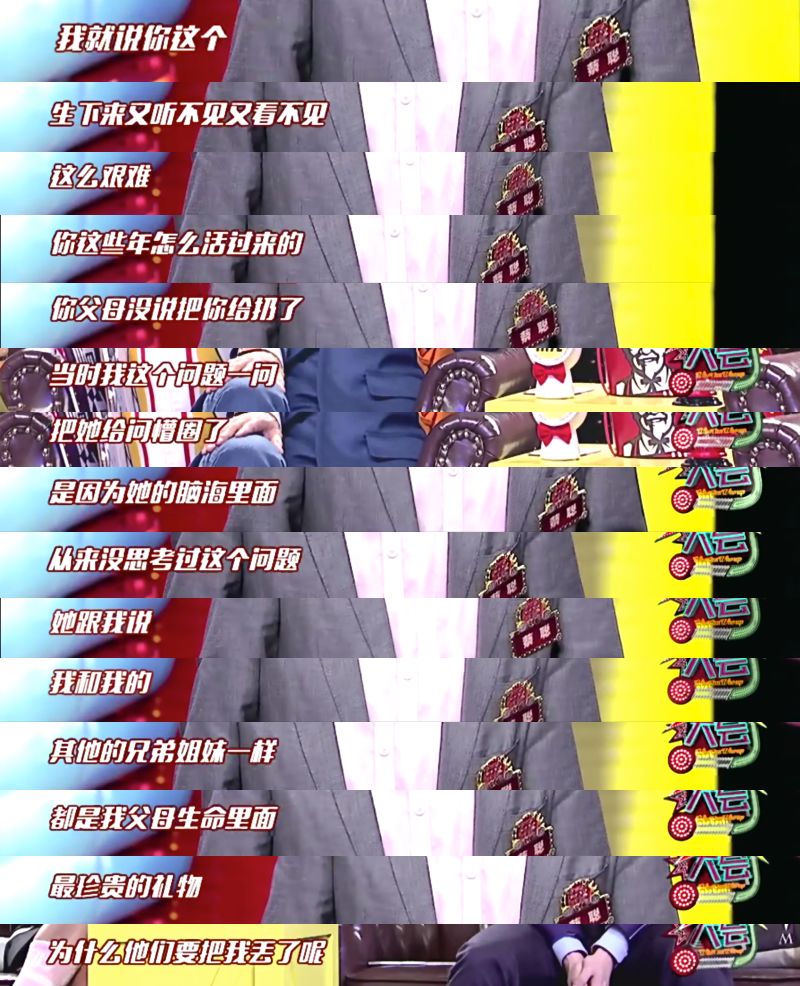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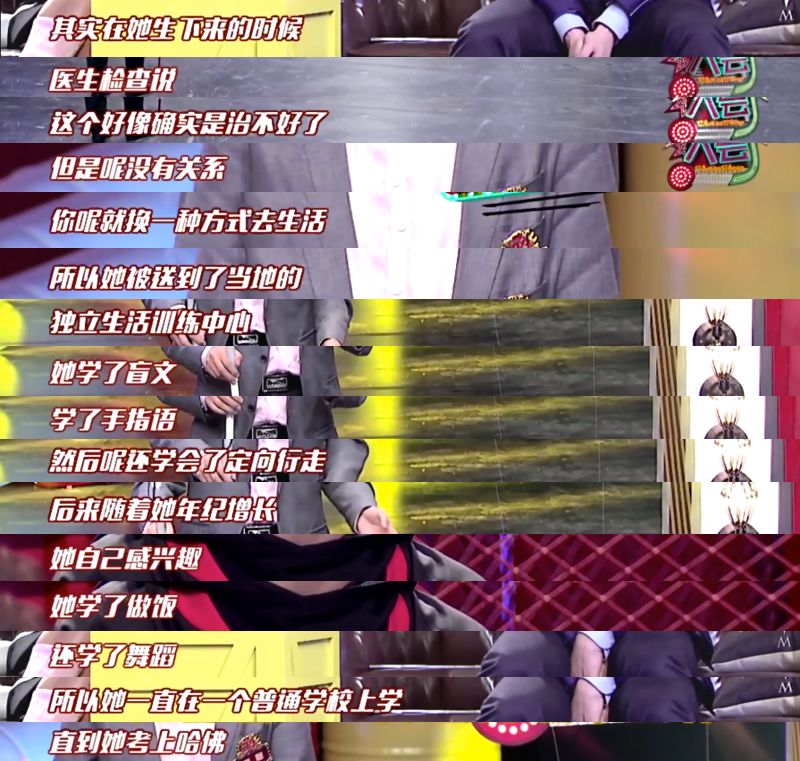
从中可见,赋能残障女性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如果让残障女性认识到,自己只是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生活,那么她们的人生该有多大的不同?
合作
如何让残障女性获得更多的关注,如何赋能残障女性,这些问题共同指向一个方向——残障组织与女性组织的联合。那么,残障组织与女性组织如何强化连接呢?
彭玉娇认为,残障领域与女性领域可以在三个方面合作。
第一,救助体系的合作。比如,残障女性拨打求救电话,普通反家暴救助组织不知道如何提供帮助,那么残障组织可以在前期为反家暴救助组织提供培训,使能更好接待残障受暴者;
第二,议题方面的交融。残障领域加入性别意识议题,性别领域可以加入残障议题,两方相互学习;
第三,就业援助。残障组织可以吸纳LGBT人士,实现性别多元化,性别组织、女性组织可以吸纳残障女性,使身份多元化,两方可以在公众倡议层面上共同发声,吸引媒体的关注。
李远红认为,残障女性以往被排除在女性范畴外,很难意识到性别暴力,没接受过性别意识教育的残障女性很难发现性别暴力方面的问题。因此,残障组织与女性组织应该在教育、实践方面多接触、合作。
有人基金会的项目官员马薇介绍了她们即将开展的残障与社会性别暴力项目,希望能通过这一项目,增强残障组织和社会性别组织的能力建设,加强两方的连接,识别出导致残障女性和女孩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的主要形式和关键因素,减少隐形的和提出更多有效阻止残障女性和女孩遭受歧视和暴力的情况,使残障女性和女孩在基于性别的暴力议题上获得关注。
国际助残的项目官员王雪洪为此次项目提供了方法论,即“行之有效”(Making it Work)的工作手法。为促进残障融合问题,“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采用多个利益相关方联合、建立联盟和合作的方式,使残障女性在与他人一样平等的基础上,充分而有效地参与到社会中。
能看到这里的读者们心中大概都已有自己的想法。回到那两个问题:当生活相遇残障,残障邂逅性别,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如何让残障和社会性别这两个交叉议题获得更多的关注?这里写的只是一部分,期待你的发言。
注: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作者井+,喜欢动物。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