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标准的自拍角度:将头稍稍偏一点,一边脸朝镜头,这样我的眼睛就一直是斜着看镜头的。我会尽量避免直视,以掩盖我双眼的不对称——因为我先天眼睑下垂,后天又做过许多矫正手术。侧面的角度再加上一点斜视,缺点就不那么明显了。我还喜欢仰拍的视角,可以清晰地拍到我棱角鲜明的下巴,这能让我看起来严肃很多。笑容也是有讲究的,我紧闭双唇的样子有点滑稽,所以我会一直保持嘴巴微张,但是不能张得太大,露出两颗大门牙就更傻了。还要做出一些表情,嘴角向上轻轻一提,神情带着些许茫然,这副模样一看上去就知道,你相信自己可能比实际上的你更好看一些。
先别急着喷我。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我每天去上班的路上都会经过时代广场,走下来至少要看到一打这样的自拍脸——不自然地嘟着嘴,眼睛睁得大大的,下巴也伸得老长。所以,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种想要捕捉和投射完美自我的欲望从何而来?罪魁祸首是我们口袋里的手机吗?是它的吸引力太难以抗拒,是它塑造了欲望本身吗?还是这种自恋是现代自我的一种本能,在技术对我们产生影响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智能手机给了我们释放天性的机会?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技术决定论蓬勃发展的时期,人们总是担心Siri、Instagram或者YouTube会改变我们的大脑,改变社会和政治的运作方式。1993年,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Technopoly)出版,警告世人文化已经成为了技术的奴隶;近些年,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The Shallows)中分析了互联网如何毒害我们的大脑,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人类变得愚钝不堪……这个书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这些著作虽然有争议,但它们已经成为了技术悲观论者的“圣经”。可想而知,自恋的话题也适用于同样的套路。社会心理学家W·基思·坎贝尔(W. Keith Campbell)以诊断“自恋流行症”(注:narcissism epidemic,坎贝尔著有同名图书,中译名为《自恋时代》)闻名,他反事实的论证打破了这一套路:“我们不晒自拍,也可以在网上‘晒妈’啊,每天给妈妈拍照上传,配文字突出我爱我妈、光辉伟大。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做了,自从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诞生以来,几乎所有人拍的都是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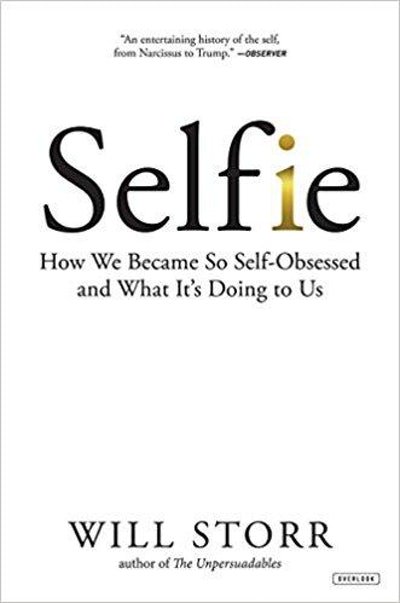
威尔·斯托尔 著
英国记者、小说家威尔·斯托尔(Will Storr)在写作《自拍:我们如何变得如此自恋,自恋对我们又会带来什么影响》(Selfie: How We Became So Self-Obsessed and What It's Doing to Us)一书时采访了很多专家,坎贝尔也是其中之一。斯托尔在书中花了很多篇幅,洋洋洒洒地描述了现代的、自我驱动的西方式自我。除了书名中所体现的数字时代特征以外,全书只在第二章和最后一章写到了硅谷。我在文章开头所描述的那种诡异的自拍脸并不少见,斯托尔一直在试图回溯自拍脸的源头,最终发现这其实源自于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生物学的基础之上,决定我们有自拍需要的是2500年来的文化积累。从亚里士多德、耶稣、弗洛伊德、安·兰德到伊莎兰学院(注:The Esalen Institute,美国加州的一个非营利静修中心和心灵社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人类潜能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专注身心联系和个体意识,很多学说在后来成为了主流)都脱不了干系——他们对自拍的影响比乔布斯要重要得多。
斯托尔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他对自己的自我厌恶。为什么他总是觉得自己不行?他认为自己和很多人一样,有一种神经质的完美主义,一直在被理想中的自我所压迫,他应当是个“世界公民,外向、苗条、美丽、个人主义,乐观积极,勤奋向上,有社会意识,自尊水平也很高,还带一点企业家的狡黠,手里还得握着一支自拍杆”。这个理想化的存在我们在Facebook上应该经常见到,那个好友跟我们并不熟,却总是能看到他度假的照片,背景是美丽的海滩,身边是相亲相爱的家人,这种不现实的自我幻想绝不只是一个小烦恼。对于斯托尔来说,幻想会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它是可以实现的,这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他甚至引用了自杀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他将这种完美主义的起源追溯至人类社会最早的部落本性,那时,为了在部落中生存下来,个体开始对社会等级和地位变得敏感。斯托尔相信,部落生活使得人类在基因上更倾向于“共处并领先”。也是从那时起,文化进入了人类社会。古希腊的山脉犬牙交错,岛屿遍布,海湾纵横,这样的自然景观不适合农业的发展,当地的个人和社群于是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相互之间是竞争关系,不论制造或出售什么商品都要一较高下。公元前8至7世纪,赫西俄德写过“陶工与陶工竞争;工匠和工匠竞争;乞丐忌妒乞丐;歌手忌妒歌手(注:译文摘自《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竞争和忌妒催生出了一种自我完善的精神。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艾德丽安·梅约(Adrienne Mayor)所写,亚里士多德认为,包括人类在内,“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在追求他们潜能中的完美”。

希腊人炫耀成功的渴望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则变成了一种禁欲的斗争,人们得通过祈祷和鞭笞来控制自我,对抗内心的邪恶,追求心灵的纯净。虽然焦点变成了灵魂,但是理想化的观念依然存在:一个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凭借坚定的个人意志和足够的努力去达到完美。中世纪过后,斯托尔跳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直接写到了弗洛伊德。他认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中,本我和超我的斗争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这只不过是基督教改造人性之恶的一个世俗版本。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弗洛伊德稍晚提出的“自我”理论(根据斯托尔的说法,这个理论诞生在20世纪的加州),这才是后世为之疯狂的理由,斯托尔的后半本书也完全转向了围绕“自我”而展开。
斯托尔也去到了太平洋海岸边的伊莎兰学院,他说这个地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当时的会心团体(注:人本主义的心理治疗小组,会心团体的原则是从“以个人为中心”发展而来的“以团体为中心”)里,人们的情绪都被充分唤起,通常是负面情绪,他们会朝着想象中的父母大吼大叫,结束时他们通常是在互相指责,甚至哭到断片都很常见。心理治疗需要从混乱的社会期待中挖掘出个人欲望,过去的疗法是让来访者学会控制压抑的情感,而伊莎兰学院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式——来访者可以去咆哮怒吼,将情绪发泄出来。很多原先信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人在伊莎兰学院被自由化了,他们在那里无拘无束地四处徘徊,赤身裸体,甚至不时伴有勃起。现在这种会心团体依然存在,只不过形式有所不同,斯托尔也去亲身体验了一把。这一流派存在的假设前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值得被爱的、有神性的,我们想要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只需要忽略别人的看法,伸出手去,接受它。
在这些认知的基础上,“自尊”开始变成了一个热门概念。斯托尔讲述了约翰·瓦斯康塞洛斯(John “Vasco” Vasconcellos)的故事(这是一个冗长而又有点离题的部分),他是一位加州议员,深受伊莎兰学院观念的影响,他将自尊当做预防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疫苗”,筹措到充足的资金后,他在加州创办起了一个“自尊运动”特别工作组。创办过程中存在不少争议,奥普拉也亲自出面为这项运动背书。没过多久,孩子们就得到了参与“自尊教育”的奖赏: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学区要求体育课上学生跳绳的时候不用绳子,目的是为了避免被绊倒造成孩子自尊心受到伤害。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自尊运动”中,斯托尔找到了“自恋流行症”的源头。

所有这些“自我优先”的做法,和战后的社会秩序是相一致的,人们开始尊崇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个体命运完全取决于他的财富和名望,经济的发展(斯托尔将其称为新的“滋生自我的土壤”)也让自恋者得以享有特权。撒切尔夫人在1981年谈到她的自由市场政策时说道:“经济学是一种方法,其目的是改变灵魂。”斯托尔还写到了纳撒尼尔·布兰登,他既信奉伊莎兰学院的自尊崇拜,也相信成功学所说的“贪婪是件好事”。他是一名心理治疗师,是安·兰德的情人(比她小了25岁),同时也是加州议员瓦斯康塞洛斯的精神导师。他在瓦斯康塞洛斯的特别工作组所做的笔记中写道,孩子应该“爱上自己的存在”,要有能力“在最大程度上,以最高尚的、最不被这个世界理解的方式去践行自私”。
历史发展到这里,社交媒体开始兴起,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Instagram账号和iPhone,这样的时代又加剧了病态的自爱。手机里无所不能、极具理想化的自我,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文化谎言”——斯托尔在书中愤怒地这样指称,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但是有趣的是,斯托尔形容社交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只是这个“谎言”的推动者,而非创造者。CJ是一位20岁的女孩,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自拍,全年无休(“我在葬礼上也自拍,很真诚严肃的那种”),斯托尔在她的身上看到了根深蒂固的自尊文化,看到了教会她推销自己的经济学。在这些原因当中,手机只是次要的。
**
斯托尔只是想简简单单地讲一个故事,结果他的主张被夸大了。就像还原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个人主义可以追溯到希腊崎岖的地理位置,自尊的概念则起源于大苏尔(注:伊莎兰学院的所在地)悬崖边的一个学院里;他们还会指责Facobook根本无法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斯托尔对历史的梳理其实并不严谨,他跳过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节点,比如说启蒙运动、科学和工业革命、民主的崛起,还有从电报诞生以来,技术的发展对传播方式造成的影响。在塑造现代社会自我的过程中,这些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斯托尔的书只是挑选了一些生物学、文化和经济学上的事实,所以你读到每一页都可以评价说:“是这样的,但是……”
自拍最好能被当做一种必要的矫正,在自拍的瞬间,人们能够专注于自身的特殊性。我不像斯托尔那样关注现代社会自我的状态。还有不少很好的论据支持我们自拍——瑞秋·赛姆(Rachel Syme)在声援女权主义者时说,把相机对准自己是在为自己赋权,因为在这时,主体和客体都是自己。我认为大多数人如果在夜里关掉手机,很快就会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即便自拍会让人沉迷无限的可能和完美的前景,他们也会认为这种谎言比伤害更让人安心。在谷歌或者亚马逊发明一款APP可以消解人必死的命运之前,我们都会一直保持谦卑的。
我们还应当摒弃这种想法:我们的技术就是我们本身,我在用什么,我就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斯托尔可是帮了大忙,他指出了现代社会的自我其实是“一袋吵吵嚷嚷的鬼魂”。袋子里有亚里士多德,有伊莎兰学院,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事物。他的书以这种方式对人文学科——对历史、文学、哲学、宗教——进行了一次致敬,而这些学科平日里都在手机屏幕的亮光下显得黯淡无光。如果有更多的人能相信,我们的文化财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看自己的方式,他们也许会愿意放下手机,仔细地去了解它。
本文作者Gal Beckerman是《纽约时报书评》编辑,著有《若他们冲我们而来,我们就会消失:拯救苏联犹太人的伟大斗争》(When They Come for Us, We’ll Be Gone: The Epic Struggle to Save Soviet Jewry)。
(翻译:都述文)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新共和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