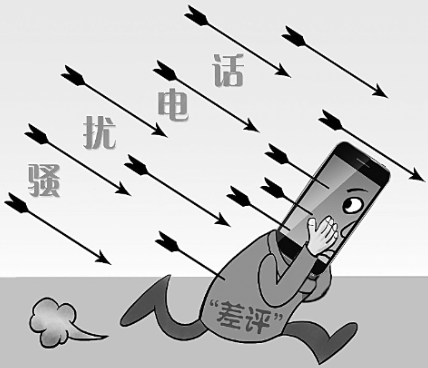
不到半个小时,陆续接到十多个推销电话,对方坦言,对不起,我无法控制给不给您打,这都是后台系统自动拨出的号码。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赵晨熙
“您好,需要买房吗?”
“您好,需要贷款吗?”
……
汽车、房子、贷款、保险……对于每天都会接到的各类推销骚扰电话,北京小伙赵亮一直自认“免疫力”挺高:“如果是疑似推销电话的,我会接通并客气地告诉对方不需要;如果是已被软件标记的骚扰号码则会直接挂断。”
不过最近他有点“崩溃”,在短时间的密集推销电话轰炸下,忍无可忍的他向政府热线投诉,却吃惊地得知,电话骚扰目前缺乏相应的政策规制。
被外包的电话推销
“半个小时内就给我拨打了10多个电话,这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赵亮想起来就直摇头。
“您好,碧桂园的别墅有需要吗?”当挂断了这个房产推销电话后,赵亮下意识地记了下这个头4位为“5350”的电话号码。
不到一分钟后,“5350”这个号码再度来袭,仍然是碧桂园房产的推销电话,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赵亮又陆陆续续接到了十多个头4位为“5350”的电话来电,他注意到,这些座机号码虽然头4位数字一样,但每次来电的后4位都不一样,这样即使用拦截软件标记了当前这个电话号码,仍无法阻止其他骚扰电话的入侵。
其间,赵亮曾质问一位推销员为何要连续骚扰自己。“对不起,我无法控制给不给您打。”对方告诉赵亮,这都是后台系统自动拨出的号码,接线员只负责和系统接通后的电话通话。
“这些打推销电话的其实都不是本公司的员工,多数都是企业找的第三方电话销售公司。”在北京某房地产企业工作的曹旭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现在很多有推销需求的企业,都喜欢将电话推销业务外包给这类电话销售公司来“广撒网”,对筛选出的靠谱客户资源,再由公司派人直接打电话做进一步深入交流。
“电话销售现在一般集中在房地产、金融理财和教育培训等几大领域。”曾在某电话销售公司任职的陈强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这些电话销售公司一般隐藏在小区或写字楼内,一部电话、一个耳机、一个记事本,就能开始工作。
陈强原来所在的公司大概有20多名“专业接线员”,其中不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电话销售公司入职门槛很低,基本只要能够熟练背诵客户提供的“推销话术”,并具备一定的心里抗压能力即可上岗,薪酬由底薪和绩效提成组成。
正如推销员向赵亮坦陈的那样,当前通过拨号机器由后台控制直接拨号基本已成为现在电话销售公司的主流模式,推销人员不用按照电话本自主拨打,而是由拨号机器自动拨打电话,用户接听后,将自动转接给分配到的接线员。
“这样做不但能节省电话推销人员自主查号拨号的时间,也能防止一些推销员出现不打或少打电话的偷懒行为,更重要的是后台电脑可以分派不同号码重复给同一用户推销,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客户将号码设置成黑名单。”陈强说。
骚扰电话:监管真空地带
不堪其扰的赵亮选择了拨打“市长热线”投诉,但得到的答复却让他大为吃惊——“如果对方给您发垃圾短信,有相关条款可以对其进行处罚,但是针对电话骚扰,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政策来规制。”接线人员无奈地表示,针对这一问题当前只能由用户自行下载拦截软件来拦截。
“骚扰电话确实是当前监管的一个真空地带。”长年关注个人信息安全领域的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直言,近年来相关部门对垃圾短信治理虽有一定成效,但却相对忽视了骚扰电话的问题。
3年前,由工信部发布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就已明确,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否则将会受罚。但这一规定并不适用于骚扰电话。
在刘德良看来,骚扰电话其实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通话、休息和工作,涉嫌侵犯了他人的通信安宁、通信自由权。虽然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中都有关于保障公民人身权益的条文,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可处以行政拘留及罚款,但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并无具体法律条文对骚扰电话现象进行直接的认定约束,所以很难对其进行处罚。
4月,360互联网安全中心发布的《2017年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示,近5年来,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数量尽管有所下降,但总量仍然惊人。2017年全年,360手机卫士平均每天为全国用户识别与拦截1.04亿次,平均每天被用户标记的各类骚扰电话号码约66.4万个。这其中,广告推销类骚扰电话占比居首位,达79%;其次为房产中介骚扰电话。
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骚扰电话屡禁不止的势头。相比企业电话推销这类相对“温和”的方式,有的公司甚至开发了恶意呼叫软件,将骚扰电话作为报复、恐吓的工具。
比如,这两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呼死你”软件,就是利用费用低廉的网络电话作为呼叫平台,在一段时间内对特定电话号码高密度集中呼叫,导致被叫电话无法正常使用。
减少维权成本,加大违法成本
“骚扰电话不仅让用户不堪其扰,更大的危害是其背后潜在的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强调,从此前针对垃圾短信的治理来看,出台专门的法律规范来对骚扰电话强化监管,加大打击力度势在必行,应通过明确骚扰电话的概念、方式、禁止性条款及处罚制度等方面来对其进行约束和规制。
“减少维权成本,加大违法成本是关键所在。”刘俊海进一步强调。
刘德良对此表示认同。他坦言,尽管当前针对垃圾短信有相应的法律规制,但实际中却鲜有因此维权的,原因就是维权成本过高。
一方面,用户遭遇垃圾短信或骚扰电话的号码非常多变,有些甚至被软件伪装成国外号码,被骚扰者往往很难取证,掌握骚扰者的真实身份,根本不知道应该告谁;此外,根据当前法律,垃圾短信、骚扰电话侵犯安宁权等权利一般只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法院大多不会受理,除了遭受诈骗外,被骚扰者也难以就单纯接到推销电话、垃圾短信等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加之司法维权成本大、时间长,很多人只得对这种行为选择隐忍。
所以刘德良建议,出台专门的法律规范,必须增加受害者请求财产赔偿的权利,“从某种程度来说,接听骚扰电话其实也是在占用用户电话的信道,有可能造成用户错失接听重要电话的机会”。
此外,可以借鉴美国等地建立的电话防打扰名单制度,用户加入这个名单之后可以通过对各类骚扰电话录音来要求相应骚扰企业等进行经济赔偿。
对于当前存在的一些电话销售公司,刘德良认为除了应对它们进行规制外,对背后雇用此类公司频繁给不定向客户打骚扰电话的企业也应追究连带责任。
电信运营商的责任义务同样不应忽视,运营商除了应对各类涉嫌频繁拨打骚扰电话的号段或虚拟号段等进行打击外,也有义务不断提高技术手段进行防范。
个人信息保护需专门立法
刚看了房就会接到各种房产中介的电话;孩子刚到上学年龄,各类培训班的消息就随之而来;实际中,很多骚扰电话或垃圾短信更是能直接准确地叫出用户的名字。在刘俊海看来,其背后的根源都直指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上学、上班、购物等日常生活中需要登记的信息;没有妥善处理的快递单;网站注册、外卖平台填写的资料……实际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在不经意间就泄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许多机构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将获取个人信息作为捆绑的前提条件,也为信息泄露留下了巨大隐患。
一些企业、政府机关内部倒卖个人信息的“内鬼”更是让信息泄露防不胜防。
“一些电话销售公司就会购买各类的用户信息。”陈强透露,用户信息完整度越高,售价就越高。此外,某些特定行业的高端用户信息也非常值钱,有的一条就能卖到几十元钱。而像普通民众的信息基本属于被倒卖过多次的“二手”信息,一般都是打包出售,一条信息平均也就0.01元左右。
其实近年来,针对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法律一直在不断完善,包括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网络安全法中要求运营者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首次就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但刘俊海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所以还是应尽快出台一部综合性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保护等制定有效的指导和规范。建立一部专门的法律也有利于为公民维权、打击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等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近年来,学界其实一直在呼吁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刘德良看来,个人信息保护几乎涵盖民众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涉及部门多、内容复杂,这是法律出台的难点所在。
从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来看,刘德良认为过多将重点放在了个人信息公开和泄露领域,但却忽视了对个人信息滥用行为的有效规制。
除了完善法律外,刘俊海强调,对于有可能造成信息泄露的行业、网络平台等也应不断加大自查、自律、自我完善的力度来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
以信息泄露的一大重灾区外卖平台为例,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从今年6月起,全国几大主流外卖平台将自动默认开启“号码保护”功能,对商家和外卖骑手隐藏用户真实电话号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