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爱尔兰共和国废除第八修正案的公投获得高票通过。该修正案“承认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权”,并要求爱尔兰政府捍卫这一权利。也就是说,在修正案通过以来的35年里,女性在几乎任何情况下堕胎都是非法的。这意味着怀孕的妇女要被拉到法庭上,政府任命律师就胎儿的死活展开辩论,然后做出医疗裁决。这还意味着这么多年来,爱尔兰女性都得出国才能做堕胎手术,而这本是可以在国内完成的——这样的女性的数量据说有17万。
66.4%的爱尔兰人为废除这项修正案投了赞成票,这个数字比最近任何一个民调都要高,也超出了公投现场组织人员的预计水平。这个结果也悍然挑战了财力雄厚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由爱尔兰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会资助(《新闻共和国》记者莎拉·琼斯补充说,还有许多来自美国右翼的资金支持)。它们依靠的是像照片一样逼真的、难以置信的胚胎漫画形象,以及堕胎率异常突起的隐晦胁迫和危言耸听。然而另一方面,出国堕胎这个安全阀门,也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扰乱了“Yes运动”的开展。“他们只需要去英格兰就能堕胎了,”这个观点在1992年被写入了爱尔兰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肯定爱尔兰公民有权出国进行堕胎。接受这个观点的人已经不自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们认为,应该允许堕胎,但实现的过程可能要费许多工夫。这和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权无关,而是要确保堕胎不是件易如反掌的事,要规范妇女的行为,让她们认清自己在家庭里的角色。

爱尔兰举行投票的同时,美国社会正在被另一个关于爱与家庭的故事所折磨——特朗普政府将未成年孩子与他们的父母在边界隔离开来。在严格意义上说,这个政策在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提高移民政策的残忍程度,其目的一来是形成威慑,二来可以引爆支持者的热情——更可能是两者兼具,这些政策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更加心怀恶意。
对于那些支持堕胎权的社会运动者来说,每当谈到堕胎话题时,那些号称自己是在保护无辜生命、捍卫“家庭价值观”的人,可能对已出生的孩子的福利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而且当两条新闻都在争抢头版时,这种观点便得到了印证。毕竟特朗普最终选择了偏激的反堕胎狂热分子迈克·彭斯(Mike Pence)作为他的竞选伙伴,而且在竞选游说之行中讲了一个关于堕胎的血淋淋的黑暗童话。与此同时,特朗普称外来移民为“动物”,也就剥夺了他们的人性,于是,像这样用暴力将父母和子女分离的政策,就能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之上毫无阻碍地落地实施了。
但这两个事件同样提醒着我们:我们所熟知的家庭并不是一个自然体系,而是由国家力量塑造的;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国家政权在巩固家庭的同时也瓦解了家庭。在美国和爱尔兰,人们所怀念的许多家庭模式都是法律确定的,并且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要求下再度打造成形。如果要说反堕胎政策和家庭之间存在什么明显矛盾,那就是因为在社会和经济的蝶变中,这种政策依然固守着一种基于尊重家庭、尊重国家或是民族的社会不平等。
女人的本分就是待在家里,爱尔兰从一开始就把这种不公平写入了宪法,比1983年投票通过第八修正案还要早得多。法律条文中明确写着:“特别是,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是由国家认可的,妇女要为国家提供支持,否则无法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国家应该尽力保证,母亲们不因经济上的需求而被迫参与劳动,以至于忽略了家庭事务。”

无独有偶,在美国福利社会的鼎盛时期,家庭也是它的重中之重(尽管和西欧国家相比,这些福利要吝啬得多)。所谓的“家庭工资”——给一个家庭成员(可以假定是男性工作者)支付工资,这份工资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以及供养妻儿——就是建立在一个核心家庭(通常是白人)基础之上的图景:妈妈在家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准备晚饭,爸爸则在工厂里制造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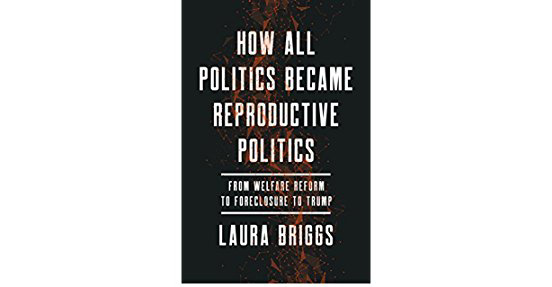
在爱尔兰,经济上的需求其实打破了上述这种模式,女性不得不去寻求有偿工作。另一方面,女权运动认为,工作和堕胎权利一样,都是迈向女性解放的重要一步,而这种经济必要性正是爱尔兰政府想要避免的。对于爱尔兰人来说,经济必要性往往迫使他们成为移民,离开爱尔兰。其中许多人来到美国,尽管近来他们并不是移民恐慌的中心,这种恐慌属南部边境特有。因为特朗普并不需要忙着把他们说成是暴力黑帮成员,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到了美国,照顾着美国家庭。正如劳拉·布里格斯(Laura Briggs)在《政治是如何全部成为生殖政治的》(How All Politics Became Reproductive Politics)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简而言之,移民问题值得引起注意,在新自由主义运动推动女性工作权、让所有母亲和其他照顾孩子的人每周工作四十多个小时后,移民问题还关乎家庭和孩子由谁来照顾的问题。”
经济上的需求推动女性加入劳动者队伍,也让她们离开了家庭——妇女到别的地方去照顾别人,有时会带上自己的家人,有时则不会;而在布里格斯看来,离家往往意味着要从自己的家庭里抽离出来。移民女性悉心照顾美国小孩,但她们的美国雇主却一点也不喜欢她们的孩子。实际上,女性移民的孩子多年来一直承受着污名化,他们被叫作“定锚婴儿”,因为孩子在美国的土地上出生,父母就有可能在美国找到一个立足之地。然而,即便孩子有美国身份,还是有大量的移民父母被遣返回国。
现任美国政府把南部边界的移民视作威胁,因为一讲到“家庭团聚”就会牵扯出“连锁移民”的噩耗,而且往届政府都对这些移民印象不佳。布里格斯表示,目前越来越强硬的移民政策其实起于克林顿时代。克林顿政府1996年颁布了《反恐和有效死刑法案》和《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行动》,布里格斯在书中写道,“跨国边境进入美国危险重重,甚至可能丧命,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些法案正是给那些冒着丧命风险、经常性非法入境的无证移民定罪的第一步。”

在爱尔兰禁止堕胎的这段时间,这种“艰辛但并非不可能”的情况也展现得淋漓尽致。毕竟,必须得有人为女性支持自己生活、继续工作提供保障,也要有人担起供养家庭的责任。在美国,正是共和党提供了这个契机。他们抑制工资上涨、撤回社会安全防护网、把所有看护照料工作抛给个人和家庭,这就意味着美国对廉价看护人员依然有大量需求。而通过法案让这些无证人士处于惶恐不安中,恰好能够压低他们的工资。
人们很容易就开始怀念起那美好旧时光——相对财富丰厚,社会凝聚力强(至少对白人家庭而言是这样的),那时候,一个人的工资足够支撑整个家庭,一个家庭也不必把育儿任务外包给无证劳工,堕胎也不像现在这样普遍。但这样的社会模式无法应对我们目前所生活的世界。更糟糕的是,这种社会模式是建立在那些最容易受伤的人肩上的。结果是,他们会形成一种危险的、近乎与现代资本主义作对的批判。悉尼大学社会学学者梅琳达·库珀(Melinda Cooper)在最近一个采访中指出:“你开始觉得,资本主义的弊病并不在于它滋生了各种不平等现象,而是它威胁到了你习惯的生育秩序。”
有些人猛烈抨击堕胎,关怀着尚未出生的无辜婴儿,但同时又把那些无辜的孩子从跨越边境的父母身边拉走,我们很容易就能撕下他们虚伪的面具。真正难以理解的,是“家庭”在政治话语中的含义——它不是一个不可侵犯的、永恒不变的体系,而是历史推动之下的产物。“家庭”这一概念揭示了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移民政策和堕胎法案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其实同根同源,就是一部分人群、一些家庭中的优先次序在社会结构变动的推动之下所产生的变化。
(翻译:马昕)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