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若干年前,YouTube上流传着这样一段办公室视频:一名身着衬衫、打着领带的男子从日常的平静中突然爆发,将成捆的文件甩出去,举起电脑显示屏砸向隔壁隔间,他把纸张扔得到处都是,然后站上办公桌,开始踢起将这办公室切割成网格状的薄薄隔板,隔板被踢得变了形,之后他又从桌后拎起一根大棒子猛砸复印机……
2008年6月,有人最早在知名科技博客Gizmodo上分享了这一则视频,并配上了一句话:“一段极致暴力的隔间监控视频,每一位格子间办公者的幻想。”除了这位男子写在脸上的愤怒与激动,从视频中人们也可以轻易看出办公室的拥挤、逼仄和压抑。这条视频下面的第一条评语这么写道:“他真正懂得什么叫活着。他的那帮狱友真该一同加入这场反抗。”
从何时起,代表着可靠收入与白领地位的办公室成为了监狱囚牢?为什么一方独立的工作空间却愈发令人沮丧甚至发狂?办公室隔间的设计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呢?其背后所包含的权力甚至阶级压迫是怎样的?办公室暴动真的有可能实现吗,就算真正实现,它努力要想推翻的又是什么呢?美国作家尼基尔‧萨瓦尔试图通过《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萨瓦尔从空间、设计、人员流动等角度,梳理出了一部办公室和办公方式的变化历史。针对办公室隔间,他如是写道:“隔间把人们拉得足够近,以至于产生了严重的社交厌烦症;隔间也把人们分开,让人们无法切身感觉到大家是坐在一起工作的。隔间给人们带来了隐私和社交的危害面,却没有带来两者的好处。隔间坏到所有人都不想它被拆掉;这三面隔墙,也算是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家园,人们可以将其视作自己的领地。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办公室员工内心的狂乱和孤独。”

在纷繁有趣的内容背后,《隔间》一书中还深藏着一记直击当代人灵魂的叩问:“我们为什么工作?我们如何更好地工作?”站在现代性的宏观视角上,萨瓦尔分析了白领阶层的变迁过程,从19世纪阴暗的账房到Google的开放式办公空间,雇员的工作地点不断变化、效率不断提高、环境不断改善,但关于人生和自我的意义却似乎正在不断迷失。“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隔间之中,”作为一个普通职员,我们在隔间里除了处理手头的工作,还能发掘出什么其他的意义呢?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隔间》一书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以期与你一同追溯每一间办公室隔间中的压抑情绪与暴动冲动的来源。
《办公室隔间里的压抑与暴动》
文 | [美] 尼基尔‧萨瓦尔 译 | 吕宇珺
一、隔间人生与病态建筑综合征
对于一名员工来说,失去办公室之时,就是他收到麻烦来临最明确的信号之时。“当我回到总部办公室的时候,”一名柯达员工回忆1980年代大规模裁员期间时说,“我就知道公司是真的发生了变化。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办公室跟家里的起居室一样大,我的秘书在门外还有独立办公室。而当我回到罗彻斯特(Rochester)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办公隔间。我能听到隔壁两个工位的人的声音,也能听到坐在附近的秘书的声音。”彼得斯和沃特曼,以及大内或许会辩称,对于美国经济新近的竞争局面,放开、开放的办公格局是更为合适的。然而,公司的做法却是给少数特权精英保留为数不多的独立办公室,然后把剩下的所有人挤进格子间。
猛烈、毫不妥协的新公司理念改变了隔间的样子。我们还记得,普罗帕斯特设计的隔间,那三面墙本意是解放办公者,给他们自主和自由的。但这些隔间慢慢地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材质易损、隔板用织物包裹的半开放小隔间,白领员工在这样的小隔间里待啊待啊,直到最后被裁掉。媒体马上跟进。在新闻故事里,“隔间”(cubicle)一词从没有单独地高贵过;总是不可避免地带些其他修饰词,比如“无窗”,比如“沉闷”,比如“隔间迷宫”(cubicle warren),比如“关押大房间”(bull pen),比如“地狱”。人们在“隔间农田”(cube farm)里劳作,彼此挨着,构成6×6的标准格局,像是六个装的产品似的。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在那本定义时代的《X世代》(Generation X)中创造了“让牛发胖的围栏”一词,并假装严肃地提供了一个“词典”释义:“小而狭窄的办公工作站,由织物包裹的可拆解的墙体隔板搭建而成,里面坐着初级员工。词源自牛肉产业中所使用的牲畜屠宰前所待的小隔间。”

好像把人放进隔间还不够侮辱人似的,这些隔间的尺寸还被做得越来越小。根据《商业周刊》1997年的一篇社论,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隔间的平均尺寸减小了25%到5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发《商业周刊》编辑部撰写这篇社论的原因是他们“获悉编辑部大部分员工将在一年到两年内失去私人办公室”。“这促使我们仔细调研起隔间来,”他们写道,“全国4500万白领工人中大概有3500万已经在隔间中工作了。”《商业周刊》半开玩笑地说,按这个速度发展,等到2097年,平均每个隔间也就0.74平方米了。2006年,隔间平均面积为7平方米,一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觉得自家的浴室都要比自己的办公隔间大。人们不禁想知道,美国人浴室这种奢华的扩张,以及郊区房子总体面积的增大,是否是一种应对不断缩小的隔间的补偿反应,毕竟这些浴室的主人可是在隔间里缩了足够久的时间啊。有些人更是戏剧性地将隔间和监狱进行了比较。给此种类比提供依据的是,在诸如德克萨斯州等地区,监狱系统处理过分拥挤的方法,就是仿照满是隔间的开放式办公室,来重新设计监狱。有着典型20世纪90年代特色名字的尤尼克公司(Unicor,组合式的名字往往是并购后的结果)雇用监狱犯人来制造隔间的墙板,有时候还生产隔间里面用的椅子。到了晚上,当白领们离开隔间回到家中时,这些犯人却是离开生产车间回到监狱的“隔间”里。
对办公环境的抱怨开始泛滥。隔间限制了空气流通,使人生病(这被称作病态建筑综合征)。老板一边给自己的办公室增添木饰家具和高级办公桌,一边强迫越来越多的员工挤进办公隔间。苹果公司的员工受不了隔间,就在家工作,于是公司便把隔间拆掉了。当某家公司试图去除隔间时,员工却担心失去最后的一点隐私空间。IBM的员工发现自己所处的隔间越来越小;他们认为公司把隔间搞得太挤太糟糕,以至于大家都不来上班,然后公司就不用花钱在办公空间上了。
正当美国大规模建造隔间的时候,它的诗人诞生了,那便是史考特·亚当斯(Scott Adams),这个名字既谦逊又平淡。在90年代中期,他用创作的漫画人物呆伯特(Dilbert)将日复一日的枯燥转化为简单便携的讽刺小品,给无数白领工人带去了某种安慰。呆伯特用一种必然的自黑精神(self-deprecation)对办公世界进行讽刺。作为漫画的主人公,这个人人充当过或正在充当的角色——呆伯特,形象勾勒草率,几无特征,且注定失败。“我在隔间工作了十七个年头,”亚当斯在他那本极度畅销的卡通以及伪商业建议书《呆伯特法则》(The Dilbert Principle)中写道,“大部分的商业书籍是由没怎么在隔间中待过的顾问和教授所写的,这就好像你根据自己吃牛肉干的经历去写唐纳历险的一手记录一样。我,也是啃过一两个脚踝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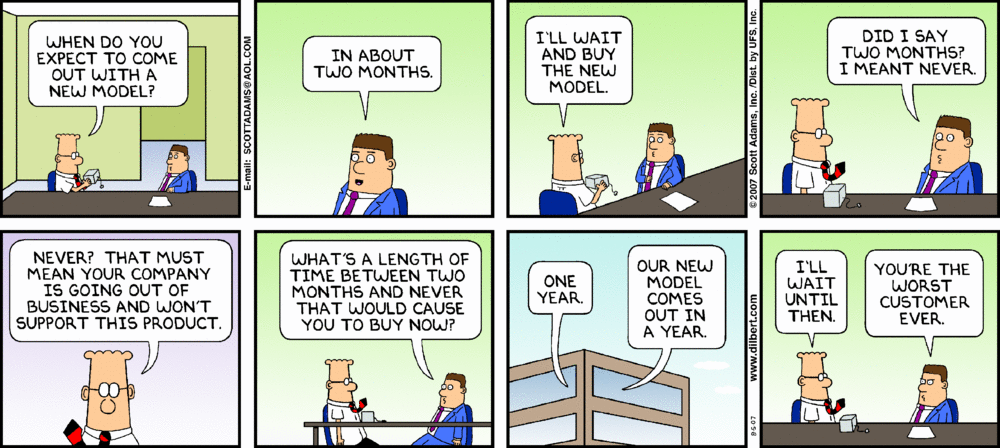
除了贴近真实生活,《呆伯特法则》的创作形式——每日漫画,也正好跟办公室日常工作那不断重复的千篇一律相匹配。每天一大早,呆伯特就来报到,跟白领工人一样准点,然后提供给他们一点可以期待的东西。哪怕报纸上系列漫画的三联(three panels)也成了一种目标,当它们构成隔间生活的轮廓时——哪怕仅仅是三面墙的形状——都在戏弄和模仿:狭窄、正方、无色、极易复制。很快,呆伯特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驻了它所讽刺的办公室。普罗帕斯特设计的布告板,本意为创造个性,结果却固定着各种剪下来的呆伯特卡通画。它很快成了办公室里的标准配置。桌面日历上,咖啡杯上,鼠标垫上,还有毛绒玩具(在网店的办公用品区均可买到),无处不在。晚年时,普罗帕斯特被呆伯特生活的始作俑者的这种指责所刺痛。“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对不起呆伯特,”普罗帕斯特说,“这些漫画中表达的东西正是我们试图减轻和摆脱的。呆伯特早就存在。我们试图展现出更有意思的事物。”
二、计算机恐慌与办公室暴动
想象一下个人电脑最开始普及那几年,在典型的办公室里工作是个什么情景。许多人都无须想象:因为他们就曾身处其中;或者有些地方这些年的变化很小,以至于今天的配置和最初那会几乎没什么两样。电脑屏幕强烈的荧光并不能补偿自然光线的缺乏;循环的空气污浊闷人,甚至有毒。由于70年代的能源危机,大楼纷纷门窗紧闭,隔绝了阳光,隔绝了新鲜空气;地毯上和建筑材料中诸如石棉和甲醛的化学物质毫无约束地在室内流通,带来了各种空气传播的疾病。开放式办公室那种善于聊天的氛围或许曾让人难以集中注意力;然而现在隔间上空盘旋着全然的安静,这来自监管的加强,键盘敲击声成了唯一的声响。电脑的使用保证了数据录入员的每秒最低键入次数;聊天,更别提起身走一走了,都会引发失误。甚至新式个人电脑视觉显示终端上的绿色字符都散发出某种恐吓意味;新闻里每天都有关于电脑屏幕潜在辐射危险的报道,并把女性流产归因于此。

计算机和自动化将忧郁情绪和工厂气息带到了白领工作场所。一段时间内,办公室员工变得越来越没有积极性,尤其是在办事员阶级中。1972年,受尼克松政府委托的一份报告《在美国工作》用极其坦白、令人绝望的言语,赤裸裸地证实了美国工作者的不满,无论是在装配线生产的工人,还是在打字机前工作的白领。(出于这个缘故,尼克松试图禁止该报告的发表。)“秘书、办事员和官员曾经对免于工厂生产这种非人性的工作而心怀感激,”这份报告表明,“(但是)今日的办公室,工作被细分,权力主义渗入其中,跟工厂并无二致。对于越来越多的工作而言,已看不到什么蓝领和白领的区别,除了衣领的颜色:计算机键控打孔机操作和打字池工作的性质,跟汽车装配线工作已越来越雷同。”办事员的收入也跌至蓝领生产工人以下。员工流失率很高;工会成员不断壮大。经理们深知此种消极怠工情绪。据调查,经理们认为办公室员工只发挥出了自身55%的潜力。他们认为“重复性工作导致的无聊和厌烦情绪”是造成这种消极情绪的一个原因。
个人计算机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如此改革性的物件却让一切似乎变得全然一样。计算机的其中一项成就是打破了秘书和老板之间自女性初入办公世界之后建立起的稳定“办公室一夫一妻制”,“办公室妻子和丈夫”这种关系受到了影响。IBM等公司开始推行单个“行政支持中心”理念。在这个中心,“文件创建者”(即经理们)将自己的请求发送出去,由“专员”(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打字员们)进行完整处理。当然打字池永远存在,文字处理软件的引入也没有消减丝毫的噪声。“一直都有文件打印出来……这声音比原来一整屋老式打字机还吵。”一位文字处理专员表示。然而文字处理软件的到来却增加了监控的程度。键盘敲击的内容会显示在屏幕上,员工的进度和速度也全都一目了然。旧有的“秘书—老板关系”所提供的个人控制,无论是怎么样的,都被剥离掉了。一方面来讲,这使得人们从老板的严厉斥责中解脱了出来;另一方面来讲,这并没有使员工增加对自身的掌控能力,反而有所削减。
人们可能会猜想说,这种毫无生气的办公环境会引发闷闷不乐的上班族掀起暴动,而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在高管的停车位上肆意停车,砸掉电脑显示屏,卸掉隔间墙板,用这些板构成路障。确实在极端情况,出现了办公室射杀,短暂地引发了诸如“隔间狂暴”(cubicle rage)这样的媒体热词。然而更多的情况是,人们以典型的办公室员工应对方式,又或许是典型的美国式应对方式,来对抗这日复一日、越来越没劲的工作:消极怠工、故意拖延、少做工赢得个人时间而不是争取更多工作机会。花旗银行银行卡处理中心的员工被要求在两分钟内处理完客户的电话,因此他们常常不等客户说完就挂断,以达到这个要求。此外,保险索赔处理员会输入虚假数据,以完成当日工作量。直到今天,各处办公室的员工仍然熟知此种对待日常工作的日常抵抗方式。

这样的抵抗方式自然是有限的、不够频繁的、无组织的。80年代的办公室,不论它如何贫瘠、如何刻薄,还是给少数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企业家”可能性。对其中的许多人而言,这似乎已足够了。时事刊物中的时代潮流人物“雅痞”,便指代了某个真实的社会群体。放开的银行管制、压制住的工会组织,以及布满花岗岩的摩天大楼,这一切组合在一起,给那些大声支持美国经济转型和去工业化的人们,带去了一种由公司生活提供的特殊兴奋感。当白领普遍感到不安时,少数高管却享受着极度的愉快和兴奋。随着中层管理人数的下降,组织似乎对个人的能力更为看重了。娴熟玩弄办公室政治,然后脱颖而出,成为高管,进入行政套间工作。对于那些还未被消极怠工掩埋志气的人们而言,对上述这种希望的渴望变得愈发强烈。这种普遍的信念大大地团结了办公室员工,其功效要远胜新型计算机系统里安装的任意哪个监视软件。
办公室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孤立”。无论装配线工作有多令人讨厌,但无意间确实让人们不得不彼此共处。工人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日日一起度过。很少有人会幻想自己能够“升职”,成为工厂的头头。这里,人们更容易团结组织起来,或者说起码能够常常彼此交谈。而办公室工作则趋向于让人们彼此疏离。办公室内在的个人主义——正如我们所见,自1930年代工会运动风起云涌以来,被经理们尤为看重——在工作和设计方面也有体现。每天坐在电脑面前,如电脑支持者所言,或许能为人们提供比纯粹的人际交往要广得多、深得多的无形网络。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当然这是在网络和笔记本电脑普及之前,人们待在电脑屏幕前的感觉更像是装配工人被困在生产工位上一般。而且大部分人在计算机上能做的事情种类是很有限的。计算机面前的白领,就好似1920年代泰勒主义办公室里对着账本的会计。隔间把人们拉得足够近,以至于产生了严重的社交厌烦症;隔间也把人们分开,让人们无法切身感觉到大家是坐在一起工作的。隔间给人们带来了隐私和社交的危害面,却没有带来两者的好处。隔间坏到所有人都不想它被拆掉;这三面隔墙,也算是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家园,人们可以将其视作自己的领地。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办公室员工内心的狂乱和孤独。
书摘部分节选自《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第7章《空间入侵者》,标题为编者自拟,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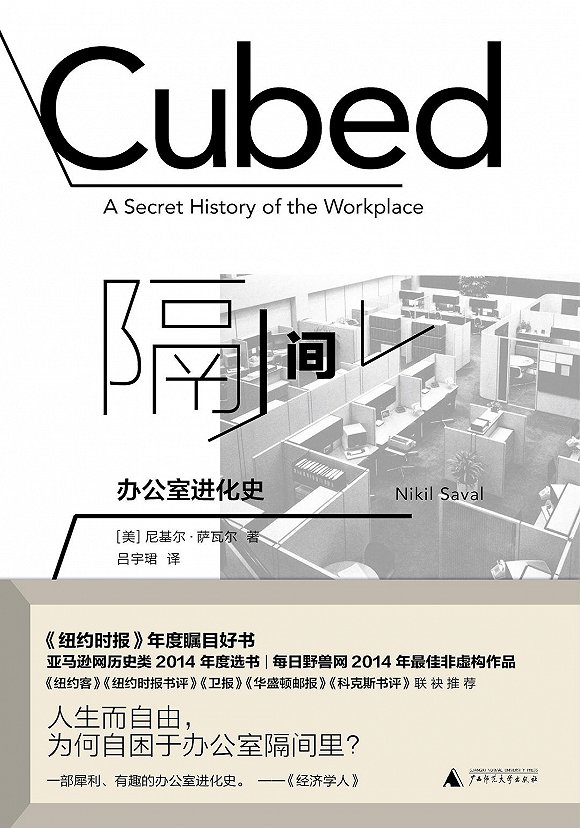
[美] 尼基尔‧萨瓦尔 著 吕宇珺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