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所有革命性的力量里——民权斗争、反战运动、披头士——没有比最高法院更重要的了。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领导下的最高法院信心十足的行动主义,不仅给美国人带来了大量的新权利,也为传统主义者攻击非民选的自由派精英好高骛远提供了靶子。在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里,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称:“《权利法案》里的特定保障有未言明的地方,从这些保障引申开来……创造了隐私的区域。”这一断言引发的嘲笑比沃伦领导下的最高法院的任何判决都多。在这一块著名(或者说臭名昭著)的不重要领域里,“隐私权”最终得以建立,最高法院用这种权利使节育合法化,最终也使堕胎、同性恋等问题合法化。
但是,道格拉斯的论证虽说在思路上略显奇特,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正如历史学家萨拉·E·伊戈(Sarah E. Igo)在《被知道的公民:现代美国的隐私史》(The Known Citizen: A History of Privacy in Modern America)一书里提醒我们注意的那样,《权利法案》的修正条款确实间接地承认了隐私权——具体来说,是第三条(关于士兵驻扎问题)、第四条(限制不合理的搜寻和逮捕)和第五条(反对自我定罪)。事实上,高等法院早在1886年就否定了“政府对一个人住所及其生活隐私的神圣性的任何侵入”。1965年的问题,不是公民是否拥有宪法给予的隐私权利的问题,而是这项权利究竟包含哪些内容的问题。格里斯沃尔德案虽然是一个里程碑,却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批评者怀疑,新的宪法权利是否会包括保护公民不受政府监控、雇主强加的心理测试、侵略性的警察执法手段,甚至是电视营销商的影响。有些人批评道格拉斯给他从未言明领域里取出的权利取错了名字:也许他应该说“个人的尊严”,或者“不受打扰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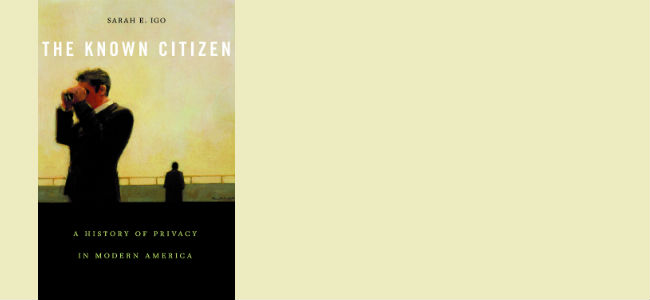
法律学者会承认,“隐私权利”这种后来的说法出现在1890年《哈佛法律评论》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里,其作者是后来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 )和他的法律合伙人萨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这也是伊戈这本书的起点。两位律师提出这项权利是为了应对当时新出现的侵略性新闻形式,这种新闻将个人的幽会和放荡,甚至是捕风捉影的传闻当做新闻头条。镀金时代里出现了“锁孔新闻”、即时成像的摄影技术、可被窃听的电话、暗中被别人拆开的信件,还有极爱窥伺性关系的道德主义斗士,比如恶名远扬的信件检察官安东尼·康姆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在许多幽默而又让人大开眼界的小插曲里,伊戈提到,就连明信片也受到了攻击。一名杂志编辑写道,明信片让“仆人和房东都能看到我们的私人事务”。
正如这些多样的威胁所表明的那样,隐私权从一开始就一团混乱,或者说像是自助餐一样——一系列截然不同但又以某种方式相联系的权利,可以让我们免受社会的侵扰。《被知道的公民》一书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段历史,美国人用“隐私权”来保护文件、信件、家庭、住所、外貌、健康、性行为、人际关系、谈话、行踪、购买习惯、网络浏览记录,甚至我们的既有行为。对它的侵犯来自爱管闲事的邻居和联邦政府,来自公司和记者,来自执法人员和青少年的家长(一个吸引人的脚注引用了一本名为《滚出我的房间!:美国青少年卧室史》的书)。
社会科学家在伊戈的叙述里扮演了非常突出的重要角色。这些进入我们的生活、收集关于我们的习惯和倾向的各种数据并进行分类的专家,也是伊戈从上一本书《平均美国人:调查,公民与制造大众》(The Averaged American: Surveys, Citizens, and the Making of a Mass Public)到这本新书的过渡环节。这本书展示了民调和行为科学调查如何改变了美国人相对于彼此来思考自身的方式。《被知道的公民》可以说是一个续篇,伊戈从公共领域转到了私人领域。新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隔绝社会的管制性压力——甚至是,我们与社会之间究竟能不能有任何隔绝。

隐私显然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概念,伊戈熟练地回顾了学者们为了抓住隐私难以捕捉的本质而给出的各种定义。她认为这些尝试是有益的,但并没有最终定论。她自己雄心勃勃的解决方案是拥抱隐私的多面性。在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得体”概念到社交媒体所展示行为的马拉松式梳理中,她重述了数十场被遗忘的公共辩论——使用指纹来发现犯罪嫌疑人;发明社会保险号码来追踪工人累积的积蓄;20世纪50年代风行的用以评估员工的人格测试;水门事件时期对政府监控的担忧。这些辩论显示出了隐私概念的灵活性,它是限制社会凝视的工具,无论这种凝视采取的是何种形式。
与大多数思想史学术著作一样,这本书的主角是思想和理论。要讲述它们的历史,作者不可避免要面对如何从无形的概念中创造出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的挑战。在那些聚焦于特定人的篇章里,伊戈有力地应对了这种挑战。其中一个精彩的故事是劳德·汉弗莱斯(Laud Humphreys),他是一个未出柜的同性恋圣公会牧师。1968年,他在社会学论文探讨了公共厕所中的同性恋搭讪,这些地方被称为“茶室”,论文于1970年作为他的一本书出版。汉弗莱斯的研究揭露了这一花柳世界里形成的复杂仪式,因为文化里的指责态度让他们产生了保持隐私的需求。伊戈对反讽的敏锐嗅觉表现在,她关注到了汉弗莱斯自己正不道德地侵入研究对象的隐私——首先是帮他们望风,即所谓的“望风女王”,然后秘密记录他们的车牌以便追踪,然后用假身份去采访他们。更吸引人的是,汉弗莱斯的研究——紧随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和菲利普·津巴多的争议实验之后——引发了一场关于隐私的新争论,即社会科学家应该对研究对象披露哪些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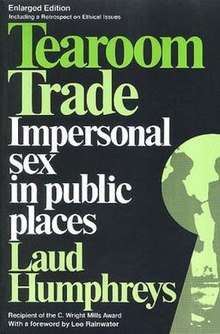
在最后几章里,伊戈讨论的不是来自政府或大企业对隐私的威胁,而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威胁。当下这种揭露和自我揭露的文化助长了坦白性回忆录的热潮,刺激新闻媒体报道政治家和名人的私生活(和隐私部位)的意愿,我们的屏幕上充满了普通民众对于他们的疾病、孩子和性经历的过度分享。但就在她似乎要提前宣告隐私的死亡时——即我们已经从对奥威尔式“老大哥”的恐惧,发展到了“老大哥”在电视上的自我展示——她强调,伴随着现代人对于公开分享的激情,关于界线问题的新担忧正在出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保护录像租赁习惯、车牌、健康记录和儿童数据等隐私的法律。而正在我(本文作者David Greenberg是罗格斯大学历史教授)撰写这篇评论的时候,Google发来了一封关于隐私政策更新的邮件。我看到了一篇关于面部识别软件危险性的报道,还看到一个讲述导航应用如何引导驾驶人加速通过以前宁静的郊区街道的故事。
这些多种多样的隐私主张有一个共同点:提出主张的人普遍抱怨说,他们应该获得一些自由,免于受到社会对个人越来越多的侵犯。这个社会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变得更加现代、更有组织、更注重记录,监控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发达,也越来越刨根问底。伊戈的书名来源于奥登的一首诗《无名的公民》,这首诗描写了20世纪中叶的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现在的每个人一样——他被政府机构、公司、舆论研究人员和社会心理学家所研究和记录,但奥登认为,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他仍然是不被人所知晓的。就社会而言,我们想尽可能多地了解它;作为个人,我们寻求保留匿名的余地,希望保留一点儿不为人知的隐私。
伊戈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社会知识的益处大于风险。尽管我们为隐私权进行了游说,甚至将其写入宪法,但我们选择了支持这样一些观察、监督和研究,它们有助于我们“报道新闻、保护国家安全、跟踪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了解人类心理、提高商业效率”。伊戈对这个话题的研究和概念化非常具有原创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故事和亚当夏娃的故事一样古老:我们对知识的追求,也让我们损失惨重。
(翻译:李孟林)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