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桌子不大,窄长,围着大红或墨绿丝绒桌围子,上面铺着同色的一块布,往下耷拉半截,垂着黄穗。桌子后头,椅子比一般高些,说书人坐上去,不能实打实,屁股跐着一点边,胯跟桌子平齐,时间长了比站着还费力。就得这么坐着,取的是高台教化的意思。
随时都能站起来,往往是比拟人物,上身有些个动作。要是人物动作太大,这人就得右跨一步,离开桌案,显露出全部身形。正经是一身大褂,中式对襟上衣也行,下着黑色水裤,裤脚扎着,满露出来圆口黑布鞋里头套着白袜。偶尔也有人穿着西装皮鞋,遇见这样的,观众就要猜这演员是不是今天得赶场,除了说书又接了别的活。
算不上书迷,我的评书经验可能跟大部分年轻人类似:小时候在电视上、广播里,避不开地听过几耳朵《白眉大侠》、《杨家将》,2005年后,听过郭德纲的相声和单口,近几年,随着音频APP的兴起,又随便听了几回评书。2017年冬天,我想听听现场评书,通过大众点评,找到了前门老舍茶馆。
前门是游客圣地,茶馆卖的是“来京必看”的老北京风情,曲艺,包括相声、评书、大鼓等等,是这风情的内容。那天人不多。我刚在书馆坐定,戴黑色瓜皮帽、穿着宝蓝大褂、肩头耷一条白毛巾的伙计便端上盖碗,黄底上描着京剧脸谱,揭开,是老北京人爱喝的茉莉花茶。他在座间穿梭,用一把紫铜茶壶开盖续水。
台上,穿着黑大褂的年轻男孩在说《水浒》,矮脚虎王英就要被人杀于马下,但场里气氛并不聚拢,十几个人,多是来京游客,带着大包小包,有人小声聊天,有人低头闭眼仿佛睡着,有人哄着孩子,那孩子渐渐从哼唧变成了哭闹。大褂男孩抬眼看过,又继续说王英。一个小时后,他拔高声音,摔了醒木,下得台去。
穿一领砖红大褂的男人掀开绣着凤凰的帘幕,手握包着扇子和醒木的白手帕卷,走上前来,微微鞠了一躬,椅子上坐下。年纪不大,留着略长的头发,额前那一片修剪过,正眉间有个豁口,恰露出眉心一颗痣来。“给您换一场”,他仰着头,声音亮堂。人群好似醒了一层,都望着他。
他说的是《三遂平妖传》,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之前的作品,最为大众所知的信息,是它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动画片《天书奇谭》。动画片讲的是一个孩子和三只狐狸,小说却是成年人的故事。宋仁宗年间,奸臣当道,妖人造反,丞相包拯平灭叛乱,又是清朗人间。这一回说到蛋蛋和尚(动画片中的蛋生)重现开封府,三戏包相爷。说书人卖着好,“您各位是来着了,这一回正是本书的热闹回目。”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将三次戏耍细细铺排,节奏或缓或急,时不时有些包袱,我精神一直在跟他走,虽然也会时不常看看手机。他语调清脆,带着一点不吝劲儿,时而站起来,捏着白手帕一角模仿被戏弄的绸缎庄老板娘,腔调是细的,脸和身段都是媚的。又学站在旗杆上的蛋蛋和尚,对包拯大加讥讽。座中婴儿又哭闹起来。说书人没翻眼皮,叙述还在蛋蛋和尚的话里,突然道了一句,“怎么哭起来还有奶音儿呢?”
人群静了一秒——反应了一下,随之大笑,拍手。我发现,现场评书比网上那些20多分钟一段的静场书好玩多了。散场后,我四处打听第二位演员叫什么名字,有人问到正在台子旁一个小房间里收拾的人,他脸上带点年轻人里常见的“躁”,左耳上挂着三只黑耳钉,“就是我啊!”一个有点“葛”的北京孩子,一点不像想象中的“说书先生”。
他叫郑思杰。

2
有好些年,北京没什么曲艺演出的地方,郑思杰记得,2005年之前,他只能在春节庙会上演,说相声,唱快板。天寒地冻,老百姓挤挤挨挨,台上的郑思杰大褂里套着羽绒服,膨起的绒把大褂撑得鼓鼓囊囊。一下台就找管事的要暖水瓶,可露天里暖水瓶放久了,水也冰凉。说一场只有三五十块,为的是锻炼,别怕见生人。
郑思杰是北京人,1990年出生,8岁学快板,拜的是快板书名家梁厚民先生。梁先生会得多,教他快板,也教相声、评书。郑思杰不拘门类,爱的是曲艺这种生于民间的艺术形式。
说到评书,郑思杰先是听,2003年北京非典那年,他跟家里磨出来1500块,从王府井书店买了袁阔成先生一套《三国演义》VCD,翻来覆去地听,听到好词儿就记,不一定知道什么意思,就觉着好。2008年高中毕业的暑假,师父把他推荐到上海南京路新开的相声会馆里,他每周五六唱快板、说相声,二三四就说书,才十八岁,愣说了俩月《封神演义》,没那么大胆像“袁爷”袁阔成那样从女娲宫降香开,他先说的哪吒闹海,热闹,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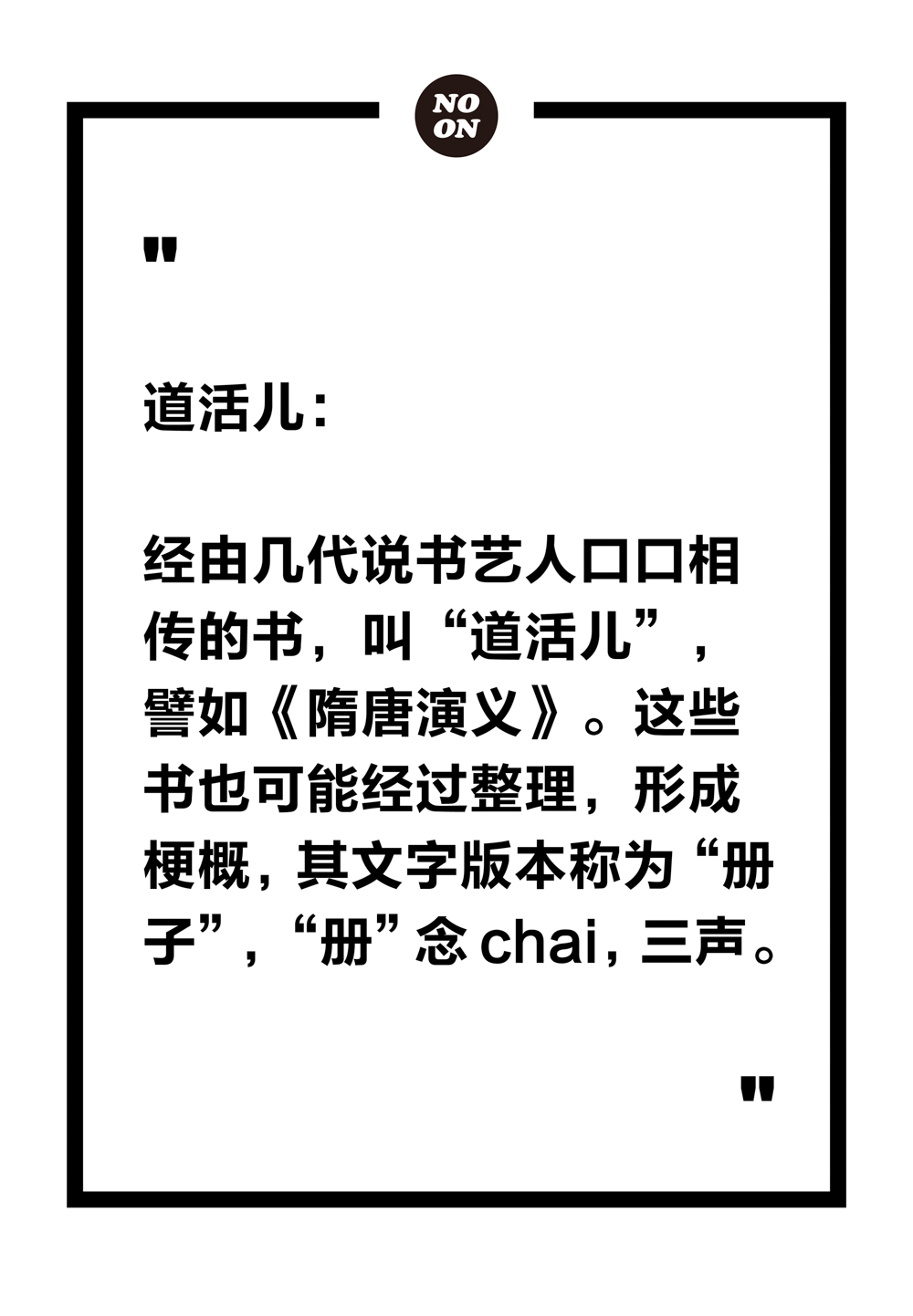
评书行当常讲一句话:说书说的是人情事理。以往学说书,学徒先在茶馆里倒上三年茶,为的是听书,听差不多了,到师父家里去,师父给说一段,学徒重复一遍,天天磨,加上对世态人情的体悟,到学成得二十多岁快三十。
郑思杰想往深了学评书,但评书市场一直不景气。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是靠相声和快板换钱。他去过好多乱七八糟的地方演出,夜总会,洗浴中心,灯光迷离的酒吧,穿着网兜跳钢管舞的兔女郎下去,穿着大褂的他上来。即使是正经剧场演出,相声越来越走下三路,他有点烦。
2015年底,郑思杰和老舍茶馆谈了合作,将二楼一个一百来平的空间做成书馆,每周六下午演出,茶馆和演员分成。说书成了他主要的行当。他不愿意提“说书先生”、“高台教化”这些词儿,好像一说书就得拉开那个架势。那是早年间老百姓不识字,靠说书先生拉典长见识,现在,他本科毕业,听书的硕士博士都有,谈不到他“教化”。
最挠头的问题是,说什么?
传统书老先生都说过了,说得好,“八个郑思杰搁一块也比不过一个袁阔成去”,还不要钱,随便听。如果他去说传统书,谁愿意花钱听他的呢?观众也变了,以往说书要“留扣”,现在一上网,观众马上知道下一回的情节,没有悬念。“不够吃的”,郑思杰说,“就得找新的。”
评书行当其实一直在“找新的”。1949年7月,连阔如出席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创编新书《夜渡大渡河》。解放后,许多传统书不让说了。袁阔成带头说新书,《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等新评书广泛传播。“文革”期间,金文声在大学校园里翻到外国小说,改编成评书《基督山恩仇录》、《三剑客》和《茶花女》,是将外国书改成评书的较早尝试。网络传播时代,年轻一辈的评书演员也在求新,王玥波曾受土豆网邀请改编漫画《火影忍者》,叶蓬说过《霍比特人》。共同特点,原著都是“大IP”,说是噱头也好,得让没有听书习惯的年轻观众知道;同时情节曲折,戏剧性强,适合改编成评书。
郑思杰琢磨了不少“新书”,《三遂平妖传》是其一。这书是他从小说改编的,情节安排、节奏处理,全靠自己掂对,还得用今天的思考赋予人物从无意识到“坏”的逻辑。说起来也都是用现在的话,没有“分列两旁、大排筵宴”,他说的都是“来来来,吃吃吃!拣贵的吃!”但因为说的是包拯、寇准,不明就里的观众还把它当传统书对待。
他又琢磨起了外国书。《堂吉诃德》挺好,就是中国版的《书迷打砂锅》,一个入迷的人闹出一连串笑话。真着手编排,他觉出外国书麻烦了,时空久远,不容易找到十六七世纪的资料填充评书需要讲述的细枝末节处,同时,他的观众,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要为了个根本没见过的公主奋不顾身,逻辑就不匹配。
“拿话构建一个逻辑太难了。”郑思杰说。
去老舍茶馆听过几回书后,我约了郑思杰,本意只是想了解一个传统行业从业者在今天的生活状态。老舍茶馆书馆的上座率一般,能坐一百人的场子,多的时候三十来人,少的时候七八人。现场买票58,团购38,这钱去掉场租还得两三个演员分,怎么算也不是个好买卖。郑思杰耐心地对我进行了一番评书知识普及,又提到想说“新书”,提到《堂吉诃德》——我惊讶极了。从没想过这两样东西能拧到一块,能行吗?
暂时他没做出成功的例子,“小说和影视不需要跟观众直接交流,都有介质,可以虚构;但我们这个没有介质,咱们都是现实中的人,凭什么你讲一个不现实的事儿?外国书不好说就在这里。就说名字,一大串,听的和说的都记不住,可是要改成中文,老王小张,外国书没了,中国元素太多,又有点违和。”
放弃《堂吉诃德》,郑思杰又改编了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这部书比《堂吉诃德》时间空间都近,便于中国观众理解,但平行结构给郑思杰出了难题:小说可以让两位主角在显现的文字中从无交集,一星期演出一回的评书却很难建立平行时空。评书是口头艺术,依靠时间的连续,“一张嘴难说两家话”。《白夜行》处处打破了传统书的套路。郑思杰设想,这一周说桐原亮司,下一周说唐泽雪穗,但隔开太久,又是侦探小说,线索得一直留着、给观众提醒,势必每次说都要大段倒书,也不是个办法。或者录静场放网上,听书人能一股脑听完。左思右想,评书《白夜行》说到小说第二章开头,也是这本书真正开始走两条线的时候,郑思杰停了下来。
他不愿意把话说死了,说外国书难是难,但他还在琢磨,还想尝试。
再找书,喜马拉雅给他推荐了小说《古董局中局》。郑思杰看过这小说,觉得挺合适,主要人物明确,“书胆”有了;过场人物层出不穷,“书筋”也有了;主角为了寻宝从北京往外走,沿途经过河南、山西等地,评书说到这儿,尽可以撕出去讲风土人情,还能用上“倒口”活,表演空间大。郑思杰下了心,细编排了一遍,开场介绍主角的小店,门外的对联,屋里沿墙一格一格的摆设,都是原文没有的,他凭着自己的想象与见识填充得细节丰满,一一道来,在评书技法中,这叫“摆砌末”。头回书上台说之前,词儿都给打出来默过,写了得有几千字。他满心想把这部书打造成自己的作品。
没有版权。他又卡住了。虽然有人说评书是“什么书都能说”,但口头形式要求它的底本最好人物连贯,情节紧凑,戏剧性强。近年来中国的通俗文学作品匮乏,适合改编成评书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合适的,也早被影视行业的大资本盯上。郑思杰在微博上给《古董局中局》作者马伯庸发过私信,人家没理他。这事又搁下了。
3
可作为郑思杰“标签”的“新书”是《斗破苍穹》,从2015年10月说到现在。
小说《斗破苍穹》于2009年到2011年在起点中文网上连载,作者天蚕土豆,1989年出生。这部小说有526万字,目前在起点上有超过一亿六千万次点击。它虚构了一个叫做“斗气大陆”的地方,没有法律,只认强力。主角名叫萧炎,借助民间小说中常见的“施惠者”角色,也就是一位得道高人的帮助,加之自己的努力,萧炎所向披靡。所有女性都倾慕他,男性要么臣服,要么被他杀死。
经过上文说到的几次尝试,改编《斗破苍穹》对郑思杰而言像是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它是“新书”,但是中国语境之内的。经过喜马拉雅牵线,版权也解决了,这部评书做成付费,和喜马拉雅分成。
郑思杰最初设想把小说揉碎了往传统评书中的短打书和神怪书上靠。中规中矩地,上台先来一首定场诗,人物出来先开脸,念的也都是传统书里那套赞赋,情节往紧凑了说,好显得热闹。
逐渐觉得怪。有一回,他说到书中一位上了年纪的人物,用了短打书里常用的套话,“那可是老一发的人物字号。”他并未想要把它处理成包袱,座下却有人笑。随即他明白,这是杂糅带来的违和。
那会儿,他说《斗破苍穹》已经快一年。在传统评书大量套路性的言辞之外,郑思杰需要寻找自己新的语言。在台上他脑子里一边过情节一边想怎么说。老词儿不能说,新词儿又没有,一个最擅长说话的人突然嘴不利索。他又去听袁阔成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看他敬重的前辈是如何在自己的时代说新书。几个月后,他渐渐觉得顺嘴了。
传统书除了语言的套路,在人物塑造上也有套路:脸谱化。好人就是“鼻直口正大耳朝怀”, 坏人就是“塌鼻梁瘪山根”。大部分主角人物是“英雄好汉”。
郑思杰也曾想把萧炎塑造成英雄,最初的回目里,他强调萧炎性情沉静,不苟言笑,修炼认真,有所担当——像个年轻的展昭。
但他逐渐发现萧炎不是英雄,他耍鸡贼,肆意杀人,伺机摸女人的大腿,毫不掩饰利己的目的。“萧炎”像是个人主义的极致形象,跟以往评书中的主角完全不同。
“撂地长出来”的评书,宣扬的总是最大范围的普通人所能接受的道德和价值观,史书《三国志》到话本《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的改变便能体现这一点。郑思杰为萧炎找到了不同于传统评书的新形象,“一面正经、一面不着四六”的“半成功人士”,“有点像王思聪”,是今日的偶像。
2018年春节,我听完了喜马拉雅上的评书《斗破苍穹》,一回现场书截三段算一回音频,一段一块钱,优惠价九毛,已经更新了300多段。每段的播放量在几百到几千之间。压缩了两年多时光去听,评书《斗破苍穹》前后变化是显著的。郑思杰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他大量使用北京方言、歇后语、俏皮话和拟声词,创造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充满当下娱乐感的世界。
他不再费心营造那热闹的打斗场面了,就他的阅读经验,看到大段的打斗场景也会跳过去,观众的心态也差不多,评书行进到打斗环节,“歘歘歘歘几道绿光闪过——反正你也知道怎么回事”。他不再试图如小说那般构建一个虚拟世界,“现在人更实质,幻想的事儿大家都没那么感兴趣了”。越往后,他越离开这部创作于2009年到2011年的网络小说——仅仅过了几年,世界好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天蚕土豆的小说读者还会为因将自己代入而在阅读中产生快感,几年后,郑思杰已经带着自己的观众超越了那种代入,改成一种自上而下观望的、有点冷漠的了然。没有人再细琢磨“讲理”了,为什么萧炎身处险境、永远不死呢?“因为他有主角光环啊!” 这一句解释就够了。
“得跟着社会大节奏去调整。”郑思杰说。
他觉得社会太浮躁,整个都有点毛病,他就喜欢在家里一个人呆着,看书,画国画,写毛笔字,养鸣虫,盘核桃。但说书总是需要观众的,现场观众给说书人直接的刺激,让他们不断去调整、创作,以求触摸到不断变化的大众心理。如今,每周五晚上,郑思杰在护国寺宾馆,继续说这部《斗破苍穹》。
4
郭鹤鸣是河北石家庄人,1986年出生。11岁,小学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暑假,他进了当地少年宫开的班,学山东快书。班里20多个孩子,其中18个照过一张合影,在老师家前的胡同里,孩子们大大小小排两排,郭鹤鸣站在后头,穿着白衬衫,面容清秀。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还在曲艺行当的,也就剩他一个。
学了快板、相声,到高中,郭鹤鸣又跟随刘建云先生学习曲艺伴奏,刘是少白派京韵大鼓白奉霖先生的徒弟。曲艺行当约定俗成,按文雅排行,京韵、单弦、梅花算前三,山东快书和相声都得往后,郭鹤鸣想深造,往上档次的学。刘老师还给他念过评书,语言身段,他习了些技巧。
2004年,郭鹤鸣高中会考结束,按照师爷的安排入伍。这段经历给他带来了一些情绪,譬如愤怒,也带来了一些收获,譬如对人情事理的揣摩。在湖北,他“干了这辈子所有的活”,又因水土不服,发烧头疼拉肚子,得了痔疮。领导照顾他,让他去哨所坐岗。日子枯燥,他想起了评书,托人买了袁阔成《水泊梁山》100回盒带,晚上执勤时听。
哨所在山里,屋里一开灯,一会儿工夫小虫子就在天花板上密密麻麻一层。郭鹤鸣把屋里灯关了,合上门,桌子搬到外头灯杆下,听一句书,写一句词儿。山里真安静啊,大灰蛾子循着光成群结队往过飞,时不时扑腾掉他本子上。他还见过一条蛇往屋里爬,拎起一把铁皮簸箕铲开蛇,接着写。这三个月是他评书砸下的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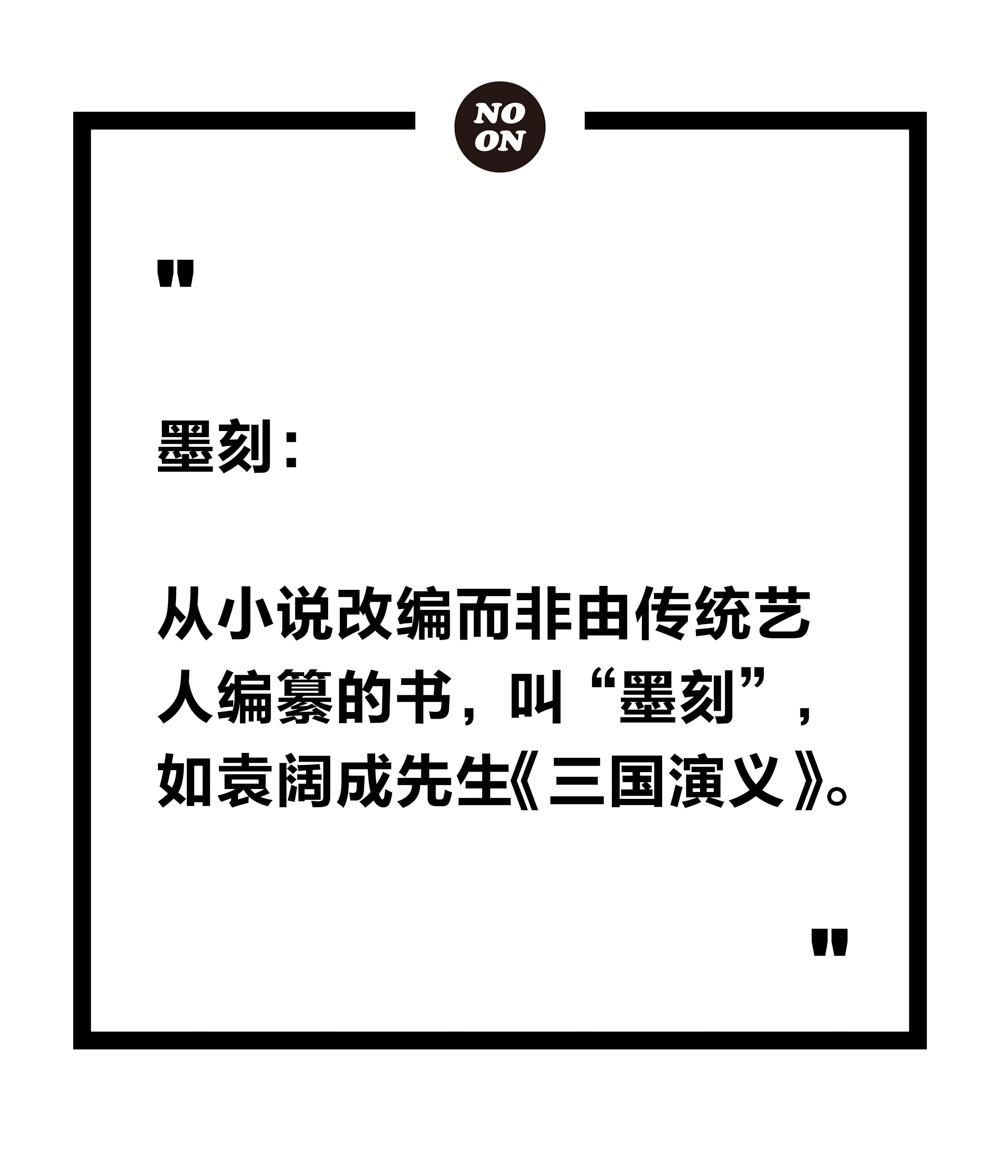
2006春天,郭鹤鸣退伍,通过艺考上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又进了德云社。因为前一年郭德纲的爆红,德云社开始扩张,对外招生,郭鹤鸣是第一批学员,每到周末就买12块钱一张的绿皮火车票从天津到北京上课、演出。那会儿,为给金文声先生留资料,德云社开了书馆,快板、相声演完,郭鹤鸣就往书馆跑,那会儿不经常见到现场评书,他觉得有意思。
后来,金先生病了,书馆闲着,郭鹤鸣上台“愣说”,有时连说仨钟头。书馆旱涝不保,有过开场时一人没有,只好对着服务员说;时而只有一两位,时而60座全满——全是没买着对面相声票被卖票大姐忽悠到书馆的游客,脸上挂着三分犹豫七分不耐烦。这样的观众令说书人心里没底,郭鹤鸣在台上,有回一天说了够一个月的书,光怕给少了。他提着一股气,想把书说好。那会儿他瘦,腰间扎一条绑带卡在骨头上,兜住丹田,说完书摘下绑带,两条腿才热乎起来。
德云书馆停了一阵,2010年重开。这一回,郭鹤鸣改编清末无垢道人的《八仙得道传》,变成一部35回的评书。这部书有一些撒汤漏水的地方,郭鹤鸣说,但它对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仙传没有道本,对说书人来说就算“新书”,郭鹤鸣改编,要按评书的节奏琢磨,要查事件背景,往里头添枝加叶。一番操练下来,他觉得自己会说书了。
寻思下一部书时,郭鹤鸣想到了《哈利·波特》。还在部队时,定期有一辆车驶入军区大院,摊开来卖书。郭鹤鸣买了一本《哈利·波特》,盗版大厚本,从魔法石到混血王子全有。他看了一遍,谈不上热爱,到2012年,他陆陆续续看完小说,去申请说这部书。他是不想再说传统书了。
“老先生的道本、册子,拿过来,故事我都吸引不了,就跟《红楼梦》里史太君说的,逢公子必然落难,逢小姐必然招亲,全这一套!”
“上头”没同意《哈利·波特》,说可能形成噱头,还是说传统书吧。郭鹤鸣本想作罢,但是,他的师兄弟李根说上了。郭鹤鸣觉得李根“说得敷衍,看不下去了”,并非深思熟虑,他开始说《哈利·波特》。
2012年7月21日,北京下起了至今仍令人闻之色变的暴雨,郭鹤鸣在德云书馆,开说这部新书,他的开场也是一场大雨,外头招牌名字写的是《魔法石》。
那时的郭鹤鸣依然没想着以后会指望评书吃饭,眼睁睁相声来钱快,八个垫话攒一块嘻嘻哈哈十几分钟就算一场,还总有观众买票;评书呢?全国光靠地上说书养活自己的演员,他几乎想不出来。至今还是这样。郭鹤鸣和郑思杰都在学校里给孩子教课,贴补家用。
但越预备这书他越觉出好来。《哈利·波特》有侦探小说的底子,前后悬念设置得多,线索埋伏得远,有点像传统评书中的公案书,不同处在于公案书一早点明凶手,《哈利·波特》把悬念留到最后。郭鹤鸣是幸运的,他找到一个好的评书底本。
2013年初,《哈利·波特》第二部《密室》第一回已经在节目单公布,但前一天,场地老板临时撤场,评书换成了相声。
北京的书馆大多惨淡经营。艺人们说,书座必得有钱有闲,清末书馆在北京兴盛,是因为拿着钱粮的八旗子弟没事干,下午泡茶馆听书晚上泡戏园子就成了固定生活。解放后,先是许多传统书不让说,断档几十年后电台评书兴起,在这种文化氛围成长下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了到现场听书的习惯。再一则,在节奏快、压力大的北京,如今“有钱有闲”的人有多少呢?
2014年,郭鹤鸣离开德云社。当年10月25日,距离《魔法石》结束过了一年零十个月,郭鹤鸣在新街口社区活动中心,开始哈利波特第二部,《密室》。这部书32回。2015年7月18日,开始说第三部《囚徒》,44回。2016年夏天,《囚徒》行将结束、第四部《火焰杯》初开之时,郭鹤鸣又失去了他的场地,甚至在马连道一家只能容15个书座的茶馆说过三回。也是在那附近,德云社“家谱”发布,他的八字评语“欺师灭祖手段卑劣”广为人知。
2017年冬天,我第一次采访郭鹤鸣,他稳稳地坐在椅子上,脸上有种被伤害过的戒备表情。往后的半年,我常去书馆听书,多次听到郭鹤鸣和他的伙伴们用那八个字砸挂,或者说,它已经成为这个小圈子里重要的“梗”,每每引起会心的大笑。再采访时,他的表情松弛了些。我的许多问题都在纠缠“用评书形式说外国书”,他总结道:
“书里主要还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你拿刀捅他一下他知道疼,只要理解了这个,就无所谓中国人、外国人,中国书、外国书。”

5
护国寺宾馆古色古香,大堂一角竖着个大鸟笼,里头一只大白鸟,时不时惊叫一声。走过大堂左拐进走廊,两边墙上挂着老北京照片,在一扇永远开半扇的防火门处上楼梯,再拐一个弯,门廊上挂着牌子,“护国寺宾馆京剧票房”,里头那间几十平的小屋,铺着团花红地毯,摆了八张八仙桌,各带四把高背椅,早上是宾馆的外宾餐厅,每周三天是京剧票房,周五周六两个晚上,便是评书小书场。六点半开,一般三人上台,每人一小时多点。郑思杰、郭鹤鸣、武启深、武宗亮,四位平均年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这里说书。
晚上八点五十,郭鹤鸣上台,常穿灰色中式对襟上衣,肩膀西式做法,显得板正,下着黑色水裤,白袜子,套黑色圆口布鞋。坐定,水杯放在左角,双臂叉开按在腿上。说书人最好没有太明显的外观特征,好隐在书后,不让观众出戏。郭鹤鸣符合这个要求,就是这些年体重见涨,脸也见圆。他的圆脸上浮出笑么丝儿的表情——笑意丝丝地漫在他的脸上。像是一个标志,他进入演出状态,用话语营造一个中西交融的暧昧世界。
“细”是郭鹤鸣的追求,信息量得大,知识面得广,郭鹤鸣把《哈利·波特》的世界铺展开去,西方的神话,中国的星相学,英国史,魔法史,女巫的社会学著作,都是他的材料。有时候他从《哈利·波特》的世界里撕出去,拿出半小时批讲中西方的民间传说,他讲过凤凰,也讲过蜘蛛,有人觉得这些“零碎儿”太多了,“不给书听”。郭鹤鸣挺高兴,“终于有人说我慢了。”按他的说法,前两部一回书能占小说原文的三四张,到如今的《火焰杯》,一回书也就一张半的文字量。
听过越多传统书,越能明了评书《哈利·波特》的包袱。《囚徒》里,海格到三把扫帚酒吧救哈利波特,一通混战闯出重围,“改了赵子龙救阿斗了”;圣诞节假期之前校园里布置起来,五彩祥和多喜气,“改了宝玉娶亲了”。三位小伙伴去找海格,谈他养的狮身人面龙尾首,跑了,没人敢抓,郭鹤鸣仿着《君臣斗》里刘宝瑞先生的口风,“跑了没罪,逮了——斩立决!”他还在评书里放了“彩蛋”,“哈利波特掏出魔杖,念了一段咒语”,说到此处,他抱起一早放在桌上的三弦,唱了起来。笑声,掌声。这些西方小说中的情节与中国曲艺的瞬时碰撞总能被他的书座捕获,一种会心的笑,互文的笑。
外国小说的翻译语言,传统评书中的赞赋,各种曲艺种类中的腔调,在评书《哈利·波特》中交融。卢修斯在海格的房间看到邓布利多,“校长先生,晚上好”,同时拱手作揖。邓布利多答道,“夤夜至此,你找老朽有何贵干哪?”用的是京剧的腔调。哈利波特有时是个思维缜密彬彬有礼的英国男孩,有时,看着一碗复方汤剂想起豆汁焦圈——北京二环里子弟的那种纨绔范儿。《囚徒》最末,哈利波特在暗湖畔看到独角兽,“头至尾,长丈二,蹄至背,高八尺。头上长角,肚下生鳞。”观众大笑起来,郭鹤鸣也笑了,“外国书别扭就在这儿”。
他努力让这些复杂的元素显得和谐,得意之处,譬如以小说为范本,把英国人的幽默变成中国人的幽默。赫敏设计一系列环节,让三位同学变成斯莱特林的学生,书中一一列举,“这么多环节都会出错”,可是中国读者乐不出来。郭鹤鸣铺垫了半天赫敏自以为得意的劲儿,先翻,“你觉得哪个环节会出错?”再抖,“我怎么觉得哪个环节都会出错!”曲艺“铺平垫稳”、“三翻四抖”的经验被他拿过来,这是中国人的幽默,起码是他的这些北方书座会懂的幽默。
《密室》和《囚徒》两部,郭鹤鸣批讲中西,常是撕出整块,中西之间有个分界;到第四部《火焰杯》,他的跳进跳出变得更为频繁细密。有些碰撞,听书的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说了过去。包袱抖响,观众挟裹在笑声里,跟着郭鹤鸣的话语往前推进。听得久了,在“外国小说”和“传统评书”的密密交织里,好像也感受到了郭鹤鸣缝补的那个世界——不用过于在意所谓“违和”,郭鹤鸣自己也没有那么在意这个。
2016年7月23日,《哈利波特》说到第四年,郭鹤鸣上台,先说了一会儿闲白。有些感慨。
“20多岁谁都雄心壮志,现在我是怕红。最后一回《魔法石》,人比现在多,现在是什么行市呢?等于我是从头再来。前几天看一知乎帖子,看我名声还不算太臭,越发不想红起来,就想守着这个几尺小书台子说书。”
他又回应了对他的若干评价,慢,掺水。在非演出状态,他的笑容不多。
“有资格评价我的,取决于您手里的票根有多厚,因为这是买卖!”
“买卖”,一个江湖气的词儿,它提醒着评书原初的目的,得换钱。谈及《哈利·波特》作为“新书”,到底郭鹤鸣也这么说,“我们指着这个活着,都阳春白雪,不挣钱也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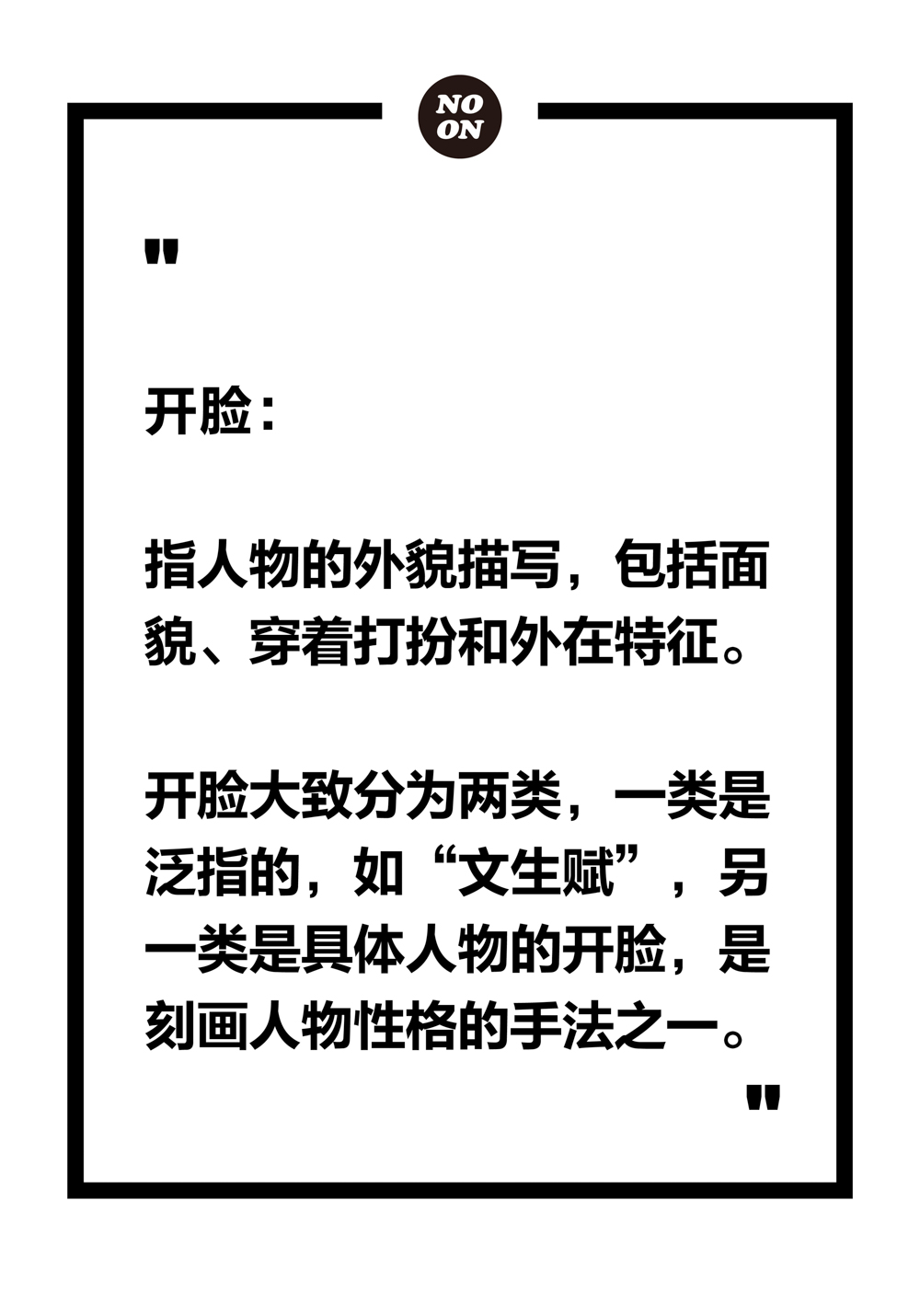
6
“鹌鹑蛋”是郭鹤鸣的老书座,她是北京人,比郭鹤鸣小几岁,打小就跟着爷爷姥爷听评书。2012年,她偶然看到了郭鹤鸣和他的《哈利·波特》。听过第一回,发现郭鹤鸣不是按小说开头,而是用罗琳后来更新的一段番外开场,鹌鹑蛋想,这是认真准备过的。她一路在网上听了下去。
鹌鹑蛋是个哈迷,从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哈利·波特》的小说就开始看,光说这部小说,她自认了解不比谁少。但听书到第13回,尼可勒梅谈炼制魔法石,她发现评书里有小说没有的东西。往后,“小说里没有的”越来越多。
“他书浑厚的程度是最吸引人的”,鹌鹑蛋说,“就是他知道的或者为了这部书刻意去了解的,都放在里头说。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尤其要上班的人,生活节奏很快,每天压力特别大,在这里就是个放慢节奏、汲取知识的过程。知识也未必有用,但确实可以丰富自己的眼界,多得到一些东西。”
《密室》开讲,鹌鹑蛋打算到现场,看好了节目单买好了票,到了却发现变成了相声。那时,郭鹤鸣找书馆场地而不得,隔了一年十个月才在新街口社区活动中心再说《哈利·波特》。鹌鹑蛋寻着去了,那是2014年底,“就觉得再听视频就不解恨了。”
“解恨”,就是这感觉。包括鹌鹑蛋在内的固定书座有十几个,都是打小听书,有如她一样的哈迷,也有一些是郭鹤鸣还在德云社时期就喜欢他的。这些年他们风雨无阻,笑称听书就如上班打卡。郭鹤鸣是个说书的个体户,小徒弟(就是在老舍茶馆郑思杰前头说《水浒》那位)帮他检票,媳妇儿帮他打理淘宝店,这些书座帮他看着录视频的相机,维持书馆秩序。郭鹤鸣下场时也常问鹌鹑蛋一句,有没有口误的地方、漏掉的细节。
老舍茶馆是个剧场,演员、观众截然分明。护国寺的小书馆因为小,前头说书,中间听书,后头候场的演员换衣服——太近了。但也是在这种亲近里,和年轻的说书人一样年轻的书座们部分建构了这些“新书”。
“新书”仍在尝试,曲艺行当仍嫌寂寞。有一回,我坐郑思杰的车从老舍茶馆到护国寺去,他打开音响,是大鼓,他左手开车,右手在大腿上拍着拍子,嘴里学着锣鼓音儿,这是京韵,这是铁片,这是京韵大鼓上变调出来的滑稽大鼓。再问,他可能是滑稽大鼓唯一的传人了,传到现在,活剩了四块整活,两块“半活”。
郭鹤鸣要学单弦,刘建云老师都不明白,你学这个干什么?光弹,谁唱啊?起初还有个女孩唱,她爸是炸油条的,喜欢听,非要女孩跟着刘老师学。女孩嗓子好,干净没杂音,就是一上课就张不开嘴,一下课就欢天喜地,骑车往外跑比郭鹤鸣蹬得还快。姑娘告诉他,不喜欢单弦,喜欢流行歌,喜欢潘玮柏。一年后,这姑娘也不学了,剩郭鹤鸣自己弹弦。
时不时地,周五或者周六,我还到小书馆去。这屋子胖子的数量明显超过北京的其他地方,于是我也逐渐融入。书座前面坐着,说书人后面候着。到点了,袋子里掏出上回穿过叠好的大褂。叠大褂有一套专门的方法,折痕留在袖子外侧,显得立正。看一个人会不会叠大褂,也能看出有没有师父传授。曲艺行里把穿上大褂叫“挑上了”,挑念三声,一个上扬的动作。
一个年轻的说书人挑上了。他一手握里头是扇子、醒子和录音笔的白手帕卷,从后排起立,往前头走。经过一扇窗户,帘子拉开一小片,黑夜使它变成一面镜子,对着那镜子他立了立头颈,整了整衣领,抻了抻下摆,顶上像有股劲儿把他猛拔高一寸,扭头转身,他款步走上台去。
—— 完——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文中说书术语,“道活儿”、“墨刻”由作者所拟,“开脸”来自1997年出版的 《中国评书艺术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