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品
《锦瑟》一诗为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名篇,也是最能代表李商隐个人风格的七言律诗,其原作如下: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约812年至约858年),晚唐开成年间进士及第,一生夹于“牛李党争”,早年丧父从浙江归乡河南沁阳,不得志。
这首诗作因为其内在的多义性,对其解读历来有争议,学界大体有如下观点:
“悼亡说” (朱彝尊等)
“世事身事说”(汪辟疆等)
以上两种说法从晚唐社会及李商隐的个人际遇论证,都言之成理,但都拘泥于诗作本身,或者说,只把——诗——这种特殊的文体看作传统意义上“咏物抒怀”的一个工具,将作者和及其作品一一对应。我们承认这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就功能性来说,在这个急剧变化,位格缺失的时代,文艺或者说文学如果超越抒情和叙述功能,作为生存本身的映射,对文本我们似乎可以再做分析和解读。
二.矛盾
李商隐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他的诗作在唐代浩瀚的典籍中属于异数:他的诗,除少数“咏史诗”外大体上未能像杜甫那样充满对现实的关照(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系),也无法如李白一样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蔑视权贵,追求自由。他的出身(与唐朝的皇族同宗,远亲)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利益;他的仕途(先后做过的几任小官都基本在原地踏步,甚至降格);他的派系(受知于令狐楚父子,但娶王茂元之女为妻,即他仕途不顺的根源之一,即:当时及后世指责的“去牛就李”);他一生的地理坐标从幼年时的浙江到甘肃泾川广西桂林四川梓州一直变换,但身份始终低微;他的人生轨迹基本都是被外力推着走,个人命运从来没有被主观意志掌控过。以上种种综合因素不免使他在将近50岁时写下的这首《锦瑟》中充满着对时间的迷惑,对命运的无力。对“此情”的回望之时,他的心中其实是无解的。
三.解读
格非先生以古诗词为蓝本进行演绎的小说有两篇:《凉州词》和《锦瑟》。后者发表于1990年的《花城》。
在这部架构非凡的中篇小说中,格非用四个相互循环的故事对“锦瑟”做了演绎,主人公都同名:冯子存。这个名字对应的社会身份和副标题分别是:
1. 隐居荒村者——“蝴蝶”
2. 赴江宁赶考的书生——“迷乱”
3. 茶商——“茶商的故事”
4. 为避战火迁居蓝田的沧海国国君——“梦中之梦”
这四段故事并非孤立成篇,而是相互交叉,相互循环。四个同名主人公的命运以锦瑟为圆心分别成为另一个自我的映照,这暗合博尔赫斯在《交叉小径的花园》、《沙之书》、《巴别图书馆》等作品中表现出的哲学观:作为最重要物理维度之一的时间,并非是像水流一样向前,而是共生。
更甚者,《锦瑟》可以直接看作博尔赫斯作品《圆形废墟》的西班牙语版本中国古典化,但在语言的节制处理,意向的塑造等等层面,格非并不输于这位南美巨匠(文学的描写对象不是判断文学作品水准和意趣的标准,这个复杂的问题另文论述)。
博尔赫斯的哲学观在本质上更倾向于东方的整体式的、隐喻式的、诗化的思维方法,换句话说,在博尔赫斯眼中,西方的二元的、Logos的、分岔化的认识手段并不适合于认识本体。
作为文本对文本的对应,李商隐的律诗《锦瑟》与后来的小说诗学演绎《锦瑟》在意向上或者说对生存的解读上并无不同。如果抛开李商隐原作中的用典不谈,其整体投射出的空灵或者说玄幻与后来的四个故事的指向性并无不同:
梦幻
玄想
时间
宇宙
无可捉摸的命运。
四.共时性
文学上所说的“通感”,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机制,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专著中对此有专文论述。我的理解,就是在主客体之间通过一个文艺媒介产生了共时性:在特殊的彼时,你的关照与作者同在,作者想表达的意向超越了个体经验成为你的触媒,使你“其心侑同”。
五. 时间
物理上的时间是一维的,即:不可逆;但文学上的时间是多维的,既在过去,也指向将来,既在此,也在彼。
“由相互靠拢、分歧、交错或永远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这是博尔赫斯对时间下的定义。作为博尔赫斯的传承者,格非先生笔下的“冯子存”同时经历着四个身份,四个存在,或者说,四个“冯子存”的集合解读了时间本身,它既指向有,也指向空无。
在“锦瑟”、“庄生”、“杜鹃”、“沧海”、“蓝田”等物化意向那里,他们既指代思念,梦幻,也指代时间流逝背后沉淀下来的灰烬:对世事的感慨,对命运的参透。
六.格非的历史观
对照李商隐的原作和格非对它的先锋演绎,就可发现,格非的小说并未停留在大多数解读者沉溺的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桑田等中国传统的古代文学意象所指代的思念或者苍茫本身,而是做了自己的推演,他只是利用了诗作的壳,来完成自己的叙述目的,(甚至,将“蓝田”和“沧海”的指代直接丢弃,将“沧海”戏仿成一个虚拟的国度)这和他的历史观有关。
陈晓明认为格非对于处理历史经常使用的方法即是:“造成历史过程的某种空缺,来给故事的历史性重新编目,故事本身为寻找自己的历史而进入逻辑的迷宫”。格非对历史揣想的合理性提出了诘难,历史与人的永恒差异使历史文本的的换喻结构常常蕴含着虚假的一面,那些貌似清晰逻辑严密的历史进程,那些自命为最合理的想象也许最不可靠,其文本的隐喻结构指向的不是真实,而执着于探寻真实过程中的一种荒诞与错位。在格非的叙事话语中可以轻易读出那些隐约浮现的破败的历史背景,它与那些无处不在的叙事“空缺”融为一体,不仅仅隐喻式地表达了生活世界的不完整性,生存没有着落与归宿,而且转喻式地表达了历史的起源性,过程及其结果的匮乏。幻想与幻觉语言成了格非抵御正统历史的侵入的利器,隐晦的修辞似乎成为他企图从“集体经验”中分离而出,建构一个自我意识的历史主体的手段。
就连格非自己都承认:“我对历史的兴趣仅仅在于它的连续性或权威性突然呈现的断裂,这种断裂彻底粉碎了历史的神话,当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仿佛发现,所谓的历史并不是作为知识和理性的一成不变的背景而存在,它说到底,只不过是一堆任人宰割的记忆的残片而已”。格非对时间的看法则与其历史观相呼应:“对我来说,午后的两个小时也许意味着天空滚过的雷声,植物和树木的清香,意味着无边无际的寂寞,隐伏的不安或欲望,意味着万物的生长和寂灭,雪片或杏花无声无息地飘落……这是因为记忆中的事物因其隐喻的性质总是与其他记忆中的片段紧紧地牵扯在一起,它有着自身的逻辑与生命”。
时间与记忆时常是格非文本里相当鲜明的历史维度表述方式。时间或历史不再被理解为连续性或有次序性,因为它不再被有次序的运动所支配,也意味着人类不可能有系统有秩序地观察或者认知外在事物的出现。
七.小结
李商隐的诗作在经历时间的洗练后依然闪闪发光,它的内在的混沌与朦胧成为它在现实风格强烈的唐代诗坛的异数。
而格非的戏仿也并非无意义的传奇推演,它背后折射出的哲学观念也值得认真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时间之于格非就像暴力之于余华和灵魂之于北村,是他们先锋文学的解读关键,由此也构成了独特的文学群像。
参考文献:
1. 陈雀倩.时间与暴力的对位:格非、余华写作中的历史蜃影与集体叙事[J].中外文学(台),200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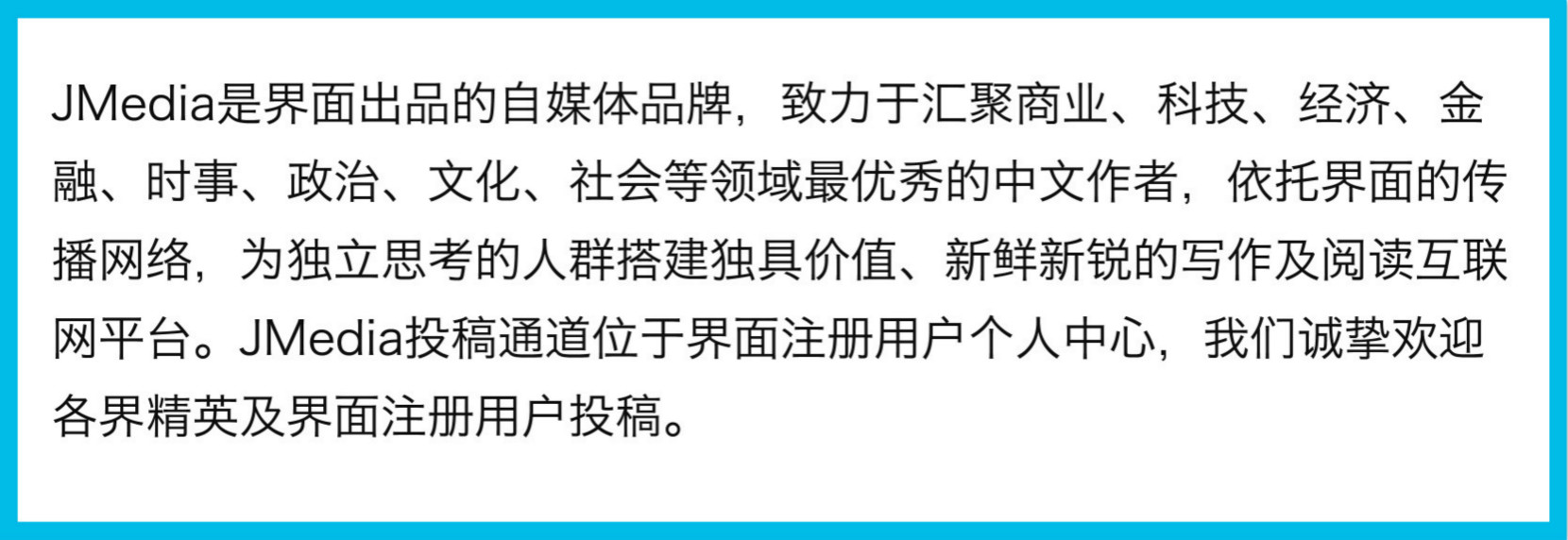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