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反乌托邦小说都有一个古怪的特色:故事开头便直奔主题。这是这种文学体裁风格鲜明的叙事模式,包括《1984》《美丽新世界》《别让我走》在内的绝大部分反乌托邦小说,都采用了这种开门见山的写作手法。作者采用这种纯叙述策略完全合情合理,毕竟一般而言,一本优秀的小说必须能够快速抓人眼球,而没有什么能比生动地描述一场灾难更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了。举个例子,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Emily St. John Mandel)在《第十一站》的开头,就描写了一种超级瘟疫席卷多伦多(随后殃及整个世界)的最初几小时,这段二十多页的叙述相当扣人心弦,让人迫切地想要阅读接下来的内容。这种风格的开头常能引人入胜——故事开门见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残酷逻辑:当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苟活,要么死。
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将在这个7月迎来第二季的完结。这部热度很高的作品也同样具备上述反乌托邦小说的特质。从第一集开始,观众就与伊丽莎白·莫斯(Elisabeth Moss)饰演的女主角奥芙瑞德一起掉进了人间地狱——一个名叫基列国的极权主义政权国家。我们在观看的过程中能大致了解基列国政权建立的背景(生态灾难、生育率直线下降、国会政变),剧中偶尔也会闪回政变前人们正常生活的样子——跟我们现在的世界大同小异。这部电视剧于2017年4月首播,当时的美国人民觉醒并发现了特朗普时代的真面目,剧中奥芙瑞德的迷茫与抗争某种角度上与他们的心态是同步的。我(指本文作者、作家Adam O'Fallon Price)和我的妻子每次看这部剧时都特别认真,同时脑子里还会浮现出一些骇人的联想,我知道许多观众也跟我们一样。这部剧把我们内心最深处对新政府的恐惧搬上了荧屏。
日子一天天过,《使女的故事》也一集集演下去,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少得可怜的、基列国建立之前的画面所吸引,那个时候奥芙瑞德的生活还波澜不惊,对自己后来可悲的命运一无所知。剧中,最让人心痛的内容莫过于对那个朦胧、美好且一去不复返的世界的匆匆一睹,它或许也是我们面对现实中这个逐渐成形的反乌托邦世界时最能找到共鸣的东西。这也是所有反乌托邦——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现实的——之专长:消除一切往日的痕迹。

我认为,我们对那些虚构的反乌托邦世界总是抱有过高的期望,要知道,它们可并不能保护我们免受现实的侵害。艾丽莎·罗森伯格(Alyssa Rosenberg)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社评中谈道:“反乌托邦小说——或者任何小说,说实在的——都不应该根据它对保护读者不受美国社会现行与彻底的变化之侵害的程度进行评价。一个故事只要情节有趣,经过精心设计,人物形象丰满有记忆点,就足够了。”
虽然要求一篇消遣时光的文字同时具备除娱乐大众以外的其他元素似乎有些太过分,但在大多数反乌托邦式的文学作品中,满足这些“高要求”已是可谓心照不宣的了。毕竟,无论是反乌托邦世界,还是乌托邦世界,与现实世界贴合的地方越多,越能让读者找到共鸣,那么作者的创作就是越成功的。“反乌托邦(dystopia)”与“乌托邦(utopia)”有着相同的“topos”词根,它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地方”,这两个词意在通过夸张的文学描述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以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我们似乎还可以对它们作出进一步的指望:它们除了让我们了解当前所处的困局外,还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以及应该怎么逃离。
拥有这种心态的人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不约而同地购买了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著作《1984》,令其销量瞬间上涨9500个百分点,这本出版于1949年的小说竟在21世纪的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列第一。在一片残酷的谎言、欺骗和伪装中,这些读者投向了虚拟世界的怀抱,不仅由于这个书中的世界同样与政治有关,而且因为他们当时很可能正在寻找着什么——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或者至少是通过《1984》了解自己当下所处的政治背景。

那他们可能会感到失望了。抛开其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见不谈,《1984》在基本结构上的留白与《使女的故事》相类似——没有把太多笔墨放在“大洋国”之前的世界。故事开头展现的已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读者跟随主要人物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的脚步,近距离观察他在第一空降场和真理部骇人听闻的生活和工作。而在《使女的故事》的基列国中,虽然新执政的宗教极端政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但作为观众和读者的我们却并不知晓太多他们上台的背景。对于《1984》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核冲突或许可以成为美国、英国等国家合并成“大洋国”、并最终由“英社”统治的政治背景。但这本书也没有对战前的生活做多少重要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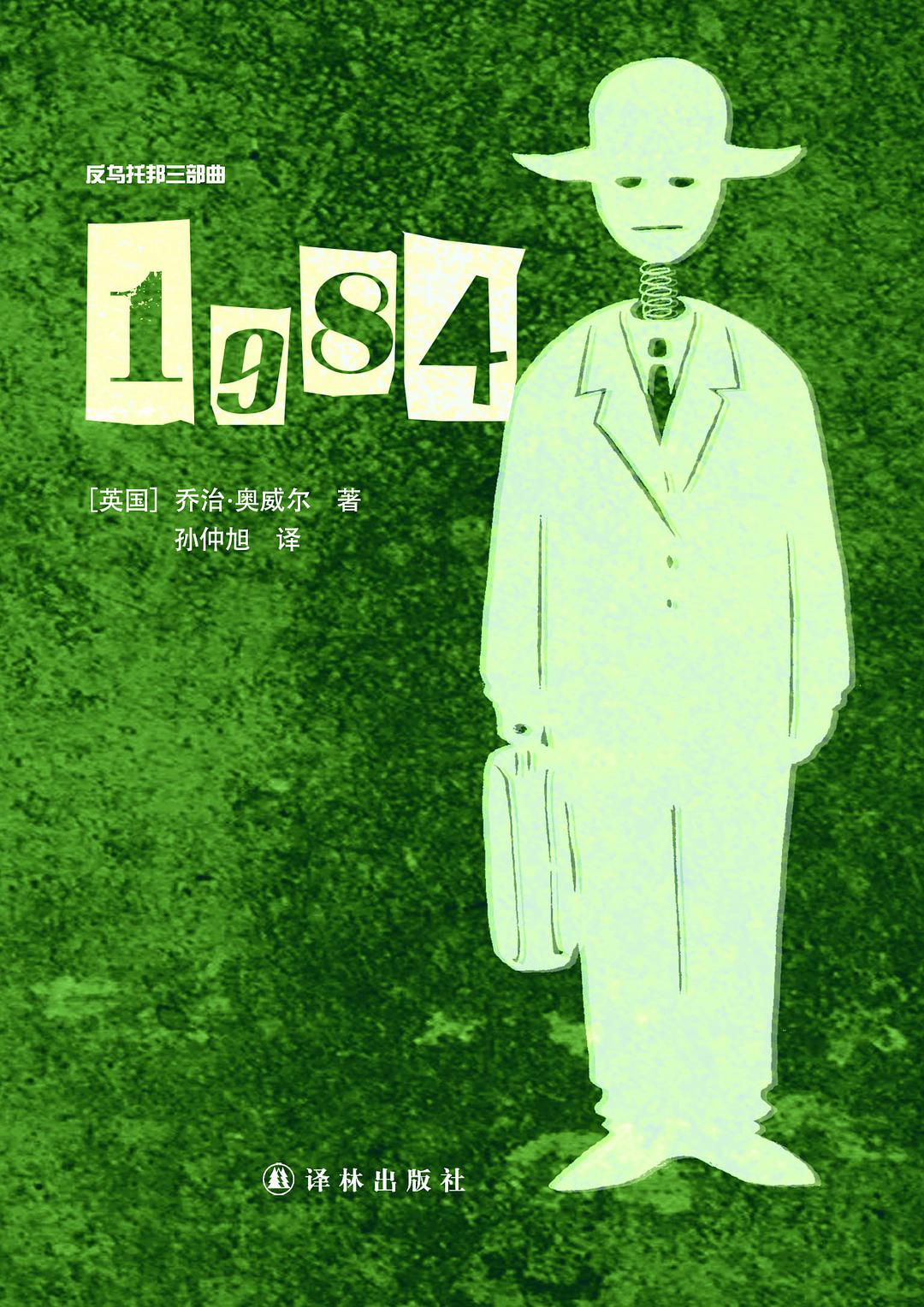
[英]乔治·奥威尔 著 孙仲旭 译
译林出版社 2013年12月
另一本反乌托邦政治小说《不会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在这方面也大同小异,这本1935年的小说也在2016年大选期间登上了畅销书榜,因为书中的主要角色巴兹·温德利普是一个特朗普式的恶棍。温德利普与特朗普一样,在总统竞选中胜出,但我们对他获胜的历史背景和胜选后紧接着的恐怖统治同样一无所知。与它们类似的还有《巴西》(Brazil)《羚羊与秧鸡》《饥饿游戏》和《机器人会梦到电子羊吗?》等作品,作品开头便已是灾难过后的残局。不远的过去已经是遥远的记忆了。美国作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曾说过,优秀的小说就像一个完好无缺、绵延不绝的美梦,而优秀的反乌托邦小说则像一个完好无缺、绵延不绝的噩梦。
反乌托邦世界与噩梦一样,具有某种“密不透风”的属性。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是无法逃离的——如果你可以逃出某个反乌托邦世界,那它就不能算是反乌托邦世界了;它可以说是《真爱至上》温馨结局之后的第三个小时。在反乌托邦背景下,创造“美丽新世界”的同时,这个新世界的棱角会被全部磨平,原来世界的记忆也会被全部毁灭。在《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回忆:“他第一次听到老大哥的名字时……大概是在六十年代,但是无法确定。当然,在党史里,老大哥是从建党开始时起就一直是革命的领导人和捍卫者的。他的业绩在时间上已逐步往回推溯,一直推到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个传奇般的年代,那时资本家们仍旧戴着他们奇形怪状的高礼帽、坐在锃亮的大汽车里或者两边镶着玻璃窗的马车里驶过伦敦的街道。(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就是历史车轮转动的方式,谁能想到,唐纳德·特朗普竟能侥幸胜选,并在当选后成为如此令人厌恶的存在呢?他的当选可以说是开了倒车,破灭了我们先前畅想的一切可能性。比如:还记得我们似乎将百分百迎来第一位女性总统的时候吗?还记得公开的种族主义会遭公众唾骂的时候吗?还记得美国环境保护局尚运作正常的时候吗?人们对灾难本身就是健忘的。

现实和虚构中的独裁主义都利用人们这一心理特点建立起了自己的优势。当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持续处于被攻击和焦虑状态时,他便失去了联系过去、以史为镜的能力。这种创伤在独裁者政治目标——毁灭记忆是其最本质的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并不罕见。在大部分反乌托邦小说中,泰山压顶般的残酷统治和严酷秩序会让人出于本能、惊慌失措地只关注“当下”,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才能暂缓一阵回顾“过去”的记忆碎片。
在暴君的视角中,记忆——无论是私人记忆还是文化记忆——都必须擦干抹净,越快越好。否则人们可能就会意识到当下的失常状态和内容,并在未来对它提出异议和修改。斯大林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武断专制和暴力(或者威胁)的使用不仅是为了让反对者和政敌闭嘴,而且是为了迎来一个全新的社会,剪掉与国家历史相连的记忆脐带。
菲利普·罗斯在其作品《反美密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写了一个与现实相反的故事: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在1940年总统大选中击败了罗斯福。他也由此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典型反乌托邦写作结构的反例。这本书用开头50页的篇幅描写了查尔斯·林德伯格就职典礼之前发生的事情,后面对灾难性后果的叙述也没有操之过急。他笔下这个反乌托邦世界的真正可怖之处在于林德伯格当上总统后的主张之一——让美国国内的反犹太主义正常化。
作者罗斯有犹太人血统,他的家庭居住在美国纽瓦克时曾遭受邻里的许多轻视和白眼。在小说中段,一个父亲收到了一封信,得知政府计划让住在城市里的犹太人统统去中西部“安家”。大多数反乌托邦小说估计会把这里作为故事的开头,因为这才是灾难的开始。这段情节也向读者说明了,一个对犹太人大屠杀依然记忆犹新的犹太作家,会对这种阈限年代里犹太人的生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加以深刻细致的描写。在这样的时代设定里,所有一切都天翻地覆,只有生活,以及重要的仪式和庆典还在继续。“生活还要继续”是这本书的隐含的中心思想之一,也是作者从犹太人大屠杀中悟到的重要一课——生活必须继续,而且必须与过去的历史紧密相连。
“历史是一个我正试图从中醒来的噩梦。”《尤利西斯》主人公斯蒂芬·迪德勒斯在辩驳迪西先生的历史观时说道,后者认为历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的代名词,凡事皆有定数。而无论是在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作品里,历史进程——即时间本身——有着专横的一面。它前进的方向只有一个,而且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
从这种猛攻当中“觉醒”的欲望——即对过去发生过和本可能发生的事情保持清醒,以及对当下有可能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我认为,是一种心理基础,它能够在这种时代为我们逐步进行如下的思想武装:这并不正常。没错,这几个字恰如其分地抓住了唐纳德·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的精髓,并且主张人们反抗。但从更深层次来说,它隐含了反抗反乌托邦世界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方法:记住这个世界以前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发生的一切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这个世界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运作了。反乌托邦——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现实的——或许无可避免,但绝不是不可逆转的。忘记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已经是老生常谈。或许这么修改一下更加符合实际:忘记历史的人注定要惨遭厄运。
(翻译:黄婧思)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巴黎评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