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著名思想家、性别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曾在美国总统大选竞争如火如荼之际表达过她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女权主义、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公平正义及反种族主义的强烈反弹的忧虑。两年后,她依旧不惮在公开场合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之所以如此难说服我的政府全球变暖是一个对未来宜居世界的真切威胁,是因为他们认为扩大生产和市场、获得盈利是增加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核心;也许他们没有想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全球,继而影响到这个我们所有人都赖以生存的宜居环境的存续。”
这是巴特勒8月14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办的“相生之道”对谈会上说的话。前一晚她刚刚结束正在北京举行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行程,她在大会上发言的最后一句中提到的“共生”(co-livability)恰好成为她在上海演讲的题眼。巴特勒不仅是酷儿理论的标志性人物,在过去的20年间,她也被认为是政治与社会理论领域的领先人物。在此次的对谈中,她从批判个人主义开始阐释了她对人权和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思考。
巴特勒的演讲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个人身份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说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是相互依赖?冲突能否以非暴力化解?
在巴特勒的讲座结束后,六位中外学者、艺术工作者针对巴特勒的发言展开讨论,巴特勒也对学者和观众的表述和问题作出了回应。她谈到了世界主义、可见性、酷儿的生活状况、集体行动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异性恋本质上是一种忧郁症?“我们”又如何克服恐惧?
“个人主义”是一种虚构
朱迪斯·巴特勒首先感谢所有当晚汇聚在一起的讲者与听众,但她旋即提出,并不能预先假设,在讲座现场的“我们”,是一个有内部统一性的概念。聚集在一起的“我们”,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彼此能否相互理解,是否能够沟通和交流?也许每个人都是自愿来到讲座现场,但每个人是否确切知道“自己”是谁?每个人追寻的目标也许都是相互冲突的,“我们”的内部也具有各种复杂性,每个人生活的环境、使用的语言、来自的地方,可能都是千差万别的,与此同时,那些不在场的人、成为历史的人,同样也对“我们”的定义产生影响。

由此,巴特勒引出了个体的概念。巴特勒提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学说建立在一种设想之上:我们是从某种自然状态过度到现在的政治社会现实的。在那种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已经是相互独立的个体,彼此会发生冲突。然而,这种学说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人际关系首先应该是冲突,而不是其他的情感,比如依赖,或者爱慕。
《鲁宾逊漂流记》的主角鲁宾逊·克鲁索可以说是这种设想中的标准形象:他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孑然一身的人,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会被社会经济生活的种种需求所打破。当他与其他人遭遇的时候,就产生了冲突。个体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产生了冲突与争斗,这种冲突只有通过一种管制的社会性(regulated sociality)来仲裁。某种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就此作为冲突解决方案诞生,它强制个人在法律的框架内约束欲望。
然而,巴特勒认为,这种所谓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虚构,但它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基础,并且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干预。在此,巴特勒无意揭露虚构背后的真实,而是想要对虚构背后的权力结构和运作关系进行分析和考察。
巴特勒指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个体的标准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成年人,他不需要经过嗷嗷待哺的阶段,不需要依赖父母亲友,也不需要依赖社会制度来学习和成长,而且,他天生就拥有了自己的社会性别——男性。这个“原始男性”(original man)仿佛生来就是一个顶天立地、足智多谋的人。在这样的一种基本假设背后,其实已经出现了异化——它通过某种排除机制,建立起了自己的等级制度。
在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看来,这样的一种“社会契约”实际上是一种“性别契约”(sexual contract)——其中没有女人,只有个体化的(异性恋)成年男性,女人是作为他们的附庸而存在的。这种社会契约论也没有假设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依赖。
“社会契约”的虚构在政治理论中极具影响力,但它同样暗藏着权力的压制关系。因此,巴特勒指出,在讨论非暴力的政治和伦理的时候,不能忽略人们习以为常的理念、状态背后蕴藏的结构关系。
相互依赖才是人际关系的基础
巴特勒紧接着提出了她关于“非暴力”(non-violence)的看法,其出发点就是假设人与人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其次才有各种冲突和矛盾。至于生命和平等的关系,每一条生命都是等价的,丧失任何一条生命都是值得哀悼的。在巴特勒看来,只有在抛弃了个体主义的枷锁之后,才能够理解一种更加激进的非暴力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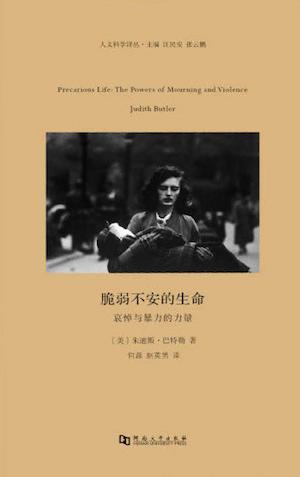
朱迪斯·巴特勒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巴特勒指出,每个人都经历了个体化的过程,没有谁是天生的个体,所有人生来就处于一种“激进的依赖”(radical dependency)关系之中。
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只有残障人士才需要在生活中获得他人的支持,但巴特勒指出,哪怕是最基本的人类需求也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周遭支持的,“无论是移动、呼吸还是寻找食物”,“所有人都需要一个建成环境来进行移动,都需要有人准备和分配食物才能将食物送入口中,都需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提供健康的空气来呼吸。”
巴特勒表示,拉康关于“镜像阶段”的著名论断能够很好地形容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的自负,即我们对相互依赖、彼此共生的无知无觉:我们就像一个站在镜子前的男婴,兴高采烈地以为镜中只有自己,满足于一种全然的自足性,却忽视了其实是妈妈抱着他或其他支撑物扶持着他。
在巴特勒看来,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将改变我们对脆弱、冲突、成年、社会性、暴力和政治的看法,特别是当我们反观当下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时,就会意识到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并没有得到承认,甚至被滥用。巴特勒指出,资本主义大公司遍布全球,但这并非全球化的全貌;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过程中确实有了一定程度的消退,然而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形式也在不断涌动。
全球变暖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他们考虑的是其他问题。巴特勒在此对特朗普政府提出了批评,“之所以如此难说服我的政府全球变暖是一个对未来宜居世界的真切威胁,是因为他们认为扩大生产和市场、获得盈利是增加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核心。也许他们没有想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对全球产生影响,继而影响到这个我们所有人都赖以生存的宜居环境的存续;或者说,也许他们知道自己采取的是全球毁灭性的行动,但这看起来也是一种权利,一种权力,一种无法妥协的特权。”
“只有我们重新思考、重视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我们才能开始思考环境威胁、全球贫困、国际移民问题,这是一项全球责任。”巴特勒说。
非暴力构建在激进平等之上
巴特勒接着阐述了她对暴力和非暴力的理解。她认为,大部分形式的暴力都和不平等有关,人们做出决定:何时、何地、针对什么人实施暴力,背后都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如果我们说不能伤害某种生物,但是对于这种生物,我们并不了解,无法描述,甚至根本就未曾给它们命名。这种情况下,就无法禁止对这种生物实施暴力。如果我们说不能使用暴力,其对象必须是活着的生命,有名字的生命。假设所有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这种主张只有在平等适用于所有生命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
防止暴力的前提是承认每一条生命都是可哀悼的(grievable),然而巴特勒指出,生命的可哀悼性是不均质、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特性与每个人活着的状态息息相关,也扭曲了我们对暴力和非暴力的看法。在巴特勒看来,先要承认这种生命可哀悼性的不均质和不平等,才能够转变我们对平等和暴力问题的争论。
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总会有冲突与矛盾,这就涉及到暴力的使用问题。什么时候使用暴力是正当的?这其中牵涉一个概念:自我防卫(self defense)。
巴特勒以美国外交政策为例,她指出,美国将每一次针对别国的攻击都称为自我防卫、正当防卫,现在还有一种“预防性攻击”概念,针对任何存在潜在危害的团体或个人,都可以进行预防性攻击。因此,自我防卫和非暴力,其实是一种孪生概念。暴力针对的是不属于“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造成了威胁,“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对“他们”实施暴力。
巴特勒指出,非暴力貌似是一个道德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什么生命值得保护?什么生命不值得保护?在此,我们已经对生命进行了区分:值得哀悼的和不值得哀悼的。用来区分两者的,是不正当运用的社会规范,也就是生命权力(biopower)。
我们如果要保护生命,就需要一种更加完全和彻底的平等主义的主张,更加激进的平等主义主张。巴特勒认为,非暴力的道德基础是对激进平等(radical equality)的承认,“更具体而言,非暴力的实践需要我们反对种族主义、战争逻辑这种区分值得保护和不值得保护的生物政治形式(biopolitical forms)”。
国家垄断了暴力形式——葛兰西和本雅明对此都有过论述——但反对暴力需要认识到:暴力不只是通过拳头的形式体现,也可以通过制度,把个体分为三六九等。谁的生命值钱?谁的生命不值钱?这都体现在当下的政治与政策中。巴特勒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认知,在道德与政治生活中不再将侵犯与悲伤自动转化为暴力相向,这是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社会联结虽然不是自主选择的,却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这个逆全球化浪潮迭起、身份对立超越身份认同的时代,讨论全球责任和非暴力看似不合时宜,但巴特勒认为并非如此。
“有些人跟我说:你怎么能相信全球责任呢,这太天真了。我反问他们:你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人为全球责任辩护的世界吗?他们说:不。也有人说:非暴力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当我反问他们:你是否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人为非暴力、为这种不可能而进行坚持的世界当中?他们总是回答说:不。”

【现场交流】“异性恋没法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
李圭(Kyoo Lee,纽约市立大学哲学教授):论语里面有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没有人天生就是朋友,我们都是成为朋友的。成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在这句话里面,把距离、友谊、好客,结合在一起。是个人偏好和选择决定了谁能够成为朋友,那么当我们承认人与人唇齿相依的生存状态时,谁被排除在外,谁被包括在内?谁会被我们认为是朋友?
何成洲(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外国语学院教授):当代新儒家重新诠释天人合一的理念,强调人、动物、自然、大地是有机整体。这些与巴特勒提出的相互依赖和非暴力有相似性。中西方学术对话是有共同基础和共同努力目标的。我觉得你的观念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意味,但是你好像没有谈论过这个概念。
朱迪斯·巴特勒:我的确对于世界主义不太感兴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尝试去思考跨越地域、语言甚至是意料之外的生命形式的团结(solidarity)。我把世界主义理解为一种道德立场,但它太过以城市为中心了,我担心的是农村被世界主义抛弃,我不认为我们能够继续这种农村和都市的分野。
林曦(复旦大学政治哲学副教授):我们在理解巴特勒教授提出的概念的时候,有一个可见性的问题。很多时候,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我们认为的弱势群体,在大街上是看不到的。这就涉及公共空间的空间设计和空间正义。用列维纳斯的一句话来讲,我们在进入到一段社会关系之前,首先看到“他者”的一张脸。我们必须要为这样的社会关系,为这样的共存,进行道义上的反思和承担。
朱迪斯·巴特勒:“看见”可以通过声音,或者通过阅读,你在阅读一篇关于移民的文章的时候,他者的脸也会浮现在眼前。并不是说一定要是那种面对面的接触。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必须强调一种超级可见性(hyper-visibility)来获得道义和响应能力。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在我做博士论文过程中发现,同性恋往往被排斥在异性恋家庭之外。由于儒家孝道的根深蒂固,原生家庭的同性恋者接受的伤害在中国社会特别明显。非常有趣的是,近年以来,越来越多同性恋父母开始为孩子争取权利。原生父母从同性恋最主要的压迫者变成了权利的维护者甚至创造者,也呼应今晚的主题:两代人如何实现相生之道。
朱迪斯·巴特勒:关于酷儿群体被原生家庭排挤抛弃的问题,我们期待更有意义的社群形式给他们提供情感支持。我们需要为那些被他们的家庭残忍抛弃或拒绝的人提供帮助。这种社区形式,我不想称为家人,我认为亲人的概念涵盖的范围更广,或是友谊,或是一种团结的共同体,这些各不相同的概念包括各不相同的关系形式。

朱迪斯·巴特勒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张涵露(独立策展人、Artforum中文网编辑):我曾经参加过一些艺术小组和自我组织。这几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差异这个问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我们最熟悉的处理差异的方式。我今天有不同的看法。一旦把“和”作为希望的结果,可能会压制差异,以此来导致生命受到磨损和伤害。当我们面对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同时,我们不该为了避免冲突而去把差异抹平。
另一种避免冲突的方式是分割空间、制造围墙。去年,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清退”互动地图。在两三天之内,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地方聚集起来,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时间制定分工。因为这件事情,我对于合作继续非常强烈的兴趣。我们是否有可能在这个充满矛盾和差异的时刻,重新去缔结一个个临时的联盟,无论是思想的联盟还是行动的联盟。我觉得是和谐的区隔而不是共同的差异,阻挠着我们的共同生活。
朱迪斯·巴特勒:我想说集体行动是有趣的。在一个团体里面工作,特别是一个艺术团体。你们并不一定需要彼此相爱,但你们依然聚在一起做事。你们在做一个关于世界的实验,试图融合世界,即便是在一个微小的层面上。这些不仅仅是短暂的“我们”时刻,这种合作方式,让我们超越个人主义的窠臼,又让我们意识到与不相识的人并肩行动的重要性,因此它更具政治性。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为我们不认识、甚至无法忍受的人创造生存空间,这意味着我们也需要思考联盟(alliance)的条件。
张念(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教授):人类如果能够团结在一起,不是基于价值、利益的交换,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恐惧。我知道我的年轻的朋友们,就每天生活在细微的、日常的、悄无声息的压力和暴力之中,这种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到的。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暴力:我说不出话。为什么?一种可能是不让我说,还有一种更可怕,我可以说,但是我没有说的发声系统。我们的边缘人群、酷儿朋友、女权主义者,他们在努力奋斗,试图发明一种发声系统。
中国人的养生之道里面,有另一层含义,不是叫你去喝汤药,而是去享受身体的愉悦,寻找让身体愉悦的对象。这时候,身体会遭受另外一个敌人——“性别规范”——说你只能按照脚本扮演男人或女人,否则你就是垃圾,只配在社会的阴暗角落悄悄生活。个体会感受到:这个描述是别人给我的,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会出现恐慌。整个酷儿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在教会我们一种政治实践的智慧,通过我的身体实践,我自己发明了自己。
观众:您有一句话:异性恋本质是一种忧郁症。能否阐释一下?
朱迪斯·巴特勒:忧郁症与被否认的损失有关。很长一段时间,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一个酷儿小孩,你不能大声说出你爱上了谁,失去了谁。无论是宣示爱情,还是公开的哀悼,都是被拒绝的。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她们依然留在柜子里,没有公共空间可以表达。我指的是那些因为并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而受苦的人——异性恋没法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也许可以生活的不那么恐惧,不那么压抑。
观众:我们如何克服恐惧?
朱迪斯·巴特勒:我们需要分辨出权力希望我们感受到的恐惧是什么。如果我们对他者感到恐惧,就是对权力的臣服。那么这种对权力的恐惧来源何处?那是对惩罚、驱逐、入狱的深层恐惧。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不同的地方恐惧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需要具备一起言说恐惧的能力。恐惧的反面不是个人的勇敢,而是团结。我认为团结能够克服恐惧,因为这展示了有人与你并肩作战的这种联结性……我认为我们需要抛掉对个人英雄、个人公共知识分子和个人勇气的执念,意识到我们有支持彼此的力量,为创造一个恐惧感更低的世界作出努力。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