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后浪出版公司新近再版的《往事与随想》分上中下三册,加起来一共有1896页。无论从体量、内容还是思想角度看,俄国思想家、作家赫尔岑这部回忆录都无疑是一部巨著。《往事与随想》是他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不仅忠实而真诚地记载了他的一生,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19世纪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的血腥镇压,直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往事与随想》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
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碰到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群众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他是作为历史见证人写他的回忆录的,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绘一切,评价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编年史或大事记,“它有统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会思想的热情探索。”

巴金很喜欢这部著作,曾希望将之译出,但因身体原因最后只译了五分之一。在这一版译本的译者项星耀完成翻译后,巴金曾致信他说:“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录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但几年来我疾病缠身,写字吃力,有话写不出,也无力写,只好等我身体养好点,或者您的译文出版时,再拿起笔写出我的喜悦。再一次感谢您。”
项星耀在这本书中的前言中写到:“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早在40年代别林斯基即已指出,赫尔岑的艺术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思想的威力’。他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赫尔岑总是站在维护进步事业的高度,评价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在赫尔岑看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是首要的,这规定了他的写作意图和目的,写作不是作家个人的事,而是人类整个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回忆录中,政论性和哲理性插话几乎随处可见,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把书名定为‘往事与随想’,便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多么精心挑选的书摘,都无法呈现《往事与随想》的恢弘全貌及艺术性,光是就赫尔岑在书中提到的人物来说——19世纪欧洲解放运动的许多历史人物,如马志尼、加里波第、科苏特、蒲鲁东、路易·勃朗等等;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如罗伯特·欧文、雨果、密茨凯维奇等等;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如别林斯基、恰达耶夫和许多十二月党人——人物众多,面貌各异,无法一一呈现。何况他在书中着重写的不是这些人的外形长相,而是试图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在适当的场合刻画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内心感受。经后浪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新版《往事与随想》节选了部分文字,相较全本而言连冰山一角难称得上,但从中我们以可以看出赫尔岑对时代图景的细致观察、高超的讽刺才能、直指社会弊病的坦诚与勇敢,以及19世纪中叶莫斯科社会气氛和文学圈子内部的幽微嬗变。
《往事与随想》
文 | 赫尔岑 译 | 项星耀
我从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发现两个阵营已壁垒分明。斯拉夫派戒备森严,作好了战斗部署;它的轻骑兵由霍米亚科夫率领,非常迟钝的步兵则以舍维廖夫(莫斯科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和斯拉夫派理论家,曾与别林斯基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及波戈金(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莫斯科大学教授)为首,此外还有前沿狙击兵和志愿兵;它的雅各宾极左派否定基辅时期(公元9至12世纪的基辅罗斯)以后的全部历史,它的吉伦特温和派则只否定彼得堡时期。他们在大学里有自己的讲台,在社会上有自己的月刊(指《莫斯科人》杂志,它出版于1841至1856年),尽管这月刊常常拖到两个月以后才出版,但总是出版了。这个大本营中有黑格尔派东正教徒,拜占庭神学家,神秘主义诗人,许多闺阁名媛,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
我们的战争成了莫斯科文学沙龙的重要话题。一般说来,俄国当时正进入对智力活动发生浓厚兴趣的时期,那时因不能接触政治,文学问题成了生活的中心。一本优秀作品的诞生(在初版中,“一本优秀作品”之后有“例如《死魂灵》”几个字)是一件大事;批评和反批评争论不休,每篇文章都受到密切注意,仿佛从前的英国人或法国人注视议会的辩论一样。社会活动的其他一切领域遭到压制,知识阶层只得在书籍世界中寻找出路,事实上也唯独这个世界还隐晦曲折、半明半暗地透露了对尼古拉专制暴政的抗议,这种抗议在他死后才变得比较公开和响亮。
莫斯科社会通过格拉诺夫斯基,对西方向往自由的思想,对解放头脑并为此而进行斗争的思想,发出了欢呼。通过斯拉夫派,它为被侮辱的民族感情,对彼得堡的比龙式傲慢态度发出了抗议。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我在莫斯科熟悉的只是两个圈子,它们构成莫斯科社交生活的两极,因此我谈的也只限于它们。起先我的周围全是一些老人,有些是叶卡捷琳娜时期的近卫军军官,我父亲的老同事,另一些是把参政院当作避风港和养老院的、他哥哥的同事。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莫斯科,文学界的上流社会,我要谈的只是这部分人。那些拿过笔和剑的老人正在等待按官级穿戴整齐之后走进坟墓,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却不想争取任何官衔,一心“读书和思想”,至于在这两代人之间保持着或存在着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中间地带是真正的“尼古拉罗斯”,一个平凡庸俗的世界,既无叶卡捷琳娜时期的独立精神,1812年的大无畏气概,也没有我们的追求和兴趣。这是可怜的一代,被压垮的一代,只有几个殉难者在那里挣扎,喘息,最后死亡。

我谈到莫斯科的客厅和餐厅,是指普希金曾经主宰过的那些地方;在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十二月党人的声音;在那里,格里鲍耶陀夫发出过微笑;在那里,米·费·奥尔洛夫和阿·彼·叶尔莫洛夫由于在宫廷失宠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最后,在那里,霍米亚科夫从晚上九时一直辩论到清晨四时;在那里,康·阿克萨科夫拿着摩莫卡皮帽为莫斯科大声疾呼,尽管谁也没有攻击它,每逢拿起香槟酒,便要偷偷祝告和祈祷,尽管大家知道这一点;在那里,列德金为了增进黑格尔的荣誉,论证了上帝作为个体的存在;在那里,格拉诺夫斯基侃侃而谈,发出了坚定的声音;在那里,大家怀念着巴枯宁和斯坦克维奇;在那里,恰达耶夫衣冠楚楚,抬起蜡像似的柔和的脸,发出尖刻的讽刺,惹怒了惊慌失措的贵族和斯拉夫派东正教徒,他的讽刺总是具有独特的形式,特地裹上了一层冰冷的外衣;在那里,老当益壮的亚·伊·屠格涅夫(俄国历史学家)谈笑风生,欧洲的一切名流,从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耶(她的沙龙曾是巴黎政治和文学活动的中心,夏多布里昂等名流经常出入其中)到谢林和拉埃尔·瓦恩哈根(德国女作家,她的家在19世纪初期成为柏林的文学沙龙),无不遭到他的揶揄;在那里,博特金和克留科夫沉浸在泛神论的享受中,津津有味地听谢普金讲故事;最后,别林斯基有时也会像康格里夫(英国将军,烧夷弹的发明者)的烧夷弹一样突然飞进屋里,把遇到的一切统统烧成灰烬。
一般而言,莫斯科生活与其说都市化,不如说更为乡村化,只是老爷们的住宅彼此连接罢了。这儿的人当然不会千篇一律,不同时代、不同教养、不同阶层、不同经纬度的俄国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模式。拉林和法穆索夫们(拉林是《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地主,法穆索夫是《聪明误》中的官员和贵族)在这儿安度晚年,但不仅他们,这里还有弗拉基米尔·连斯基和我们的怪物恰茨基(连斯基是《叶夫根尼·奥涅金》中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恰茨基是《聪明误》中一个进步的贵族青年),至于奥涅金,那太多了。他们可干的事都很少,生活清闲,无忧无虑,得过且过。地主的放任不羁,说句老实话,我们是欣赏的;这中间包含着某种气魄,是我们在西方的市民生活中看不到的。那种奴颜婢膝的买卖人气质(在达什科娃的《回忆录》中,维尔蒙特小姐曾提到这一点,我自己也还见到过)在现在谈到的这些人中间是没有的。构成这个社会的是不做官的地主,或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安慰亲属才做官的地主,一些生活富足的人,以及青年文学家和教授们。这个社会是自由的,各种关系还没有凝固,各种习惯也还没有成为清规戒律,因而与从前欧洲的生活不同;同时,它还保存着西方彬彬有礼的传统,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养,可是在西方已每况愈下;此外,它还杂有斯拉夫人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放纵逸乐的脾性,这构成了莫斯科社会独树一帜的俄国特色,也使它十分伤心,因为它梦寐以求的就是与巴黎看齐,但这个愿望大概只能是愿望而已。
我们所知道的欧洲还是从前的欧洲。一提起它,我们就想到伏尔泰在巴黎的沙龙中执牛耳的时代,那时,听狄德罗的辩论不过是家常便饭;那时,大卫·休谟的莅临巴黎竟使整个社会为之轰动,所有的伯爵夫人和子爵夫人都对他百般奉承,竞相卖弄风情,致使她们的另一个宠儿格林(德国文学家及外交家)大为恼火,认为这简直不成体统。我们的脑海中有的仍然只是霍尔巴赫男爵(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的晚会,《费加罗》初次上演的盛况,那时,全体贵族整整几天站在那儿排队买票,时髦的夫人们不惜以干粮代替午餐,只为了要弄到一个座位,看一下一个月后将在凡尔赛宫上演的这出革命戏剧。
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不仅18世纪的那些客厅不复存在——这是一些奇怪的客厅,在珠光宝气、花团锦簇中间,贵族用自己的纤手和乳汁哺育和养大了一头小狮子,这就是后来的革命巨人——而且另一些客厅,例如斯塔尔夫人(法国著名女作家,她的家曾成为巴黎的文学沙龙)和雷卡米耶夫人的客厅,也已收场了,在那里聚会的是贵族中的一切名流,文学家和政治家。现在他们却怕文学,而且文学也根本不再存在;党派分歧如此之大,不同政见的人不可能互相尊重,会集在一间屋子里。
恢复原来意义上的“客厅”的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它就随着它的女主人一起消失了。德尔芬·盖(法国女作家)用尽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思想,才使彼此猜疑、彼此仇恨的客人勉强相安无事,保持体面的和平。这种一触即发的、紧张的休战状态,决不能带给人任何快乐,主人送走客人之后,只觉得精疲力尽,倒在沙发上,感谢上帝,这一晚总算太平无事,没有出什么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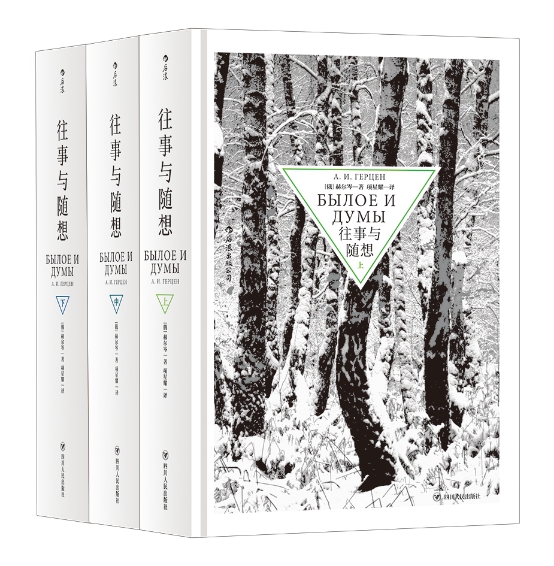
[俄]赫尔岑 著 项星耀 译
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08
确实,今天在西方,特别在法国,文人的清谈,优美的风度,高雅的仪态,早已失去魅力。把可怕的马蜂窝用皇帝的龙袍覆盖之后,小市民将军们,小市民部长们,小市民银行家们便寻欢作乐,成百万地赚钱,成百万地花钱,等待石客(指普希金的小悲剧《石客》中的石客,这里是指革命)的清算了……他们需要的不是轻快的谈话,而是丰盛的酒肉,庸俗豪华的生活,在这里,正如在第一帝国时期(1804至1814年拿破仑称帝时期)一样,黄金代替了艺术,卖淫妇代替了贵夫人,交易所代替了文学。
社会的瓦解不限于巴黎一地。乔治·桑在诺昂是周围一切邻居活动的中心,凡是与她认识的,不论身份高低,都可以作她的座上客,大家不拘礼节,随随便便,非常融拾地度过一个晚上。那里有音乐,有朗诵,有戏剧即兴表演,最重要的是乔治·桑本人也参加这些活动。但是1852年后,气氛开始变了,好心的贝里人已经不是为了休息和谈天来串门,他们眼色凶恶,心中充满怒气,不管当面背后,彼此挖苦,有的炫耀自己的新官服,有的担心遭到告密陷害。那种轻松愉快、说说笑笑、无拘无束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经常忙于调停纷争、解释误会的乔治·桑,对这一切感到苦不堪言,非常讨厌,终于取消了诺昂的这种晚会,把接待的客人缩小到只限于两三位老朋友……
……据说,现在莫斯科(年轻的莫斯科)老了,它的活力没有保持到尼古拉去世之后,它的大学也退化了,而在农奴解放问题面前,它的地主性质又显得过于刺目,它的英吉利俱乐部也愈来愈缺少英国风味,索巴凯维奇在那里大叫大嚷,反对解放运动,诺兹德廖夫(索巴凯维奇与诺兹德廖夫都是《死魂灵》中的地主)则声嘶力竭,要保卫贵族“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可能!……但是40年代的莫斯科不是这样的,这个莫斯科曾积极参与拥护或反对男用平顶皮帽的活动;太太小姐们细心阅读非常枯燥的文章,静听漫无止境的辩论,还亲自发言,拥护康·阿克萨科夫,或者拥护格拉诺夫斯基;她们觉得可惜的只是阿克萨科夫太像斯拉夫人,而格拉诺夫斯基则太缺少爱国精神。
在一切文学和非文学性晚会上,论争一再展开。我们在这些晚会上见面,一星期大约两三次,星期一在恰达耶夫家,星期五在斯韦尔别耶夫(莫斯科的贵族,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常在他家的晚会上展开辩论)家,星期日在叶拉金娜(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的母亲,1830至1840年莫斯科文学沙龙的主持人)家。
除了参加辩论的人,除了持一定观点的人,还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出席晚会的,其中甚至有妇女。他们坐到深夜两点,看这些斗牛士怎样厮杀,谁胜谁败。他们来听辩论,就像从前去看拳击,或者上罗戈日门外的竞技场一样。
书摘部分节选自《往事与随想》第三十章,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