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作家王占黑凭借《空响炮》获得了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作为评委的台湾作家唐诺认为,王占黑的作品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但是《空响炮》“是好看的小说,但不是难写的小说”,“年轻的作者借着街头巷隅的传说和对腔调的模拟,而触及了某种世故的层次”,可是这个文体和世界已是充分开发过的,他希望王占黑“不要在这里待太长的时间”。
在由作家唐诺、金宇澄、阎连科,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音乐人高晓松组成的评委阵容当中,唐诺显得格外严格。他不仅指出了王占黑的作品“不是难写的小说”,还认为唯一一篇入围的长篇作品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虽然“最像会获奖的作品”,可是因为“浓墨到已经接近浮雕,属于雄强的、力量的呈现”,因此丧失了中间灰色调子的层次。唐诺告诉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他心目中的前三名是双雪涛、沈大成、张悦然,但这三位作家也都面临着不同的难题。
此次担任评审,唐诺自称只是凭着一个单纯的身份——小说读者。其实,他曾经当过20年图书编辑,让他在这个行业坚持下来的是“那些因为太好、太深奥而注定没有市场的书”,因此,他过去常常在十本受市场欢迎的书里面,藏一本只能卖两千册的书(一本书在台湾卖出2000册、大陆卖出8000至1万册,就能大概收支平衡),这会让出版社赔一点点钱,却不知道会给哪位读者带来一生的影响。格雷厄姆·格林、翁贝托·埃科、劳伦斯·布洛克等作家的作品在台湾引进,都多少与他有关。
在离开出版社之后,唐诺每天到咖啡馆“上班”,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多,只带着写作用得到的参考书,专心书写。在反复删改后,每天所得大约有五百字。无论是四十五万字之巨的《尽头》还是《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他的作品通常篇幅很长,他不愿意简化,“如果一直用简单的话来讲,一定要切掉很多细腻的东西,”他在接受专访时说道,如果作者一味将就读者,那么,“一开始是你说给他们听,久而久之会变成你说他们要听的话。”
日前,唐诺作为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接受了界面文化的采访。“我相信马克斯·韦伯的话:告诉学生一种不舒服的真相,是老师的道德责任。”他曾这样说过。他首先点评了进入此次文学奖终选的五部作品:张悦然《我循着火光而来》、王占黑《空响炮》、沈大成《屡次想起的人》、双雪涛《飞行家》以及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而后进一步提出,大陆书写者一方面拥有着优渥的书写环境,一方面又面临着城市书写的挑战、通俗化的诱惑和读者流失等方面的压力。

【谈评奖】双雪涛是心中第一名,阿乙有很多几乎不该犯的错误
界面文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设立旨在发掘和鼓励优秀并具潜力的青年华语作家,这次评选你的整体感受是什么?
唐诺:我对文学奖心情很复杂。我对这个工作不陌生,但是不很喜欢。因为有些作品看起来相当不错,但是在文学奖的形式——尤其是仅有一名获奖者的情况——下会很吃亏,这次有一两部作品就会呈现这样的结果。有些作品看起来像得奖的作品,但是和我理解的文学书写作为长时间的、一日复一日的事情有差距。
在台湾,书写本身既没有好的收益,又因为读者都消失了而没有荣誉可言。但是台湾的小说奖特别多,大家好像是为了获奖而写作,经常出现虚张声势的作品。这些作品想去找到接近完美的形式,但选择避开文学应该处理的东西。其实,如果要突破某些书写困境,第一二部作品不可能完美,甚至可能有点丑,只有冲破困境,到第二第三阶段才会出现比较完美的作品。可是在台湾,我们会看到有人去研究评审的口味,甚至开写作补习班教授如何写出获奖作品,比如说摆出一些书写上政治正确的因素。因此,从题材的选择到书写的过程,都存在太强烈的参奖之心。这次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是从既有的作品里选择的,参赛的都是45岁以下用汉语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过中文简体版作品的作家。不过,大陆有各种奖,这种(参奖)意识是存在的。就算不在参奖的层次,也可能受到一些媒体的引导。真正在面对自己的书写、自己的困境的作家,在这一类的筛选上就会很吃亏。
界面文化:你在颁奖典礼的现场提到了张悦然对城市的书写,认为这是一种突破?
唐诺:张悦然正是我说的,在五部决选作品里是最吃亏的。因为她写城市。城市现代书写很麻烦,最难写、最难讨好。欧洲大叙事时代过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伟大的旧俄作家把什么都写尽了。作家不得不走到城市,现代书写几乎和城市书写同步同义。小说进行到当代,在欧美、在日本、在台湾,几十年来都在面临困难:怎么写现代?怎么写城市?在中国,这一进程一直方兴未艾,这和社会进程有关系。
大陆上一代的书写者,李锐、贾平凹、莫言这一批人,好像列祖分封,一人写一地,山东归谁写,山西归谁写,东北归谁写。当然这是必要的,在文革以后,一方面文学重新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大陆改革开放,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外在世界变化这么大,充满着新的东西,文学常常要重新描述世界。一直到现在,上一代作家还在这样的圈子里头,比如,贾平凹的作品我还蛮喜欢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说要最后一次写陕西,可是我去施耐庵奖评审,看他写的《带灯》,他还在那里。我知道,这与他们整个生命、文化构成有关,要让他们进到现代写城市是有困难的,所以要仰赖新的书写者来完成这件事。
(上一代)书写者中最特殊的就是王安忆,因为她生在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奇怪的地方,它很多东西是外来的,很复杂。上海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进入到城市化的地方,所以王安忆不得不写城市。她感慨,城市无故事。在一个小乡村、一个小镇,故事是完整的,人的经验是完整的,从生到死都看得到。可是在城市里,人走到一个地方,拐个角就不见了。这非常难写。
小说的有些部分开发得很成熟,比如今天盖房子你不用去砍柴、搬石头,只要打个电话让人过来;有些部分是还在拓荒的阶段,很多东西要自己打理,能够得到的资源也不多。以现代小说书写城市的情况来说,这条路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台湾很快走到了人口太多、充分开发、乡村不断消失的情况,而且除了冷战对峙以外,很快没有饥馑、没有贫穷,虽然有一些政治迫害,但都是局部的、一般人不察知的。书写者没有强烈的故事可以写,具体经验高度重复,这一切都逼迫着台湾小说提早往这个方向走。我计较说这不是突破,因为虽然对大陆来说这是一条方兴未艾的路,但是对普世的书写来说,这条路已经走了很长时间。
张悦然(的作品《我循着火光而来》)是这五部作品里最直接处理城市的。我说的不是她在城市书写里的突破,而是说这部作品比她以前的作品有很大的进步。读过小说之后,我去查了查她的状态,看到她在一场座谈会里讲自己变得心软了,这证实了我的猜测。后来她也谈自己的写作的状态,好像不是那么耍帅,而是经常会碰到困难。张悦然讲,她过去用批判的角度,冷眼看世界,我觉得这不仅是人生观的选择,而是人的意识在变化。心软经常是察觉了较复杂的状态。我非常开心她变得心软。昆德拉说,小说家会告诉你事情永远比你想象得复杂。举例来说,最早的刑法《汉谟拉比法典》,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而现在的法律当中,杀人有各种状况,充满了各种解释,有些杀人的确是残暴、冷血的,有些杀人是值得悲悯、同情的,因此从无罪到枪决,有不同裁决。这是一种意识的进步,我们理解了世界的复杂度,愿意往内多看一眼。黑暗是一个词,可是真正的黑是有层次的,它有各种调子。进行城市书写的时候,如果不把自己练得敏锐,就捕捉不到那些细微的声音。

张悦然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0
和她以前的小说相比,张悦然有着明显进展的部分在于多了层次,而不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小说很过瘾、不模糊,容易讨好、容易获奖,而张悦然的文学构成、书写的走向是最困难的,在这五部里面最吃亏。除非评审充分意识到,中国小说这条路要不要有人好好走?张悦然的成绩有她个人的部分,我相信也对中国城市书写的进程有推动,毕竟她是大陆从年轻到接近中壮代里的醒目的书写者。
界面文化:在颁奖典礼上,评委阎连科在评价王占黑的作品时,称小说的成熟超乎想象,他说,“一看这个小说的语言,这完全不是一个91年的人写的,一定是68年、58年或者48年的人的。”年龄和写作有关系吗?
唐诺:年龄和写作有关系,但关系很复杂。一方面,文学和人的情感很贴近,我们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可以表述的东西。博尔赫斯说,作品里充满了爱情和死亡的印记,这是年轻小说的印记。另一方面,文学有一个成熟期,从青涩到成熟有锻炼、锻打的过程。文学专业的技艺——如何适当、准确地表述自己——经常被轻视。更复杂的问题在于有各种文体。像诗这种文体,巅峰来得相当早。它直述本心,调用的字句少,它不需要世界,只需要自己,通常在你独处的时候就会来找你。十五六岁甚至十三四岁的作者就可以写出非常好的诗来。巅峰来得最晚的可能是小说,小说不得不有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他者的理解,这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生命经验。我经常说,不到40岁以后,小说写作者通常不会进入成熟期,因为不能仰赖“我”。今天城市小说常常不小心就会进入“我”的世界,可是如果不能意识到外头的世界,“我”是挖不深的,能够表达的只是低层的情感。当然,由于每一个书写者的天赋、个人境遇、投注的工夫之间的差别,情况当然会有参差,有人成熟期会来得早,有人会稍晚。
以这次王占黑的小说来说,因为她年纪很小,所以评审很惊讶。评审除了高晓松以外,年纪都偏大,被年轻人骂惯了,说这个年纪的人怎么会写我们,关怀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觉得很受宠若惊,也感到很温暖。金宇澄写《繁花》,他喜欢那个世界,曾经上海巷弄里的风情嘛。我猜想,王占黑的书写方式在这次的五部作品里面是最容易的。果戈理最早的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上下卷,把普希金和别林斯基吓了一跳,说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写老头老妇,怎么会那么世故?他们视为瑰宝,努力培养果戈理,但是最后也害了他,关于这件事我写过一篇《果戈里:被思想扭曲的小说灵魂》。那么他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同时可以连接到张爱玲。三十岁的张爱玲为什么那么世故?为什么两手不沾阳春水的女生可以去理解那些东西?秘密就在这里:他们是通过传说、歌谣了解的。根据研究,果戈理的创作也的确是通过歌谣、传说开始的。契诃夫也是这样,契诃夫短篇多达上万篇,他是一个书写者也是一个采撷者,他的书写是在街头巷尾传说故事里面已经完成了的。张爱玲从小由老妈子照顾,听东家长西家短的故事,如果她足够敏锐,就会模仿这个腔调。可是到我这个年纪,回过头去看张爱玲,她的人情世故是有问题的,是用聪明cover过来的。我读她的晚年三书(指《小团圆》《雷峰塔》《易经》),完全证明了这件事情。因此我对张爱玲的晚年三书评价很高,虽然很多人认为最好的张爱玲是华美的三十岁之前。
这些东西已经不是外头的世界,它们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打磨成了文学世界本身里面的东西。王占黑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她可以通由这条路进入这个世界,因此她写出来就好像她非常了解那个世界。所以王占黑的东西非常讨好,很好看,非常顺,充满机巧,里面有很多生老病死又不会让你沮丧,好像只是付诸一叹,而且它带着某些猎奇、记录人物众生相的意味。说真的,我没有给王占黑特别高的分数,那是好看的小说,但不是难写的小说。
这次比赛最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张悦然的小说,一个是王占黑的小说。在张悦然的小说里,你会发现一些不成功的地方、一些磕磕碰碰的东西。可是,就文学书写技艺丰富度来讲,张悦然远比王占黑要高明得多。我说的不是作品的结果,而是从技艺层面,从作品成熟度来讲,可是张悦然碰到了一个较为困难的书写方式。

王占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3
界面文化:再谈谈沈大成和双雪涛吧。
唐诺:这次我觉得很大的惊喜是沈大成,《屡次想起的人》这个书名也是几本里最好的。她距离现实最远,用很超现实的写法,带着华丽的想象。18本(参评)作品里有几部这样的东西,有一两部还不坏,比如说双翅目写的《公鸡王子》。但是我多少有点介意,因为她对科幻的部分、杂学的部分准备得太好。这让我想起了阿城,他下棋不好,可是在写了《棋王》之后,他说,如果我的棋下得好的话,《棋王》就会去写棋,而不是写这个人了。双翅目在科幻里面写得太精密了。在我的理解里,科幻小说有一个历史进程。人类曾经在科学上寄托了拯救人类的全部希望,希望人类学、经济学、文学都往这个方向去,希望所有的学问都变成科学的模样,用博尔赫斯的话讲,成为“准确度稍差的科学”。科幻小说有一部分是带着宣扬科学福音而来的。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了科学的限度,如今真正好的科幻文学反而注重对人文的思考。
我更喜欢沈大成的《屡次想起的人》。在大陆,非正统的小说书写很容易被拉往通俗的方向。魔幻现实被大量运用和误用之后,作者常常往通俗去写,出现了穿越等内容,沈大成的作品则紧守分寸。她是一个广告人,笔非常干净,风格清澈,想象力华丽,作品好就好在是出于对生命处境里某种状态的关怀而打开的想象,不断和生活有很自然的连接点。小说里有一个王国,所有的胖子都想去那里,因为那里大家都是胖子,过得很愉快。现实当中肥胖一直备受指责,受到歧视,人们不仅关注他们个人身体的毁坏,而且还讨论社会医疗的负担,讨论他们是不是应该交更多的税。沈大成用非常清澈、愉悦的风格来讲,蛮厉害的。但是这样的作品在单一选择里面很难变成唯一的作品,这是小说奖的限制,但它是我心里前三名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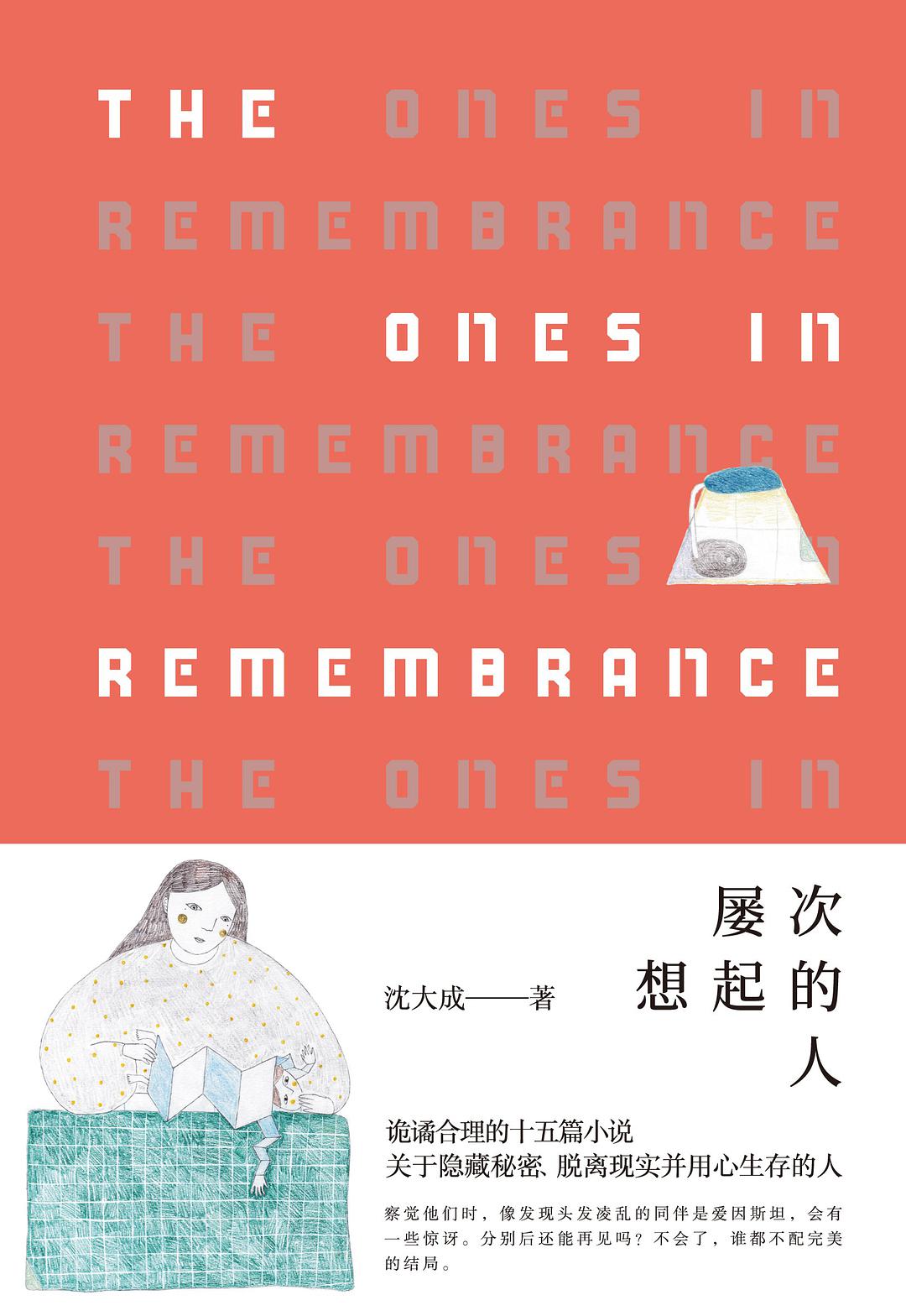
沈大成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6
我之前看施耐庵奖,上一代的人比如李锐、贾平凹、王安忆、金宇澄,都是大陆最好的作者。而这一次年龄限制在45岁以下,他们的作品远比上一次我看到的不成熟,但远比我上一次看到的多样、复杂。上一次那些作品真的让我有点东北写东北、上海写上海、山东写山东的感觉,可是这一次,从体例、形态到作者关注的东西,相对来说复杂了。在文学较为主流的书写里面,这一本《屡次想起的人》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惊喜。但是我也会说,清澈的风格也会有一个阻挡,因为广告要求准确度非常高,但广告不会自讨苦吃。遇到不容易讲清楚、不容易讨好的,就不要说,可是如果碰到很想写又没有办法讲得那么干净简单的东西怎么办,是舍弃它还是冲下去?这会是一种挑战,但是没有关系,还有时间。我可能是过早把问题丢了出来。
虽然张悦然、沈大成的差距也不大,但双雪涛是我的第一名。大陆的上一代与下一代,有一点泾渭分明。大家都有一块地,而城市书写这里,大家一不小心写坏了,就无病呻吟。我开玩笑讲双雪涛写的是城乡结合部,东北的部分和城市的部分两者都在他的小说内发生,这是好的。暖流和寒流交汇的地方,浮游生物最多,事情发生最多,可是也最难写,因为事情相互渗透,非常微妙。评论中有对他不利的说法是他控制过度,认为他太聪明甚至狡猾。双雪涛事实上是很安排情节的,会丢一个谋杀案在里面。现代城市书写里往往不会做这个事情,因为这因素太过剧烈。我倒觉得那不是坏事,像朱天心讲的,“很怕用无事写无事,用无聊写无聊。”小说要有一个特别的事发生,但不是从生活里中拣一块出来,它和现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关系。
纳博科夫说,我的小说当然是由我控制,我就是小说的上帝。另一种看法是,要让人物活起来,让人物自己去反应、自己去走,说自己的话,所以有些小说家原本的计划到书写的时候会产生变化,甚至博尔赫斯会说,一个小说写出来如果和预想的一模一样,那一定是失败的小说,因为书写的时候没有产生有趣的化学变化,书写变成一种执行工作,那是最无聊最单调的。这两种说法都成立。可是,如果太迷醉后一种说法,认为书写就是重新思考的过程,那仰赖直觉的人就常常会写出混乱的小说,因为没有充分的准备。这是纳博科夫反对的。双雪涛的短篇小说集《飞行家》里有一篇《光明堂》,他说这篇他不放心,不像以前写的时候知道要往哪里去,写得开始摇晃,所以一再修改过。我对《飞行家》的评价没有对《光明堂》没有那么高。《光明堂》是《飞行家》里出色的小说,但是最控制不住的小说,所以说在控制和不控制之间分寸很难拿捏。我的建议是,如果书写的时候心中某个铃“铛”一下发出声音,其实可以稍稍自在一点、放松一点,让小说带着你看看。但是,我不赞成靠直觉、被文字拖着走的书写方式,因为书写毕竟是深思熟虑的。朱天心说,这是小说开始起飞(take off)的时候,是写小说最放松的时候,很多东西不招自来,但这也是充分“苦”的产物。

双雪涛 著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8
界面文化:阿乙的作品怎样呢?
唐诺:某种程度上,阿乙的小说其实是这次最像会得奖的作品。首先因为它是长篇。长篇在书写上要费劲,可是我不认为要因此太强调它的重要性,因为要突破书写困境,长篇没有办法准备得那么周全,通常要先用短篇先做探路和攻坚。而且如今书写有通俗化的倾向,比较容易召唤出长篇,因此写短篇不论是在评论的重量上还是在读者的阅读上都比较吃亏。所以这一次我不会强调长篇。
阿乙还有一种强烈的风格,力道最足。但是我对阿乙这部作品有较多的批评。我开了个玩笑,希望不要太冒犯。高中时候学校老师有次公开骂我们说,各位同学什么都好,就是缺点太多。我到四十年后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阿乙有很多问题,几乎是不该犯的错误。他可能太呕心沥血了,创作态度非常认真,认真是我喜欢的,可是不能僵硬。或许他在作品中刻意追求文字的美学效果,因此非常深浓。可是真正的黑暗不是一种色调,黑暗有各种层次,书写基本上在灰色地带,而不是纯粹的黑和白。阿乙的东西会强烈到只剩下两端。年轻时候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虚张声势。文字都是强烈的,声音都是大的,细微的地方就进不去。昆德拉说,不让那些声音静下来,小说家就听不到隐秘不可察觉的声音。大陆可能因为城市书写的困难,有一种想要回到雄性书写的趋势,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力量和粗糙之间有关联。《水浒传》某些精致的描述——比如桃花林里的酒肆——十分精彩,可是我对里面雄性的书写受不了到极点,那种情感用台湾的说法就是共同犯罪的“哥儿们”,阳刚到单调,是非常狭窄、粗糙的,尤其那种洋洋自得的感觉让我特别不舒服。
结构上也有蛮大的问题,阿乙太孤注一掷,就像马尔克斯在讲自己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的时候说,他年轻的时候,以为这一辈子只会写这本书,所以把他所有知道的东西全部都放进去了。阿乙好像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摆进去,中间插了一大段雌雄大盗的故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全部都放进去会给结构过大的压力,因此产生结构崩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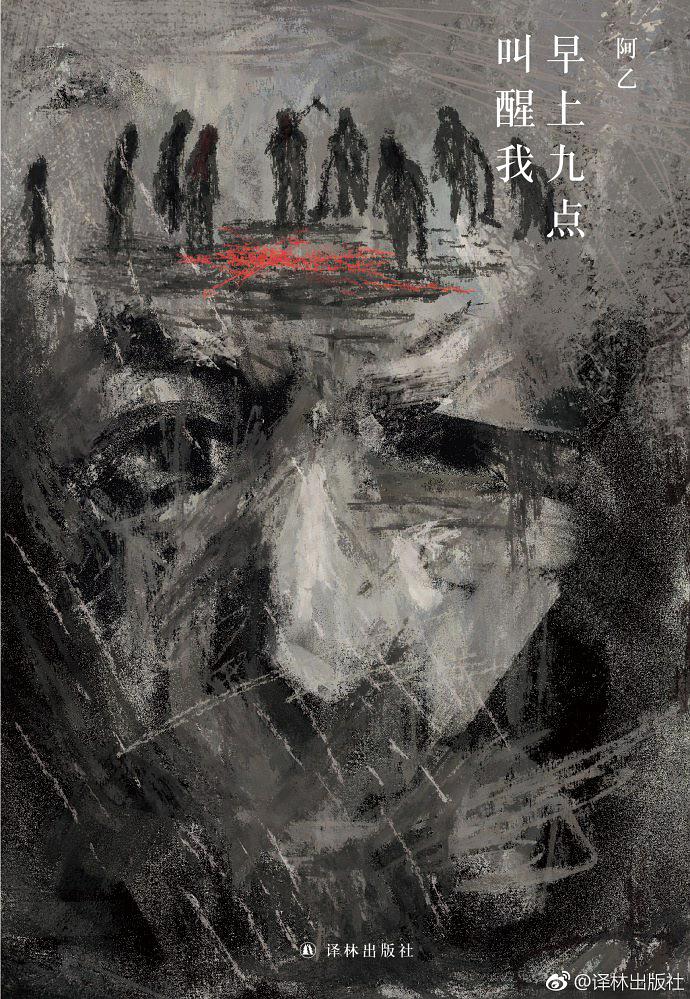
阿乙 著
译林出版社 2018-1
另外一个小说常见的麻烦就是对话怎么写。现代小说里的对话通常最受诟病,因为很无聊,对话要成立通常是靠语言,而小说呈现的是文字,这两者通常会互相冲犯。见了面说你好、今天怎么样,写这个干什么?可是你不写这个,见了面就开始吟诗作对,又很恶心。马尔克斯讲西班牙文是优美的文字,可是变成对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很虚假,其实所有文字都是这样。阿乙的很多叙述是用两个人对话完成,可是那个对话完全不是人讲话。为了完成某个东西偶然犯规可以不计较,可是阿乙对话的问题明显到你会感觉不对劲。
这部小说里人物调度得也多,可是人物都是同样的人,没有因为人物的不同而产生各种不同角度的变化,使得整个小说的幅度变得狭窄。因为每一个人的视线都受到阻挡,在这个角度看到的和别人看到的、关怀的角度不一样,人物的调度会消弭掉很多物理上、心理上、意识上的直角,使得整个世界较为完整地、纤毫毕露地呈现。而在阿乙这部小说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黑暗、一样的大声、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会产生这样的层次变化。我对阿乙有较高的要求,他算是这里面比较老练的、备受期待的作家,我觉得这不是他的最佳演出,甚至不是他的好的演出。可是,阿乙因为长篇和强烈的风格,的确是原来看起来最像会得奖的。
【谈写作】中国作家未来有两种可能:好的待遇消失,往通俗方向走
界面文化:从整体上看这18部参评作品和5部终选作品,大陆中青年作者给你的感觉和你以前的感受有差别吗?
唐诺:我原来的要求不高,但是较为严格地讲,展开的幅度和深度还是不够。也许要慢慢来,而且这只是这一年来交出的成绩,很多作家或许并没有在里面。
在城市书写方面,台湾挣扎了很多年,大陆还在书写当中,我觉得张悦然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另外一部相对接近、我认为可以进前五的是李静睿的《北方大道》,她在小说最终的表现形态上比张悦然要完美,但是有一点轻描淡写,太困难的地方不去碰,我对王占黑的批评也是这样。写自己能够控制的,刮上头最甜美的那一层,这其实是卡尔维诺讲的海明威的书写,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张悦然比较勇敢,敢冲进去,因此这两部我选择了张悦然。这是两部我觉得比较醒目的,她们在城市书写方面的确比上一代做得要好。大陆的先锋派没有那么真实的城市生活的感受和好奇,反而是理性的产物。而在相当程度上,李静睿和张悦然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因此写得稠密而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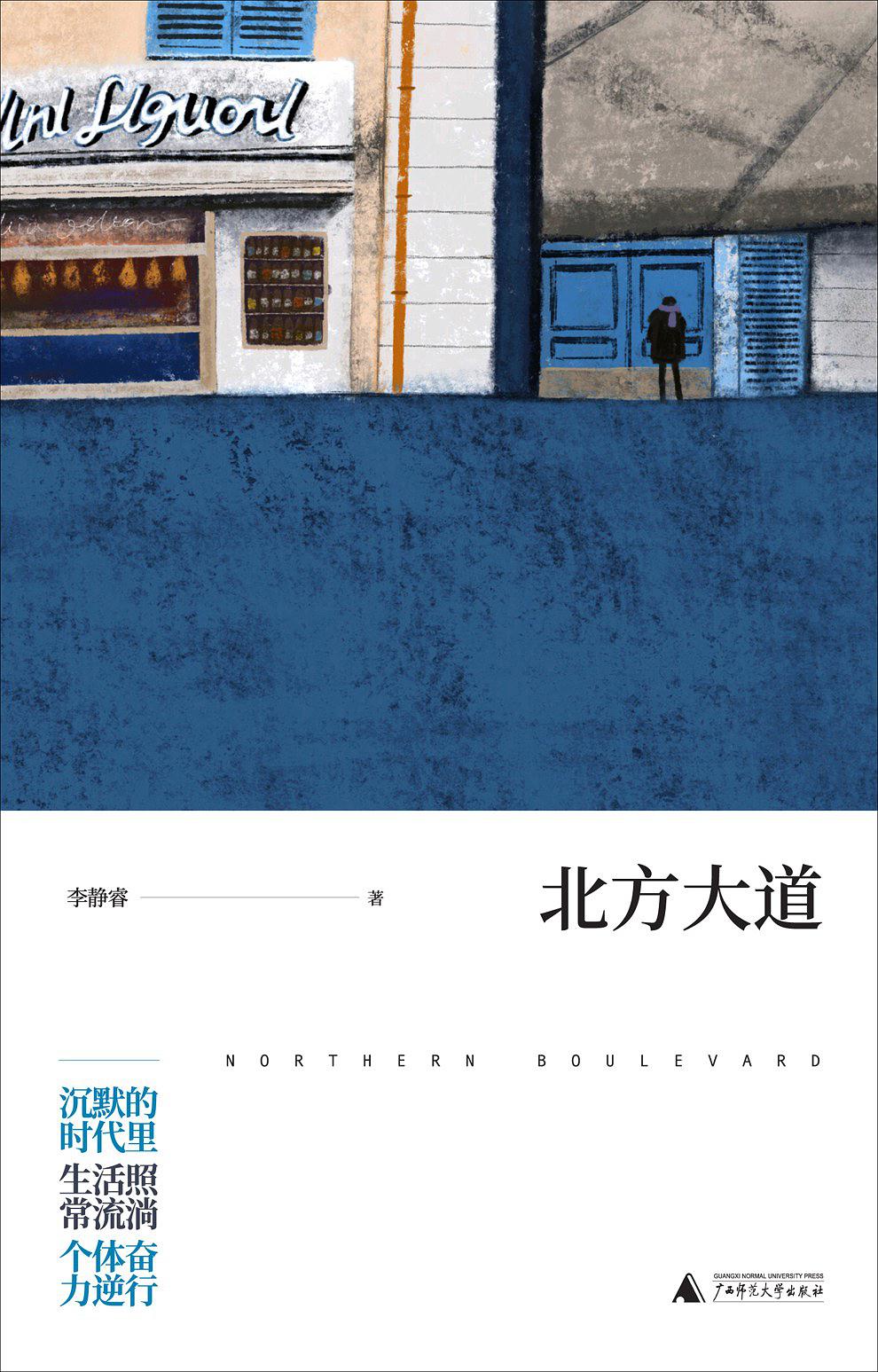
李静睿 著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06
界面文化:“展开的幅度和深度”就是针对城市书写而言吗?
唐诺:一个书写者要往哪边写去,没有人能够置一词。托尔斯泰说,契诃夫的东西我一辈子也写不出来,因为托尔斯泰是贵族,无法像契诃夫那样去理解农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他一辈子把自己搞得那么狼狈,差点被枪毙,所以他理解那些被侮辱者。
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文学和史学一样,从关注英雄豪杰、上层社会开始,本来地球上好像只有刘邦、项羽,其他都不是人,可是你慢慢会看到引车卖浆之徒、鸡鸣狗盗之徒,这也是《史记》伟大的地方。后代的史书都是样板,不像司马迁是真正关怀他们。欧洲的书写方式从中世纪到现在往下层发展,关注被忽略的人甚至被侮辱、被伤害的人,这是整个书写的展开,这是所谓的多样性。中国大陆当然有高高低低的领域,也有被侮辱、被伤害的人。生命有生命的走向,我们对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单独的要求,可是中国这么大,如果让有些东西溢出关怀之外、排除在书写之外是否有些可惜?是不是应该提醒人们去关注?
对了不起的书写者来说,我们希望他/她在不取消深度的前提下涵盖面更广。我们希望一个好的书写者能够展现恢弘的图像,在每个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托尔斯泰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伟大而多少有点虚张声势的好作品《战争与和平》,对我来讲他更好的作品无疑是《安娜·卡列尼娜》,我称之为历史上完成度最高的长篇小说。可是他到五十几岁的时候,写了一般认为他最失败的小说《复活》,技艺如此高超的大师写出了犯这样错误的小说,这是为什么?有些作者是“刺猬型”,好像只会这一招,一种是“狐狸型”,好像什么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偏“刺猬型”的,托尔斯泰是偏“狐狸型”的,《复活》就是一只狐狸试图变成一只刺猬的经过。我一直不认为张爱玲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因为她只写一种声音讲出来的东西,这和她的选择有关,她一辈子把自己藏起来,保护自己,没有利用过她文学的生命。一直到看了她晚年的三本书,我才认为张爱玲堪称伟大。但是三书之前,大家喜爱的张爱玲对我来讲未免还是窄了一点,因为她只写一种东西。我对一个伟大小说家的定义远比这个要深刻、复杂。
界面文化:你曾经说,大陆小说作者拥有优渥的环境,但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唐诺:我讲过中国大陆三个奢侈。第一是题材的奢侈,大陆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土地,这么剧烈的世界的变化,这非常少见。西欧已经安静了很多年了,台湾50年来变化是缓缓的,都不新奇,台湾小说家看大陆莫言他们写的,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没有啊!张大春要写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都非要去写兰屿(台湾旁边一个很小的岛)不可,我说“辛苦你啦孩子”。第二是待遇的奢侈。台湾一直在说社会普遍工资没有调整,其实工资真正没有调整的是作家——我小时候刊载的稿费是1字1台币(约为0.2256元人民币),半个世纪,经过了通货膨胀,现在还是1字1台币,甚至在纸媒萎缩之后,作品无从刊登,稿费还在倒退。作家必须要做很多事情养活自己的书写,这迟早是大陆某一批作家必须要面对的状态。第三是声名的奢侈,中国大陆将本国作品向海外推广的力度在全世界是最用力的,大陆很多书的外译都是由大陆自己出资。
日本现在中壮代的作者不能去想象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时代。我去过三岛由纪夫的书房,从书桌、钢笔每一样都是精品,生活好得不得了。可是后来,太宰治的女儿津岛佑子带着一批日本中壮代的作家来台湾交流的时候,把我们吓了一跳:日本很注重衣着光鲜,可是日本中壮代最好的一批书写者穿的衣服比我们还糟糕。来到中国大陆我看到的作家的阵仗,在世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但是我怀疑下一代书写者会不会还是这样,除非大量转向通俗与自媒体。《神秘河》《禁闭岛》作者、美国作家丹尼斯·勒翰,写作技巧好得不得了,作品里有分镜,有场景的变化,完全是为了好莱坞电影而写。在中国这个事情也正在发生,不是吗?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是电影故事大纲吧?故事大纲、场景转换都有,细节全部不处理,果然很快看到电影了。
未来有两种可能:第一,好的待遇可能消失,现在八零后、九零后在书写,他们问我,写小说是不是买不起房子?我说写小说如果买得起房子那才叫奇怪喔,你在台湾不要说买房子,连过活都有问题。第二,往通俗方向走。这两件事在中国都会发生,而且正在发生。书写者要留在较纯净的文学领域里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次做评审,在初选的18本当中有很多通俗的作品。通俗作品有些也不坏,我们也愿意读,但是它们经常在市场上就取得收益,好不容易办一次文学奖,最好聚焦在那些并没有外在资源可取得的、属于纯文学核心的书写。
界面文化:经常有一些作家说不在意读者、评论家的评价。你怎么看待作家和读者或者评论家之间的关系?
唐诺:读者是泛指所有,还是说在芸芸世界里只在意某些人,这很难讲。阿城曾经说自己不在意读者,是写给远方的几个厉害的朋友看的。
书写是一个公共的形态,你为谁而写?许知远问我为什么不选择大的媒体,让更多的人听到你说话?我毫不犹豫和他讲,这是一个悖论,我有很多机会走进电影圈、走进广告圈,但我拒绝了。这里有公约数的问题。人理解程度的整体构成的确是金字塔状的,越困难的方向人就会越少。如果使用一个热门的媒体,一开始是你说给他们听,久而久之会变成你说他们要听的话。究竟是谁限制了谁,谁带领了谁,很难讲。朱天心二三十岁就开始收到非常多的读者来信,直到前些年还是这样的状态。近年来有一批读者说你现在写的东西我们都看不懂,甚至有读者说你要写我们喜欢的那个朱天心的东西,但她不可能回到二三十岁。我过去的工作是写导读,写解释文章,把困难的东西用一般人能懂的方式写出来,同行里梁文道、杨照也做这件事。可我有一个警觉,如果一直用简单的话来讲,一定要切掉很多细腻的东西,你原来是你,久而久之,会变成你不想讲,再变成你不会讲,最后变成只能讲简单的东西。

书写者自己的选择决定了他往哪里去。你要停在哪个层次?十万人,一百万人,一亿人,你最后只能说他们听得懂的话。为什么高中老师、幼教老师的程度会停留在那里?因为他们永远在和程度不如自己的人相处,永远由上往下说话,久而久之就会往下掉。一个书写者永远必须有一个远方,有一个“厉害的朋友”,其实这个朋友是一个广义的朋友,可能是某个希腊人、某个英国人,那样才能够持续往困难的方向走。
界面文化:许子东在颁奖典礼上说,“唐诺先生的本领,是他讲任何一个现代作家,马上可以给你在三分钟里面讲二三十个外国作家的渊源。”一方面,我们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很深;另一方面,莫言的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曾经发表评论说,中国小说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西方社会。你是怎么看的呢?
唐诺:许子东可能是调侃我。之前讲到现代书写,中国小说进展还处在第一阶段。我多年来一直谈的一个东西叫做“文字共和国”,有时候我们继承的疆域并不足以解释某些状态。我住台北,可是在某些事物上,我离希腊比离高雄更近。今天我们也不必把中国的书写者推到那么特别的位置上,好像他们写的东西全世界没有看过。就像博尔赫斯说的,夸张一点说,文学书写者,就是大家在共同书写一本大书,回答一个共同的大问题。就是马拉美讲的,一切都为了那一本书。这是我们共有的智慧之海,我们从里面取得饮水,我们把自己的东西交回去。
沈从文是完全中国特殊的吗?不是哎。沈从文有很特别的王维的境界,可是他的基本书写方式一条脉数下来,是源远流长的小说书写传统。我们看到果戈里、契诃夫、扬·聂鲁达承继的是写熟悉的下层生活、生命第一现场的传统,会出现甜美、温暖的书写,生老病死都可以化解。在我们看到老舍、巴金、鲁迅批判性那么强的时候,沈从文像清流一样,让人看得很舒服。王占黑继承的就是这个路数。这是全世界共有的,可以在欧陆找到,也可以在美洲找到。
文学不是一个人的事,写小说不是从你、从此刻才开始,你可能也不是全世界第一个发现这件事情的,有时候只是你知道不知道而已。就像当年李白讲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他对黄鹤楼有感觉,可是崔颢已经写了,所以后来他也模仿写了“凤凰台上凤凰游”。文学对我来讲是这样一个世界,它可以跨越国界,是“文字共和国”,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当你把作品放到大的脉络里,才能去理解它做到和没做到的事。
界面文化:你曾经说书是两千本的奇迹。就算全世界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它还是会被写出来。在当今网络时代,需要书的人会不会更少了?
唐诺:台湾现在更少了。我常常引用昆德拉的话讲,我们现在是后文学、后音乐的时代,因为大家逐渐不要文学了。大陆现在还好,可是它逃得过这个历史进展吗?托克维尔说的“无可阻挡的平等”还在继续推进,我们慢慢变得没有远方,没有可以敬畏的东西,就像台湾人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也是一个专业不断丧失的时代,物理学、经济学也许没有那么快,毕竟有一些比较坚硬的东西。文学的专业丧失得比较快,大家觉得文学纯粹是个人的喜好。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周杰伦的歌和巴赫的音乐还是有差别的。
界面文化:两千册读者还分了三类:真正的读者、假装的读者和买错了书的读者。
唐诺:现在,错误的读者不来了,假装的读者消失了,他们看的可能是郭敬明或者安妮宝贝。假装的读者的消失是最严重的,因为他们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读者。
要写好的字,我们都会从临帖开始,练习颜真卿的字、王献之的字。假装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可以解释为“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问题在于你想成为的是怎样的人而已。在《孟子》里,大家在批评五霸,孟子对五霸的心情有一点复杂,觉得他们也还不错,起码比后来战国的君王还要像样一点,所以他说,“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五霸想要假装做三皇五帝那样的人,假装久了不变回来,就真的变成那样的人。过去大家都笑三毛,觉得她很戏剧性,比较夸张,所以批评说三毛很假。台湾诗人痖弦淡淡地说,可是假了一辈子也就是真的了。我说的“假装的读者”就是这样。假装的读者消失,因为他们不再拥有那样的目标,不再想变成那样的人。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