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苦差的走火入魔 ,”叶芝写道,“攫干了我血管中的元气……”在关于今年布克奖得主——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的《送奶工》(Milkman)——的媒体评论中,许多文章都用到了“攫干血管”这个词,却没有提到这本难读的小说也会让人“走火入魔”。
评论中频繁提到的是“奇怪”、“难以理解”、“难读”、“绞尽脑汁”等词。我(指本文作者、英国《观察者》杂志文学编辑Sam Leith)认为,这些评论并没有称赞的意思。布克奖总评委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的谦辞可能也没帮上什么忙:“我经常阅读《哲学期刊》上的论文,所以以我自己的标准来看,这本小说并不难。”但他补充道,《送奶工》的难读程度“堪比攀上斯诺登峰,但当你读完后,你会认为它提供的视角值得你付出努力”。
至少这是一个有用的出发点。阿皮亚认为,书籍的易读程度不该成为评价文学价值的主要因素,当然现代主义已经发展了一百年,这个概念似乎也不再需要更多的辩护了。我们喜欢看到运动员挑战极限,我们更愿意从音乐、电影、电视和艺术中寻求所谓更“烧脑”的元素。只要一本小说被认为是文学经典,我们就愿意阅读这样的“难读”书籍。我们都读过《荒原》(The Waste Land),抓耳挠腮地想弄清楚这本书究竟在讲什么,但我们现在才接受一个事实——它并不想被我们轻易发现其本来面目。为什么到了新出版的小说这里,“难读”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批评家因为一本获奖小说不符合自己的“可读性”标准,就攻击整个奖项,这纯粹是一种没有文化修养的表现。问题不在于一本书到底是难读还是好读,而是这本书是否在自己构建的难题中给出了答案。问题不在于一本书有多大难度,而在于它为什么难读。它为什么会难读?它对读者有什么要求?难读的程度是否能够值得读者为此付出的时间?《泰晤士报》的詹姆斯·马里奥特(James Marriott)认为读完这本书后获得的满足感与他付出的努力并不符合,他当然有权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如果要抱怨所付出的努力,就意味着读者付出的能力和注意力不值得任何形式的艺术收获。
伯恩斯自己对《送奶工》的评价也很明确,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写法,她确实在玩弄着“难读”的文字。让批评家最愤怒的一点是,书中的所有角色都没有名字,这并不是作者随意的决定。“这本小说不适合给角色命名,”她说过,“这会让小说失去其能量和气氛,让它变成一本不那么深刻的小说,甚至有可能变得截然不同。我刚开始创作的时候试着命名过几次,发现并不合适。我的叙述会变得沉重,失去生气,直到我删掉所有的名字,才能够继续写作下去。”也就是说,这本书必须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
有各种难读的书,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难读方式与《芬尼根的守灵夜》不同,《白鲸》 的难读程度也与前两者不同。有时候,一本书的难读是浅层问题,是因为读者的词汇量不够。比如《发条橙》就很难读进去,但只要你搞懂了书中自创的“Nadsat”语言,问题就迎刃而解。有时,一本书的难读是形式的问题。阿兰·霍灵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的《陌生人的孩子》使用了清晰易懂的语言(但用词极为谨慎),但时间和视角的跳跃会让读者在每一章开头感到迷惑。有时,像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一样,有些小说是以上两种难读方式的结合。有时,小说因为其主题晦涩而难读,比如玛里琳·鲁宾逊(Marilynne Robinson)的作品要求读者了解宗教学和心理学,克里斯·克劳斯(Chris Kraus)的《我爱迪克》则有一种文学戏剧色彩。《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那种简单的难读:它在段与段之间并没有给读者呈现问题,但其主体结构却能够吸引住读者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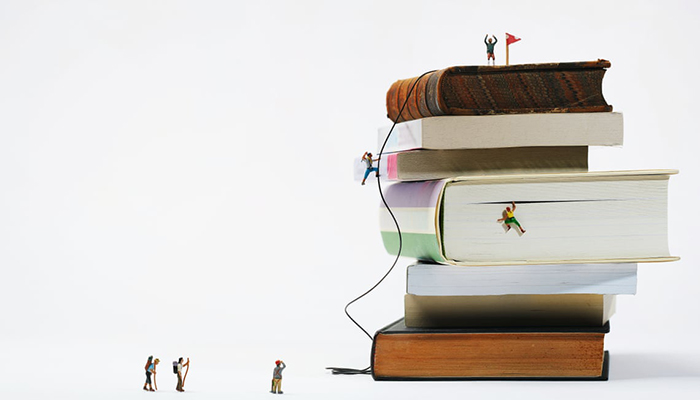
妮可拉·巴克(Nicola Barker)是一位也被频频评价为“难读”的小说家,她说,“我认为小说应该被分为两类,一类擅长巩固、迎合和称赞,另一类致力于提供复杂、挫败和挑战。我的作品和安娜·伯恩斯一样‘难读’,因为我们试图理解和加入想法、情绪,塑造一个不直率、不连贯且难以控制的世界。有时,一本书的形式或风格需要反映生活的复杂性;有时,我们需要试着去描述那些难以描述的东西。生活是困难而又矛盾的——生活不会简单,小说也不会。”
她补充道,实验作家既不会凭此赚到很多钱,也不会吸引到太多的注意,“我们在试图创新、挑战和实验,却要得到双倍的嘲讽。写作实验小说是出于纯粹的爱,实验小说的重要性在于它构建了我们创意生态系统的基石。其他食物链顶端的艺术家(音乐家、画家、建筑师等)会阅读我们的小说,然后用另外的方式呈现和翻译我们的想法。”

图片来源:Ray Tang/Xinhua News Agency/PA Images
今年与往年一样,总有批评家声称布克奖已经屈服于自负、政治正确、实力或其他枝节问题、这些“缺陷”都可以变成吸引眼球的新闻标题,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布克奖是每年由全新的评委、按照全新的目的评价全新的作品。今年的赢家伯恩斯和去年的赢家桑德斯都曾被认为“不会卖出很多册”,但这从不是布克奖的重点。提升书籍销量只是奖项带来的一个结果,偶尔也是部分类似奖项的目的,但如果说这意味着评委的任务是选出能够因为获奖而极大提升销量的作品,这就是因小失大了。
“你希望这些作品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布克奖文学总监加比·伍德(Gaby Wood)说,“你希望尽可能多的读者能够读到它们,但你不能假设普通读者无法理解所谓‘难读’的书。我问过去年的评委们一个问题:‘你们是想选出能够探索文学边界的作品,还是想选出一本能够让全世界更多读者看到的作品?’关键在于,对于评委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书。这种现象也发生过,评委很难做出统一决定。不过,今年安娜·伯恩斯的获奖似乎同时是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幸运的话,易读的好书也能找到它们的读者;易读的烂书也是如此,因为这些书太烂,反而会带来不少乐趣。难读的烂书会在下水道里腐烂;如果难读的好书没有一点助推,可能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弗里欧奖(Folio)、布克奖和金匠奖(The Goldsmiths Prize)都能够产生助推的作用。一批严肃有思想的评委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发掘那些很可能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内容,绝不能说是一件坏事。这些奖项是为了奖赏最出色的纯文学小说。但是,我们又陷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纯文学小说”到底是什么?
我听说过一个解释,“纯文学小说需要意识到,它只是一个文学类型,不该把自己当回事。”这个解释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认为,这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只是为了宣扬一种很多人相信的理念:“没有所谓的文学小说和流行小说之分,只有好书和烂书之分。”如果我们要固执地进一步分析,才算是把我们和批评家们区分开来。确实有好书和烂书之分,但是根据小说的分类不同,也有成功和失败的小说之分,读者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
无论如何,纯文学小说确实是一个常用的类型。如果它不该把自己当回事,没问题,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能够将其归入其他类型的特征。如果有外星人和纳米机器人,就是科幻小说;如果有枪、帽子、尸体,就是犯罪小说;如果档案和情报秘密传递点,那就是间谍小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指出“纯文学小说”的特点。抛开“重要性”和“严肃性”等文化价值判断,纯文学小说和大部分小说一样,也可以毫无重要性。纯文学小说也可以不严肃,我认为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绝对是纯文学小说,但这部作品既不算重要也不算严肃,而是一部壮丽的文学游戏。

有人说纯文学小说会让你在重读时获得更多感触,有人说纯文学小说会一直留在你的记忆中,有人说它“更为深奥”。也许有时候是这样的,但这些论断更像是文学给我们带来的症状,而不能作为纯文学小说的特征。我认为,其主要特征在于故事的复杂性和深度,也正因如此,文学写作才能和任何其他类型融合起来。所谓复杂性,可以指道德和心理上的复杂性,因此所谓好与坏也不会有明显的区分。但是,最出色的纯文学小说一般会把重点放在形式和语言本身上。我之前说文学写作能和任何其他类型融合起来,我的意思是,纯文学的特征在各种类型的小说中都能找到踪迹。你可以说伊恩·M·班克斯(Iain M Banks)的“文化”系列小说属于纯文学科幻小说,也可以说莎拉·沃特斯(Sarah Waters)写的是纯文学历史悬疑小说,也可以说约瑟夫·卡农(Joseph Kanon)或者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写的是纯文学间谍小说,也可以说《罗杰疑案》中的元小说写法是纯文学的特质……我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
我有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拿音乐举了一个例子:爵士乐比蓝调布鲁斯更复杂,更难演奏,也更难欣赏。但这并不是说爵士乐是一种更高级的意识形式,只是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形式区别。同样,当我们说到“纯文学小说”这个概念时,我们通常是说这值得我们仔细地去阅读(当然也有例外)。小说不同,仔细的程度也不同。比如,阅读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或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aard)那种暗流激涌的小说,肯定和阅读纳博科夫(Karl Ove Knausgaard)透彻精确的小说付出的精力不同。出于明显的原因,仔细的程度有可能会导致难读,但这也不是一个定律。
如果情节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主要引擎,那么作者总会(但也并非一直如此)用一种能够吸引读者的方式去写作情节:就像是窗玻璃一般的散文风格,清晰而敏捷。如果作者有其他企图,也许就会有意地让读者放慢速度。他们也许想要构建一种声音、一种气氛,或者(像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那样)玩弄小说形式本身。文学理论中也讨论过形式上的厄运。自然主义小说呈现的是世界一角,并让读者相信这是世界的唯一一面;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认为类型体现的是现实:比如19世纪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小说呈现的就是非常保守的世界观。小说在选择主题、背景和叙述方式时,特定的选择视角就会将其绝对正常化。如果你的小说核心是种植园的年轻富家白人子弟的恋爱故事,那么读者们也会考虑到小说发生的社会背景。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说过,他讨厌在小说中写爱情故事,因为“如果角色找到了真爱,那故事就结束了,哪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哪怕天空中全是黑压压的酱汁,都不重要了”。
所以,叙述方式的形式是一种政治或现象的选择,而不是事件自然组合的结果。自由的间接形式、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意识的流动,无论你选择何种讲述方式,这本质上都是人和历史的选择。作家当然可以选择让读者注意到这种选择,也可以选择让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去理解。小说家、评论家加布里埃尔·乔西波维奇(Gabriel Josipovici)在《现代主义发生了什么?》(What Ever Happened to Modernism?)中写道,这是读者的义务,而不是读者的权利。

无论是形式上的自我意识,还是叙述方式上的技巧,本身都会造成作品的难读。有些畅销纯文学作家(比如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也充满元写作元素,戏中有戏,并使用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声音。很多人认为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是一部纯文学科幻小说,这本书玩了许多时间线跳跃的技巧,但(我觉得)并不难读。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一直在运用结构和声音的技巧。《云图》让他成名,这是一本类似于俄罗斯套娃的复调小说,融合了多种类型。但就连米切尔也说,为读者提供阅读兴趣是他与读者的合约,毕竟读者要花几个小时阅读他的作品。
我们不要假设难读的作品就像是某种食之无味的高纤维减肥餐。许多著名现代主义作家和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不止是形式上让人难以理解,它们也非常有趣。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虽然是位存在主义荒诞作家,但他的作品也很有意思。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T·S·艾略特(TS Eliot)也是一样。更近一点,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算得上是一位精神错乱的恶作剧大师,品钦也是。A·L·肯尼迪(AL Kennedy)的《终战日》曾荣膺科斯塔图书奖,讲述了二战中炸弹飞行员的故事。这本书极其严肃,叙述方式也比较复杂,但同样充斥着不少笑话。我认为,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的《撒丁岛》是当年布克奖短名单中最幽默的作品。此外,那些喜欢《送奶工》的读者并没有称赞这本作品的严肃性或深度,而是赞扬了其幽默感。
这说明,有些所谓难读的小说并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如果伪善是善与恶中和的结果,那么中庸和天才中和的结果就是自负。我记得布克奖的一位评委在浏览完入选作品后,翻着白眼说,“这些作品有不少……写得很好。”但他的意思是,写的糟糕的作品更让他头疼。从本质上讲,纯文学小说的地位更高,换句话说,更“重要”,因此许多野心勃勃的二流小说家为此绞尽脑汁。所以我们总会读到那些充斥着装腔作势的比喻、假正经的、没有情节的小说,它们把难读当作是一种成就,更有甚者把难读和严肃划上了等号。在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小说《信息》(The Information)中,主角理查德·图尔(Richard Tull)令人难以卒读的第七本小说“有着八条时间线和十六位不可靠的叙述者”。如果说纯文学小说没有讲述一个故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小说还是有故事的)还频繁变换形式、过于注重语言的话,那么并不意味着你把这些特征加倍,就能写出来一部旷世奇作。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感谢文学奖的评委每一年都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些真正值得阅读的“难读”作品,而不是为他们的决定感到愤怒。
(翻译:李思璟)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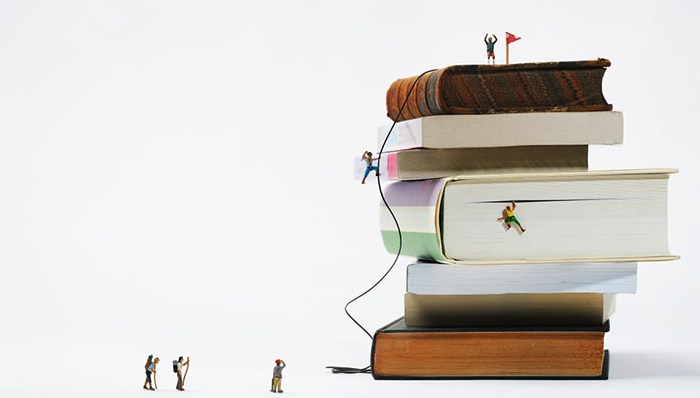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