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李洱的长篇新作《应物兄》在2018年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以济州大学儒学院筹备建立的过程为线索,讲述了中国大学乃至知识界的众生百态。
一经问世,《应物兄》迅速斩获了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第一名以及《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长篇第一名。在名为“且看《应物兄》如何进入文学史画廊”的作品研讨会中, 有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因为其“特殊的中国风度而具备了世界级文本的因素”,也有学者盛赞,小说堪称“一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的人文、思想的大百科全书”,还有评论者抓住了《应物兄》的学院小说题材特点,认为这部小说体现出了与西方学院小说的共通之处,也表现出了中国大学、中国知识界人士的精神与生存,因此和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戴维·洛奇的著作一样,成为世界学院小说体系中的独特存在。
果真如此吗?单从学院小说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应物兄》是如何讲述中国大学故事的,如果与英美学院小说相比,又呈现出了哪些引人深思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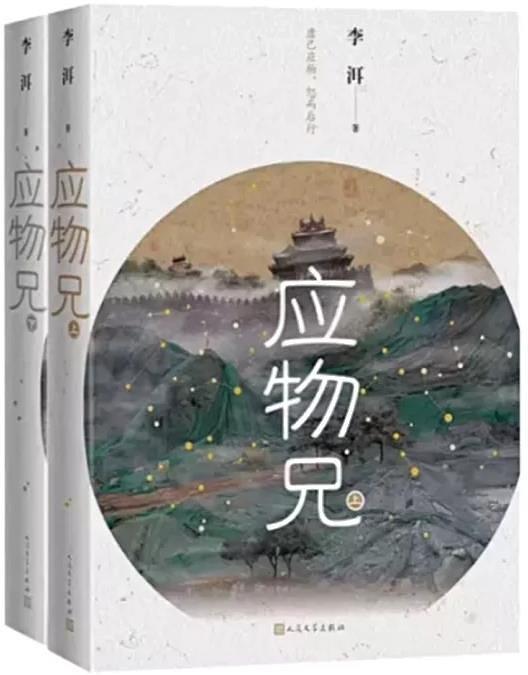
李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
性话语:逼视、暴露和戏谑
在小说《应物兄》里,性话语超越夫妇床帏,体制性地漫漶至整个学院和学术生活之中。这些性话语多数是针对女性的,无论是女同事、女同行,还是女学生或是女家眷,不管她们是出现在校长办公室、广播电台还是教室里,似乎只要在场就需要接受情色滤镜的逼视,并在此逼视下“暴露”出具有魅惑力的、甚至随时可能失控的女性性征。一位教授如此观察校长的女秘书,那个穿着套裙的女人“屁股饱满,裤子绷得很紧,随时都有可能绽开”。主角应物兄看到当地女主持在公交车上的一个广告,在他眼中,她做广告的形态是“傲然挺着自己的乳房、撅着屁股,身子扭成S形”。当应物兄十几岁的女儿出场时,她被父亲首先注意到的也是波涛汹涌,“比母亲还要大”——这一点与毕飞宇笔下的少女玉米首次出场就被父亲观察到“胸脯鼓鼓的”极为相似。

在逼视暴露女性性征的同时,《应物兄》中更多的性话语添加了嘲弄和戏谑的意味。应物兄的女学生会在小课上与他分享闺蜜在私处的纹身,用体液排泄“尿到一个壶里”来比喻她和闺蜜的情谊,还会对异性同门自嘲道,“每次洗完澡,看见自己的好身材,我都想把自己给上了。”——虽然这些话语是从小说的某个人物口中说出的,不能代表作者的声音,但读者或许不应该把这些性嘲谑单纯地视作人物性格使然,如果结合整部作品看来,我们会发现,性嘲谑无所不在,且比这些玩笑更加过火。在课堂以外,学院之中,酒桌之上,学者、商人等各色人物不分场合地开着暗示或明示的性笑话,这构成了统一口径的性嘲谑语言:在酒桌上,一位领导在众人面前提起自己的夫人,毫不避讳地将她的大腿和肾器比喻为“起落架”和“发动机”,并笑言她这两个器官运作已经失败了。书中最为“德高望重”的儒学教授、也就是太和学院最想引进的哈佛学者,在学术会议上对一个做翻译的女生产生了兴趣,他认为,从她的翻译可以推断她“性爱经验丰富”,她的身体就像“一座自由的港口,像一个买票就可以进去的剧场”。
事实上,不止是关于女体的玩笑而已,男性性征也在知识界诸众的高谈阔论中多次被提及,有些地方明显带有夸张色彩。犹如《肉蒲团》中有男性接动物鞭增强性能力的传说,《应物兄》中有一位美国华裔商人号称自己经常换肾,身边的保镖都是他的备用肾器,而保镖的性交次数以及深入女体的长度等此类统计数据,也是可以在饭桌上、由商人的医生“引以为傲”地公布的谈资,“若是放任他们,他们一天可做十次,一次半小时,那就是五个小时。每次插入十厘米,一秒钟抽送一次,一天就相当于在女人体内走了三点六公里,一个月下来就相当于在女人体内走了上万里。 ”
如果说女同行的性吸引力以及华裔商人的七颗肾是刻画人物形象必不可少的笔墨,对于小说情节发展也有着重要推动力量的话,那么,《应物兄》更多处的情色话语已经脱离出了主文本,可以看作是逸出的“闲笔”或是段子小品,类似《儒林外史》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故事串子,更多地呈现出了作者在性话语方面的博闻强识和特殊趣味。比如小说讲到黑人留学生和亚洲女朋友的性事,借用黑人之口,抖露出了“阴户很紧,需要助跑”的段子。提到与学院有利益关联的商业大亨,他们有的从事安全套生意享誉全球,作者特别提到安全套的名字全都取自中国的词牌名,诸如念奴娇、后庭花、摸鱼儿,具有强烈的性暗示色彩;有的大亨则坐享“多妻多妾”的艳福,比如某位富商甚至娶了同卵双胞胎姐妹,分为“大嫂子”和“小嫂子”,二者共侍一夫、和谐相处,更属猎奇。正因为有诸多闲笔,其中也就包括了事实错讹。有一章中讲检查女生是否受到侵犯,结果发现处女膜“完好无损”,侥幸道,“要是破了,还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呢。”然而,以生理常识来说,女性的处女膜天生就不是“完好无损”的,用处女膜“破不破”来检验处女属于民间讹传。
小说主角应物兄对于不合时宜地谈论性是非常敏感的,这似乎保证了主角的个性淳厚与“出淤泥而不染”,小说里不止一次地讲到他对于他人公开暴露性趣味、尤其是关于女性私密趣味的惊讶,甚至撞破了妻子与同事的奸情都不会戳破,反而认为自己应当感谢对方帮助自己照顾了妻子的“妇科健康”——但是矛盾之处在于,他的这种惊讶并不会阻止他在自己的著作里畅想别人的床笫细节。他在自己的书里写道,有些女人喜欢做爱之后“倒蜻蜓”,这会使得精液更顺畅地流入——这倒让他与小说整体层面的性话语,诸如“助跑进入阴户”、“二女同事一夫”等等,又保持了趣味上的一致性。
应物兄在实际行动中也保持了这种统一性,在电台节目里,他援引《关雎》和《孟子·告子篇》的“食色性也”作为自己的传统理论支持,事后也和女主持睡在了一起。事实上,他的行为与书中那位最为德高望重的儒家学者在行动上是一致的,在学术会议上,那位学者半开玩笑地认为,儒家的核心理念“仁义礼智信”都集中在男根上面,后来,他也用自己集聚儒家理念的男根征服了现场女翻译,让她非婚生子,之后忘记了她。
性入侵:纵欲辩证法与“体制性阳痿”
《应物兄》在泛性化的程度上,可与毕飞宇的《玉米》相比。在毕飞宇笔下的那个村庄里,通奸无处不在,所有的妇女都是村支书的姘妇,连农民耕耘的大地都是“丰乳肥臀”,“洋溢着排卵期的孕育热情。”不过,与《玉米》最大的不同在于,《应物兄》中的男男女女都是知识分子,而非农夫农妇。如上文所说,他们更善于挪用知识包装指导男欢女爱,为纵欲安插正名。这样的知识,正经的有“食色性也”,半正经的也有“男根中有儒家核心”,这也使得文本变得更为复杂。

毕飞宇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年
复杂之处在于,一方面,《应物兄》在小说开篇就向读者展现了关于纵欲和禁欲的“辩证法”。应物兄认为,有的人好像一直觉得有欲望,并且一直在获得满足,但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阉割了,因为本人已经没有了内在的、强烈的欲望和冲动,反而只得认同他人给予你的性欲与性消费;结合整本书的性话语狂欢来看,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整本小说的精神纲领——就像那个为了满足欲望不惜安装七颗肾的商人,也等于被膨胀的性欲阉割了七次。
另一方面,过多的性话语也令人怀疑作者是否沉耽于性事趣味,就像《儒林外史》中的“包袱”破坏小说结构、加重小说的散漫感一样,李洱在小说中频繁地引用性事、性癖好、性数据,甚至对于排泄意象的迷恋,也迫使文本多次在对阳具、阴户以及屎尿的地方散荡开来,也让人们无从分辨,那些话语究竟是作者对于说话者的讽刺、对于“纵欲禁欲”辩证法的思考,还是作者借用他人之口、如同披露丑闻似的抖包袱,以至于让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高官及大亨——都被“自己上自己”这样的性话语所吞噬。书中一位出版人如此反思婚姻与欲望的关系,“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占用和利用对方的性官能,但是,当你在合法利用对方性官能的时候,你所获得的只能是体制性阳痿。” 如果将这段话稍加改编,就可以作为对《应物兄》一书性话语的批评,那就是,当一个人在小说中合法地书写性泛滥,他获得的或许也是“体制性阳痿”。
如果与其他以学院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加以对比,我们便可以进一步确认《应物兄》性话语的特殊之处。在《斯通纳》这部讲述美国中西部高校文学教授斯通纳学术人生的小说中,斯通纳在婚姻之外也有了一个情人,他们的相处充满了新鲜和愉悦。他在早晨来找情人,他们经常来不及说话就开始做爱。斯通纳对于袒露在他面前的身体充满了单纯的激情,毫无逼视之意, “他粗硬的手指抚弄着大腿以及腹部潮湿、隐约散发着粉红色光泽的皮肤,惊叹着她那小小的硬实的乳房,精巧而细腻。”

约翰·威廉斯 著 杨向荣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
斯通纳对于情人是非常满意的,但即使是面对导致他性挫败的妻子,也并没有流露出贬低对方身体器官、将之比喻如“起落架”的倾向。《斯通纳》在他们婚后生活不和谐的这一节中,也提到了妻子的性征,但没有以丈夫的目光呈现,而是透过妻子站在镜子前的自我观察道出,流露出一种寂寞的味道,“她双手掠过小小的下垂的乳房,让双手轻轻地顺着长长的腰部落下去,落在平坦的腹部。”面对妻子在婚后的冷淡和僵硬,斯通纳很快就自省道,二者之间的性确实缺乏爱的因素,因此即使好像充满热情地交合,也无法真正地使双方得到满足,“很快斯通纳就意识到,把他们的肉体拉到一起的那股力量跟爱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交合时那种决心既凶猛又超然,被扯开,然后又交合,并没有那种满足他们需求的力量。”
与《应物兄》的性话语广泛地渗透入学院生活不同,斯通纳的性挫败与性满足是止步于个人生活的,只限于他与妻子和情人之间,但却不因仅仅关乎个人生活就丧失了其重要性,反而体现出性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职业生涯和精神世界的影响:斯通纳和情人做爱、看书、做学问,他们认为自己同时拥有了“情欲与学问”(lust and learnings),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紧密地合二为一。
与之相比,《应物兄》中的诸多性事,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说辞和浮花浪蕊,对于知识分子个体而言并没有更深层的影响。比方说,应物兄即使发现妻子与别人通奸,作为丈夫,他自己都无法确定自己的情绪,“我生气了吗?没有。我不生气。他妈的,我确实不生气……据说女人长期不做爱,对子宫不好,对卵巢不好,对乳腺不好。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哎,其实我还有些遗憾。如果他确实爱乔姗姗,我倒愿意玉成此事。”
这段跳跃在各种情绪中的内心独白,与其说是在确认妻子通奸对于自己的情绪影响,不如说是试图用“为妻子健康着想”、“玉成此事”的糊涂托词,将自己从性挫败的事件中迅速开解出来。事后证明,他的自我开解是成功的,这件事确实对他的婚姻和生活造成了破坏,但对他本人的精神世界几乎毫无动摇。多年后,他再次来到事发地点,想看看自己有什么反应,结果发现“总的来说,并没有感到太多的不适”。
也就是说,虽然书中的知识分子善用“知识”为欲望和行为镶以金边,但是性并未真正进入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之中,而只是安插在他们酒桌饭局的笑谈之中。大儒虽然赞赏女学生的翻译才华,与她发生关系,还让她为其产下儿子,但并没有与她产生爱情——“情欲与学问”远远没有统一。可以说,虽然《应物兄》中的学院与国外高校有着密切的交往关系,也有着诸多海外访学、海归回流的场面,但在泛性化的精神上,却与斯通纳所在的美国高校相去甚远,反而与毕飞宇笔下的村庄同根同源。
学院运作:师承姻亲,八卦暗流
小说《应物兄》以大量篇幅描写了新学院筹备期的人才引进和人员调动,而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进入学院,又应怎样将人才吸纳进入学院,也透露出了中国学院的运作规则。小说的开头就展现出了一副混杂着上下级关系、师徒情分以及姻亲关系的学院人事图谱:应物兄就面临着不得不将曾经不和的晚辈调入新学院的难题——因为这是校长的授命,这位晚辈一直在校长身边工作;更重要的是,此晚辈还是自己导师的关门弟子,由是一次人事调动又导致了师门关系的内部矛盾。事实上,他不得不听从导师,因为他遵循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娶了导师的独生女儿。而弟子娶老师的女儿,师承关系叠加姻亲血亲,小说中写道,这是孔子开创的传统。也就是说,不仅应物兄是一位儒学家,要建立的学院是一个儒学院,就连这个学院的人际关系,都是儒家传统的体现。
在这样师承姻亲不分、同门还是同事的“传统”影响下,应物兄难免进退两难,不仅如此,他还夹在商界、政界各方力量之间,负责尽量拒绝着外界强塞进来的外行。他曾拒绝过某富商的两位姘妇之一,那个号称“小嫂子”的姘妇。在富商和应物兄关于进不进学院的讨价还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人将把自己的姘妇安排进学院这件事,看成与海南买别墅差不多的恩赐。书中如此写应物兄对商人要求的愤慨,“一对姊妹花,两个姘头。一对神经病,两节朽木。一对女博士,两堆粪土。从她们当中挑一个进太和研究员?这是挑朽木来雕?还是糊粪土上墙?”事实上, 朽木、粪土又有什么呢?书中还有比加塞姘妇更可怕的八卦,比如某个教授利用录制的另一个教授的嫖娼视频,勒索对方在成立新学院的时候聘请自己作为荣誉客座教授。
借助新学院成立之际的人员调动,《应物兄》呈现了一个学院的纷繁乱象。《斯通纳》中的学院也并非一方净土,只是斯通纳与应物兄在工作中遇见的典型事件并不相同,小说由这些事件揭示的学院运作规则也有所区别。在成为中世纪文学教授多年之后,斯通纳参与了一位学生的博士资格综合预答辩的评审,他严重怀疑这位学生的学术水平。在此前的研究生课程中,他已经领略了这位学生的夸夸其谈和不学无术;通过答辩环节,更证明了这位学生连任何一部莎士比亚之前的重要戏剧都没看过,没有资格通过考试。但斯通纳的同事,也就是后来成为他的上级系主任的劳曼克斯教授,却坚持认为这位学生可以通过资格考试,他们僵持许久,劳曼克斯教授几乎恼羞成怒,指责斯通纳是在破坏这位学生的前途,而斯通纳却说,“我这是阻拦他拿这个学位,我这是阻拦他在某个学院或者大学教书……对他来说,要是当上教师,那将是一场灾难。”
斯通纳拒绝学生通过答辩这一事件,几乎是整本小说中最针锋相对、火药味最浓的场面了,但这一状况发生在一间教室里,通过老师向学生提问文学知识的对话来体现,所有冲突都围绕着学生是否应通过学术水平检测,以及是否应该让这样的学生进入学术界,整件事指向的也是学院运作的规则,而非仅仅“学术八卦”。与应物兄主要面对的是姻亲、同门、商业赞助这类缠绕交叠的外部问题相比(应物兄也有学术问题,他也为研究生上讨论课,比如有一节对留学生写《黔之驴》论文的讨论,但那一节讨论课的内容,更接近于插科打诨而并非学术探讨),斯通纳考虑的是学术诚信、学术规范以及研究生的考核标准,然而在他捍卫学术原则之时,却也触犯了到了人事上的风险。当“对手”当上了系主任之后,斯通纳给高年级和研究生的课程被取消了,换成了低年级的写作课和概论课。斯通纳符合好友对他的称呼——“中西部堂吉诃德”,这位堂吉诃德职称评定被上级冻结,一生中处处碰壁;但他找到了作为教师的意义,就像书中写的,他意识到,“教师不过是这样一个人,对他而言,他的书就是真,就是一种艺术的尊严。”也就是说,当他进入了这个富有使命感的、可以持续一生的角色,就可以脱离愚钝的、软弱的、不足够的人生。

所以,在探讨学院运转规则的写作中,《应物兄》与《斯通纳》的重点是不同的,但也许我们不应该去责问《应物兄》的中国式学院为何缺少《斯通纳》式的现代大学学术机制和环节,因为,书中的程大儒就是在美国第一学府哈佛大学任教的。他理应非常熟悉现代学院的要求,但他在书中显现出的对于新学院的热情,也依然不是对于学术原则的,而仍旧落在了血缘、地缘的层面上。他回归学院是出于“叶落归根”的“人伦之常”,他想要新学院建在仁德路,因为那儿原来是程宅——也就是他家,这也在应物兄令人头疼的人际关系之外,进一步突出了《应物兄》中国学院的儒家色彩。
知识游戏:兜着圈子,插科打诨
《应物兄》广泛地引经据典,被评论者赞誉为“以知识入小说”,加入了词曲、对联、书法、绘画、音乐、戏剧种种元素,有显著的智性色彩。对于这部小说中的“知识”,我们或许还应当做进一步的讨论。上文已经提到,知识分子会引用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纵欲”正名,以经典来注解性欲,比方说男根集中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是一种对于知识的挪用和游戏;除了这般明显玩笑的,这位程大儒在更多的场合发表的言谈,也都体现出了善将知识腾挪转化并精于变通的特点。
当听闻中国计划生育遭到美国人的反对时,程大儒如此辩护道,“他们有他们的宗教,我们有我们的宗教。他们有他们的现代性,我们有我们的现代性。我们的儒教文化强调实用理性。孩子嘛,需要了就多生几个,不需要了就少生,甚至不生。”此后还举出了孔子、孔鲤、孔伋三代单传的儒家传统。在讲到包饺子时,他以包饺子的方法比喻了中国现代性与美国现代性的不同。他说,中国包饺子凭的是经验,面硬了就加水,软了就加面;美国人包饺子要面多少、水多少、问得清楚;中国人处理的是变量,中国人的价值观就是“道”;西方人处理的是定量, 西方人的价值观是不会变化的。
不仅程大儒善于如此经营知识的游戏,应物兄的学生也深得腾挪变化的本领。在研究生的讨论课上,应物兄让学生们讨论某位留学生所做的《黔之驴》的论文,诸位学生在讨论时引经据典,但本质上都在兜着圈子插科打诨,讨论从儒驴、回驴发展到佛驴,还有文人的驴脾气,甚至在人课堂上学起了驴叫,然而终没有真正切题。当然,这篇论文本身的立论——将驴子和儒家文化相提并论——就已经十分挑战常识了,应物兄对于这篇论文的评价是“有些胡扯”,但对于留学生能知道这些“杂七杂八的知识”,还是“吃了一惊”。这些“杂七杂八的知识”包括老子喜欢骑驴、王安石喜欢骑驴出游等等;而其中的考据和论证——诸如由老子喜欢骑驴,来论证骑驴与老子哲学的关系;又由老子和驴子的关系,扯到孔子与驴子的关系——则纯属“胡扯”了。
有评论者认为,小说《应物兄》中的旁征博引体现出了作者百科全书式的渊博,但我们也许应该问,这些旁征博引的知识是确实阐明了问题,还是以其密度和厚度遮盖住了问题本身?不必提中西二元分法有多么简单粗暴,单说以上这段由《黔之驴》论文展开的纷繁讨论,既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杂七杂八的知识”以外的内容,也并不可能真正回答驴子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只不过是以这种如驴拉磨般绕圈子的无意义回答,嘲笑了真正想要知道答案的人。
有趣的是,可与这种兜着圈子、插科打诨形成鲜明比照的,正是那个斯通纳不予通过答辩的学生的表现。在博士资格考试中,他对于自己论题的介绍引经据典,对答如流,侃侃而谈。由斯通纳看来,“这是一场控制的游刃有余的表演,毫不唐突,充满了某种巨大的魅力和不错的幽默感。”于是,他抛给这位学生几个关于英国文学的基本事实问题,比如任意说出三部中世纪戏剧的名称,不料这位学生竟套话连篇,诸如“中世纪的戏剧,以自己的风格方式,对文艺复兴的巨大成就做出过贡献”,以及“xx批判了xx主义,对xx充满同情”。学生没能用口才把斯通纳欺骗过去,他的套话只是在掩盖自己对文学一无所知而已。斯通纳对他的评价是“毫无才能”,中等本科生的程度都达不到,“既懒惰又不诚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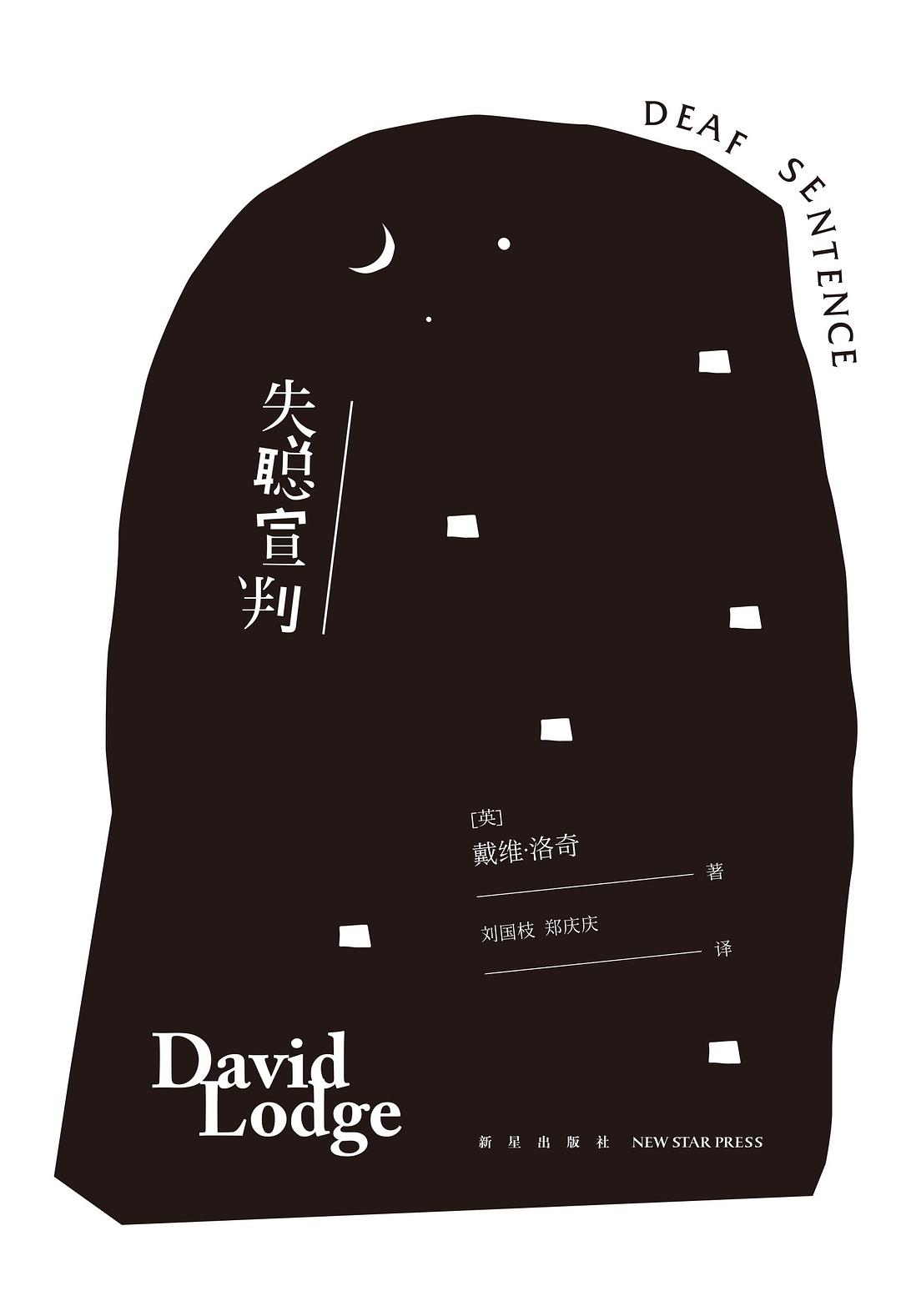
戴维·洛奇 著 刘国枝 译
新星出版社 2018年
知识难道不可以用来插科打诨吗?当然可以,英国学院派作家戴维·洛奇对于这种知识游戏非常熟悉。在小说《失聪宣判》里,他的主角、一位语言学教授几乎听不见了,但是为了不陷入接错话的困窘,他要掌握主动权,就自己选择的话题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作为教授,他有着知识自我生产的能力,可以就一个话题,说出一大段合情合理、却也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来。洛奇戏谑地写道,当他知道对方是一位左翼剧作家,写过一个矿工罢工的戏,就从采矿业对于英国人心灵的幽暗影响讲起,从左拉的《萌芽》讲到奥威尔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对方最开始听到这段讨论时还非常高兴,后来却借着要去看酒水的理由抽身。知识的游戏翻出花样,令人忍俊不禁。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戴维·洛奇笔下的教授是听不见别人说话的,在这些段落中,他与他人的“交流”只是为了场面。然而,《应物兄》中的程大儒或者研究生们,也不需要与他人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吗?还是说他们对事实已然洞察于心,完全可以靠兜着圈子、插科打诨、游戏知识过活呢?这也是《应物兄》留给我们的诸多疑惑之一。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