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代都市常被诟病的一点,便是人情稀薄、彼此冷漠,社会失去了亲密感和协同感,但在某种程度上,一部分生活在城市的人正是被其陌生化的、匿名式的生活“权利”所吸引,人与人之间“可以无限靠近,但要保持冷漠;可处盈尺之地,但要保持距离”,互相尊重,从不言语。
在从德国慕尼黑前往法兰克福的一班高速列车上,德国当代社会学家亚明·那塞希(Armin Nassehi)也不禁从坐在眼前的几位陌生人出发,思考了关于陌生人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在制度不同的社会中,陌生在什么情况下是一种威胁,在什么时候又是一种资源?是否只有在陌生化的社会中,亲密和亲近感才会具有价值?陌生人边界清晰、彼此无言,这究竟是冷漠和尴尬,还是一套成熟的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导致的自然结果?与陌生人相对的概念,是“自己人”,还是“强力的社会管控”?小到邻里,大至欧盟,我们还有多大的可能性放弃区别与个性而组成新的共同体?
那塞希发现,“现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最大成就,或许就在于不再直接掌控社交,转而由陌生感来加以协调。”陌生作为一种资源“创造了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城市风格”,而城市风格是一种共存形式,万物在城市汇集,且必须相互包容。他认为,“社会需要允许人们拥有不为人所扰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保障可以最终用来作为现代性的衡量标准。”然而匪夷所思的是,“一直以来,陌生感和距离以及冷漠和情感中立都含有丰富的潜台词,而人们则对此极为排斥。现代乌托邦社会的历史不乏各种叙事,而且都假定了陌生感和冷漠的对立面——左的右的皆是如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那塞希对共同体的概念并不感冒,相反,他提出,“对未来而言,我们不应该再去大肆兜售共同体的观念,而是应该去普及陌生感的观念,但我并不希望通过颁布法令来实施这一点。”

亚明·那塞希是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社会学家,也是社会学三大理论之一“系统论”的领军人物。在收录了他对于陌生化社会思考的《穿行社会:出租车上的社会学故事》一书中,他借助周游四处的“出租车”这个隐喻,讨论了由不同情境构成的复杂社会。他以此分析问题的是:为何处于不同角度和不同位置,我们看到的世界会如此不同?为何我们会拘泥于自己的观点?为何我们身处的社会总是不完整的、未结束的、不安定的?
那塞希在书中一路奔波,穿行于各个场所,探讨的话题似乎和政治毫无关系,但他自己却认为,本书实质上政治意味十足。“这个社会有如此多的不同,以至于我们几乎对它们一无所知,”他试图从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场景出发,悄然而出奇地描绘这个社会。
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或许仍未成熟到陌生由威胁变为资源的程度,在很多时候,面对不平等或不公平,我们仍需相互守望与伸出援手。但我们也不妨变换一下视角,让这位德国社会学者带我们“穿行社会”,尝试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穿行社会》的《陌生:为什么我们之间的距离是一种关键资源》一节中节选了部分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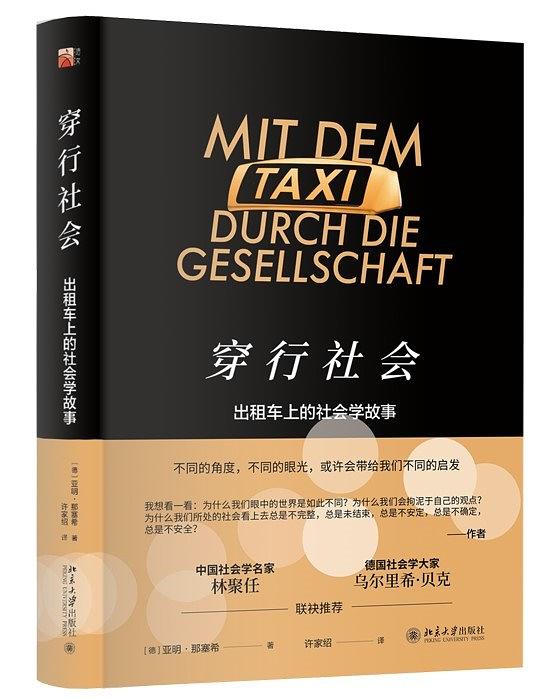
[德]亚明·那塞希 著 许家绍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01
《陌生:为什么我们之间的距离是一种关键资源》(节选)
文 | 亚明·那塞希 译 | 许家绍
1、陌生人是威胁还是资源?清净独处的“特权”
在冰冷的ICE列车内,四个陌生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但我们却并没有理由感到恐惧。这些陌生人固然素昧平生,但也并非不能了解。有时,有些人意图明显,或者动作手势颇具威胁性,我们仅凭本能准确而迅速地打量一番,很可能就不会让他们搭上我们的出租车。这种冷漠一直存在,但却直到这位老太太托人看管物品这件事发生才开始让我们察觉。
如果将进化意义上恐惧的功能和威胁感考虑在内,那么这恰恰不是一种自然行为。实际上这是遵循文明标准的结果(但却很难给予这种标准过高评价):我们跟不认识或不想认识的人打交道,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变幻莫测或协调一致,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我们四人一路无言,这绝不是缺乏社会关系的表现,而是表达稳固社会关系的方式。这种冷漠的社会关系普遍存在,在火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在大街或公园等公共场所内,都有表现。
乍看之下,人与人之间缺少密切关联,也缺少相互关注(由此也就有了对现代城市生活丧失了旧世界的社会亲密感的普遍抨击)。留心观察日常生活,你会发现陌生人之间类似的场景在一幕幕上演:在地铁内,在人行道上,在电梯里,在超市里,在办公室里,或在顾客盈门的工作场所里。
但是,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频繁上演的这一幕幕场景,而是在于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我们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不再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而是一件件模具,或者是一具具躯体,抑或是一个个角色的载体,只是完成特定角色的无名之辈而已。我们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陌生感和冷漠感为共同在都市生活的人们提供了基本资源。我们庆幸自己不需要认识工程师、机长、邮递员、垃圾清运工或药剂师。最终,我们才能有幸独处。现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最大成就或许就在于不再直接掌控社交,转而由陌生感来加以协调。
这并不是要淡化熟人关系——事实恰恰相反。大多数社会关系在本质上都是陌生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这种亲密和亲近感才会具有信息价值。为了尽可能寻求在社会中隐身,密切关系显得愈发重要。想一想爱情和伴侣的情感期望,这些在之前的社会中并不存在。对于少数关系密切的人,情感期望会增强,而对于其他人,这些期望则会降低。
我们千万不要把陌生感当成威胁感的先决条件,因为事实恰恰相反;比如,由邻里或警察强力施加的社会管控反而会给我们带来陌生感。在很多地区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例如,在有些地区,警察形式的国家控制已经瘫痪,公共秩序已然失常;在还有些地区,合法协议却得不到履行。在像阿富汗或伊拉克这样的战争区域,抑或国家或经济秩序陷入危机的非洲某些地区,陌生感都不是一种资源,而是一种威胁感。这些地区所需要的资源就是强力社会管控。

这一点看起来很好理解。同时它还可以进一步强化“社会秩序会极大地影响其他情境问题的处理方式”这一认识。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境让人们彼此远离三分,或者在不同的情境中不断转换角色,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上述危机地区的例子中,我们关注的是社会利益。这种关注是必要的,这样就无须再去彻底核查陌生的情境。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救助组织会给前往危机地区的员工发放行为规范手册。其主旨就是:赶紧离开,这里不是你的家,不要信任任何人,事情不会像你预料的那样。
这时还能落个清静真是自在。但这种自在却是来之不易,很多时候这种特权都是脆弱不堪,这一点在我们身上显而易见。封闭社区设置门禁控制出入,其公共空间不向公众开放,这种社区在美国再寻常不过,但在德国也开始大行其道。只有获得授权的人才能自由出入,于是陌生人——那些并无恶意的陌生人也就被拒之门外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区内的人们就彼此亲密无间。在慕尼黑就有这样一个封闭社区,那里的居民整天因为花园边界或停车位的事情而冲突不断。究其根源就在于,无关人员都得远离三分,这些无关人员貌似恶意十足,连参与冲突的资格都没有。
另一个例子则是停车场中设有女性停车位,旨在防范女性容易面临的危险——也是男性可能不会想象的危险。透过“女性停车位”这一标识,我总能看到陌生人的危险面庞,而不是他所能提供的资源。
2、“社会需要允许人们拥有不为人所扰的权利”
我们在火车上的举动表明,我们就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秩序并非游离于个体之外,而是浓缩于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都是社会稳定的媒介。我们四个人围坐在ICE列车内同一张桌子旁,都在维持那种确保彼此陌生的秩序——与此同时这种外部秩序也在通力协作。
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身上实践社会秩序。我们终身都在学习,我们关注成功的行为,我们体验偏离正轨所带来的耻辱和尴尬,我们实行协调行动的策略,我们习惯于失望并解释自己决定的必要性。我们都在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得到社会认可,这就是社会秩序所在。所以我们都在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在ICE列车内的举止反而创造出了一种通常可以相互依赖的秩序。
列车刚刚启动,两位男士就在我们身旁的空位上坐了下来,看模样都生1940年代后期。两人举手投足极为夸张,成功人士的自信表露无遗。见面伊始,两人谈话就很投机。听得出来,他们正在关注一桩公司兼并案,两个人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兼并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一个人认为,某个部门的主管“一无是处”,所以那个部门不得不关闭。另一个人则表示,那名主管操刀设计了这一兼并计划,不可小觑。
这两个人聊得如此投机,也不顾忌其他乘客是否会听到,这一点也折射出了现代陌生感的另一层面内容。显然,我们认为在公共空间中,我们的所作所为相对不会引起他人关注。如果是在他们公司的餐厅,或者是在表现活跃的行业协会的会议上,他们当然不会坦率且自由地发言。但在列车车厢内,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无信息价值——因为任何人都能听到,所以即使别人听到也无妨。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都有过类似经历,大家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安之若素。但是,先前两位乘客共同保持沉默,为人认同;而这两位商务人士高谈阔论,却是无人欣赏,这是很有必要的。在这里,一个稳定的架构已经预设完成,对注意和非注意进行了高效的管理。
当然,总是会有一些人横加干涉——特别是在与陌生人同处尺寸之地内时。但这只是情形有变而已。假定我像一位教授那样参与其间并大加评论,即使我的观点全都正确,这两位先生也定会不堪其扰,认为我在干扰、干涉乃至冒犯他们。这样一来,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谈话过程中再营造一个社交空间——想听想看随你便,但就是不能参与其间。
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陌生感可以清清楚楚归结为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创造了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城市风格。顾名思义,城市风格是一种共存形式,历史上主要在城市出现,万物在此汇集,而且必须相互包容。如今,城市风格已不再局限于城市。陌生人不是外星人,人们只是想要猎奇,但又要在某种程度上恪守城市中的普遍规则:可以无限靠近,但要保持冷漠;可处盈尺之地,但要保持距离。就这层意义来说,在这趟开往法兰克福的ICE列车内,在这张四人小桌上,城市风格同样展露无遗,连赞同都可以心神意会,还有什么威胁感可言。
城市资产阶级有权利不被打扰,这也是城市风格的源泉。只有在城市里才有机会见到众多陌生人,而且也没有人会带来威胁感。只有在城市里你才能真正不为人所扰,因为无关人等实在太多。也只有在城市里我们才不会成为关注对象,因为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我们渴望不为人所扰,他人同样如此。每个人的行为都要得体,不要影响他人。城市风格源于内部监管,而非外部监管。
但必须保守一份陌生感。我们要做到目光冷漠,不理不睬,视而不见,承受关注,体验失落,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内在注意力和自我意愿的反映。作为一种实践,城市风格在于人们之间行动的相互作用,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无为而动,区别性地漠然处之。我们四个人围坐桌边,轻轻松松就做到了这一点。
社会需要允许人们拥有不为人所扰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保障可以最终用来作为现代性的衡量标准。匪夷所思的是,一直以来,陌生感和距离以及冷漠和情感中立都含有丰富的潜台词,而人们则对此极为排斥。现代乌托邦社会的历史不乏各种叙事,而且都假定了陌生感和冷漠的对立面——左的右的皆是如此。国家有亲善的需求,需要找出潜在的同志,或者至少是同胞。各种形式的劳工运动都期望人们精诚团结,而且这些人最好既不相识,也不相爱,只要抽象的阶级立场相似就可以。在民主社会中,对人民的统治是借助于构想中的公民社区来实现的,公民遵循市民规范,团结一心,认同并非源于自己信念的决定。无独有偶,欧洲目前正在尝试创造一种共同体认同,以推动欧洲继续前行,这种认同会让陌生人成为自己人,其中至少要有新世界主义善意的思想意识形态,让人们不堪回首自己的殖民历史,用左的思想武装他们,鼓动被奴役的人们(也包括所有陌生人)团结起来,共同创建人类大同社会。

在这里,我很乐意进一步申辩:我反对这些共同体意识形态,因为它们多少有些自相矛盾。我只想再强调这一点:要把陌生感当成一种资源。围绕这一点,我不想再去打口水仗,我还是想强调社会乌托邦论点的框架。现代性与团结性的意识形态协同作用(替代先前的共同体和承诺)并为其提供令人同情且至今仍在沿用的模式(至少对全人类中那些受到影响的团体而言),这无疑表明,类似形式的接近性和共同性已很渺茫。
3、各司其职,“隐身”生活:匿名身份维持城市风格
城市生活方式逐渐演变,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轻,但最终还是相互容忍。在城市中,多样化的举动紧密结合,互相关联,实时互动。权力乃至情欲充斥其间,由此城市演变成为现代化中心。
城市内部在经济与政治、教育与艺术、科学与宗教、风格、观点、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都有所不同,所以很难保持同步发展。因此,在城市中总能看到各种标识和标语。公共领域由此得到界定——从对他人的可辨别性以及拒绝交流所造成的长久危险性来看,它是一种矛盾,也是一种社会不平等的体验。贫富差距在减小,国家及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节节胜利,人们选择报酬丰厚的就业岗位,新型生活方式由此得以发展。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有组织的团体都没有忽略陌生感这种资源,而是在消费这种资源。这样一来,福利国家所支持的也就不是那些它具体了解并且赏识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什么声望的普通受益人。比如说,一个人的房子烧掉了,他不会去向邻居求助,因为他需要跟邻居培养一种紧密共生的生活形式,不容任何闪失。他会首先向消防队求救,而后是保险公司。一般而言,这种受损个体的保险精算集体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明如何将匿名性和陌生性用作资源。在这里,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就是在进行精算——采用计算机科学家计算保费额度的形式。从国家当局,如行政官僚机构、警局、社会救助机构、青少年救助机构那里,我们公民会期望那些基于“道德匿名”的行为。底线就是:社会团结建立在陌生感之上——而这也正是要把陌生感作为一种文化资产加以保护的原因所在!
我有两个博士生,她们一个来自中国台湾,另一个则来自日本,但都是富有同情心并且天资聪颖的年轻女科学家。她们接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项目资助,在我的指导下学习两年同时撰写博士论文。她们的报告中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德国经常会讨论“疏远”这种资源。显然,国家官僚机构更加关注的是他国国民而非本国公民,其举动有时令人匪夷所思。我在15岁时成为德国公民,之前我还是一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的公民,所以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两位年轻女士在报告中提到的就是偏见和无礼,我们在与“未知”的陌生人接触时经常会遇到这两个问题。她们通过观察各种人群,尤其是男性群体,甚至是自己的同学,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她们亚洲人只有通过跟欧洲人结婚或者在这里工作,才能养活远在亚洲的家人。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上有些群体并未从陌生感这一资源中获益;而人尽皆知,少数民族个体身上会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陌生感。我的两位博士生在报告中指出,他们无法保持“隐身”。

但是,维持城市风格靠的就是这种“隐身”。如果秩序丧失,匿名身份公开,城市风格也就岌岌可危。城市中涉及种族、性别和文化等方面,少数民族的情况是最好的,因为尽管他们很显眼,但却并没有人关注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人们之所以可以旁若无人般地生活,恰恰是因为他人就在旁边。在城市里,你无须刻意观察,因为人们总是在守望。如果只能通过部署警力和监控探头,通过规避危险地带以及同化与隔离的方式,城市秩序才能得以维持,城市还会继续存在,但是城市化却将消失殆尽。
城市风格的维持有赖于社区限制和外部控制缺失。然而,如今的城市对社区和外部控制的依赖却是与日俱增,这对城市风格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检验城市风格的试金石就是考量一座城市能够容纳多少社会不平等现象,群体多元性有多大,能否让移民、性别弱势群体、残疾人和外表怪异的人保持陌生且不那么显眼(但他们要能被社会所容纳)。城市风格并不只是一种理念或理论,也不只是一段崇高而又规范的话语或者是一个概念。城市风格需要我们亲自去实践。
也许这是欧洲特有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与那种被误导的、强迫性的、暴力性的欧洲共同体意识形态的经历相关,是现代欧洲社会出现的前提。也许我们应该为欧洲保持这一成就感到自豪和自信。世界各地有很多社会都在不断尝试建立更强大的共同体(如宗教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其动机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对未来而言,我们不应该再去大肆兜售共同体的观念,而是应该去普及陌生感的观念,但我并不希望通过颁布法令来实施这一点。
书摘部分节选自《穿行社会:出租车上的社会学故事》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