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
全球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美国知名历史学家,纽约大学(NYU)校座人文讲席教授,纽约大学国际高等研究中心负责人,研究涉及文化史、思想史、城市史等领域,是美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宣告美国史的寿终正寝,这一点我们早已知晓。
“终结”(end)既可以指一种“(主动的)目的”(purpose),也可以指一种“(被动的)终止”(termination),这两重含义对我导入主题都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我有意吸引大家来关注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的终结,美国史也位列其中。各国的历史通过学校教育被带入公众话语中,进而打造和维持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自足的国家被呈现为历史的天然载体。我认为:这种写作和教授历史的方式早已黔驴技穷。
我们所需要的史学是一种能够把民族国家史理解为自身不断构成了多重历史,同时又被多重历史所塑造的史学。而多重历史(的范畴)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民族国家史(的范畴)。
民族国家并非决然独立、封闭自足的;它跟其他各种人类团结(的形式)一样,不仅与外部相关联,也或多或少地被自身之外的环境所塑造。事到如今,(我们)不应再忽略(这种观察)民族国家史的显而易见的维度了。19世纪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嵌入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史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但它遮蔽掉了民族国家多重社会中的真实经历,并在一个我们更加需要宽广的世界主义的时代中造成了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
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s)一样,各民族国家史的研究也经历了种种现代的发展。作为合众国之首部民族国家史著作,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的《美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出版于1789年。
事实上,拉姆齐有意拖延,将此书的出版拖到了美国宪法被批准生效之后。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史学——特别是学校中的历史教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人们)将国家视为人类团结的最主要形式。它成为学校和各类机构中公民教育的核心,这些学校和机构都致力于将小农、移民和各边远民族(provincial peoples)造就成民族国家的公民。
一种共同的历史有意要为一种共享的民族认同提供依据,它既裹挟了人类共同的记忆,也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即忘却差异。
这种对公民的构想是完全且绝对的,被认为是能够压倒其他所有的认同来源的。地域、语言、种族、阶级、宗教和其他团结或关联的形式,相较民族国家而言,要么微不足道,要么大而无当。它们都应当完全服从于那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此外,国家的领土也被明确地限定。为了维持一种国家公民或国家主体的观念,国家的空间和人口都被假定成高度同质的。相应地,现代民族国家承诺在国家内外都会对其国民提供保护。一种既能表明国之边界至关重要,又能许诺提供保护的人为创制就是护照的出现——它是19世纪的一项新发明。
新兴民族国家的领袖们把国家自然化视为一种最基础的、最显而易见的人类团结形式,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帮助。
尽管这种对国家意义的抬升仍算是一种相当新鲜的做法,但当习惯成自然,把一千年前发生在法兰西当下国界里的事都当作“中世纪的法国史”时,人人都越发对这个概念泰然处之了。显然,在这个大谈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散居(diasporas)的时代里,我们当下的切身经历并不能与民族主义者那时的假设相匹配。
生活着实更为复杂难辨。历史学家们跟其他人一样也都深谙此理。
人们常说,19世纪的史学在意识形态框架上展现出来的明显缺陷之所以延绵不绝、难以根除,可以用别无选择、了无他途来解释。
在这本书中,我的目的就是要在超越国家的背景下,提供另外一种理解美国史中心事件和主题的方式。
不同于“美国例外论”的概念,我的这一框架坚持认为:民族国家并不足以构成其自身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它早已逼迫着,将其生存的环境推展到了最终端的大陆尽头,即整个地球。
在此,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和事件,包括像革命和内战这样独特的美国事件,都应在一种全球史的背景下接受检视。超越民族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要置民族国家于不顾,相反是要将其历史化并澄清其意涵。
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曾写道:“抽身于史学和民族国家的源流之外,不是为了非难史学,相反,是为了把握一些强有力的假设,而这些假设业已形塑了我们的思考。
在过去数年间的美国史研究中,在最具原创性且令人振奋的学术志向里,有一些并不必然束缚于民族国家的方面已经被搭建起来——它们包括在社会史中对性别、移民、民族散居、阶级、种族、族裔特性以及其他各领域的研究。
如果(我们说)这类学术志向并未屈从于民族主义者的框定,但它也没有改变或取代后者。它只是日渐壮大,日益与盘踞于我们脑海中的那类老旧的既定叙事渐行渐远。
它带来了关于美国史中先前未被研究或未被充分辨识的某些团体和主题的新知,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处于主导地位的叙事结构。民族史的单一逻辑看上去已经陷入僵局,新的学术志向貌似可以有所突破。
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类新型的学术志向被打上了括号、割裂另置(在各类教科书中确实如此),而不是被整合收编。虽然学者们不断添枝加叶,但基本叙述却岿然如故。
这也解释了教科书为何日渐冗长、越发难读、鲜有读者问津,因为19世纪的老旧叙事被淹没于芜杂的新研究之下。这种叙事必须经受更为直接的挑战。
大约10年前,我开始更认真地思考,并从相当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早已被写就、定型的美国史。对我自己当时教授美国史的方式,我不想再提。困扰我的并非是当时饱受争议的政治史议题,至少不是对所谓文化战争中此方或彼方狭隘的支持或反对,也不是要迎合自由派或保守派的阐释,因为在困扰我的事情上,两派并无异见。
我面临的是一种更为根本性的、方法论上的难题:
在我看来,那种盘踞在我脑中的既有叙事似乎限制了我理解美国史中心主题的能力。什么是美利坚民族经历的真正边界?什么样的历史是美国与他国共享的历史?如何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背景为参照来改写美国的核心叙事?
我开始反复思量核心叙事中的两个方面:它未加检视的假设——民族国家是历史天然的容器和载体;以及它所忽视的真相——不逊于时间,空间同样也是历史解释的基础介质。历史既在时间中延绵,也在空间中展现。
你我都曾被教授过一种美国史,那种美国史看上去似乎是封闭自足的。
在学校历史课程中出现的种种新变化,更是突显了问题的存在而非解决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在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中,为了把我们的年轻人更好地培养成合格的公民,美国大多数州如今都要求学校开设世界史课程。这貌似是一种富有成效的课程变化,但在实践中,这种新课程却颠覆了动议的美好初衷。大多数世界史课程并不涵盖美国史。
不知何故,无所不包的世界史(的课程内容)却不容我们(自己的历史)栖身于内。在此类课程中,美国与其边界之外的世界的相互联结和彼此依赖鲜有提及,并且这种修订后的课程再次强化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分裂,而这正是当代公民必须克服的一种分裂。
如果美国人倾向于将某些“国际化的”事务视为“外在的异数”(out there),而非以某种方式与他们自身相关,那么对于这种错误的认知,我们合众国的历史学家们难辞其咎。我们的学科训练致力于让我们把国家视为自足的历史载体,我们讲授历史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地方主义(parochialism)的眼光。
我们把这一点假定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但我们却并未对其加以证明。如果历史学家想把学子和公众教化为真正的公民,他们必须更为深入地思考其用以架构各民族国家史的方式。民族国家史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但也应当以揭示共同性和互联性的方式来坚守。
令人费解的是,研究外国史和地区史的许多学者——区域研究的专业人士——往往共享甚至强化了这种内外二分的研究方法(binary approach),把合众国和它外部的世界放在了两个不同的匣子里。在美国的大学中,美国研究和区域研究的计划是同时发展起来的,然而直到最近,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彼此都是同一个全球史中相互影响的组成部分。
由此,我们限定了自身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理解,也忽略了他国之历史在构成我之历史的组成部分时的种种方式。
美国人需要更加意识到自身是作为“异邦的一部分”(a part of abroad)而得以存在,正像纽约《商业周刊》在充满希冀的1898年所观察到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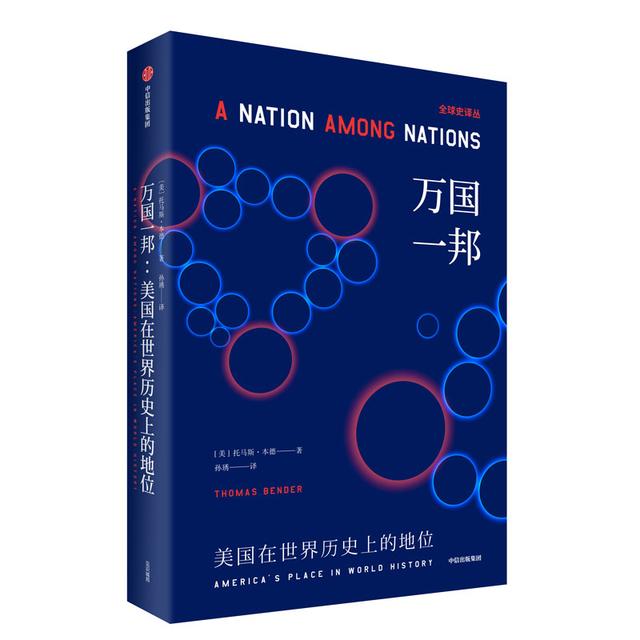
万国一邦 : 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 (美) 托马斯·本德著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埃里克·方纳、《经济学人》重磅推荐!从世界的边缘到中心,从与世隔绝到息息相关,全球视野下重塑美国历史。
将美国史纳入更为广阔的全球史视野中,已是大势所趋。托马斯·本德是当代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首倡跨国史理念并付诸实践。《万国一邦》是本德的代表作,已成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作品。本德摒弃单一而孤立的民族国家史,打破早已定型的研究框架,将美国重新放置在全球视野下,重构美国历史。作者将美国独立战争、西进运动、内战、工业革命、现状与未来等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和独特事件,全部放在全球史背景下接受检视。从16世纪新世界殖民时期到20世纪的社会改革,美国必须被视为全球的一部分,并作为其中一分子与世界互动。
本书详尽阐明了两个嵌套在一起的论点。
第一个论点是:全球史开始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史开始的时候,以15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为开端。第二个论点紧承第一点而来:除非把美国史整合进全球的背景,否则对它的理解将不可能是充分且完全的。
唯有如此,才能使美国史研究成为一种有所改观且更具解释力的史学研究。这种史学重新连接了历史学与地理学。它整合了因果性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既体现在延绵的时间中,也跨越空间发挥作用。它也丰富了我们对在历史中不断被打造和再造的合众国的理解。
此外,这也是勘测和评估一种变动不居的位置转换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唯一途径,正是它们将今天的合众国同地球上的外邦(the other provinces)联系了起来。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在19世纪末将民族国家定义为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所有者。这一定义自然拥有证据上的支撑,证据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有证据又不足以说明问题。
民族国家同样也有赖于民众对民族认同的接纳。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很大程度上可以在一种共享记忆的感知中被发现。打造和教授这种共享的记忆与认同,正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也是民族国家历史课程的构成要义。
两者都广泛支撑并促进了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公民的形成。但是,我们也需要揭示出人类团结的样式和规模所具有的历史性。人类团结的各类样式与规模,有早于民族国家的,也有与之并存的。它们与民族国家竞争、互动,甚至构成了民族国家本身。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偶然的、依情势而生的结果,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作品,它绝非一种理想型或自然的事实。
它是一种互动的产物,也是一种民族国家与历史上或大于或小于国家范畴的各类社会形成、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的交相互动的结果。近年来,社会史家们业已着力描绘出了那些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更微观”(smaller)的历史;
如今,相对于民族国家更宏大的历史的描绘也已初现端倪。
要虑及民族国家史的全球维度,历史学家们必须迈出民族国家闭锁的匣子——然后才能带着对民族国家发展的全新且更丰富的解释回归。
他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民族国家在人员、货币、知识和物资上接触并交流的区域与边界是极具渗透力的,史学研究的原材料并不会在国界线上止步不前。一个民族国家并不足以构成其自身的背景。(民族国家)绝非隅于一个(不来电的)中子或(孤立的)细胞中,对它的研究必须在一个大于它自身的框架中展开。
本书把合众国视为集体构成人类整体之诸多行政区划中的一部分来进行检视。我将要讲述的故事始于1500年前后,那时,跨洋航行首次将所有大陆连接为一体,并创造了一种囊括所有民族的共同史(a common history)。美国史的发端也正是构成全球史重要事件里的一部分。我(的故事)将结束于20世纪,那时,合众国已经以一种在故事发端时所未曾料想的模样赫然耸立于全球性事务之中。
美国的民族建构计划已经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的历史并不能够也不应该被拿来宣称并维持一种历史上的独特性或范畴上的差异性。不管今天的合众国享有怎样的独特地位,它依然只是全球区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地区彼此联系并相互依赖。合众国的历史只是多重历史中的一种而已。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的争论甚嚣尘上,由此也激发了事关民族国家衰落和后民族国家史(post-national history)(兴起)之可能的对话。
但是,我并不认为民族国家有可能会很快消失。诚然,民族国家曾经对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y)造成过严重的伤害,但它们也恰恰是保护人类和捍卫公民权的唯一可行的强力实施者。只要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囊括了对社会中权力的分析以及对人类共同体中道德责任的明辨,民族国家就必定仍是历史探寻的中心对象。在此,我的目的并非要摒弃民族国家史,而是要为它建构一种别样的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尊重经验记录并能更好地服务于作为民族国家和世界公民的我们。
如今已经有相当多的学术文献以多样的形式挑战了传授民族国家史的老旧方式。甚至还有些宣言号召(人们采取)别样的途径,其中也包括我提出的两条。
这两条宣言都是专门针对我在学科内部的同僚——学术圈的读者们和专业历史学家们,同时也呼吁我们要另辟蹊径,探寻未曾践行过的别样路径。本书面向的是更为广泛的受众,并在事实上践行了宣言中提出的主张。
本书没有在既定叙事的边边角角零敲碎打,而是检视了美国史中的五大重要主题并将其视作全球史的一部分来重新加以解释。这样做可以显著地改变——依我看来可以充实——我们对这些主题的理解。我也会讨论其他主题,但我选定的这几个主题是中心性的,在任何一种合众国的通史中都不能忽略其中的任意一个。
第一章探讨并重新定义了“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的意义。新世界新在何处?这一章奠定了全球史的开端,为后续故事铺就了舞台。下一章,从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一条评论中受到启发,扩展了美国革命的时间范围和地理空间,将其置于18世纪各大帝国的竞争,特别是“大战”——英格兰和法兰西从1689年一直持续到1815年的全球性冲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合众国本土之外诸种势力的发展在美国对大不列颠的胜利以及这一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也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危机只是众多全球革命危机中的一种,所有这些危机都来自各大帝国间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革新。
随后,我把(美国)内战放在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背景中。林肯对欧洲的自由派深表关切与钦佩,那时欧洲自由派在民族国家和自由之间铸造了一条锁链,他们重新定义了民族国家的版图并对林肯的关注做了回应。特别是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后,他们将联邦(the Union)的事业放在追求自由民族主义这个更宏大野心的中心一环。这类对国家、自由和民族国家之领土的全新理解逐渐渗透到各大洲,并经常狂风暴雨般地向前推进。
大多数美国人在承认其历史中的帝国中心性问题上犹豫不决,更不用说正视美利坚帝国只是诸多帝国中的一个这一现实。
但是,1898年的帝国冒险并非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一种偶然的、未加思索的行动,在第四章中,我将探寻某些理路,顺藤摸瓜,人们会发现当时帝国被提上民族国家的议程已经有几十年了。无论从目的上还是从风格上看,美国的西部扩张与1898年的海外殖民都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延续性。同样延绵不绝的还有工农业商品不断扩张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在20世纪获取原材料并确保美国海外投资的政策。
第五章关注1890年之后几十年里美国的进步改革、社会自由主义以及对社会公民权的诉求。借助广角镜头的观察,人们必然会认识到美国的进步改革只是那个时代人们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大型城市极度扩张的一种全球化回应的一部分。一份席卷全球、事关改革理念的菜单已经摆在所有人面前。他们只是有选择地采纳并做出差异性的改编,从一国到另一国,纷纷呈现出民族国家的各类政治文化在更大范围中的、共享的、全球史中的重要性。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我并不是说只有一种历史,或者说美国革命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类似。我也并不是说美国内战与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农奴解放或者德意志和阿根廷的统一毫无差异。我也不是说美利坚帝国与英格兰、法兰西或德意志这样的帝国无法区分;
或者合众国的进步运动类似于日本和智利的进步运动。然而,我们曾忽视的家族相似性是存在的,同时我们也忽视了每块大洲的历史行动者在面对共同挑战时形成的自觉的相互交流。
也并不是说所有民族国家史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背景内容的延展可以让我们更清楚、更深刻、更准确地看到什么是合众国之民族国家史的独特性。由此,重大事件和主题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它们的起因和后果也被重新定义。在此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对当下的馈赠。
美国总是与其他国家分享历史。真正接受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更具有世界性,也可以使我们的史学更易被外国学者和公众接受。这会让我们更开放地接受来自历史学家以及疆界之外的其他人对我们的历史的阐释。
我希望由此能够更好地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受教,接受一种友善的世界主义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毫无疑问,这将推动我们更加接近一种世界主义的道德无缺、正直无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