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自传《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的第一部分记录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从1917年在埃及亚历山大出生,到1936年踏入剑桥大门为止。末了,他以一串连珠炮般的自嘲自虐结束了这个篇章:
艾瑞克·约翰·欧内斯特·霍布斯鲍姆,高个子、棱角分明、摇摇摆摆、相貌丑陋的金发伙计,十八岁半了……这个人没有任何道德感,完完全全自私自利。有的人觉得他极度讨人嫌,有些人则发现了他的可爱之处,更有一些人(其实是大多数人)觉得他荒谬可笑。他想成为一个革命者,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展现多少组织才能;他想成为一名作家,却既没有经历,也没有能力来组织材料。他虚荣而自负。他是个胆小鬼。他深深迷恋自然。他还把德语给忘了。
霍布斯鲍姆对自己“二十世纪的生活”的追忆和反思堪称直击灵魂。1917年6月9日,这位历史学家来到人世,十月革命仅在几步之外。霍布斯鲍姆的父亲是移居英国的波兰犹太后裔,母亲是奥地利犹太人。12岁那年,他的父亲离开了人世,两年后母亲也相继离去,他和妹妹南希便迁居柏林,投靠叔父和姨妈。此时此地,经济崩溃,整个社会如同燃烧的坩埚,涌动着革命的烈火,希特勒正准备迈过权力的门槛。就在这里,霍布斯鲍姆发现了共产主义。不久后,这两个孩子又被转移到伦敦,不到两年他就赢得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奖学金。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霍布斯鲍姆来到法国,见证了人民阵线的巴士底纪念日庆祝活动。在西班牙内战早期,他又搬到了不久后被佛朗哥取消自治的加泰罗尼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皇家教育训练部队(Royal Army Educational Corps),因为霍布斯鲍姆的共产党员身份,当时的安全部门屏蔽了这一情报的发布。二战后,他又重拾学术生涯,写了一篇关于费边社会主义的博士论文,并且在校园里维特根斯坦的书房中找了一个房间,负责运营当地的共产党团体。和大多数英国历史学家相比,霍布斯鲍姆是一个极致的世界主义者:他精通多国语言,足迹遍布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充当了切·格瓦拉的翻译。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白天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讲师,到了晚上,他就化身成为“弗朗西斯·牛顿”,他同时还是《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爵士乐评人,热衷于解密伦敦苏活区的下层社会——在这个贫民聚居的地方,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得以从制度规范里找到解脱。当编辑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让他为杂志的主要受众——中年男性读者——找点“刺激”的时候,霍布斯鲍姆便对伦敦的脱衣舞俱乐部展开了一项社会学研究,结论是强推迪恩街的Nell Gwynne俱乐部,因为那里的“头牌女孩靠的更多是舞姿而不是胸围”。
霍布斯鲍姆是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创始者之一,也是那一代群星闪耀的历史学家中的一员,他的同侪们还包括布赖恩·帕尔默·汤普森(E P Thompson)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这些学者推动着原本迷信王侯将相和军事政治的英国史学走向社会和经济历史。霍布斯鲍姆本身呢,他的代表作包括1959年的《原始的叛乱》、1969年的《匪徒》,还有关于现代世界的史诗级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以及续作《极端的年代》。这些著作无一不是全球畅销,在今天看来,这些文字融合了方方面面的细节,观察全面,叙事冷静,无与伦比。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周全 译
中信出版社 2016-1
刚起步时,他的晋升之路走得非常缓慢,但学术上的成就最终把霍布斯鲍姆送上了英国体制内的最高位置。他虽拒绝了骑士爵位,但在1998年接受了名誉勋位荣誉,这让他的左翼同僚很是懊恼。可以说这位历史学家是沐浴在名誉学位、学术交椅和各种荣誉中,并且坐在他汉普斯特德的家中就能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致敬。到2012年离世的这一天,霍布斯鲍姆已经成为了他那个时代里名声最响、赞誉最多的历史学家。
《趣味横生的20世纪》记录了以上大部分的故事,这绝不能说是一本毫无个人情感的回忆录,然而,霍布斯鲍姆在写作时几乎完全没有突破他表面的公众形象。而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精心编写的传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史人生》( EricHobsbawm: A Life in History )则带我们走进了这位历史大家私密的内心世界。
埃文斯的焦点主要在于霍布斯鲍姆的“个人经历”:早年日子里他是一个孤儿,漂泊到德国、英格兰,生活在一片人生地不熟的土地上;在战争中,他是一个无聊而孤独的士兵,先后被困在诺福克、多塞特和怀特岛;他还是一位情人,和一个已婚学生有过一段情,并在1958年有了一个孩子,名叫约书亚;同时,他也是一个忠诚的丈夫、称职的父亲,会给孩子们大声读《丁丁历险记》的故事,他会突然变身阿道克船长,大喊“成千上万的臭贝壳”,或者是像女儿茱莉亚说的那样,在电视跟前无所事事地呆上一天;霍布斯鲍姆还是一个“胡思乱想,战士一般”的老师,总是坚持让学生选择一个立场。埃文斯还绕到了这位历史学家魔法般的文学作品背后,详细记录了写书合约、经理人和编辑一团乱麻的关系,以及他被退稿(几乎难以置信)以及未完成的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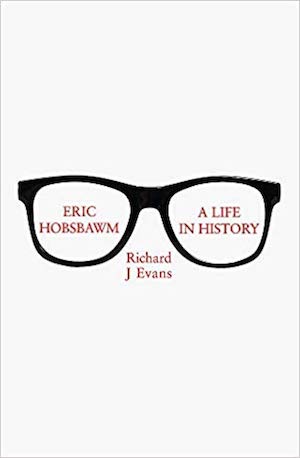
埃文斯并不是为了流言蜚语和桃色新闻本身而流连忘返,虽然霍布斯鲍姆自己倒是挺享受这种茶余饭后的笑话。在这些故事的背后隐藏着更加发人深省的启示。比如说在1949年,当他帮助第一任妻子穆里尔在家里堕胎之后,这位历史学家内心受到了重创,不久后,穆里尔提出要求分开,他极度抑郁,几近自杀。军情五处1951年的一卷档案记录了霍布斯鲍姆当时的状况:“我们认为他最近情绪崩溃了。”
更重要的是,埃文斯对霍布斯鲍姆的整体刻画还展现了私密的内心世界对他的公众生活和学术生涯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打个比方,正因为童年的贫困经历,加上上世纪三十年代残酷的政治境况,导致他在十几岁就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那个年代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柏林满溢着狂热的气氛,这也给了他一个持久的信念:学术争鸣犹如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确乎能改变点什么。正是这种对文学的热爱让他出口成章,遣词造句优美悦耳。不过霍布斯鲍姆这一生中的巨人还不是马克思,而是玛琳,他的第二任妻子。两人在1961年开始谈恋爱,从此以后这个女人就一直为他注入源源不断的爱与支持,成为艾瑞克后来事业成功的定心丸。
霍布斯鲍姆这一生中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他一直是个局外人,但最终还是被接受,进入了体制。个中紧张的拉扯也反映了二十世纪来到英国的犹太移民的人生经历。家庭给他留下的文化传统和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归属格格不入,这就导致霍布斯鲍姆和自己的同学同事们稍微疏离了一些。在柏林,他是“那个英国人”;到了伦敦,在圣玛丽伯恩文法学校的孩子们眼中,他是一个出生于亚历山大,有着维也纳口音的柏林人,这可不是件寻常事;作为一个有自觉意识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剑桥国王学院里也是占少数的那一拨;进了军队后,霍布斯鲍姆和那些差不多零教育背景的工人阶级士兵几乎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回到剑桥攻读博士时,他被执拗的本科教员包围了,尽管剑桥使徒社(剑桥大学的一个秘密社团,其成员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当过双重间谍的剑桥五杰)的伙伴们让他感受到了短暂的友爱,霍布斯鲍姆依然觉得,因为年龄的原因,他被社团中年轻的小伙子们孤立了。
就连后来打入苏活区,在这些离经叛道的居民中间研究爵士乐,这位“弗朗西斯·牛顿”也从未真正融入这个“酷猫”和“疯狂小妞”(俚语,爵士乐迷)的世界。另一方面,霍布斯鲍姆还是众多权威机构的成员,例如英国国家学术院和雅典娜神庙俱乐部(Athenaeum Club),他从未关上通往上层社会的大门。历史学家罗伊·福斯特(Roy Foster)说,他“喜欢自己局外人的身份”,但最好保持一个“自愿接受的舒适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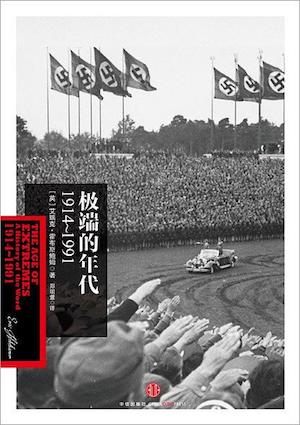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郑明萱 译
中信出版社 2014-1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深信1917是救赎之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这场运动的局外人”。尽管如此,霍布斯鲍姆还是对苏联计划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以这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之名,不顾几百万死去的亡灵,为苏联正名,而这一点后来也成了他职业生涯上的一个污点。作者埃文斯对这位历史学家还是有所偏爱的,竭尽全力为他辩护。他在书中指出,霍布斯鲍姆到了晚年承认,斯大林给人们造成的痛苦“是耻辱的,不容辩解,更找不到什么政党的理由为之辩护”。埃文斯认为,“我们需要设身处地,想想当年那黑暗的三十年代,当你面前的选择只剩下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时候,任何懂得理性思考的人都不会投靠后者。”在这方面,埃文斯轻易放过了他的传主,并没有像他原本设想的那样,对这个问题纠葛争辩。
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已经深入霍布斯鲍姆的骨髓,但他和大不列颠共产党对积极党员所期待的样子截然不同——他一方面为最不可饶恕的资产阶级小报《泰晤士文学副刊》供稿,他笔下没有一个字能敲出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的“理论盔甲的铿锵之声”。然而他的作品又有很明显的左翼倾向,“年代系列”四本书中,每一卷呈现的观点都能看出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子,起于经济,终于文化。但他意识形态的印记并不多,如同埃文斯所说的那样,他的著作植根于“尊重事实”。如果说要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给霍布斯鲍姆找个位置的话,他应该属于人民阵线所倡导的那种政治——带着1789的革命精神,充满希望,最终注定联合起格格不入的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1936年赢得选举,组建政府,1938年最终瓦解。
透过霍布斯鲍姆的一生,埃文斯的这本书及时地给这个局外人唱起了颂歌——这是一位矛盾而边缘化的世界主义者,他是一个世界公民,漂泊四海而不失家的感觉;他天生能够与受压迫的底层人民建立友谊,对他来说,兄弟情谊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生活状态。就连常常批判霍布斯鲍姆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也这么写道:“文明的饰面就薄薄一层,依附在我们对共同人性的虚幻信仰之上。但不管这是不是幻象,我们都得努力坚持下去。”然而很少人能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那样做到这一点,聪明而体面。
(翻译:马昕)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来源:新政治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