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起拍电影 Victor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日本人民的动漫,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攻城略地。《机动战士高达》《宇宙战舰大和号》《咪咪流浪记》等作品,起到了和后来传说中中餐一样的效果:美国人看哭了,法国佬吓尿了。
当然,美国本来是没那么容易哭的,全赖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战》。和今天国内影视剧题材跟风扎堆一样,当时的美国的内容制作人,也要想办法去满足《星球大战》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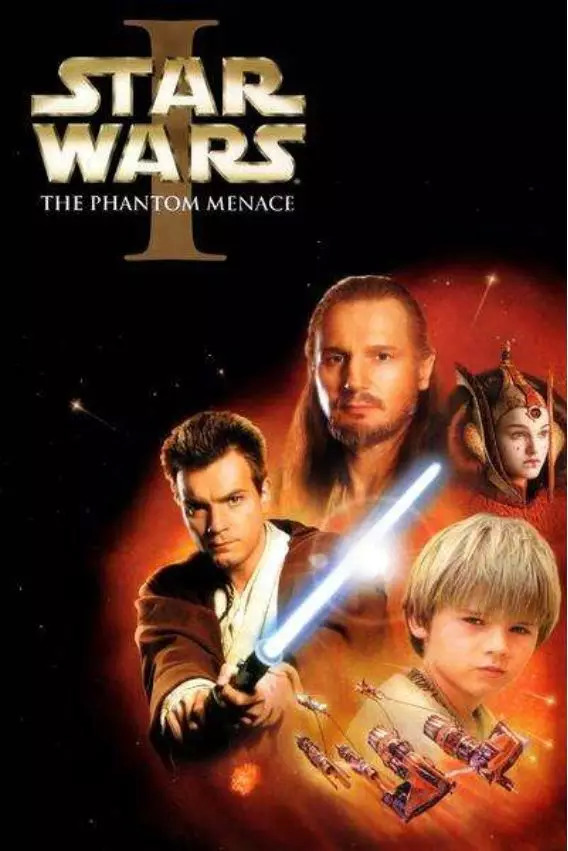
盛产科幻题材的日本动漫于是得以在美利坚大陆焕发新生,一位制片人把动画片《科学小飞侠》重新包装改编成两部作品:《星球之战》(Battle of the Planets)和《重力战队》(G-Force)。结果收视爆火,五百万美元的制作费用,换来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收益。
日式动漫从此开始了他浩浩荡荡的美利坚征服史,这个过程过于浩荡,以至于让傲慢的美国人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被“和平演变”了,一篇博士论文引用了美国的研究文献:“(《南方公园》第三季第十集)在虚构的剧情中,《宠物小精灵》成为了日本人企图侵略美国的武器,渲染日本给美国小孩们放《宠物小精灵》的动画片,来达到洗脑的效果,教育他们要去轰炸珍珠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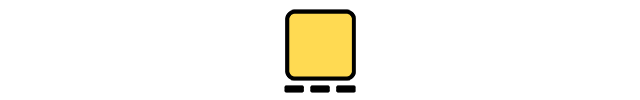
故事自此进入了正轨,在如山如海的动漫书中,有一部叫《铳梦》的动漫,入了《水形物语》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的法眼,他是漫画迷。他对卡梅隆推荐了这个作品,卡梅隆说你咋不拍啊,吉尔莫说大兄弟这个还得你来。
但最后根据《铳梦》改编的《阿丽塔:战斗天使》,导演也不是卡梅隆,而是以低成本独立电影制作闻名的罗伯特·罗德里格兹,卡梅隆只是制片和编剧。即便如此,从宣发到受众,人们还是对卡梅隆和电影的关系更为津津乐道。

卡梅隆与罗德里格兹
毕竟这里面足够有故事性:卡梅隆在有了女儿后,对拍摄《铳梦》的兴趣愈发强烈,因为他觉得这描写了父女、家庭间特殊的关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根据《铳梦》改编的《阿丽塔:战斗天使》“确实是有几个画面呈现了我和女儿间的关系”。
有一种传闻甚至是,《阿凡达》有一个功用,便是检测在技术层面,《铳梦》能否拍摄成功。
而他在另一个采访表示,自己之所以要去做科幻导演,是因为1977年看了《星球大战》,于是他决定不干卡车司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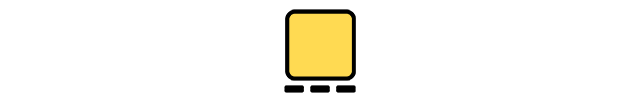
《铳梦》的作者是日本漫画家木城雪户,也有人把他名字翻译成木城幸人。他出生于1967年,从小喜欢画怪兽和机器人。国内对他的履历介绍不多,一般能看到的,是他17岁以短片漫画《气怪》入选第15回小学馆新人赏。此后,《怪洋星》、《飞人》等作品都受到好评。

木城雪户
但类似“1998年开始,木城雪户一度陷入创作低谷”的描述,可能并不准确:《铳梦》虽然在1992年才在连集英社旗下的《Business Jump》上连载(这部杂志的主要受众是30岁以上的上班族)。可在此之前,这部漫画已经在“多家出版社之间游荡了三年”。
“我要让30岁以上的人也看SF”。木城雪户在动笔之初想,“sf”是一种漫画类型,全称是“SCIENCE FICTION”。强调想象在科技、社会学等方面的可实践性,“高达”、《超时空要塞》、《攻壳机动队》都属于此行列。
而在《铳梦》的世界观里,在26世纪,末日大战后的300年,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地上的废铁城和天上的“萨雷姆”,其实“萨雷姆”还连接着另一个空中城市“耶鲁”,二者合起来就是上帝之城“耶路撒冷”。但在电影里,“萨雷姆”直接叫“撒冷”了。
可惜神的子民缺乏必要的同理心,废铁城由萨雷姆倾泻而下的垃圾建造而成,原著里,废铁城标志性的建筑物便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
我们的女主人公阿丽塔的残躯,就是在垃圾山被“医生艾德”发现,并被其赋予新的身躯和名字。她将历经战斗,在死亡、欺骗、反抗中寻找自我。至于她的专属技能“机甲术”,则是更新过程中编辑的建议:“希望主角能够有武士般的必杀绝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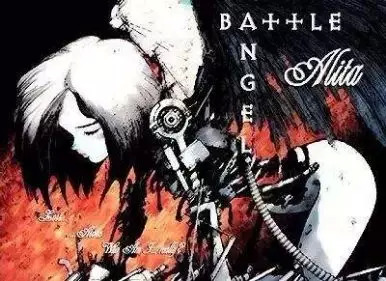
“感谢所有优秀的工作人员,令《阿丽塔:战斗天使》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在日本举行特别首映礼上,木城雪户对电影大加赞赏,称自己每看一次,都会找到新的东西,“最令人兴奋的是,我无法相信我是原创故事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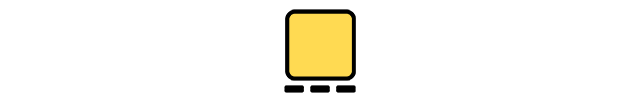
但原著粉们表示也不敢相信这个是原来的那个《铳梦》。
最大的槽点是雨果之死。在漫画里,雨果的哥哥是机械师,他出于对美好的向往,一心想要探索萨雷姆及更宏大的宇宙,结果却在制造热气球中被妻子举报,惨遭杀害。
雨果由此被被种下了对天空的渴望,后来更是因为机缘巧合,把哥哥的手腕移植到自己身上。为了去萨雷姆,他不惜杀人打劫。直到有一天,当他终于攒够了钱的时候,却被告知,想要去沙雷姆,除非被拆解成一堆人体器官。
绝望而狂热的雨果,最终死在了废铁城通往沙雷姆的铁管里,在阿丽塔的目光中,他决绝而地前进,然后被清扫器齿轻易打碎。

但在电影里,雨果的这些复杂的动机被砍掉了,只剩下一个中二少年,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零杠五——虽然这并不妨碍中国观众,从中看到了阶层流动和北京户口。
被吐槽的还有对废铁城的处理——“战斗天使”中,废铁城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就差路不拾遗了,全无《铳梦》“脏科幻”的范。让人不禁感慨,从漫画到电影,短短二十几年间,废铁城当局在精神文明、法治社会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治理。
在此之上,复杂混沌的人性,被简化为简单的对立也就不足为奇。哪怕是卡梅隆得意的一个桥段,阿丽塔掏出自己的心脏交到自己的男朋友雨果手里。在娱sir这个亚洲人看来也若有所失:既失掉东方式暧昧感的意味,又不如原著把心脏当比斗筹码来得有豪杰气。

“电影只有两小时的时间,条件非常有限,根本没有办法把一个那么大的故事讲清楚。这可能要么只能拍一小段,要么你都拍,但是会很肤浅。我觉得这是科幻的一个老难题,我们最爱的小说,都是有很多内涵,你要把它在银幕上呈现出来真的很难,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科幻电影都是原创的,不是改编的。不是说不可能改编,只是说有难度而已。”卡梅隆在和刘慈欣对话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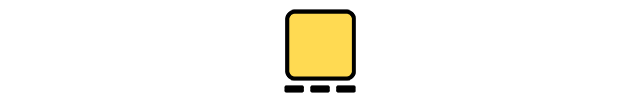
当然,“战斗天使”只是让一些观众失望而已,它是一部合格的美国大片,命运也比此前日漫改编的美国电影强太多——《七龙珠》、《拳皇》、《死亡笔记》、《攻壳机动队》等直接用票房打脸。寡姐穿连体秋裤都救不了他们。
真正出彩的是那些“洋为美用”,取出一个日漫元素,用来讲讲美国故事的电影。比如每次漫改失败大家都会拿出来缅怀的《黑客帝国》。沃卓斯基兄弟不仅多处化用了《攻壳机动队》里的情节,甚至《黑客帝国》片头弹出字幕的方式,都和《攻壳机动队》一模一样。
或者《杀死比尔》里女主人公漫画风格的造型,以及它那些极致精美或者极致粗犷的打斗布景。

不同于日本动漫传入美国的进程:六十年代单纯配上英文翻译、八十年代本土化处理、九十年代日美合作,美国改编的日漫电影,既想着保持日漫的精髓,又想着秀操作本土化,最好再具有点创新实验的性质,还老找欧美人演,最后一改就被骂。
文化差异是确实在存在的,不谈日本所谓的“物哀”,美国做不出来日本的神魂在于它没有日本的“不安全感”。日本的科幻题材、机甲题材动漫师承美国,但日本的战争记忆却是二战被美国打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更是催生出绵延不断的群体心理阴影。这种创伤反应在漫画里,就是满目疮痍的战后世界,和痛苦迷惘、尝试找寻某种真相的灵魂。
于是美国和日本,在动漫—电影的链条上,就这么彼此咬合着,谁也离不开谁。链接它们的元素倒是轻易可以看到,那就是对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对人产生的异化的恐慌,人的创造物反过来威胁到人自身的存在——尤其在《阿丽塔:战斗天使》这类赛博朋克、反乌托邦的电影中,马尔库塞所谓的“科技异化”、“单向度的人”,处处可见。
“合成人、废铁镇、沙雷姆是现代社会的暗喻,并不是用来批判具体的什么事物。废铁镇是所有价值观毁灭后的世界,没有所谓的传统、神话、思想。我们早已活在这种世界。”木城雪户在《铳梦》后记里说,“要认识现实,不被空虚与嘲笑控制,而能生存下去。这不是一种情结,而是一种意志的力量,也就是真正的保有个我的“战斗”意识。”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