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始祖——这位思想家的理念在其忠实追随者柏拉图的多部著作里得到继承,形塑了2000多年以来的思想。“不管是好是坏,”古典学家狄斯金·克雷(Diskin Clay)2000年在《柏拉图式追问》(Platonic Questions)一书里写道,“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就是我们所知的那个苏格拉底。”长久以来,这一出自柏拉图之手的苏格拉底形象都是这样的:一个出身低微、未受教育、家境贫寒且其貌不扬的男人,一个机敏聪慧、能言善辩的哲学家,娶了以好辩闻名的女子克桑蒂贝(Xanthippe)。柏拉图和另一位苏格拉底传略的主要作者色诺芬(Xenophon)都生于公元前424年前后,他们所知晓的苏格拉底已经是一位长者了(他生于公元前469年前后)。二人都倾向于捍卫苏格拉底的名誉,驳斥“引进新神”和“毒害青年”这两项最终令苏格拉底受审及获刑的指控,因而都将即将迈入老年的苏格拉底刻画为了一名虔诚的教师以及不屈不挠的伦理思想家,一个为追求更高的教化目的而坚决拒斥身体欢愉的男人。
但这种对苏格拉底的理想化描绘显然不是故事的全部,也不能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的思想源头。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一些古代作家就对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做出了一些修正。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亚里士多塞努斯(Aristoxenus)和苏利的克里阿库斯(Clearchus of Soli)留下了一些传记残篇,其内容可能是他们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得知的。根据这些残篇可知,青年苏格拉底和另一位杰出的老哲学家阿基劳斯(Archelaus)过从甚密;他结过不只一次婚,元配是一个名叫米尔托(Myrto)的贵族女子,二人育有二子;他和米利都的阿斯帕西亚有外遇,这个聪明而又小有名气的女人后来成了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的伴侣。
如果这些说法不假,那么一个迥然不同的苏格拉底形象便呼之欲出了:一个属于雅典精英阶层的青年,身处上流社会的个人经验激发了他的灵感,促使他创立了一种风格新颖的哲学,左右了此后多年里人们的思维方式。但我们能否相信这些后世的作者?距离苏格拉底生活的时期已有两代人乃至更长时间的作者,何以觉得自己有资格反驳柏拉图?答案之一是,亚里士多德可能从柏拉图本人那里了解到了一些信息,而非通过其著作,且将这部分信息转述给了他自己的学生;另一种可能是,作为一个有20年资历的柏拉图学院成员,亚里士多德也许对柏拉图为捍卫苏格拉底名誉而刻意隐去某些事实一事有所听闻;第三种可能则是,较之于柏拉图,后世的作者有更丰富的信源(口头和书面的),在他们看来这些信源更为可靠。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个怪人。苏格拉底声称自己年轻时脑海里曾有一些声音浮现,据说他曾在公共场所伫立良久,完全沉浸在思想当中。柏拉图只是提及了这些现象,没有任何评论,他接受了苏格拉底自己的描述,即那些声音乃是“神圣的指引”,也原封不动地记录了苏格拉底可以连续沉思多个小时这一令人叹为观止的能力。身为一个医生的儿子,亚里士多德的笔法不无问诊的意味:他认为苏格拉底(也包括其它一些思想家)有所谓的“忧郁”(melancholy)症状。近来的医学研究者同意这一看法,并推测称苏格拉底的行为跟强直性昏厥(catalepsy)患者毫无二致。这很可能导致苏格拉底早年颇为不合群,进而诱使他过上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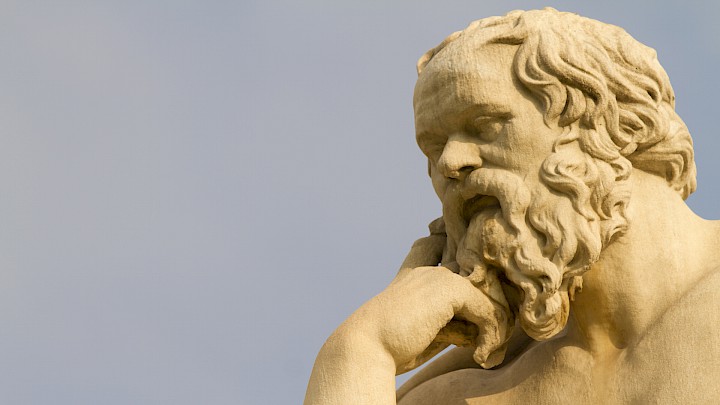
如果说,既有的苏格拉底生平及性格描绘确实值得进一步商榷,那他的思想呢?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明确表示,柏拉图在涉及到所谓的理念论(Theory of Forms,希腊原文为Eidos,汉译多有争执,也有理型、理式、型相等说法——译注)时误读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关注的是伦理学,无视自然世界而探求伦理事务中的普遍性,他还是第一个坚持下定义的人。柏拉图继承了此学说,但主张普遍性并不适用于感觉对象,而是适用于其它类型的实体。他认为单单一个描述是不能定义所感知到的事物的,因为这些事物总是处于变化中。他称不变的实体为“理念”……

亚里士多德自己对这种过于凌空蹈虚的观点不感兴趣。作为一个生物学家和科学家,他最关心的是对世界的经验性探究。他自己的著作就抨击了理念论,代之以对普遍之物的逻辑解释及其具体的实例化。对他来说,苏格拉底也并不是柏拉图企图描绘的那番样貌,而是个更接地气的思想家。
再来看某些古典时代晚期的说法,5世纪的基督教作家西尔哈斯的提奥多雷(Theodoret of Cyrrhus)提出,苏格拉底至少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双性恋者。此类论点令人更倾向于相信在柏拉图著作里偶尔也可以窥见一斑的那个接地气的苏格拉底,譬如,在《查密迪斯篇》(Charmides)这部对话里,苏格拉底就声称自己看见年轻男子裸露的胸脯后性欲大发。然而,柏拉图提到的唯一一个苏格拉底伴侣也就只有克桑蒂贝;不过,鉴于苏格拉底70岁时她怀里都还抱着一个婴儿,他们不大可能结识于10年前或者更早,那时苏格拉底都已经有50多岁了。柏拉图之所以没提到那位早年的贵族女子米尔托,可能是想尽量不让人产生如下的印象:苏格拉底出自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与社会里的上层人士也有联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格拉底据称与在雅典夺了权的反民主贵族群体有染,他也因此而受审并于公元前399年被处死。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证词是个颇有价值的警示,它提醒我们:不应不加分辨地接受柏拉图所描绘的苏格拉底。归根结底,如果苏格拉底年轻时曾一度成为阿斯帕西亚的情人——她以雄辩家和情感咨询专家而著称——那我们对苏格拉底的改观就不止于他的早年生活了,更得延伸到他的哲学理念的形成上。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我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一无所知。”但他在柏拉图的《会饮篇》里则宣称自己确实知道一样东西,那就是爱,这是他从一位聪明的女子那里学到的。这名女子是否就是他一度热恋的情人阿斯帕西亚?真实的苏格拉底想必是难以捉摸的,但按照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塞诺斯和苏利的克里阿库斯的说法,我们起码可以窥见苏格拉底颇为迷人的另一面,迥然不同于柏拉图在其著作里描绘得惟妙惟肖的那个苏格拉底。
本文作者阿芒德·丹古系牛津大学耶稣学院古典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古希腊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
(翻译:林达)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