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三声 罗立璇
4月17日,《三声》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以「中国电影工业升级的一种实践」为主题,首次聚集《流浪地球》的核心主创团队,进行了两场圆桌探讨。第一场以《流浪地球》为案例,主要讨论在电影工业化的语境中进行创作管理与开发管理。
参加讨论的嘉宾包括《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编剧严东旭,以及中影股份北京电影制片分公司副总经理陶鹃瑜;最后一位则是融创文化集团总裁助理、内容与投资中心总经理李宇浩,从场地和实际操作的角度来探讨如何进行重视效电影的后方支持。主持人为《三声》联合创始人贾晓涛。

《三声》联合创始人贾晓涛
在本次圆桌中,一个已经形成的共识是,中国电影距离真正的工业化实际上还有一段不算短的距离。郭帆强调,工业化不应该被神化、困难化,创作者们应该转变观念,将工业化作为一种规范化的创作方式来看待,“它就是我们画画用的纸和笔”。但同时,他也认为只有中国电影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在制作商业电影时才能够实现科学和规范的制作方式,从而直面来自好莱坞体系的强势商业电影的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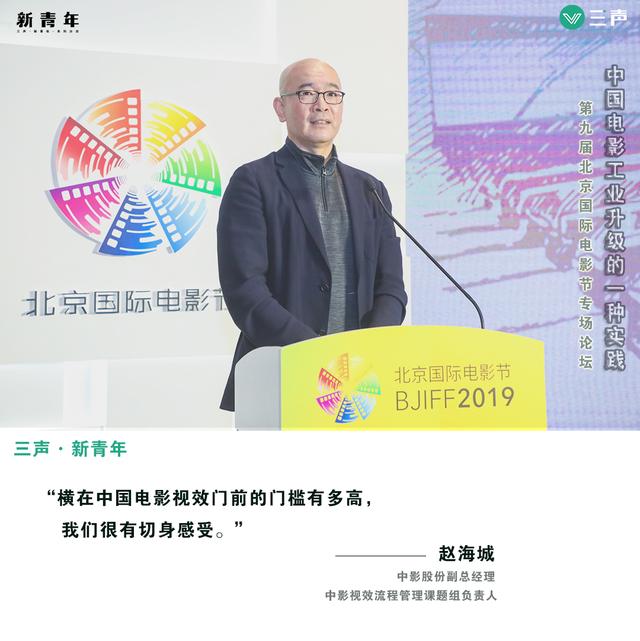
但在向好莱坞学习的过程中,作为真正研究并且实践过的从业者,这些嘉宾都认为这更像是学到了对方的观念,而要真正地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创作与管理,则需要自己真正进行执行和实操。
以下是本次圆桌嘉宾与《三声》的部分对话整理:

贾晓涛:第一个问题是给郭帆导演的。你在几年前和宁浩等几位导演有机会到美国参观,在很多采访汇总都提到那段旅程让你对电影工业化产生很多新认知。在完成了《流浪地球》以后,你在认知上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
郭帆: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我先简单讲一下我对工业的理解。什么是电影工业?我们首先不要神化它,它就是一个工具,跟画家的笔和纸是一样的。在好莱坞,你会发现很多奇思妙想可以直接转换到屏幕中,变成一个个镜头;而我们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笔和纸,所以在转换镜头这个环节上就会变得很困难。甚至有时候编剧还得跟导演商量,这个能实现吗?
当我们有了笔和纸之后,才会进入艺术层面、创意层面和决策层面的比拼。我们不能继续骑自行车,得开上车,才能跟别人飙车、展现车技。当然,工业电影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电影,你在最后字幕中能够看到7000人的名字。这部电影是7000人付出的心血,而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
贾晓涛:我看到郭导说写的东西能不能拍出来的时候,严老师一直在点头。站在编剧的角度,你怎么理解电影工业?
严旭东:我觉得编剧首先要做好一个基本工作,就是讲好一个故事,搞清楚到底故事要表达的是什么,更多的工作还是在这上面。但在这以外,比如要做一个科幻片,作为编剧可能要了解什么能做出来,而什么不能;比如要给导演一个什么样的文本,是整个工业组能够理解的、能落地的东西。
贾晓涛:《流浪地球》应该是融创接手得比较早的一部片子。在这部片子的拍摄前后,(拍摄地)东方影都正在进行工业升级。在未来,东方影都还会为类似《流浪地球》这样的科幻片提供什么样的支撑?

融创文化集团总裁助理兼内容与投资中心总经理李宇浩
李宇浩:中国电影工业化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融创文化正式成立于去年的12月31日,还非常年轻。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成立得晚,所以没能投进去这个片子,而我们对于电影工业的发展方向的认知是比较一致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电影制作的每个环节离真正的工业化、产业化、标准化都还有一定的距离。以我们为例,东方影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我们有40个影棚,是一个很大的影棚集群。在我们接触别的项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础设施的缺失会增加创作的难度。比如你拍一个片子可能需要十几个棚,有大有小,数字的,高的矮的,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环境?刚才郭导说到纸跟笔的问题,我们很愿意成为那个纸跟笔。
第二点是我们愿意提供补贴,为工业化的探索留有余地。我们会补贴项目在青岛拍摄费用的20%-40%,让大家能够做更多探索的工作。当然,《流浪地球》可以拿到40%。第三点就是我们希望具备提供配套服务的能力,比如后期、服化道、制景,甚至在材料供应、住宿和餐饮方面,来提供一个能够让大家进行特别好的创作的平台和环境。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把这个试点打造出来。
贾晓涛:接下来我想提问陶总,你们的课题组成立和《流浪地球》立项是几乎同时进行的。不知道你是否能介绍一下你们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以及相对应的尝试?
陶鹃瑜:一个大前提是,近十年以来,电影票房、银幕数量的急剧增长,为我们来带了非常大的电影容量市场,在这样大容量市场的背景下,观众对于电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方面是对制作要求更高,他们希望能够看到制作更加精良、视听感受更好的影片。在早年,我们的制片管理流程是基于胶片拍摄内容而建立的。当变成数字化以后,制片的管理流程就会发生一些调整和变化。当大量的重视效电影,也就是说视效在一部片子当中占的比例很高的这样一些片子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视效管理流程发生的变化就要更大了。
《流浪地球》虽然不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例,但确实是我们探索出了很多成功经验的一个案例。对于我们来说,整个开发流程管理都在发生变化。比如,我们不能够将电影剧本作为开发阶段的唯一成果,更多的是要加入视效预览、世界观的建立,前置大量的后期工作,在拍摄前,我们就需要做好很多镜头分解、确定具体拍摄计划。。
贾晓涛:还想问郭导的一个问题是,你在拍摄这部片子的过程中,有哪些必须坚持的工业化的创作方式和管理方法?就是您刚才说,大家都还在骑自行车,你突然意识到必须要开车,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郭帆:其实在好莱坞学习的那段时间里,很难说学到什么具体的东西。更多的树立一个观念:我们必须用工业化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类型的电影。它是一个思维的方法,也是在最终去实践的时候,唯一一个找到工具的方法。
当时编剧的时候,我们连最基本的工业基础都还没有,就是编剧格式。大家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我本科是学法律的,我有一个同学在美国当律师,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递出去一封文书,就是因为格式不对、字体大小不对、行间距不对。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政府机关单位就是工业化的,他们所有的文书都统一格式、字体和字号,这是标准。
所以,工业化的基本逻辑就是,我们要让文艺创作可被量化。可被量化之后才能被细分,才能提高效率。什么叫格式?就是相当于工业化楼房中的每一块砖,有了一块块砖石才能砌墙、建楼。在统一格式以后,我们在后边才能应用剧本软件,让内容可被数据库收录,再对应后端所有的工具和软件。我们会碰到一些大编剧,说他们就习惯这么写了,那怎么办?这需要我们先去转变观念,然后再寻找工具、方式和方法。转变观念可能是这里面最难的一点。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现场会让场记不要用纸记东西了。万一纸丢了怎么办?万一我们想检索怎么办?如果我们前期花一段时间完成培训,那我们所有的资料都能够被保存。
后来我们在推行工业化的时候还发现一个问题,管理的方式与方法需要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比如在好莱坞,很多东西都流程化了,有硬性的规定继续往下推行,是一个契约型社会。而我们还是人情社会,使用契约社会的东西和观念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在中国干很多事情都需要情商,我们也正在寻找我们自己的方法。
贾晓涛:在这部片子里面,科幻的中国化是很多人都交口称赞的一个部分。你们当时是怎么思考视效的中国化这一个命题的?

《流浪地球》编剧严东旭
严东旭:我们编剧组考虑更多的是一个情感的结合点,怎么让这个故事回归到人的身上。因为所谓的科幻的中国化,其实就是科幻的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未来世界,但我们不能纯粹就说架空、完全和观众割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寻找一个让当代的中国观众能够理解的情感着力点,比如小家和大家的联系、中国式的父子情感是怎么样的,中国人对于英雄主义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这都是我们在编剧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贾晓涛:李总,你说你是一个特别深入的科幻迷,对于科幻中国化你怎么看?
李宇浩:接下来代表我自己。我认为科幻中国化的说法挺好的,因为我们从小看科幻作品、国外的大片太多了,那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哪里?大刘的《三体》抵达了一个高度,我们的文学或许已经成熟了,但我们的影像在哪里?其实我们一直等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需要满足两个点。一个是把作品做到一个水平,不能以国货、中国化的概念来降低自己的要求,这是基本的。当然,《流浪地球》离《星际穿越》这样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们希望它能够继续向世界最顶级的碎屏接近。
第二个是感情线,《流浪地球》太难拍了,这里面的共鸣是一种中国人情感的共鸣。其中确实有争议的部分,比如韩子昂同志对于太太的选择,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女儿,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泪点。但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人隔代的爱的共鸣。还有刚才讲到的集体英雄主义与个体英雄主义之间的平衡,比如我作为一个父亲,怎么拯救自己的孩子,同时又不能辜负国家的期望,这里面的度把握得特别好。所以有朋友让我预测票房,我真不能预测,因为我无法客观看待这部作品。
贾晓涛:我记得在电影上映之后,大家在采访中不约而同地提到,可能之后不会再有这样的状态了。从整个电影工业升级的角度来看,或许这部作品只是一个开始,或许说只实现了“半工业化”?
郭帆:半工业化可能都做不到。其实我们在中间依然缺失了大量的部门、人和经验。我记得有一天拍完戏,吴京老师跟我说,什么叫工业化?工业化是我们拿人扛。
当时他拍失重那场戏,我们还是用威亚。按理说,他已经有20年的动作经验了,吊威亚是没有问题的,但谁也没有穿过六七十斤的衣服吊威亚。同时那名俄罗斯演员也没有经验,所有的重量点都在吴京老师身上。那一天拍了十几个小时,拍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演员的大腿根都磨烂了,手都是肿的。
后期也是,视效都是累倒了起来打点滴,再累倒,一遍又一遍。最近996讨论得很多,我们都是007。我们必须拿人填补、不停地加班,以一种不吃不睡的状态来填补确实的部分。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至少得知道它的难处和难点在哪,包括创作过程中会有什么雷区,才不至于浪费掉这四年。
说雷区这个东西也挺容易得罪人。我可以举一个关于文化差异的例子。当时宁浩导演做《疯狂的外星人》,特别是在美国做的那部分,就遇到了刚才说的文化上不可跨越的部分。
比方说,我们想做一个“道上的社会人”,脑海中就是金链子、大金牙,坐在马路边撸串。但让美国人做就是马龙·白兰度,他们认为撸猫的才是教父。你很难用语言来描绘什么才是撸串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反而是亚洲地区更容易合作,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更加接近。
同时这个文化在我们剧本创作时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把电影形容成一个人的话,你的灵魂就是你的文化。什么叫中国科幻?科幻我觉得是一个外衣,爱情片穿这个、文化片穿那个,但内核是一致的。最后我们发现内核就在原著小说里,大刘早就赋予给我们了,因为推着地球离开这件事情就是特别中国的想法。
我们当时在工业光魔跟人家介绍这个项目。他们为什么会对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感兴趣,觉得有意思、好玩?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们中国的思维好奇怪,为什么跑路还要带着一个家?
因为不管是《星球大战》还是其它的电影,一旦出现大危机的时候,里面的人物往往选择自己离开。这个很有可能是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他们本身就选择从英国一个岛屿型国家离开;而我们是内陆型的农耕文明,所以土地是最重要的。更何况北京的房子还这么贵。
从大的层面上来讲,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就是对于我们目前创作上的最大波阿虎。好莱坞从前年开始陆续进入中国,中国市场很快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拍中国观众喜欢的电影。
这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或许是十来年,他们会努力地学习如何拍中国观众喜欢的电影。他们的优势是他们有“纸和笔”,我们的优势是我们了解中国观众和中国文化。一对比,我们找到自己的纸和笔至关重要。
贾晓涛:从中影的角度出发,我想问陶总,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必须具备制作重视效电影的能力的急迫性?

中影股份北京电影制片分公司副总经理陶鹃瑜
陶鹃瑜:刚才您也提到了底子薄的问题。但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对全球一流的视效公司、尤其是他们的管理经验,都有了解。了解完了以后,我们最大的感受是,但凡一个专业的、拥有自己优秀的流程管理的团队,一定是基于本土实际情况,这样总结和提炼上来的。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如何根据中国本土的电影情况,来做适合我们中国电影自己的视效管理流程。
说回到科幻电影这个类型,我们有自己非常成熟的科幻文学作品,也有在世界上拿过大奖的科幻作家,但在科幻电影这一块,我们中国电影一直是缺席的。我们会反过来想,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国产科幻类型一直是缺席的?其实无非就是觉得很难,第二个就是投资回报的可能性比较低,但中影作为一家国有电影企业公司,不管有多难,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尝试,把这一块的空缺填补上来,这是我们中影作为国企的责任和担当。
郭帆:我补充一下陶总说的科幻片的部分。我也一直从小看科幻片长大,但都是看海外的科幻片,也会一直问为什么没有中国的科幻?但除了对于制作难度、投资体量的要求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成长土壤。说白了,国家不够强大都拍不了科幻片,这跟观众的自信心相关。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在电影院看到自己的宇航员和航天器时,才不会感到怀疑。纵观中国科幻片的发展历程,包括美国科幻片和日本科幻片星期的时间点,和他们的经济复兴的时间点是一样的。所以,科幻片的出现不仅仅是导演们说可以拍一个科幻片,而是到这个时机,这个土壤可以慢慢孕育出科幻片。
同时,我特别呼吁大家一定要重视软科幻作品。只有硬科幻作为土壤的基础上才可以做软科幻,这是一个语境和审美建立的过程。举个例子,《西游记》带动了一代人的认知。在今天,只要我们聊到孙悟空,一定是虎皮裙、金箍棒。我们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培养出了这个预警的认知。
但比如,我们编一个机器人和姑娘谈恋爱的故事,那个机器人突然站在这,观众会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们没办法把世界的语境直接放到这个地方,所以语境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也是需要科幻剧打底的。美国可以做软科幻,是因为他们有几十年的时间,打了硬科幻的底,建立了语境和审美规则。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