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可能连苏州第壹制药公司的负责人都没有想到,在这个厂的厂区搬迁后,最关心其选址进度、厂区建设的不是自己厂里的员工,而是一群病人和其家属。
几毛钱一粒的药买不到了

这家药厂生产的盐酸哌甲酯片(俗称国产“专注达”)主要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俗称“多动症”)和发作性睡病。因其效果不错、价格便宜而受到了许多患者,尤其是多动症患儿家长的青睐,在很多家长眼中,这个药甚至是唯一一种可以控制孩子的症状、不至于因为过于“离谱”的行为而遭到老师和其他同学及家长投诉的药品。
2015年12月中国发布了《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下称“指南”),预计中国儿童多动症总体患病率约为5.7%。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0-14岁儿童为2.42亿人,粗略一算,那就是有1379万该年龄段儿童可能受多动症影响。
多动症是一部分儿童期最常见的行为障碍,并非只是“孩子天性调皮”那么简单,它影响的远非学业,还包括了孩子们的行为、情绪和社会适应性,可能会产生持久甚至终生影响。

一般来说,对于6岁以下的孩子,首选方案是行为和心理社会治疗,而在6岁以上,药物治疗为首选,“指南”主要推荐的药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中枢兴奋剂,包括哌甲酯长效制剂(专注达)、哌甲酯短效制剂(利他林);一种是中枢去甲肾上腺素调节药物,即托莫西汀(择思达)。
两种药都为一线用药,不过药理完全不同,所以适用于不同的患者人群。择思达在改善“过动-冲动”的症状上,略优于专注达和它的亲戚利他林;专注达在改善“分心”的症状上,则略优于择思达。此外,因为这些药都可能产生严重副作用,比如择思达会让人产生严重食欲减退,有的孩子服用一个月就瘦了好几斤;而有的患者服用利他林可能出现上瘾和自杀倾向,所以患者一般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用药偏好,这样也比较好控制用量、观察副作用。
苏州第壹制药生产的国产专注达在市面上是一种较受欢迎的多动症药物。但是自2013年以来,患者就发现,很难买到国产专注达了。
国内拿到该药批文的一共有三家药企,分别是通化仁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州第壹制药有限公司,前两家明确表示已停产该药,苏州第壹制药则称原因在于厂区搬迁,其母公司中国泰凌医药集团在2016年6月发布公告,表示开始在泰州建立分公司,核心产品仍包括盐酸哌甲酯。预计新厂区在2017年竣工,盐酸哌甲酯于2017年底或之前上市销售。
家长和患者开始紧密关注这家厂的施工进度。在此期间,就只能拿进口药代替。但花费一下子高了不少:国产专注达一粒几毛钱,体重轻的孩子一个月的费用是42元。而吃进口利他林缓释片的话,一粒药20块钱,一个月药费是640元——药费一下子就贵了近600元。
再算一笔账: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5974元,拿出其中近三成买药,很多工薪阶层是会吃不消的。
到了2017年,位于泰州中国医药城的苏州壹药果然如期竣工了。家长们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国产专注达总归能重新上市了吗?
并没有,时至今日,该药仍然完全被进口药品所垄断。在最近搜索泰凌医药的官网时有槽发现,该公司的核心产品中已经完全没有了盐酸呱甲酯片剂的踪影。
对于国内药企纷纷放弃了国产专注达的生产,外界有很多猜测,有说是因为该药利润太薄,厂家没有生产动力;有说是因为该药属于“红处方”,是国家管控严格的一类精神类药物,因此从原料到生产都受到很大制约。
靠药吊命的没了药
前面说过,专注达不光用于儿童和成年多动症的症状控制,还对另一种疾病有效:发作性睡病。
这个病可能大家听说得少,媒体偶有报道,患者的症状一般是说睡就睡,比如上着课或者在高速路上开着车就会突然睡着。更危险的情况是猝倒:面临某种压力或情绪时会突然倒地。此外还可能出现睡眠瘫痪、睡眠紊乱等。严重时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危及生命。
说它是罕见病,其实也不罕见,在人群中差不多每2000个人中就有一例,也就是说中国至少有70多万发作性睡病患者。该病无法治疗,只能缓解症状,而像专注达或利他林这类神经兴奋药物,可以帮助病人保持清醒。一些患者生动地形容说自己多年来就是靠着这些药吊命。

然而和多动症患者一样,指望靠它来吊命,维持学业、养家糊口的患者也吃不上国产药了。这个打击对该群体可以说尤其大,毕竟考虑到其病情的特殊性,他们在求学和就业中就已经要承受大量的歧视和阻碍。
不该吃药的却在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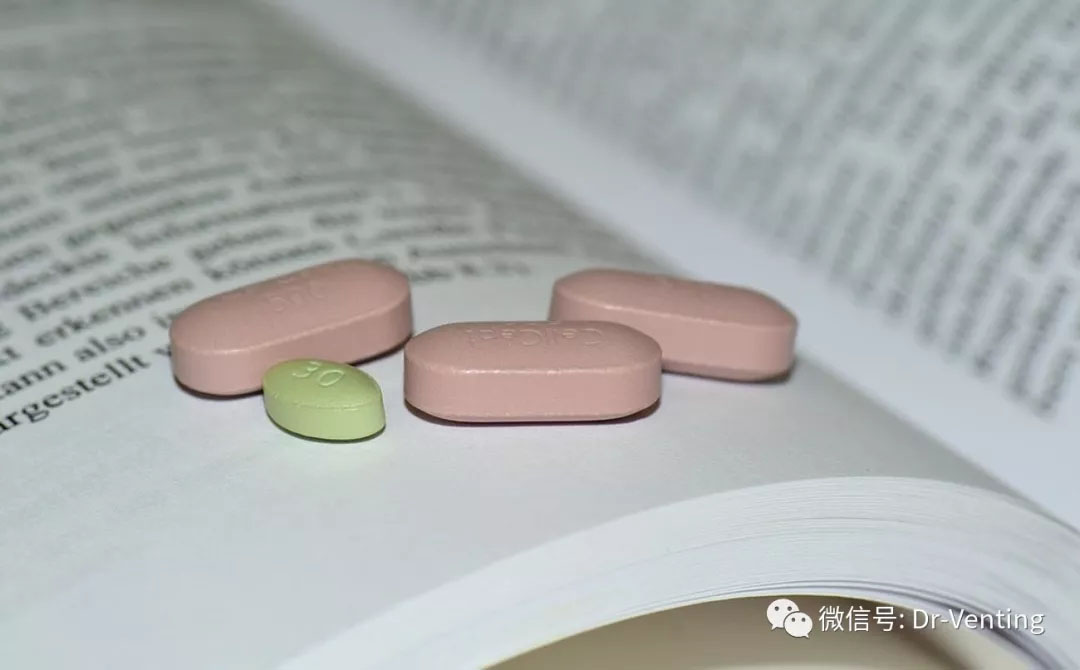
在进口药过于昂贵的情况下,有些患者和家长开始寻求代购这条路线:光是利他林,市面上就有所谓巴基斯坦版、美国版和瑞士版这几类,部分药品代购价低于医院药房门市价,因此对低收入家庭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但这甚至比代购肿瘤药还更加不靠谱:大多数买家对于利他林的“红处方”性质心知肚明,知道自己的购买行为很难受到法律保护,所以买到的药货不对版、收到假药,或者卖家收了钱根本不发药,都只能自认倒霉。
还有更多的人购买黑市药,本身并没有确诊患有多动症、没有医学指征,他们购买的动机纯粹是为了学业和工作。
有家长替孩子买药:在中考、高考前夕,各大医院精神科都会碰到这类焦虑的家长,希望通过临时服药提高孩子在备考和考试期间的注意力。但因为医生把关严格,通常开不出来药,那怎么办?孩子被确诊患多动症、正在服药的同事和熟人突然间成了香饽饽,“匀两粒药给我家娃”这种看似天方夜谭的要求并不鲜见。
“看到别的家长给孩子用这种助考兴奋剂,我们既担心又无奈,同时感到不公平,这类所谓的‘神药’都是歪门邪道,扭曲了家长与考生的心理。”一位学生家长曾这样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家长承认,给孩子弄药是担心别的小孩都吃,自家娃不吃的话等于是输在起跑线上。
这一点和《自然》(Nature)杂志在2008年所做的调查结果一致:在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如果孩子的同学正在服用这些药物,他们也会有让自己的孩子服药的压力。
更有许多孩子私下里自行交易药品。追求高分、追逐名校的压力正在将为数不少的孩子引上一条相当危险的道路。很多孩子安静地购买黑市药,安静地一点点提高药量,等到家长发现时,可能已经到了需要强制戒毒的程度。
全球都在吃药
一项2018年发表在《国际药物政策杂志》上的全球药物调查结果显示,在这项针对数万人的调查中,在2017年,14%的人报告称自己在此前的12个月内至少使用一次像利他林、阿德拉(Adderall,主要成分为安非他明,较利他林成瘾性更强,在中国、日本、韩国被禁止进口)和莫达非尼(这也是一种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的药物,但很多人将它用于连轴转学习和工作中)这类兴奋剂,而2015年的比例为5%。

在调查包括的所有15个国家中,非医学用途使用所谓“聪明药”来增加记忆力或注意力的比例都有所增加。其中美国受访者报告使用率最高:2017年,近30%表示他们在过去12个月中至少使用过一次聪明药,而2015年为20%。
调查还发现,绝大多数人获得这些药都不是通过合法渠道。近半数(48%)的人表示他们是通过朋友获得药物的;10%是从经销商或互联网上购买的;6%的人从家庭成员那里获得;只有4%的人说他们有自己的处方。
越是竞争激烈的学校和行业,使用聪明药的比例就越是广泛。一项对英国剑桥大学学生的研究表明,受访的学生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在没有获得处方的情况下自行服用“认知增强”药物。
在美国,调查显示,东北部的精英大学学术压力最大,学生对聪明药的使用率也最高。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神经科学家安扬·查特吉(Anjan Chatterjee)表示:“在大学校园乃至高中,使用这类认知增强药物已变得越来越普遍。学生们认为这些是学习辅助工具,就像人们在工作前喝咖啡一样。”
而据《纽约时报》根据采访学生、家长和医生得来的信息,在某些大学和研究生院中已经司空见惯的兴奋剂,如今在一些学业竞争激烈的高中里也开始变得寻常。费城一所高中的高年级学生说,光靠把处方药以每粒5到20美元的价格卖给同学,他每周可以赚上几百美元,据他说,他的“客户基本上是那种‘好孩子’。”
不一定有效,但是危险却是明摆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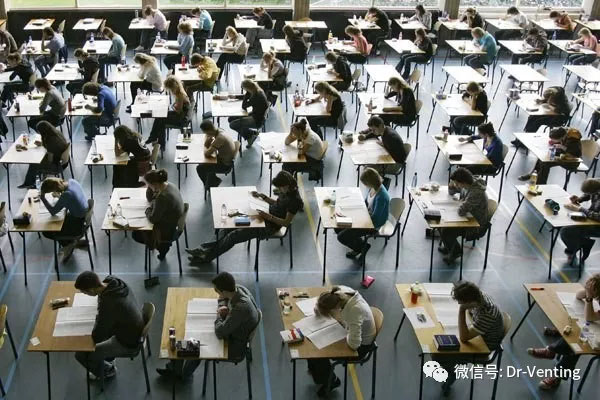
学生和职场中人通常都知道,利他林等兴奋剂虽然俗称聪明药,但并不能提高智力,而主要是让人更专心,他们使用认知增强剂主要是出于三个原因:通过专注达等药提高专注度,获得竞争优势;通过莫达非尼等药克服睡眠不足的影响,长时间保持头脑清醒、思维敏锐;通过利他林等强增加与工作有关的动力,坚持繁重的脑力任务。
但是果真如此有效吗?
研究结果好坏参半。
一些小型研究表明,认知增强剂对于正常人或许会产生积极影响。在1996年对28名健康年轻男性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利他林被证明可以改善短期记忆。在斯坦福大学对18名飞行员进行的测试中发现,服用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盐酸多萘哌齐(Aricept)30天的人更好了记下了在模拟器上学习的复杂航空任务。
剑桥大学的芭芭拉·萨哈奇安(Barbara Sahakian)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阿拉·达兹(Ara Darzi)发现,一整晚没睡觉的医生在服用莫达非尼工作记忆和计划性有所改善,并可以减少做出冲动的决策。
然而,总的来说证据是混杂的。比方说在2012年关于阿德拉对健康人群的影响的研究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尽管服用药物的人认为他们的表现得到了提高,但通过客观测试可以发现,其认知能力并没有得到持续改善。
2010年,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克莱尔·阿德沃凯特(Claire Advokat)表示,兴奋剂药物如利他林可能会提高记忆力,但“实际上可能会损害需要适应力、灵活性和规划的任务的性能”。
由于迄今为止,对认知增强剂并没有大规模的长期研究,所以加拿大蒙特利尔研究所的生物伦理学家埃里克·雷辛(Eric Racine)及其同事发表了一份报告,告诫医生应该拒绝为健康人开处方类认知增强剂。文章强调了与兴奋剂相关的成瘾、心血管疾病和精神病的风险。“我们并不知道服用这些药物对健康人群的长期健康影响是什么,”雷辛说。
在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BMJ)的研究中, 安简·查特吉(Anjan Chatterjee)教授同样反对服用利他林来提高表现:“不幸的是,健康人服用这种药物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医生通常根据相对风险和收益的计算来决定是否进行干预。而在这里,风险大于收益。”
“聪明药”对于健康人群的益处尚无定论,但风险却是显而易见的——否则各国不可能将其列为一类或二类精神类管制药品。
比如在联合国公约《精神药物公约》中,利他林在四级分类中被列为第二类药物,与安非他明、四氢大麻酚(大麻中的主要精神活性物质)并列。
在美国,禁毒署将阿德拉、利他林这类处方兴奋剂列为二类受管制物质——等同于可卡因和吗啡——因为它们均属于成瘾性最强的药用物质。
在中国的《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依据不同的药物依赖性和人体危害程度将精神药品划分为第一类、第二类,利他林、专注达、安非他明、莫达非尼被列为第一类、也就是管制最严格的精神药品。而未成年人大脑前额叶皮层仍未充分发育,会更容易受到药物的影响。
一方面,在服用这些药物后,可能会不断提升阈值,《纽约时报》接触到的一位高中生患者说,在他被一所排名不错的大学接收时,他每天服用的剂量已高达300毫克。到了一次服下400毫克药物后,他的心脏开始狂跳,出现幻觉,随后全身抽搐,被紧急送往急诊室。
另一方面,这类精神药品可能是滥用其他药物和毒品的“入门药”。比如在习惯了一般的处方药之后,开始滥用奥施康定(OxyContin)这样的处方镇痛剂。
如果人人吃聪明药,结果会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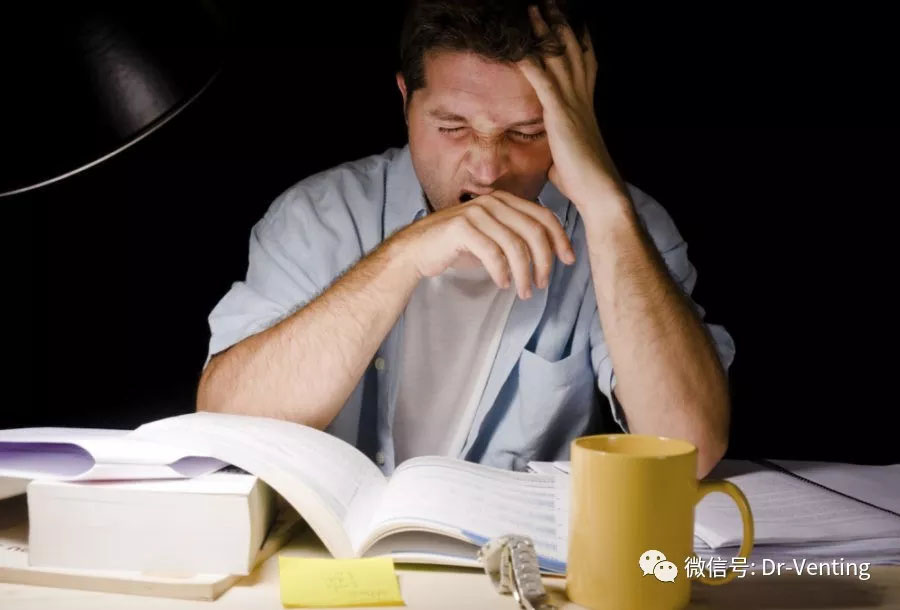
巴尔扎克是早期聪明药的狂热信徒——为了文思泉涌,他每天晚上都会在巴黎的街头寻觅一家午夜时分还开门营业的咖啡馆,然后一直在里面写到次日早晨。据说,他一天能喝50杯。
到了后来,他开始整勺整勺地吃咖啡粉,一口咖啡粉下肚,“灵感纷至沓来,就像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前往传奇的战场,战斗正酣。”
在创作了近100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戏剧后,51岁的巴尔扎克死于心脏衰竭。当然,在他大量摄入咖啡因和心脏病发作之间,没法直接建立因果关系,但可以看出一点:对于兴奋类物质的需求很容易不断突破门槛,喝惯了咖啡的人,偶尔早上少喝了那么一杯都会出现戒断反应,更何况更刺激的物质。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希望能借助药物的力量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但大量研究证明,现在的药物并不完美,确诊患有多动症、发作性睡病的患者在服用药物后也要为焦虑、厌食、失眠、狂躁等不良情绪所苦,大量患者表示服药的感受“绝不舒适”,但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学习又不得以要服药甚至苦苦觅药;而正常人群在服用后,更有可能泥足深陷。
焦虑,竞争,压力——是这个社会的常态,连孩子也无法幸免,然而,为了领先,付出多大的代价才算够呢?




评论